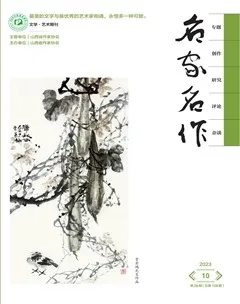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世說新語》神童形象成因研究
郭逸松
本文以劉義慶《世說新語》正文所記載的神童及其事跡作為研究對象。雖然劉義慶在《夙惠》一章中專門描寫了7 個神童的8 條事跡,但是在《世說新語》的其他章節中依然存在大量關于神童及其事跡的描寫。本文擬整合《世說新語》中零散的神童事跡,歸納分類神童形象,概括神童的特征,探究產生神童現象的原因。
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兒童并非現代概念中0~9 歲的兒童,而是古代概念中的兒童。鄭玄在《禮記》的注中寫道:“成童,十五歲以上”,提出十五歲以上則不屬于兒童,故而本文所研究的兒童年齡均為0~15 歲。
關于“神童”這一概念,北宋王若欽在《冊府元龜》中有這樣的記載:
識洞于未萌,智表于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辨足以解紛。
有特稟異質,迥越倫萃,岐嶷兆于襁褓,穎悟發于齠齡。
即神童具有超齡的思維能力、語言表達能力。這說明神童是天賦稟異的,在童年時期就展現出了遠超同齡人的智慧與悟性,即早慧。
一、《世說新語》神童記載狀況和形象特征
(一)記載狀況
《世說新語》全文總共記載人物故事一千二百多則,分三十六個門類。由于《世說新語》沒有記載部分神童的具體年齡,因此筆者即以《世說新語》所記載的“年幼”“總角”“年少”為依據。
在《世說新語》全文中,體現出早慧特點的神童有52 位,涉及的條目有58 則。按照現代標準,這些條目中不僅有兒童,也有少年。但以古代15 歲之內均為兒童的標準來看,僅曹操等6 人涉及6 則可能無法算作兒童,其余52 則均確定為兒童。
而這些條目在《世說新語》各門類的分布中,《言語》篇以14 則的數量占據首位,《文學》篇中有6 則占據第三,《德行》《政事》均為2 則,孔門四科累計共有24則,幾乎占了總數的一半,可以看出編者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不過由于兒童自身年齡的限制,《德行》《政事》兩篇均各自只有2 則,《言語》《文學》兩篇占比較大,充分展現了神童的性情、氣質。
與此同時,《識鑒》《賞譽》兩篇共占12 則,從內容上看,多是借長輩,尤其是高官名士之口,以小觀大、見微知著。通過對神童的贊許來側面表現神童的氣質、性情、才干,品評人物的痕跡較為明顯。而在《排調》中則是成年人故意通過調侃,甚至嘲笑刺激兒童,以此來觀察兒童的反應,體現了魏晉士人的幽默。《夙惠》篇是劉義慶專門為聰慧過人的神童設置的。魏晉時期,在玄學盛行,清談思辨之風大行其道的社會背景的浸染下,兒童的潛力被極大挖掘,在表現出遠超同齡人才智的同時,仍不失善良,遵循儒家的道德規范。
(二)形象特征
關于神童形象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在司馬遷的筆下,堯、舜、禹、湯等被公認為上古圣人的君主,除堯以孝道出名以外,其他人的早慧都帶有一些共性:諸如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帝嚳高辛氏向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后稷“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都帶有非常濃厚的神話色彩,依據常理來看真實性極低。
隨著時間的流逝,儒學的教條逐漸成為精神的束縛。東漢中后期以王充為典型的理性學風開始反思這種日趨僵化的社會風氣。到了魏晉時期,士人更加專注于個體的內心世界。而嚴酷的政治環境讓士人不得不避開現實,轉向“清談”的形式,討論一些人倫或才性名理的話題。這些話題的探究既需要很強的思辨能力也需要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折射到兒童世界即體現為能言善辯的應接對答。同時,隨著東漢以來世家大族交流走動的頻率增加,家族中的孩童也多有參與,對成人世界的模仿以及對成人話題的討論,也使部分早慧神童對人情世故有著超乎年齡的練達。因此,在個體意識日漸覺醒的社會背景之下,多元化的早慧得以萌芽,并在魏晉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為《世說新語》關于道德型與才智型兩類神童的記載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材料。而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結合玄學與清談之風盛行的社會背景,主要從能言善辯、恪守孝道、思維靈活縝密三個方面來描繪神童的形象。
二、神童現象的成因
(一)社會政治因素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一段動蕩不安的時期,皇權衰微,門閥林立,政治斗爭尖銳,朝代更迭頻繁。傳統儒家積極入世的愿望無法實現,士人們為尋找出路,將目光投向了道家。這一時期的士人為了明哲保身,對于社會現實的關注大大減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談玄說理之中。同時,世家大族為了保證自身長期享有特權,將大量精力投入對下一代的培養之中。那么,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社會政治因素就成為影響神童出現的首要因素。
在東漢及三國時期,士族往往以夙惠為忌,對事功型的早慧現象持否定態度,而對保全身家型的早慧大加贊賞。例如對同樣具有夙惠特質的李膺、鐘覲,他們的長輩就做出了不同的評價:
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
覲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之言白(鐘)皓,皓曰:“元禮(李膺字),祖公在位,諸父并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覲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
鐘皓是鐘覲之父,他由于李膺“好招人過”、執著于“好惡是非之心”,擔心他日后招來禍端。而對兒子守身克己的行為加以肯定,認為是保全身家之道。
同樣,三國時期的諸葛瑾也對自己的兒子,吳國公認的神童諸葛恪表達了擔憂,認為諸葛恪“非保家之子”:
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諸葛瑾去世之后,諸葛恪便因卷入吳國政治斗爭被殺,株連全族,印證了諸葛瑾的話語。與童年時期的孔融相似,諸葛瑾也鋒芒畢露,讓成年人難堪:
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后,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神童在幼年時因自己的聰明才智令成人難堪而得到認可,在其成年后可能會形成不知收斂乃至于恃才傲物的性格。在一個社會動蕩、政治斗爭尖銳的時期自然難以保全身家,進而被否定也實屬正常。那么為什么同樣在朝代更替頻繁且時代緊密相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樣的神童卻得到認可,甚至作為兒童名士被載入《世說新語》中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漢至魏晉時期經歷了皇權不斷衰微、士權逐漸崛起的過程。
(二)家庭教育因素
魏晉時期,玄學滲透到了各個家族的家庭教育之中,不僅與儒學教育分庭抗禮,更是到了“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的程度。兩晉時期,以儒學著稱的世家大族如果不入玄風,就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可,其地位也會下降。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地位與特權,有眼光的士族政治家就會致力于對族中子孫進行玄學方面的培養。
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士族名士在教育子孫時將玄學提高到了與儒學相同的高度,王昶教育族中子侄“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明確地把玄學列入了家族教育的內容,將《老子》《莊子》《易經》等玄學經典加入蒙學教育中,使族中子弟在幼年時期便接觸玄學,為將來參與清談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另一方面,清談之風盛行,長輩之間的清談活動對神童也有相當大的熏陶作用。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論議”即指清談,內容往往具有很強的抽象性與思辨性,諸如著名的“貴無論”“得意忘言論”等。如果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學習,是極其枯燥且難以理解的。而陳元方、陳季方兩兄弟不僅有興趣一同偷聽,而且因為專注于偷聽而耽誤了做飯。如果不能理解“論議”的內容,又怎么至于連手頭煮飯的工作都忘記了呢?
正是由于士族的玄學教育與長期受到玄風熏陶的影響,故而有的神童小小年紀就開始思考玄學問題: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經月不得,遂成病。
雖然魏晉時期玄風盛行,崇尚清談,就像趙翼所說:“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為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閣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震”[2],但是儒學在維持社會秩序、保證家庭和睦方面發揮的作用是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玄學無法比擬的。儒家經典依然是當時許多家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正是由于儒家道德教育的長期熏陶,才使魏晉時期的神童群體普遍具有積極維護尊長聲譽的行為與恪守孝道的內在特征。
(三)思想環境因素
魏晉時期,神童事跡種類多樣,涵蓋了道德、學問、事功、機辯等方面,呈現出了多元且早慧的特點,而在時代上與之相連的東漢時期的神童事跡則多局限于道德、學問兩個方面,這種現象是魏晉時期多元的價值取向導致的。而多元的價值取向的背后,則是一個多元化的思想環境。
思想環境的多元化絕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受到社會政治環境與社會風氣的影響,在其潛移默化之下產生的。然而任何一種社會風氣或時代精神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一定有其源頭與逐漸發展的過程。目前學術界的主要觀點認為:魏晉時期思想風氣源自東漢,尤其是東漢中后期。賀昌群先生認為:“按兩漢學術思想之變遷,可分三期。……第三期自東漢中葉以后,沿第二期之流波,加以外來方術之興起,諸子學之復興,及佛教經典之移譯,直至魏正始之際,乃又為之一變。”[2]他把東漢中葉至曹魏正始放在同一時期,也可窺見其中的淵源關系。如果想充分了解魏晉多元化的思想環境,須先了解東漢中葉以后的社會轉變及其帶來的思想上價值取向的變化。
東漢時期,皇權衰微、政局混亂,取而代之的宦官外戚專權以及接踵而至的黨錮之禍使士人在心理上與大一統政權逐漸分離,再加上經學日趨僵化,“漢自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來,儒生多宗陰陽,解經時雜讖煒,崩離繁瑣,愈演愈烈。……此種大患,久而彌烈,到了東漢之末,已成了窮極必變之勢”[3]。儒家經義的神圣性開始受到質疑,而法、名、道等諸子學說則有了復興的趨勢。
然而,東漢后期諸子學說的復興只不過是在儒家思想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絕大多數士族仍然以儒學為正宗。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宣揚的忠孝節義的部分,仍然是被大部分知識分子認可的官方意識形態。事實上,就算是在玄學盛行的魏晉時期,儒學和儒家思想依舊占有一席之地。
隨著晉代魏,出身于儒學大族的司馬家掌權之后,在國家層面上,諸子學說復萌的思想環境再度被儒家思想所取代。但是這一次儒家思想并非復歸到漢儒那里,而是產生了經由王弼等人玄學化的儒家思想,“其基本內容為儒道同、名教與自然同。而所謂儒道同,名教與自然同,其主旨又在把儒家名教說成道或自然的產物,在宣揚儒學的核心名教思想,宣揚禮法”[4],在經歷了東漢經學崩塌之后,又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儒家思想與東漢時期相比,已經有了很大改變。
王弼的“貴無”“得意忘言”“名教自然同”之說通過清談論議的方式在漢魏學術界扎根、傳播,進而引發了一系列學術爭鳴,出現了玄學清談之風盛行于世的局面,許多天資聰穎的神童也在清談活動中脫穎而出。為了回避作為魏臣不忠的道德困境,維護政權合法性,司馬氏建立政權之初,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但其弒君的惡行日益凸顯其倡導的禮教的虛偽,導致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士人對“名教自然同”的觀點產生了懷疑,認為名教與自然不能兼容,進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提出,對社會上原本奉為圭臬的傳統儒家禮教觀念產生了巨大沖擊,社會價值觀念、價值取向進一步多元化。體現在神童事跡上則是一些原本不符合儒家禮儀標準的行為也得到了社會認可,例如神童謝仁祖在社交場合中,面對眾賓客“一坐之顏回”的贊美之辭,他以“坐無尼父,焉別顏回”之語反擊。這一行為盡管明顯與儒家“中庸”“溫柔敦厚”的價值觀念不符,卻被認為是其作為神童的表現。
三、結論
綜上,《世說新語》中神童形象的成因主要由以下三點組成:第一,隨著皇權衰微、士族崛起的局面逐漸形成,社會政治環境趨于穩定,士族政治家為了保證家族特權的延續而對神童與早慧現象的態度逐漸轉為肯定,為神童群體的出現做了環境上的準備。第二,隨著士族家庭教育中加入了玄學方面的內容,而玄學對思辨能力要求較高,使具有天資、悟性較高的神童很容易嶄露頭角。加之士族家庭良好的學習氛圍與優厚的物質條件,大大增加了神童出現的機率。第三,從東漢至魏晉,經歷了社會思想環境逐漸多元化的過程。而魏晉時期多元化的思想環境導致士人價值取向的多元化,進而各種類型的神童都被社會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