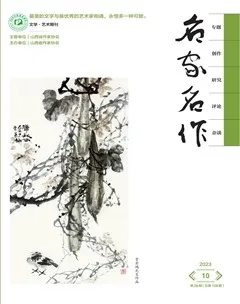試論郁達夫小說 “自我敘述”的表現與實質
李郭成
郁達夫是“創造社同仁中最具唯美色彩,最有頹廢嫌疑的作家”[1],他從西方唯美主義文學中汲取養分,奉行非功利的文學觀。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認為“郁達夫的全部小說都是盧梭式的自白”[2],郁達夫開創的“自敘傳小說”有悖于傳統的道德觀念,立足張揚個性的理念,大膽地剖露自己的本相,竭盡所能地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自我敘述”的先聲,在其“自我敘述”的背后卻隱含著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和政治自覺,是夏志清所言中國現代文學“感時憂國”傳統的另一種暴露與呈現。
一、唯美主義:郁達夫小說“自我敘述”的表現
(一)唯美理念
郁達夫提倡“為藝術表現自我和內心的自然流露”與他在留日期間接觸到西方唯美主義思想密切相關,作為對現實主義的一種反撥,唯美主義提倡藝術至上,反對文學作品的功利主義和道德教化功能,可以說王爾德、濟慈和波特萊爾等西方唯美主義作家對郁達夫審美傾向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王爾德認為“藝術的目的不是簡單的真實,而是復雜的美”[3],郁達夫在其小說創作中就注重表現作家內心的真實情感,往往以自身的真實經歷與遭遇為基礎,盡情地進行情感的“自我敘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郁達夫所創作的自敘傳小說幾乎都帶有他本人的影子和情緒。《沉淪》中的主人公留學日本,作為弱國子民在異國蒼穹的皎日下,感受到了極大的陌生與恐懼,自卑、屈辱乃至性的苦悶深深煎熬著他,這種孤獨、壓抑的憂郁情緒正是郁達夫的“自我敘述”。夏志清先生就曾說:“《沉淪》雖然用的是他敘法,但實在是露骨的自傳。”[4]無獨有偶,《南遷》中那個身穿大學制服,頭發有一寸多深的“我”,《銀灰色的死》中那個在這沉寂的午后的空氣中獨坐的“我”,也似乎都是郁達夫本人,這種“求真”的復雜之美真切體現了唯美主義的氣質。在《詩的內容》中,郁達夫主張“詩的實質,全在情感,情感之中,就重情緒”[5],他推崇王爾德所說的“生活模仿藝術”的觀念,在其小說中將性的苦悶、生的苦悶和社會對個人的壓迫與不公結合在一起,對黑暗的現實進行大膽的剖露,并在這種現實境況下流露出自身真實的情感體驗,以“唯真唯美”的創作理念自我敘述出內心的矛盾與痛苦。
(二)唯美形式
郁達夫認為“藝術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6]。立足唯美主義的創作理念,他遵循內在的傾向性,強調藝術地、真實地表現自我本相。縱觀郁達夫的小說,“性生活”的生理本能訴求和“精神生活”的審美訴求始終纏繞交織在一起,共同成為其自敘傳小說“自我敘述”的情緒突破口。在生理訴求方面,郁達夫主張真實地展露小說人物對異性美的審美意識和由審美引起的熱情沖動,將可怕的丑惡和莊嚴的美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在審美訴求方面,他認為“近代小說真正的開始,就在這里,就是把小說的動作,從稠人廣眾的街巷間轉移到了心理上去的這一點”[7],主張把一個沒有任何矯飾的真實本我展示給讀者。小說《沉淪》基于對社會功利的拒絕和傳統道德觀念的抗議,把人的私生活的內容以第一人稱的描述方式,坦白、率直、赤裸裸地表現到令人害羞的程度,使得中國現代小說在“人的文學”中第一次有了新鮮異樣的文本。這種根植于作家自身的內省,對身為弱國子民的留學生在生活上的性苦悶心理和變態性行為進行大膽剖露的描寫形式,能使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乃至現今的讀者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情緒穿透力和個體認同感,夏志清先生稱之為“維特式”[8]。
(三)唯美內容
王爾德、波特萊爾等西方唯美主義者主張“靈肉并重”,追求“靈肉合一”,認為藝術家在靈與肉、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應當追求一種快樂主義和精神主義并行的美,講究用完美的藝術形式帶來更多的感官享受。郁達夫在留學日本期間較多地接受了西方唯美主義思潮的影響,同時吸收了日本“私小說”和現代主義小說的敘述技巧,認為“美與情感,對于藝術,猶如靈魂肉體,互為表里,是缺一不可的”[9]。郁達夫的早期作品側重于表現“靈肉生活之苦惱”,在作品中把性苦悶、性壓抑等“肉”的內容表現得惟妙惟肖,社會的黑暗、時代的壓抑、滿腹才學無以施展,是郁達夫心理憂郁的病根,他的病是時代病和才子病。王爾德曾在《道林·格雷的畫像》中反復強調,藝術“無非是尋求刺激的一種手段”,“通過感官治療靈魂的創痛,通過靈魂解除感官的饑渴,那是人生的一大秘密”[10]。因此,郁達夫推崇西方唯美主義者的那種“靈肉并重”,以“唯肉”的頹廢內容抒發自己對丑惡現實的不滿,慰安自己傷痛的心靈。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我們也發現,雖然《沉淪》中有窺浴、《茫茫夜》中有同性戀等“肉”的內容,但隱含其中是“靈”的傷痛,人物的內心隨時都會發出道德自責的聲音,沉淪的罪孽感與嚴厲的道德批判相互交織。郁達夫的小說通過對病態的真實體驗的描寫,毫無保留地暴露了當時在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心里苦悶和內心焦慮,并將其統一“自我敘述”成游離于社會邊緣的“零余者”的典型形象。
二、“感時憂國”:郁達夫小說“自我敘述”的實質
唯美主義作為19 世紀中后期盛行于西歐文壇的文藝思潮,“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論也是其一直所標榜的,然而唯美主義并不是企圖拋棄良心,它提倡的只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已經成為本能的道德。拿王爾德的戲劇《莎樂美》來說,在工具理性主義大行其道的維多利亞時代,社會關系全面物化,功利性的藝術泛濫,莎樂美對男性權威的反叛和對純粹道德的忠誠,或許代表的是對資本主義時代既定文化的深刻反思與積極反抗。正如唯美主義在維多利亞時代未能成功地創造出新的社會秩序,莎樂美也沒有成功地構建“新的關系”,于是唯美主義提倡的“生活模仿藝術”的生活藝術化觀點最終卻造成了資本對審美感性的全面滲透與重新控制。因此,這也說明唯美主義本身并非“不道德”,而是表現了一種對社會道德的求索與困境,它并不是單純地沉湎于感官享樂,也不是停留于對那些社會及人性中丑惡現象的深刻審視,而恰恰是去見證“美的東西”的墮落與毀滅。
這一思想在郁達夫的小說中也得到了繼承與發展,郁達夫在其小說創作中深切受到西方唯美主義思潮的影響,盡管他極力推崇“唯美的天性”,然而正如他在《懺余獨白》中談到《沉淪》的創作初衷時所說:“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里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沉淪》。”[11]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下,社會的黑暗讓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一方面,為了逃避嚴峻的社會現實,郁達夫苦心經營著“藝術至上”的唯美主義文學,在官能的頹廢享樂中尋找精神上的慰藉,對社會進行著無聲的批判;另一方面,在郁達夫看來,那些被壓迫的藝術家總是神經最為纖弱,能最先感受到時代精神,對來自現有時代的壓迫和不公也感受得最為深切,郁達夫認為他們是舊時代的反叛者和新時代的開路人,而波特萊爾、魏爾倫等頗帶唯美頹廢色彩的“藝術家”在他看來就是最具有反抗意義的人物。
李澤厚說:“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欲求和留戀。”[12]伊藤虎丸在《〈沉淪〉論》中也認為“郁達夫創作《沉淪》的動機是試圖以小說中主人公的姿態表現社會或民族的反抗”[13]。所以在更深的層次上,郁達夫以其敏銳的感性觸角、獨特的文學筆法寫下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苦悶、迷茫的心態,在平凡的生活基調中寫出了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對祖國命運的關切、對未來前途的摸索。郁達夫是大膽的反叛者,勇敢地反叛著舊有的一切,追求著個人自由,但同時他也是一個熱切的愛國者,在矛盾與苦痛掙扎中鮮明地表現出他以身殉國的民族主義感情。為了更好地呈現如夏志清先生所說的“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形象”,郁達夫在其小說中也往往將個人的愛情創傷與弱國子民的屈辱感聯系在一起,如《雪夜》中所寫的“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或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那一剎那”[14]。我們聽到在《沉淪》小說最后的吶喊“祖國呀祖國!,你快富起來,站起來吧”,是郁達夫“自我敘述”的最強音,在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發現,郁達夫早年受到豐富儒家文化濡染,對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精神十分贊賞,從其后期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中我們都可以窺見作者對于儒家禮教的謹守。在郁達夫的小說中,盡管那種頹廢與沉淪的氣質是唯美主義所標榜的,然而在那個黑暗時代,這種追求靈肉生活所出現的苦悶與“自我敘述”的自傷、自哀,與中國古代士人如屈子一樣,都是將內心的極度矛盾與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放置于表面上的不羈與頹廢之中。這樣一種氣質未嘗不是對唯美主義的一種繼承與超越,這是不甘于被欲望束縛的自我救贖,一種對祖國未來最赤誠的希冀。阿爾都塞在其著作《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指出:“借助主體的范疇的作用,總體意識形態將具體的個體當作屬民招呼或質詢。”[15]祖國在召喚,人民在召喚,郁達夫通過“自我敘述”的形式在其小說中將作為知識分子的現代自我與民族國家的召喚緊密結合在一起。
三、結語
夏志清先生說“郁達夫的全部小說都是盧梭式的自白”,其批評觀點也認為“文學是替真和善服務,是包含一切人性的。必須體現對現實社會的獨立思考”[16]。郁達夫的小說創作直接受到盧梭《懺悔錄》的啟示,盡管在西方唯美主義的影響下,他追求著個性與自由,然而同盧梭一樣,他以“自我敘述”的方式將自我本相直接地、赤裸裸地暴露給他人,通過對真實的自我和自己真實需要的發現,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和政治的需要,其內質就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面對祖國黑暗現實的精神焦灼。有研究者就認為“郁達夫渴望通過國家民族來確定自身存在意義并不是如后來在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國家或集體對個體生命和意志的壓抑和剝奪,相反,郁達夫對國家民族的呼喚所反映的是他對人性的肯定,對自由意志的追求”[17]。因此,不難看出郁達夫小說中的那種沉湎與享樂的自我沉淪,也只是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獨特反抗方式,這種有心拯救卻無力回天而產生的危機感和幻滅感,有助于激勵讀者自省和矢志去改變落后的社會現狀。正如他在其全集的自序中說:“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殺賊。我只希望讀我此集的諸君,讀后能夠昂然興起,或竟讀到此處,就將全書丟下,不再將有用的光陰,虛廢在讀這些無聊的囈語之中,而馬上就去挺身作戰,殺盡那些比禽獸還相差很遠的軍人。那我的感謝,比細細玩讀我的作品,更要深誠了。”[18]祖國的社會現實和郁達夫對祖國的期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反差,他要借唯美主義去“自我敘述”出自己的憤懣,但這也決定了郁達夫的眼光是時刻著眼于祖國和社會的,他并沒有脫離現實。郁達夫小說中的頹廢和傷感是因社會而來,其作品中的反叛也正是因為他對社會和祖國的時刻關注,因此他不必也不可能躲進象牙塔,這也正是后期創造社的文學方向之所以轉向“革命洪流”的一個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