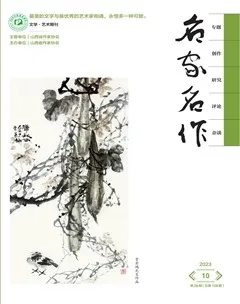從維護(hù)語(yǔ)言文化多樣性看《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典藏·哈爾濱》
李曉鑫
語(yǔ)言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重要的遺產(chǎn)。2001 年11 月,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發(fā)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shí)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xiàn)是構(gòu)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huì)的特性所具有的獨(dú)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chuàng)作的源泉,對(duì)人類來(lái)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duì)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應(yīng)當(dāng)從當(dāng)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rèn)和肯定。
語(yǔ)言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記錄并傳承一個(gè)族群、一個(gè)地區(qū)乃至世界獨(dú)特文化的主要載體,它有助于人們通過(guò)共享的行為模式、互動(dòng)方式、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和理解方式來(lái)交流,推動(dòng)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語(yǔ)言記錄了人類千百年來(lái)積累的傳統(tǒng)知識(shí)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這一知識(shí)寶庫(kù)促進(jìn)人類發(fā)展,見(jiàn)證了人類改造自然和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能力。
然而人類的語(yǔ)言文化多樣性卻面臨著一個(gè)巨大的危機(jī),即語(yǔ)言和文化多樣性向語(yǔ)言文化單一性轉(zhuǎn)變,大約每周就有一種語(yǔ)言消失,據(jù)估計(jì)現(xiàn)存語(yǔ)言的一半會(huì)在未來(lái)幾百年內(nèi)消失。每一種語(yǔ)言都蘊(yùn)藏著一個(gè)民族獨(dú)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種語(yǔ)言文化的消亡都將是整個(gè)人類的損失。
一、我國(guó)為維護(hù)語(yǔ)言文化多樣性所采取的措施
為維護(hù)世界語(yǔ)言文化多樣性,世界各國(guó)采取多種措施,開(kāi)展了一系列保護(hù)搶救語(yǔ)言文化的工作。如設(shè)立語(yǔ)言政策機(jī)構(gòu),制定語(yǔ)言政策,通過(guò)官方和教育渠道保護(hù)和傳承多種語(yǔ)言;采取立法措施來(lái)保護(hù)語(yǔ)言文化;將文化遺產(chǎn)納入教育領(lǐng)域中,通過(guò)教育來(lái)保護(hù)本國(guó)的語(yǔ)言文化;鼓勵(lì)和促進(jìn)語(yǔ)言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保護(hù)傳統(tǒng)文化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等。
我國(guó)是一個(gè)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guó),積累了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擁有豐富的語(yǔ)言資源。近幾十年來(lái),我國(guó)保護(hù)語(yǔ)言文化的意識(shí)不斷增強(qiáng)。 2011 年 10 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huì)報(bào)告《中共中央關(guān)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首次從國(guó)家層面提出了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文化強(qiáng)國(guó)戰(zhàn)略,報(bào)告指出要“大力推廣和規(guī)范使用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科學(xué)保護(hù)各民族語(yǔ)言文字”,首次提出“科學(xué)保護(hù)各民族語(yǔ)言文字”的要求,并與“大力推廣和規(guī)范使用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這一基本語(yǔ)言政策并列;同時(shí)提出要“維護(hù)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抓好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承”“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2012 年11 月,黨的十八大報(bào)告特別強(qiáng)調(diào)要“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繁榮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事業(yè)”。[1]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jiàn)》,明確指出要“大力推廣和規(guī)范使用國(guó)家通用語(yǔ)言文字,保護(hù)傳承方言文化”。其中,“保護(hù)傳承方言文化”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的重要方面,首次出現(xiàn)在黨和政府的文件里[2]。
為了保護(hù)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資源,維持語(yǔ)言文化多樣性,2015 年,教育部、國(guó)家語(yǔ)委啟動(dòng)實(shí)施“中國(guó)語(yǔ)言資源保護(hù)工程”(以下簡(jiǎn)稱“語(yǔ)保工程”),語(yǔ)保工程把語(yǔ)言視為重要的文化資源,認(rèn)為語(yǔ)言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信息溝通、文化傳承、文明交流、情感系連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每一種語(yǔ)言無(wú)論其使用人口、通行范圍如何,都是一個(gè)信息豐富且不可替代的文化資源庫(kù),語(yǔ)言多樣性是文化多樣性的前提。
語(yǔ)保工程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開(kāi)展語(yǔ)言資源調(diào)查、保存、展示和開(kāi)發(fā)應(yīng)用。目前已完成1700 多個(gè)田野調(diào)查點(diǎn)的調(diào)查,范圍涵蓋全國(guó)34 個(gè)省(區(qū)、市)120 余種語(yǔ)言和各地方言,收集原始文件數(shù)據(jù)1000 萬(wàn)余條,建成了目前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語(yǔ)言資源庫(kù)。
《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典藏》是語(yǔ)保工程的標(biāo)志性成果,共包括50 種語(yǔ)言文化圖冊(cè),第一批20 冊(cè)于2017 年出版,包括漢語(yǔ)方言文化19 冊(cè)和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化1 冊(cè);第二批30 冊(cè)于2022 年出版,包括漢語(yǔ)方言文化18 冊(cè)和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化12 冊(cè)。圖冊(cè)以調(diào)查條目為綱,收錄語(yǔ)言文化圖片及其語(yǔ)言名稱,以漢字記錄名稱,以音標(biāo)標(biāo)寫(xiě)讀音,用漢字對(duì)圖片代表的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解說(shuō),以圖代文,圖文并茂,對(duì)于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動(dòng)進(jìn)行錄像,條目后附有二維碼,閱讀時(shí)可用手機(jī)掃碼,在線訪問(wèn)錄音、視頻,通過(guò)融媒體技術(shù)打造了音、像、圖、文四位一體的閱讀體驗(yàn)。
《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典藏·哈爾濱》(以下簡(jiǎn)稱《典藏·哈爾濱》)是《中國(guó)語(yǔ)言文化典藏》系列第二批叢書(shū)之一,該著作對(duì)哈爾濱傳統(tǒng)方言文化進(jìn)行了全面的調(diào)查、記錄和保存,對(duì)哈爾濱文化特點(diǎn)進(jìn)行了深入挖掘。
二、對(duì)哈爾濱多樣性語(yǔ)言文化的挖掘和展示
哈爾濱語(yǔ)言文化呈多元一體性特點(diǎn),多種文化要素的融合正是哈爾濱語(yǔ)言文化的獨(dú)特之處。
哈爾濱地處中國(guó)北端,冬季漫長(zhǎng)寒冷,冰雪文化久負(fù)盛名,是世界冰雪文化發(fā)源地之一;夏季涼爽怡人,是避暑休閑的勝地,有“冰城夏都”之美譽(yù)。
哈爾濱的歷史源遠(yuǎn)流長(zhǎng),早在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這里就已經(jīng)有人類活動(dòng)。曾先后有肅慎、夫余、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在這一代生活。公元1115 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上京建國(guó)稱帝,即今哈爾濱阿城。清朝建立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在阿城設(shè)阿拉楚喀副都統(tǒng),哈爾濱為其所轄,屬于吉林將軍。清中后期,隨著“京旗移墾”和“開(kāi)禁放荒”政策的實(shí)施,大量滿漢百姓移居此地。19 世紀(jì)末,已形成了香坊、傅家甸、顧?quán)l(xiāng)屯、松羅堡、白旗窩堡等數(shù)十個(gè)自然村屯,居民有3 萬(wàn)左右,交通、貿(mào)易、人口等經(jīng)濟(jì)因素開(kāi)始迅速發(fā)展,為城市的形成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至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隨著中東鐵路的建設(shè),工商業(yè)及人口開(kāi)始在這一帶聚集,中東鐵路建成時(shí),哈爾濱已經(jīng)形成近代城市的雛形。20 世紀(jì)初,哈爾濱發(fā)展為國(guó)際性商埠,先后有各國(guó)僑民16 萬(wàn)余人聚集在這里。同時(shí),中國(guó)民族資本也有了較大發(fā)展,一批民族工商業(yè)精英在此開(kāi)商鋪、辦實(shí)業(yè)。哈爾濱很快發(fā)展成一個(gè)華洋雜處的城市,多國(guó)文化帶來(lái)的濃郁的異域風(fēng)情使得哈爾濱被冠以“東方小巴黎”“東方莫斯科”等稱號(hào)。
多種文化元素在哈爾濱相遇、碰撞,如本土少數(shù)民族文化,尤其是金源文化、移墾京旗帶來(lái)的京城滿族文化、“闖關(guān)東”移民及關(guān)內(nèi)民族資本家?guī)?lái)的中原文化、僑民帶來(lái)的各色歐陸文化,在這里疊加、融合、沉淀,逐漸形成了獨(dú)特的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在這里,老榆樹(shù)、丁香花、古老的歐式建筑互相映襯,異域文化與本土自然景觀和諧共生[3]。
《典藏·哈爾濱》對(duì)哈爾濱語(yǔ)言文化中的多元要素進(jìn)行了挖掘,中西合璧、南北融合的特點(diǎn)正是哈爾濱語(yǔ)言文化的獨(dú)特之處。該著作從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飾、飲食、農(nóng)工百藝、日常活動(dòng)、婚育喪葬、節(jié)日、說(shuō)唱表演九個(gè)方面展示了哈爾濱語(yǔ)言文化的獨(dú)特魅力,分析了每類語(yǔ)言文化現(xiàn)象的多元性和獨(dú)特性。
以建筑為例,哈爾濱被稱為世界建筑藝術(shù)博物館,這與哈爾濱城市的形成發(fā)展歷史密切相關(guān)。哈爾濱近代城市的建設(shè),是從中東鐵路的修建開(kāi)始的。建城初期,哈爾濱建筑有明顯的俄羅斯建筑風(fēng)格,而俄羅斯建筑藝術(shù)受當(dāng)時(shí)歐洲的影響較大,歐洲建筑藝術(shù)經(jīng)由俄羅斯帶到哈爾濱,所以,早期的哈爾濱城市既有俄羅斯民族風(fēng)格建筑,也有西方的折衷主義風(fēng)格、新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巴洛克等風(fēng)格的建筑。中東鐵路建成后,大量的歐洲移民涌入哈爾濱,他們又修建了大量不同風(fēng)格的歐式建筑。同期,關(guān)內(nèi)大量的民族工商業(yè)者紛紛來(lái)到哈爾濱,他們大多在傅家甸開(kāi)店辦廠,在那里修建了一批中西合璧式的中華巴洛克建筑。市內(nèi)也有純粹中式的傳統(tǒng)建筑。多種風(fēng)格的建筑留存到現(xiàn)在,如哈爾濱的中央大街以歐式建筑為主,哈爾濱老道外有世界上最大的中華巴洛克建筑群,哈爾濱南崗區(qū)有“黃房子”保護(hù)街區(qū),屬于俄羅斯傳統(tǒng)民房風(fēng)格建筑群。
哈爾濱郊區(qū)保留了一些東北地區(qū)特有的草房和土房。所謂草房,指的是以草苫房頂?shù)钠鸺沟耐练浚@類房屋與滿族、達(dá)斡爾族等少數(shù)民族的房屋架構(gòu)相似,應(yīng)是受到了早期生活在這里的少數(shù)民族的影響。土房是指屋頂墻體都是用土建造的平頂房屋,這類結(jié)構(gòu)的房屋應(yīng)是受到以種田為主的關(guān)內(nèi)漢人的影響,因?yàn)槠巾斂梢杂脕?lái)晾曬糧食。
20 世紀(jì)初期,西方的、中國(guó)南北方的、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建筑文化元素,都可以在哈爾濱建筑中略窺一斑。多種建筑文化要素集結(jié)于哈爾濱,打造出哈爾濱獨(dú)特的建筑文化風(fēng)格。
《典藏·哈爾濱》對(duì)哈爾濱現(xiàn)存各種類型的傳統(tǒng)建筑進(jìn)行了拍攝、整理、歸納,介紹了每種建筑的歷史、建筑特點(diǎn)以及目前保留情況,讀者在這里可以概覽哈爾濱傳統(tǒng)建筑文化的全貌。書(shū)里的一些建筑圖片,建筑本身目前已經(jīng)被拆遷,尤其老舊土房,或坍塌,或改建,好多已找不到建筑實(shí)體,它們以圖片的形式保留在書(shū)里。
三、對(duì)哈爾濱瀕危性語(yǔ)言文化的搶救和保護(hù)
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的消亡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個(gè)問(wèn)題,哈爾濱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同樣的趨勢(shì),一些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項(xiàng)目逐漸走向?yàn)l危。哈爾濱語(yǔ)言文化是世界語(yǔ)言文化的組成部分,搶救保護(hù)哈爾濱語(yǔ)言文化,也是對(duì)世界語(yǔ)言文化多樣性的保護(hù)。
哈爾濱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的瀕危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一些語(yǔ)言文化現(xiàn)象正在消失;二是對(duì)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缺乏認(rèn)知和認(rèn)同,人們對(duì)傳統(tǒng)語(yǔ)言文化缺乏了解,尤其是年輕一代,對(duì)家鄉(xiāng)文化了解較少,缺乏認(rèn)同感。
傳統(tǒng)文化中消亡速度較快的如農(nóng)耕文化,隨著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水平和機(jī)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耕作方式已經(jīng)大大簡(jiǎn)化,春種秋收基本實(shí)現(xiàn)了機(jī)械化,只有一些不方便使用機(jī)械的山地還保留了一些傳統(tǒng)的耕作方式。傳統(tǒng)農(nóng)具基本派不上用場(chǎng),多數(shù)收進(jìn)倉(cāng)庫(kù),由于傳統(tǒng)農(nóng)具多用木頭、麻繩等材料制成,這些材料不耐風(fēng)雨侵蝕,多數(shù)都已腐化。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化幾近消亡。
有些傳統(tǒng)文化也在走向消亡的過(guò)程中。哈爾濱歷史上繁華一時(shí)的老道外商業(yè)街區(qū),有世界上最大的中華巴洛克建筑群,其中一些建筑年久失修,在天長(zhǎng)日久的風(fēng)雨侵蝕中變?yōu)閺U墟,有的則在城市規(guī)劃和改造中失去了原貌,隨著這些見(jiàn)證城市歷史的建筑的變化和消失,人們對(duì)這座城市的認(rèn)識(shí)也將逐漸變得抽象和殘缺。
哈爾濱中央大街是深受哈爾濱人喜愛(ài)的一個(gè)歷史文化街區(qū),是休閑娛樂(lè)的重要場(chǎng)所,也是哈爾濱重要的旅游景點(diǎn),那里有很多充滿異域風(fēng)情的歷史建筑,每座建筑的背后可能都有著復(fù)雜曲折的故事,然而到這里休閑娛樂(lè)的人們,可能沒(méi)有多少人有興趣去探究它們的過(guò)往滄桑。
《典藏·哈爾濱》對(duì)一些即將消亡的農(nóng)業(yè)、建筑等項(xiàng)目進(jìn)行了搶救性的拍攝和記錄,對(duì)面臨瀕危的項(xiàng)目進(jìn)行了梳理,并呼吁人們關(guān)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保存和傳承。
從語(yǔ)言的角度來(lái)看,文化通過(guò)語(yǔ)言表征,對(duì)文化的搶救保護(hù)也是對(duì)承載文化的語(yǔ)言的搶救和保護(hù)。《典藏·哈爾濱》以詞匯為落腳點(diǎn),通過(guò)詞匯展示文化,而詞匯中又往往保留了方言語(yǔ)音、語(yǔ)法等現(xiàn)象。口頭文化本身就是以語(yǔ)言為表現(xiàn)形式的,口頭文化中保留了大量的方言現(xiàn)象。如歇后語(yǔ)“三九天穿布拉吉兒——抖起來(lái)了”,這里有典型的哈爾濱方言詞“布拉吉兒”“抖起來(lái)”,“布拉吉兒”為俄語(yǔ)音譯詞,即連衣裙,“抖起來(lái)”即發(fā)達(dá)起來(lái)了。再如謎語(yǔ)“紅公雞,綠尾巴,一頭扎到地底下——胡蘿卜”。“尾巴”方言中讀[i21pa0] ,“胡蘿卜”方言讀[xu24luo0pei53]。這些方言詞語(yǔ)在方言中的使用越來(lái)越少,語(yǔ)音上越來(lái)越向普通話靠攏。
四、打造優(yōu)秀城市文化名片,助力家鄉(xiāng)傳統(tǒng)文化教學(xué)
《典藏·哈爾濱》全面展示了哈爾濱文化的特點(diǎn),濃縮了哈爾濱文化精華,全方位彰顯了哈爾濱的魅力,對(duì)擴(kuò)大城市的影響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義。它讓本地人感到親切,讓外地人感到新奇,堪稱不可多得的城市名片,對(duì)國(guó)內(nèi)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了解哈爾濱具有重要參考價(jià)值,可以為哈爾濱各種文化宣傳活動(dòng)提供參考。2025 年,第九屆亞冬會(huì)將在哈爾濱舉行,該成果或許可在亞冬會(huì)的文化宣傳中發(fā)揮作用,助力哈爾濱文化走向世界。
語(yǔ)言文化保護(hù)的最終目的在于傳承,學(xué)校教育無(wú)疑是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當(dāng)前高中語(yǔ)文統(tǒng)編必修教材中設(shè)置了“家鄉(xiāng)文化生活”單元,其教學(xué)目標(biāo)是厚植家國(guó)情懷、樹(shù)立文化自信,借助多彩鄉(xiāng)土文化鑄魂,提升學(xué)生人文素養(yǎng),培養(yǎng)學(xué)生健全人格,實(shí)現(xiàn)立德樹(shù)人。《典藏·哈爾濱》匯集鄉(xiāng)土文化精華,可以作為實(shí)現(xiàn)語(yǔ)文學(xué)科在地化教育的參考資料,為“家鄉(xiāng)文化生活”教學(xué)提供教學(xué)資源,利用學(xué)校教育使優(yōu)秀地域文化一代一代更好地傳承下去。
五、結(jié)語(yǔ)
《典藏·哈爾濱》對(duì)哈爾濱語(yǔ)言文化的保護(hù)傳承進(jìn)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對(duì)于哈爾濱語(yǔ)言文化傳承保護(hù)來(lái)說(shuō)僅僅是個(gè)開(kāi)端,哈爾濱語(yǔ)言文化的保護(hù)既任重道遠(yuǎn),又迫在眉睫,如何對(duì)哈爾濱語(yǔ)言文化進(jìn)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更有效的保護(hù),如何引導(dǎo)全社會(huì)的參與,喚起全民關(guān)注,尤其是吸引年輕人的注意,獲得年輕人的認(rèn)同,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新性傳承發(fā)展,都是急需思考和解決的問(wèn)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