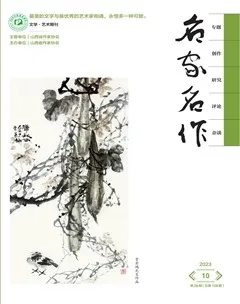袁枚《隨園詩話》詩歌批評論
楊宇茜
袁枚是乾嘉詩壇的重要人物,是清代中期極富才情和個性的文學家。其諸多著作中,《隨園詩話》集中體現了袁枚的詩學思想,尤以其“不論朝代、不論門戶、不拘人品”的批評原則和“尚趣、尚俗、崇清”的批評標準而聞名。
袁枚的詩歌批評理論以“詩境甚寬”總之,代表其在詩歌批評領域的視野和氣度。“此詩之所以為大也”,要求既有學士大夫終身難以參透的神妙精髓,又有鄉野間黃發垂髫村婦們能夠淺談一二的思想,隨口幾句卻能得到李太白的贊許,此謂“詩境甚寬”。以其開放的眼光和心態面對大眾,不論朝代,不究門戶,不拘人品,不再是“學人之詩”,而是學百家之長。
一、批評原則:不論朝代、不論門戶、不拘人品
(一)只論工拙,不論朝代
南宋以后,詩學界的唐宋之爭愈發激烈,到了袁枚所處的清朝強盛之世,文化環境已經相對開放許多。此時,對于這場跨越千年的爭論,袁枚提出了“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認為詩歌的主旨和所傳達的詩人性情才是最重要的,唐和宋只是朝代更迭,過分強調有失偏頗,因小失大。“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初唐張謂之的《安樂公主山莊》和盛唐名作《詠柳》的風格,與中晚唐詩風十分相似,但不能將其歸于中晚唐時期的作品。《隨園詩話》中提出“我道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論詩,能合吾意吾取之”,論詩應掩其朝代姓名才更加客觀,而非唯經典是從,不以前人之是非為是非,做到不厚古而薄今。
《隨園詩話》不喜評古,為數不多的評論里極為推崇楊萬里,譽其為“一代作手”,認為楊萬里詩作有含而不露的“天才清妙”,可比肩李太白。不拘于瑕,不掩飾,頗為后人詬病,實為其作精妙之處。袁枚“只論工拙,不論朝代”的評詩標準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詩歌批評標準作為一種新風向,對詩歌批評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門戶須寬,采取須嚴
“江海雖大,豈無瀟湘?”袁枚反對詩分唐宋,更反對以門戶論高下。袁枚認為對前人及其作品輕佻評論甚至肆意菲薄的詩歌批評者是“以宮笑角”,一些不知所謂讓大方之家為之一笑的“陋儒”。詩人向來各持己見,歐陽修不認同杜甫的詩作,而杜甫又不喜歡陶淵明的作品,明代竟陵派和公安七子互相詆娸、派別林立,清代王世禎宗王孟而貶元白,蔣士銓、錢玙沙則貶低王世貞而贊賞查慎行。對此,袁枚認為皆是、皆非,批評應有獨到見解,詩歌應自由表達性情,多元化詩風彼此映襯、互相兼容、求同存異地發展。此外,袁枚還提出采詩原則:“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采取須嚴。”“隨意閑吟沒家數”,只論精妙,不論門戶。
(三)《國風》雖好,究與人品無干
傳統文學批評的慣性認知是“文如其人”,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提出“吐納英華”皆源于自情自性,認為文與人之間是“表里必符”的。文學作品真實反映了作者的人品性情,直至清代,施閏章在《蠖齋詩話》中仍提到“詩如其人”,可見“文如其人”“詩如其人”對傳統文學批評影響深遠。
袁枚論詩重性情,提倡“有我”“著我”,此“性情”并不局限于道德上的人品,傳統意義上的“人品”指在道德教化下形成的以仁為核心特征的道德品質,在強調恪守綱常倫理、節制個人欲望的同時,忽視了人之所以能成為人而擁有的豐富、復雜的情感世界。因此,對于“人品”的認知,并不能完全將之等同于詩教訓誡,這通常都是追求一種溫柔敦厚的謙謙之風,還應尊重個人體驗與情感由心而出的抒發,“詩緣情”,文源“必不可解之情”。在情感迸發時,道德品質欠佳的詩人也能寫出動人悱惻的詩。袁枚秉持“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的公正立場,認為奸臣嚴嵩的《鈐山堂集》描繪的卷幔山霧、村聽禽啼、沙上柳松、水邊樓閣等景象亦有可觀之處。可見,“《國風》之好,究與人品無干”。
“《國風》之好,究與人品無干”,倡導詩人應注重本真、個性化的創作,對于詩作的品評要從詩歌本身出發,重視詩歌中展現出的才情,詩人的人品納入衡量范圍是欠妥的。與袁枚同處乾嘉時期的沈德潛等人,過分強調道德情操的重要性,認為詩歌并非作游戲用,“本是六籍之一”,能夠為王者提供一些政論依據與參考,“觀民風,考得失”,因此雖其表是在寫男女之情,其里卻“關乎君父友朋”。由此可見,論才情而不論人品的這一評詩原則,從另一個角度體現著袁枚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追求。
二、批評標準:尚趣、尚俗、崇清
袁枚詩論從前代詩學中吸取經驗形成于我國文學發展的成熟期,提出以“詩境甚寬”為基本原則的“不論朝代、不論門戶、不拘人品”的詩歌批評原則,在批評標準上,袁枚提出“尚趣、尚俗、崇清”,即重視詩趣、以俗為美、崇尚清境,做到詩境寬、采詩嚴。
(一)有格無趣,是土牛也
“趣”在歷代詩話中為文學評論家廣泛使用。“興趣”是嚴羽《滄浪詩話》中最重要的詩學主張,“興”是意興,“趣”則是指意趣,興趣是詩人情感自然流露后產生的審美趣味。明清時期,“趣”備受推崇,更是言論“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趣”同樣受到袁枚的重視,這很符合當時的時代特征。
袁枚推崇的“趣”,不僅指傳統意義上的幽默詼諧,而且與真實、性情有密切聯系,指詩歌抒寫性靈后產生的新鮮、活潑的生氣。真實是詩趣應具備的重要特征。“味欲其鮮,趣欲其真”,唯正確認識并做到這一點,而后才可品評詩歌。不僅如此,“真”才是“趣”的核心內涵,唯有真實,才能打動人心。詩是否有“趣”,與詩中是否傳達了詩人的性情有必然聯系。楊萬里“風趣專寫性靈”的創作風格備受袁枚贊譽,袁枚認為“有性情”自然“有格律”。以《三百篇》為例,其內容多為未受教育的勞人思婦抒發真摯感情,其中格、律是“誰為之”,將風趣與性靈、詩人的天賦才情聯系到一起,并指出只有“天才”才能做到“風趣專寫性靈”。所以,格、律乃性情反映于文辭而為之。無“趣”詩,徒有其表而無內在生機,不如不作。
袁枚還認為好詩必動人心目,動人心目必有風趣,反之,“詩有格無趣是土牛也”。他論詩講求感官的新鮮感受,把握對生活細節中所蘊含的美好情趣,有感而發作成詩。風趣是袁枚的一種審美思想,也是一種市民意識影響下的審美反映。
(二)家常語入詩最妙
乾嘉時期,文人審美心態世俗化,在袁枚的詩學理論里,“俗”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尚俗”在袁枚自己創作的詩歌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袁枚的詩歌不同于傳統詩風的溫柔敦厚,其崇尚熱烈奔放又直白的風格,與主流詩論含蓄蘊藉的風格背離。沈徳潛的《畫菊》全篇都在描寫晚開菊花面臨的種種境況,本為晚輩的桃李一夜之間成了前輩,還“憐爾枝頭帶曉霜”,實際上如果深究起來,其中描寫的不是菊花,而是自己晚年的境況,整首詩含蓄蘊藉,正是當時主流崇尚的風格,氣度內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袁枚的《喜魚門主事改官編修》,兩首詩雖然都在談“晚遇”,但袁枚豁達地表示“當年老子也婆娑”,這種肆意的調侃說笑,與士人傳統的自持之風截然不同。袁枚是“市民才子”,其審美取向不復傳統的溫柔敦厚,反而趨向市民語言的直言不諱,故展現出反含蓄、尚刻露的詩歌創作傾向。
其次,詩歌屬高雅文體,“雅”的傳統能使詩歌保持自身氣質的高貴,然而過度強調詩歌“雅”的傳統必然會造成其自身的老化。袁枚的詩歌吸收接納通俗文學,將通俗文學的筆法引入詩歌,創新詩歌文體。中國古典詩歌強調抒情,其輕視的人物描寫與情節刻畫反而成為通俗小說的評論標準,為其所擅長并追求的創作特點。用夸張手法來渲染和反映人物形象,同時用細致的情節刻畫呈現人物性格等手法也被袁枚借用,然后,尚“俗”在袁枚的詩學理論中關于詩歌語言層面的反映可以概括為“家常語入詩最妙”,強調平易自然,在《隨園詩話》中提出“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試圖通過白描的手法來極力營造平易、自然、和諧的文學語言風貌。《隨園詩話》非常重視收錄白描佳作,如黃岱洲的《過桃源》,“行過溪橋云密”,就聽到了不遠處的漁歌聲聲傳來,描繪桃源之景象,僅對小山河、薛蘿、溪橋、云、漁歌等意象進行白描,便勾勒出恬靜、美麗的桃源景色,淡而有味。
最后,袁枚對“俗”這一審美范疇的崇尚還體現在大量摘錄地位卑下之人的詩句,對其中一些作品極為認可推崇,如《隨園詩話》中提到的青衣鄭德基,“橫眠牛背唱山歌”,直白又充滿野趣。除此之外,還記錄了另外十幾首類似的詩作,認為作者雖本身地位低下,皆為一介奴仆,但氣度高華不下名士,尤其是鄭德基的詩句,更認可其天然去雕飾的意蘊,寥寥幾眼,直白卻彰顯靈氣,二月風光,如在眼前。
由此可見,袁枚無論是對“家常語”俗詩的喜愛還是自身詩歌的創作,都不乏對“俗”的追求與表露,并將之應用到自身史學理論中,既是踐行,也是有意地進行倡導和宣揚。
(三)詩貴清真
縱觀中國古代文論,可見大量的“清”,無論是論文還是論人,都離不開“清”。“清”本是自然詞匯,與水相結合,形容清澈。發展至魏晉,清談開始成為一種流行,一時之間文人雅客都開始以“清”自詡或以“清”為美,并將之大量用于人物品藻,慢慢滲透到文化內核,變成了一種士人的理想人格,并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審美意涵。自此之后,歷朝歷代,論文論人都未脫離“清”這一審美范疇。以唐為例,李白、杜甫、王維等人追求營造清雅、清靜的詩歌意境;宋代的蘇軾、姜夔、朱熹等強調清曠高潔,詞要清空騷雅,人格上要追求清正;明清兩朝依然如此,如胡應麟極欣賞曹植和李白,認為二者皆具“神骨之清”,賀貽孫強調關注詩作透露出的俊逸品格,劉熙載認為“清”“厚”合一的詩歌境界才是理想化的。同一時期,朱庭珍則認為要兼具“雄”和“清”,唯有達到這兩點,才是真正理想的詩歌。
袁枚認為,作詩要對淡與枯、新與纖、樸與拙、健與粗、華與浮、清與薄等相似卻截然不同的概念進行清晰的辨析,清麗與淺薄失之毫厘便會謬以千里,實則是要求對詩歌不同風格進行辨析。袁枚“清”的審美風格較偏重于意境中表露出來的清雅淡遠。“清”以其極強的包容性衍生出了諸多復合概念,“清真”占據著重要地位——“詩貴清真”被視為袁枚詩美理想的宣言。所謂“清真”,就“清”而言,主要指清雅,“雖真不雅,庸奴叱咤”;就“真”而言,指真實、真率、真切,“人之詩文,先取真意”。
袁枚的詩學思想中,清、真二字的含義談不上涇渭分明,至少可以稱得上是區分明顯。“清”字細細從其話語語境下推敲,其中有學力或功夫的含義,如《哭秋卿四妹》,談到謝靈運的詩作,對其評價為“最幽清”,之后又對這個評語進行詳細描述,是因為有推敲和學養作為支持,即前人所述的人巧和學問,由這里可以看出,清、真并非互斥的關系,反而是相輔相成的。
對性情的要求與標準是“真”,對情感的要求和標準是“濃”,在學問與功力等方面,士人本身就需要對具備的能力提出要求和標準,其在《答相國勸獨宿》中提出評斷詩歌“清真”的標準,先“真”而后得其中“清”,有言“別之欲其真也”,后要求“冽之”,然后淬煉或提純出其中的“清”來。由此可見,“清”與“真”關系緊密。在《隨園詩話》中提出“詩貴清真”,對“清”與“真”的關系進行了更細致的討論,認為“有性情而后真”,且在一首詩歌的品評過程中,難點在于其中是否有真意,不僅要有真意,還要雅,“有學問而后雅”,否則難免流于鄙陋。
“詩貴清真”作為袁枚提出的重要詩論觀點,其中“清真”既是詩歌風格,也是審美境界,它根植于真實性情,又輔之以深厚的學力,從而達到“清”“真”融合、不落凡俗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