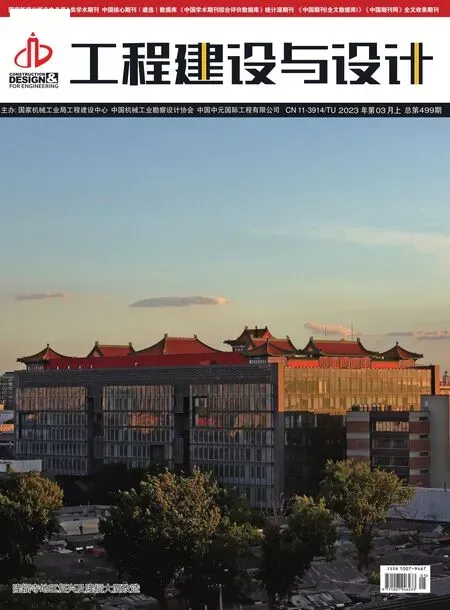建筑類型學(xué)視野下的廣州騎樓灰空間探析
王子龍
(長江大學(xué)城市建設(shè)學(xué)院,湖北荊州 434000)
1 引言
“灰空間”也稱泛空間,是由日本建筑師黑川紀(jì)章提出的,灰空間是介于封閉與開敞之間的過渡空間[1]。揚(yáng)·蓋爾將空間的過渡分為了私密、半私密、半公共、公共4 個(gè)部分,彼此之間和緩、流暢地銜接。“灰空間”的營造正是為了滿足人們對(duì)于社交尺度的需求。廣州騎樓采用了底層架空、柱廊、檐廊等公共空間不同的異質(zhì)要素來營造生成灰空間。
2 嶺南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與氣候特征
騎樓的街道灰空間形態(tài)的形成與當(dāng)?shù)貧夂虻牟煌兄懿豢煞值穆?lián)系。廣州屬于海洋性亞熱帶季風(fēng)氣候,地處沿海地區(qū),北回歸線穿過從化地區(qū)。氣候特點(diǎn)是夏熱冬溫,雨熱同期,季風(fēng)明顯。春季降雨頻繁,有回南天,天氣潮濕,秋季臺(tái)風(fēng)頻發(fā)。氣候?qū)Ξ?dāng)?shù)厝藗兊娘嬍沉?xí)慣和生活方式都有所影響,廣州騎樓的空間建造方式也適應(yīng)了廣州的氣候特點(diǎn)。騎樓的空間為步行購物環(huán)境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促進(jìn)了廣州商業(yè)的發(fā)展。同時(shí),廣州商業(yè)發(fā)展又帶動(dòng)了騎樓商業(yè)街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使騎樓成為廣州的一大特色建筑名片。
3 廣州騎樓灰空間的人群活動(dòng)類型及使用情況調(diào)研
揚(yáng)·蓋爾提出人們?cè)诠部臻g的戶外活動(dòng)有3 種類型:必要性活動(dòng)、自發(fā)性活動(dòng)和社會(huì)性活動(dòng),而空間作為催化劑加速了人們的交往活動(dòng)。筆者分了3 個(gè)時(shí)間段對(duì)北京路騎樓灰空間下的人群活動(dòng)進(jìn)行觀察調(diào)研。早上休息玩耍的人占10%,購物的人占70%,行走交通的人占20%。下午休息玩耍的人占20%,購物的人35%,觀賞的人占15%,行走交通的人占30%。晚上購物的人占75%,行走交通的人占10%,觀賞的人占15%。以上人群活動(dòng)類型的占比與騎樓空間的作用(優(yōu)化環(huán)境,共享交流)和騎樓的功能屬性(居住、商業(yè))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4 騎樓建筑灰空間
廣州騎樓建筑有單開間、雙開間及多開間的平面類型。在北京路騎樓群里有些騎樓仍保留二層以上是居住功能,也有部分騎樓的二層以上改造后是商業(yè)功能,也是公共空間。騎樓仍保持著中式的室內(nèi)平面布局,西式的立面特征。廣州騎樓建筑的灰空間有入口空間、天井、雨篷、陽臺(tái)及露臺(tái)等。
4.1 天井
由于騎樓建筑室內(nèi)的空間進(jìn)深較大,在采光方面會(huì)受到影響,因此,通過天井的置入可為騎樓內(nèi)部空間增加采光照射,同時(shí)也豐富了騎樓建筑的內(nèi)部空間感受,營造中國的傳統(tǒng)院落空間,形成灰空間。天井的置入模糊了建筑內(nèi)部的空間邊界,在一層平面空間布局中形成了一個(gè)小型庭院空間,在二層以上結(jié)合了走廊形成了一個(gè)邊庭空間和院落空間。天井是也是一個(gè)冷巷空間,起到通風(fēng)降溫的作用。
4.2 陽臺(tái)
北京路的二層陽臺(tái),有些是嵌在建筑內(nèi)部的凹陽臺(tái),與立面平齊,也有些陽臺(tái)是挑出立面,作為雨篷為一層遮風(fēng)擋雨,形成新的灰空間。起伏的陽臺(tái)為騎樓立面增添了光影和層次。
4.3 檐廊空間
在建筑學(xué)中“過白”的傳統(tǒng)空間序列營造方法中,檐廊空間的適宜尺度是站騎樓檐廊下的人能看到檐廊的天花板界面和對(duì)面騎樓屋頂上的天空,合適的檐廊D/H 值影響檐廊灰空間的體驗(yàn)(其中,D 為寬度;H 為高度)。
5 騎樓中介灰空間
5.1 轉(zhuǎn)折體
在街道口和城市的轉(zhuǎn)彎處,通過轉(zhuǎn)折體將兩個(gè)方向的騎樓建筑群銜接在一起成為過渡灰空間,轉(zhuǎn)折體能延續(xù)騎樓建筑的連續(xù)性。轉(zhuǎn)折方式分為弧形和折線形。轉(zhuǎn)折體作為騎樓轉(zhuǎn)角的處理手法,在轉(zhuǎn)折體灰空間里能體驗(yàn)新視角和多方向空間的變換,成為城市景觀變化的視覺審美焦點(diǎn)。
5.2 連接體
連接體由騎樓與門洞組成。連接體有樓與樓之間的連接,也有街與巷的連接,也有樓與廊的連接,通過簡(jiǎn)支結(jié)構(gòu)或者懸挑結(jié)構(gòu)連接兩棟騎樓,形成騎樓廊道寬的小型過廊和小型跨巷樓,并成為后院入口或者巷道門洞[2]。高低錯(cuò)落的連接體增添了騎樓的虛實(shí)感。
5.3 附加體
附加體為騎樓本體建筑頂部的附加小品塔樓。這些附屬建筑是騎樓或騎樓街本身的有機(jī)組成部分,也有的作為某種公共輔助設(shè)施,其影響著騎樓的藝術(shù)景觀。
5.4 冷巷空間
騎樓之間的冷巷面積小,太陽直射空間的面積也小,照射時(shí)間短,溫度較低。另外,風(fēng)經(jīng)過冷巷產(chǎn)生狹管效應(yīng),風(fēng)速增大,起到通風(fēng)降溫的作用。
6 騎樓城市灰空間
騎樓空間既屬于建筑空間,也屬于城市空間,既屬于私人空間,也屬于公共空間,既是居住空間和商業(yè)空間,也是交通空間,既是室內(nèi)空間,也是室外空間,根據(jù)綜合功能屬性,屬于過渡空間,稱為城市灰空間,屬于動(dòng)態(tài)灰空間。騎樓的城市灰空間包括廊道灰空間、街道灰空間和廣場(chǎng)灰空間。
6.1 廊道灰空間
廣州騎樓的廊道灰空間寬度大概在3.5~5 m。廊道的架空空間,具有良好的通風(fēng)性和連續(xù)性[3]。在廊道空間里有看與被看的藝術(shù),廊道空間的柱起到了框景的作用,外面的人能看到空間內(nèi)購物的人,廊道內(nèi)的人可以看到街道外的美景。同時(shí),這也是功能上的模糊美,既能購物,也能休息玩耍,也能通行。
6.2 街道灰空間
6.2.1 街道寬度
美國人類學(xué)家霍爾在他的《隱匿的尺度》[4]一書中,提出了人們的社會(huì)空間距離的幾個(gè)層次:第一個(gè)層次是親密距離(約0.15~0.45 m)。在這個(gè)距離上,可以發(fā)生愛撫、安慰、保護(hù)等行為。第二層是個(gè)人距離(約0.45~1.2 m)。在這個(gè)距離上,人們可以看清對(duì)方的神態(tài)等,并接受交流信息。第三層是社交距離(約1.2~3.6 m),在這個(gè)距離上,有一種社會(huì)互動(dòng)的意向。第四層是公共距離(約3.6~7.5 m),在這個(gè)距離上,人們是陌生的。
在霍爾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在社會(huì)空間距離以外的空間活動(dòng),人與其空間不會(huì)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當(dāng)人在社會(huì)空間距離以內(nèi)活動(dòng),人會(huì)與空間內(nèi)的事物發(fā)生交流互動(dòng)。因此,在廣州騎樓灰空間調(diào)研中可知,在廣州騎樓街里,當(dāng)人的社會(huì)空間距離大于3.6 m,即人離商鋪距離大于3.6 m 時(shí),游客購物的欲望比較低,而距離商鋪3.6 m 內(nèi)的游客,可能會(huì)與店家發(fā)生交易和聯(lián)系。因此,當(dāng)街道寬度大于7.2 m 時(shí),中央就形成一個(gè)不與周圍空間交流的區(qū)域,這樣給空間的行為帶來了多樣性。在騎樓的灰空間中,親密距離、個(gè)人距離以及社會(huì)距離都在騎樓公共空間的尺度范圍內(nèi),因此,在騎樓空間里因?yàn)樯鐣?huì)空間距離的不同可以看到多種空間行為。
6.2.2 街道長度
傳統(tǒng)騎樓街道的尺度多為小尺度街道,適宜步行。北京路步行街長度在600 m 以內(nèi)。隨著長度的增加,北京南路和周邊道路的繁榮程度逐漸銳減。
6.2.3 街道D/H
蘆原義信的《外部空間設(shè)計(jì)》書中提到街道D/H 的比例可以影響人的心理感受:D/H 等于1 時(shí),建筑與街道給人的感受親切舒適;D/H 小于1 時(shí),帶給人壓迫沉悶感;D/H 大于1 時(shí),會(huì)有寬闊感[5]。北京路的騎樓街道寬度為14 m,高度為15~20 m,D/H 值在0.8~1.0,空間的感受比較適宜。
6.2.4 騎樓街道灰空間節(jié)點(diǎn)形態(tài)
廣州騎樓的街道空間節(jié)點(diǎn)有丁字形、十字形和混合形。因?yàn)榻值揽臻g節(jié)點(diǎn)的多樣性,騎樓的街道灰空間也相應(yīng)形式多樣,廣場(chǎng)灰空間也因此具有多樣性(見圖1)。北京路街道有些是馬路,步行街里布置了景觀小品與樹,也布置了商業(yè)攤位還有休息空間,北京路的中段街道有千年古道遺址,在街道中央用天窗將遺址保護(hù)起來,向游客展示北京路是廣州古城發(fā)展中軸線的歷史文化。

圖1 北京路騎樓街道空間節(jié)點(diǎn)圖
6.2.5 街道灰空間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組合生態(tài)灰空間
在北京路騎樓步行街里的街道隨處可見街道灰空間與樹下灰空間的組合生態(tài)灰空間。建筑與自然是個(gè)有機(jī)共生整體,生態(tài)灰空間對(duì)人的行為和視線也起到了限定的作用,樹為當(dāng)?shù)刂参铮臻g也具有地域性,在灰空間下設(shè)置了游客座椅,游客坐在樹下乘涼休息,具有行為支持,這也是城市空間設(shè)計(jì)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相適應(yīng)的體現(xiàn),做到了騎樓建筑與自然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
7 廣州騎樓灰空間評(píng)析
7.1 騎樓灰空間的場(chǎng)所精神——城市的集體記憶
騎樓的底層架空的連續(xù)廊道灰空間在廣東夏季炎熱多雨的氣候中發(fā)揮著遮陽擋雨的功能,給人們帶來安全感,也是孩童玩耍的場(chǎng)所,是人們童年的美好回憶。同時(shí),在灰空間下進(jìn)行商業(yè)活動(dòng)等,展現(xiàn)了嶺南市井風(fēng)情,同時(shí)也蘊(yùn)含著濃厚的廣府文化特色,成為城市的集體記憶。
7.2 騎樓灰空間對(duì)建筑立面造型的塑造及影響
騎樓下段的梁柱或券柱廊道灰空間采用架空和立面掏洞的手法,削弱騎樓建筑的大體量,變成虛實(shí)空間,使空間變得通透和富有層次,同時(shí)連續(xù)整齊的廊道柱子增加了建筑的韻律感,結(jié)合自然光照射陽臺(tái)空間形成的光影效果,營造出了嶺南建筑的氛圍。
7.3 騎樓與現(xiàn)代建筑之間的銜接過渡
北京路的現(xiàn)代建筑有些仿照騎樓建筑的風(fēng)格進(jìn)行設(shè)計(jì),也有些現(xiàn)代建筑(北京路古籍書店)運(yùn)用現(xiàn)代手法設(shè)計(jì),但是運(yùn)用了底層架空和柱廊的灰空間塑造方式與當(dāng)?shù)仳T樓建筑進(jìn)行過渡銜接。
8 結(jié)語
廣州騎樓灰空間將人、建筑和環(huán)境聯(lián)系起來,使人與建筑與環(huán)境之間通過灰空間發(fā)生了交流和互動(dòng),優(yōu)化了廣州騎樓灰空間,豐富了灰空間形式,傳承了騎樓歷史文化。
騎樓灰空間的尺度影響著人的活動(dòng)和心理,不同的騎樓灰空間產(chǎn)生不同的互動(dòng)和聯(lián)系,把握好騎樓灰空間的尺度,對(duì)城市的經(jīng)濟(jì)和發(fā)展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北京路等騎樓街也與城市一起在慢慢發(fā)生變化,騎樓街區(qū)也在設(shè)計(jì)改造中更新和變化,但是廣州騎樓空間帶給我們的場(chǎng)所精神和歷史情感記憶沒有發(fā)生變化,滲透在我們每個(gè)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