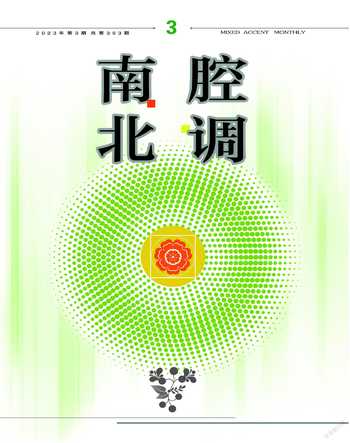散簡淡逸 大道無形
黃丹麾
中國寫意花鳥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現代寫意花鳥大師齊白石、潘天壽、李苦禪、王雪濤、湯文選、崔子范、張立辰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銳意求變,使寫意花鳥畫出現了更加嶄新的面貌。所謂寫意,即為“寫”其精神,具體來說就是不拘泥于“形似”,而著意于“神似”,這種“神似”主要表現在中國寫意花鳥畫的立意上,即抓住花鳥的內在特質,以比興手法表達人的志趣、情操和精神風貌,凸顯畫家的內在思想與審美追求。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走的是“傳統出新”之路,他以散簡淡逸之筆墨傳達藝術家對生命的熱愛,在深研傳統與“妙悟自然”的雙向整合中不懈地創新,進而形成不同于古人與他人的個性審美形式。筆者擬從四個方面對他的繪畫予以解讀,希冀讀者從中領會出周永基寫意花鳥畫的堂奧所在。
一、惜墨如金,大道至簡
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作品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簡”。“簡”亦可被理解為“大”和“無”,也就是說,“道”無法用具體的事物加以描述,只能予以極致的概括。這種審美觀念其實源于老莊哲學與禪宗美學。老子認為,“道”作為宇宙本體是一種無形無狀的存在,即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1] 。藝術創造活動是對宇宙萬物的審美體察,是語言概念和知識形式所無法涵蓋的,它是對一般語言概念和一般知識形式的超越,所以,藝術是妙不可言的,這也正如唐代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含蓄》中所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2]也就是說,藝術創作做到含蓄蘊藉、意在言外,無需太多華麗的詞藻和過多的烘托,只用含蓄簡明的語句,就把所包含的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老子關于宇宙本體超驗的思想對中國書畫美學的影響很大。宇宙本體超驗思想的核心觀點是:主張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而直接認識真理,強調超然分析與推理之上的直覺的重要性。唐代張懷瓘在《書議》中說:“言象不測其存亡……理不可盡之于詞,妙不可窮之于筆。”[3]在張懷瓘看來,“言”“象”“筆”屬于形式美的范疇,這是藝術的“語言”,但是“理”“妙”則是對藝術的超驗性質(這與宇宙本體息息相關)的很好說明,即藝術之理和藝術之妙在藝術語言和筆墨技巧之外,即“理”與“妙”生于象外,這與老子的“道常無名”異曲同工。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哲學與美學思想,他指出:“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4]其又曰:“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5]在莊子看來,人類的感官無法把握宇宙本體之“道”,因為“道”是一種“無形”的超驗存在。但是,宇宙本體之“道”的超驗性質,還是可以通過超越經驗性質的更高意義上的直覺化“視”“聽”被把握和感知的,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獨見”“獨聞”。“獨見”“獨聞”這種直覺方式與中國書畫美學一再強調的審美觀照是一脈相通的。謝赫所說的“取之象外”、郭熙所言的“景外意”“意外妙”、蘇軾所云的“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祝允明所謂的“無言之妙”都是對莊子美學的發揮。

禪宗美學是以道家為主兼顧佛家的綜合美學,它的特點在于借助神秘的直觀證得自身的佛性,一方面將以往人們視為實有的大千世界視為不斷變幻的現象即假象,另一方面又比任何學派都更重視人對自性、佛性和自省的親證。在禪宗那里,內觀外觀所見都是“空”,只有“自在”才是真如佛性。禪宗最關心也最重視人的靈魂的解脫,把人的主體性推到極致,強調頓悟和漸悟,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境界的意境化,這些都與人的審美經驗息息相關。禪宗美學的首要特征在于自然的心相化,禪宗美學的第二個特征在于將自然現象作為人化的映射,進而形成境界和意境。在中國美學史中,境界和意境作為藝術范疇,在唐代由于受到禪宗的深刻影響才得以成立。禪宗的世界觀使中國的山水畫、寫意畫具有了精神的深度,走向了心靈化和意境化。例如,虞世南的“心悟”、張彥遠的“妙悟”、張懷瓘的“玄妙”,都是將禪宗美學具化到書畫美學之上得出的真諦。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無論是構圖、筆墨還是設色、意境,都是務求簡潔、力避繁雜。他的作品可謂“筆簡墨精”,作者不是對審美物象進行面面俱到、事無巨細地描繪,而是有所選擇、有所取舍,抓住最能表現對象本質的典型形貌特征,從而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見一葉而知秋”的藝術效果。藝術家的這種概括能力和錘煉本領,使他的“筆”與“墨”能夠“舉一反三”“以一當十”,在有限的語言中揭示出無限的心象。

《入冬得其味一》只畫一顆蘿卜、兩朵蘑菇、一只螳螂,而蘿卜只用兩條弧線加以概括,達到不能再減的審美效果。但是,簡潔不等于簡單,該作用筆至簡,線條圓潤有力,如錐畫沙,所施翠綠和草綠二色亦極為單純,題跋上寫的“入冬得其真味在,尚見農家臘菜香”使一股濃郁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質樸的田園生活充滿著歐陽修所說的“山林者之樂”,這亦是“富貴者之樂”難以體會、無法企及的超越物欲的自然之美。

《入冬得其味二》屬于團扇作品,仍以簡潔之筆墨繪制一顆綠纓白蘿卜,首尾各有一只紅綠相間的螳螂落于其上,二者通過肢體語言彼此呼應,表達出獲得食物的喜悅之情,此畫的細節刻畫細膩感人,構思卓爾不群,給人以擬人化的遐思與想象。

《三月至味》(封二)以簡略至極的筆墨描寫瓶中蘭花、盤中櫻桃和散落的硯臺,墨色濃淡相宜,色彩對比醒目,充滿生活情趣。題跋上寫道:“又是一年三月三,世事如水身似船。未尋轉眼至知命,筆槳硯舟渡前川。2018年春月修稧之日永居畫于筆山書院舊址并記。”這里有必要介紹下農歷三月三,這天亦被稱“上巳節”“修稧節”,有登高、賞花、祈福、沐浴等傳統活動。至今,在我國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三月三”仍是一個隆重而盛大的節日。周永基是貴州安龍人,求學和任教時均未離開過生養他的這片熱土。永基在此畫中感慨世事如流水,身心似渡船,轉眼自己已到知天命之年,他以筆為槳,以硯為舟,在藝術長河中不斷前行,讀來令人無比動容,能深切感受到藝術家創作心路的波瀾與變動。

談到疏簡這一美學風格,馬上會讓人想到南宋的梁楷、明代的陳淳、徐渭、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濤以及近現代的齊白石,這些大家肯定對永基有深刻的影響。《防疫之三》正是這種影響的體現,該畫作借用傳統團扇的方式創作,在作品下方繪一個口罩,右上角繪一只蜻蜓,二者形成對角線式構圖,該作用筆簡約,設色清雅,構圖疏朗,大面積的留白更增強了作品的空靈虛寂,頗有“無畫處皆成妙境”之趣。題跋上題寫的“不平凡的夏天”點明曾經疫情肆虐的主題,蜻蜓與口罩似乎形成矛盾焦點,暗喻抗疫的艱難。

二、縱橫放逸,不拘常法
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作品的第二個特點就是“逸”。“逸”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美學范疇,最早見于東漢崔瑗的《草書勢》。崔瑗在《草書勢》中曰:“蓄怒怫郁,放逸生奇。”[6]南朝的謝赫在《古畫品錄》中也有“縱橫逸筆”的說法[7];唐代的虞世南在《筆髓論》中則多次提到“逸”,如“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 [8] “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 [9]等。

最早提出“逸品”概念的是唐代的李嗣真,他在《書后品》中將“逸品”置于庾肩吾提出的“九品”之上。后來唐代的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序》中,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又提出了“不拘常法”的“逸品”概念。較早全面地對“逸格”加以界定的是北宋的黃休復,他在《益州名畫錄》中將朱景玄提出的“四格”加以重排,將“逸格”提至首位,并對“逸格”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10]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黃休復將“逸格”的內涵作了兩點規定:第一個規定就是“筆簡形具”。所謂“筆簡形具”就是指筆墨簡練,但形象具體而完備。第二個規定就是“得之自然”。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無為之義。“得之自然”就是消解一切人為痕跡,達到隨心所欲之藝術境地。第三個規定是“莫可楷模”“出于意表”。這就是說,“逸格”沒有辦法作為楷模,語言難以表達,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意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逸格”表達的是一種“技近乎道”的自由創造審美狀態。
“元四家”之一倪瓚在《題自畫墨竹》中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11]他又在《答張仲藻書》中云:“說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12]倪瓚在這里強調“逸氣”“逸筆”和“形似”的對立,十分類似黃修復所說的“逸格”和“能格”的區別,但是又和黃修復有所不同,他不是從審美創造和藝術風格意義上來看待這種對立的,而是從藝術家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境界上來理解這種對立的。首先,“逸氣”說代表了一種超脫塵世、歸隱山林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境界;其次,“逸氣”說代表了一種蕭涼自寂、悲慨孤絕的主觀意向。

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中的“放逸”表現在他不著意于鴻篇巨制,作品多以小品為主,小而精,小而有趣,創作隨性亦隨意。其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放逸”表現在“得之自然”上。這種“自然”就是清新明靜、率性致遠,毫無雕琢、刻意之感,給人以曠達、閑逸、疏散、爽放、活脫的視覺享受。當然,這種“自然”不是任意地放縱和涂鴉,而是歷經“凝神遐想,妙悟自然”之后的“隨心所欲”,也是“衣帶漸寬”后的“燈火闌珊”。
《田間》繪一只斜倚的竹筐內裝一顆大白菜,四朵蘑菇散落筐前。該作呈梯形構圖,逸筆草草,線條率真,墨色虛實相生,陰陽互補,頗有潘天壽、齊白石的遺風。題跋上寫有:“2019年夏月炎熱難耐,寫此田間之物,以正心中多生涼意。永基于筆山書院桂園西窗之下并記。”以此可見作者的散逸心態。其實,心靜自然涼,只要清心寡欲,必然“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13]。
《荷風一》在形式上仍屬于傳統團扇,該畫采用環形構圖,繪制一簇荷花正在含苞待放,荷花左側描寫一只青蛙正在蹬腿前行,十分逼真生動,它與荷花形成動靜對比,二者交相輝映,妙趣橫生。《荷上有風》畫一簇荷葉迎風而立,施筆隨性,用線鏗鏘,墨色酣暢,濃淡有序,黑白共生,頗具文人風骨。
《過眼心酸》以擬人手法描畫一只松鼠面對一串掛于高空的葡萄,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具有“過眼心酸”之感,此作構思奇巧,不落俗套,讓人感到詼諧幽默,不由會心一笑。
《田間偶遇》以靈動放逸的筆墨描繪絲瓜和松鼠,線條爽利,用筆入木三分,墨色的陰陽、濃淡恰到好處,筆墨與色彩彼此交融,天然成趣。絲瓜與松鼠在構圖上形成縱橫互補和動靜相生之勢。
三、恬淡寡飾,素樸天成
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作品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淡”。“淡”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美學范疇,最早來源于老莊。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中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14] 其又在《道德經·第五十五章》中云:“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15]老子所說的“淡”是一個和“巧”相對立的概念,“巧”是人為的、做作的,“淡”是自然的、無為的;老子所說的“淡”也是一個和“華”相對立的概念。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三章》中云:“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16]所謂“華”,就是一種表面的裝飾(“薄”),它的特點就是繁瑣。相反,所謂“淡”就是素樸、恬淡。老子認為“恬淡為上,勝而不美”[17],所謂“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就是說,恬淡就是“不美”,而“不美”就是大美、至美,是一種由宇宙本體“道”所顯示出來的樸素、自然、恬然之美,即天地之美。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他在《莊子·刻意》中云:“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18]莊子又在《莊子·天道》中云:“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19]可見,在莊子看來,恬淡是萬物的根本,也是宇宙本體的客觀規律。

老莊之后,推崇“淡”境者甚眾。宋代的歐陽修在《六一跋畫·試筆》中云:“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復,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20]在明代董其昌看來,“平淡”是一種崇高的審美理想,這種風格正是從“清曠”“淡然”的情懷中生發出來的。他說:“昔劉劭《人物志》以平淡為君德。撰述之家,有潛行眾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而大雅平淡,關乎神明……質任自然,是之謂淡。”[21]由此可見,董其昌認為“平淡”是一種美德,超越功名和利害關系,是一種自然無為的人性之美。



周永基的作品之“淡”首先體現在“清淡明澄”上。這種境界朦朧縹緲、若隱若現,給人以“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感,這種婉約、隱晦好似一曲裊繞的清音或韻律,細水長流、綿延不絕,頗具空曠、靜謐、嫻遠、淡泊之妙。他的很多寫意花鳥畫無論是筆墨還是設色,總有一種“霧里看花”的審美效果。比如,扇面作品《福壽》繪兩只葫蘆橫亙枝干之上,作者在作畫的過程中采用“折枝”畫法,同時借鑒清代石濤的“截斷法”構圖,即所謂“剪頭去尾,寫其精英,不落全相”。畫家畫出的橘黃色葫蘆筆墨寡淡至極,設色也以清淡為主,葫蘆諧音福祿,以此暗喻福壽,而落款“福壽雙全”則鮮明地點出主題。團扇作品《荷風二》以淡淡的花青和胭脂描繪西南冬日里的荷花,一只蜻蜓欲落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畫作的用筆和施色都極為雅淡,具有一種“欲說還休”的美感和安詳之境,這種“點到為止”的繪畫手法,極大地調動觀者的審美欲望。它一方面強化作品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給觀者以巨大的再創造空間,達到畫家與觀眾的雙向交融、彼此互補的藝術效果。



其次,周永基的作品之“淡”還體現在作者善用淡雅的筆墨和設色,其作品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其筆下的花鳥均處于“似與不似”之間,筆淡而意周,色淡而境足。
再次,周永基的作品之“淡”,還體現在他對筆下的物象進行 “自然的人化”和主體精神的對象化,這種主觀的變形有時構成了一定的抽象意味,進而開闊了藝術家的主體心胸和主觀心源,因此達到再現與表現的統一、物象與心象的共振,這無疑提升了審美形象的境界和意趣。


四、以西潤中,二元共生
周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作品的第四個特點就是“合”,即以西潤中,中西合璧。周永基的創作風格既來自古典先賢的傳統,也來自觀察生活的寫生,他的寫意花鳥畫將中國傳統的白描和西畫的寫生與素描相整合,使寫實與寫意達到融會貫通。《三月至味》中的硯臺、《田間》里的蘑菇、《雅室》中的花盆、《防疫之三》里的口罩都被打上西畫速寫、素描的印記,具有一定的立體感和空間性,顯示出藝術家打通中西繪畫的雄心與抱負。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永基的畫仍有可以提升之處:其一,從他寫意花鳥畫作品中的題跋可以看出,其書法造詣還有擢升的空間,因為書法是線條的根基,線條是筆墨的基石;其二,繪畫作品中的款識可以更加詩化,因為詩意之美是文人寫意畫的核心所在;其三,小品畫易于小巧有趣,但是能以咫尺之幅描繪出天地大美的雄強廣袤最為難得,所以,永基的畫的境界還可以進一步雄闊強碩。中國寫意花鳥畫重在意境的營造,是一種類似音樂或舞蹈所引起的一種精神空間的想象,它不受現實的時空制約,如天馬行空般任情肆意,創造出只屬于畫家自己心靈之景,在有限的幅面上可以畫千里之景,有咫尺萬里之感。在此方面,可以潘天壽的畫作為鑒。



總之,瑕不掩瑜,永基的寫意花鳥畫以“簡”“逸”“淡”“合”為宗,以任意無為、自然天成為美學依托,進而“不以目視”“而以神遇”,在簡括、放逸和恬淡的藝術追求中臻于隨性、天意,走向“書畫契于無為,心悟至于大道”的妙境!衷心希望他在“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藝術之途上繼續砥礪奮進,踔厲前行,為達到光輝的藝術頂點而忘我獨造!
參考文獻:
[1][13][14][15][16][東周]老子.道德經[M].陳忠,譯評.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25,69,65,122,71.
[2]郁沅.二十四詩品導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55.
[3][5][6][7][8][9][11][12][17][18][19][21]樊波.中國書畫美學史綱[M].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34,38,187,252,363,366,508,509,52,55,55,594.
[4][戰國]莊子.莊子[M].韓維志,譯評.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119.
[10]云告,譯注.宋人畫評[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120.
[20]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42.


作者單位:中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