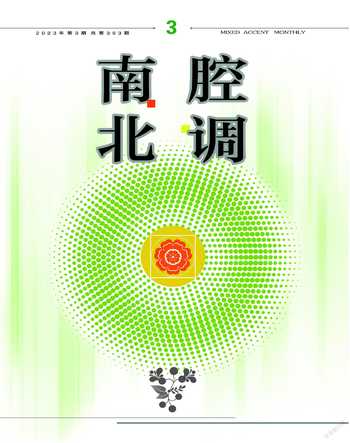消費語境下新世紀小說“女性形象”敘事的新向度及邏輯
梁婉月
摘要:在消費語境下,新世紀以來的小說關于“女性形象”的敘事主要呈現出三個向度的特點:一是身體與后現代性:都市女性的修羅場;二是想象、出走與留守:鄉村底層女性的困境;三是歷史的隱退:“文革”女性形象敘事的日常世俗化。這三個向度的寫作有消費社會外部及文學內部的生成邏輯:新世紀大眾文學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引導的寫作偏移;同時,作家在對于消費社會現象的觀察及反思內化于自身寫作中,力圖突破慣性思維等。但在“女性形象”敘事中也存在部分問題:過于表現人物個性化而設置離奇、巧合的情節,人物形象缺乏內在變化邏輯,寫作價值立場顯得迷茫或市場化傾向明顯。
關鍵詞:新世紀小說;女性形象;向度;邏輯

21世紀以降,消費社會強大的市場經濟邏輯,以不可抵擋之勢全面延伸到了文學領域,尤其網絡技術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傳統主流文學固有的一套發布、傳播模式,以讀者與資本為支撐的大眾文學,迅速占領了文學市場的“多壁江山”。如從網絡文學來看,“網絡文學近年來穩步高速發展,網絡文學用戶2011年2.03億,2012年2.33億,2013年2.74億,2014年2.93億。與網絡文學龐大的用戶數量對比的是,傳統主流期刊每年不過幾十萬的訂戶數”[1]。從消費讀者數量這一直觀數據對比,就能看出消費語境下大眾文學對傳統主流文學的強勢擠壓,曾經流行一時的穿越、玄幻、宮斗及仙俠小說等都是典型代表。在大眾文學的沖擊與影響之下,傳統主流小說的敘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中關于“女性形象”的敘事改變尤為明顯。從社會語境分析,21世紀的女性較之以往,在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女性擁有了更多的空間及可能,因此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敘事,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嬗變。縱觀中國當代文學,十七年文學中“女性形象”的敘事受官方話語支配,一般處于勞動、非勞動,集體、非集體的語境中;“文革”文學中幾乎未有任何與“女性形象”有關的敘事;新時期文學,在改革開放政策導引下,人性解放、人道主義的討論一度成為熱潮,以林白、陳染為代表的“身體寫作”開啟了女性“身體覺醒”的個人化敘事;而21世紀以來的文學,在消費文化語境下,大眾化、世俗化已成趨勢,女性本身也具有待挖掘的可能性,“女性形象”敘事明顯具有了消費文化的某些特征,如對感官刺激的追求、夸大情節以迎合讀者等。本文主要以傳統主流小說文本為對象,重點考察新世紀以來小說文本對于“女性形象”敘事的向度,探討敘事話語背后的生成邏輯因素,以及存在的問題及反思。
一、身體與后現代性:都市女性的修羅場
在西方中世紀,“身體”是受到壓制與道德譴責的對象,這與柏拉圖追求理性自由免除欲望的哲學一脈相承,文藝復興運動打破了教會對于身體的禁錮,開啟了解放身體、發現身體之美的哲學思潮,尤其在尼采喊出了“一切從身體出發”的口號后,開啟了與形而上學相對的形而下的哲學思潮,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則是發現了身體的剩余價值,即身體的消費價值。在中國,“五四”時期與新時期的兩次啟蒙思潮解開了對身體的禁錮后,“身體”又迅速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成為消費時代的“最美的消費品”[2]。尤其對于生活在都市的女性而言,一旦擁有姣好的面容、身材,也就意味著擁有“深入開發能使自我興奮、享受、滿意的一切可能性”[3]。同時,新世紀以來經濟的高速發展,催生了一批所謂中產階層,這一階層人士通常在社會中占有更多的物質財富、政治話語權或文化領導權,“欲望化”是這一群體的主要特征。而都市女性處在消費神話的修羅場中,一方面,她們的身體容易成為被中產階層開發與消費的資源;另一方面,自身物質經濟優越的中產階層女性也有著自覺解放身體、享受欲望的沖動性。面對這一社會癥候,文學領域的創作也表現出同步性,分析研究此類小說文本,表現出以下兩個向度的敘事特征。
向度一:書寫對于物質與性愛的無節制迷戀。這一類文本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已呈現出洶涌之勢。如《欲望》《上海寶貝》《盡情狂歡》《我愛美元》《像衛慧那樣瘋狂》等。“欲望美學和快樂原則成為日常生活審美至高無上的價值標準”[4],是這一類文本共同呈現的主體精神。新世紀以來的都市小說文本基本延續了這一創作審美原則。閆真的《因為女人》中的柳依依,在校園時期沉醉于與初戀男友的一次次“小旅館性愛狂歡”,畢業后又成為中產階層已婚男性秦一星養的“金絲雀”,并依賴著秦一星所給的金錢沉迷于高檔物質消費。除了柳依依,其兩個好朋友苗小慧和阿雨,也是在由中產男性形成的權力、金錢的圈子里不斷沉淪。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因為從小物質的極度匱乏,成年之后靠著“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5]的強大“信念”,混跡于北京的商業圈,各種名牌服裝加持,依靠非法集資獲得的金錢在商業社交圈中將自己塑造為成功美麗女強人的形象,但最終的牢獄之災打破了其一手創設的“完美女人”泡沫。石一楓的《紅旗下的果兒》中找不到存在感、真實感的陳木,只能盲目地投入不分性別及年齡的“戀情”與不能自已的性愛循環中。吳玄的《陌生人》中的何燕來更是通過混亂無節制的性愛、墮胎及吸毒等行為徹底走向了自我毀滅的結局。當然,還有一類文本中的女性敘事,女性本身對物質及性愛的迷戀帶有一定的被動性,通常具有特定環境中無奈與別無選擇的屬性,但從文本敘事角度思考,這似乎是作家迎合讀者及市場的一種技巧,在收獲了閱讀者對文本主人公的同情與憐愛的同時,依靠巧妙的性愛敘事,博得市場的頭彩。如海男的《花紋》中的女主人公之一夏冰冰,為了回報賴哥對其家庭的幫助,在毫無社會背景及經濟基礎的現實下,只能用自己的處女之身作為交換,并與賴哥維持著長期的性關系。
向度二:對于“中產階層女性”生存狀態、精神困惑及出路的自覺探尋。此類文本通常站在旁觀者的視角,將“中產階層女性”作為敘事的對象,雖然仍強調對欲望的表達與現時的體驗,但更多地關注“精神”領域,有著對于“精神出路”這一主體精神的建構嘗試,以賈平凹的《暫坐》為典型代表。《暫坐》中以海若為核心的眾姐妹們,生活在西京城中,似乎都擁有了獨立女性追求的金錢、婚姻及事業的自由,過上了所謂中產階層的優越生活,但是小說中處處都在揭露這表面自由背后的生存邏輯:一個受制于男權管理的社會法則。海若的茶莊生意需要依靠市長秘書的關系幫襯,嚴念初為了經營好醫療器械生意與口腔醫院的王院長之間有著曖昧的灰色關系,向其語經營的能量艙館也要通過不斷地討好“領導們”來維持客源等。再如唐穎的《初夜》中的編劇葉心蝶,在功成名就之后,卻無法從現有的一切中獲得精神的自足,于是,她一遍遍地找尋記憶中的戀愛樂園,在與初戀、好友及外國友人等的肉體碰撞中,仍未能找到想要的答案,但卻需要承擔在男性視角下女性要守婚姻底線、貞潔等道德譴責的風險。
縱觀作家們對于消費時代中都市女性形象的兩大向度的不同敘事,在一定程度上,確然能映射出當下女性生存的特殊癥候:處于弱勢中的女性,憑借自身的條件在獲得了物欲帶來的愉悅與自我欣賞的同時,也承受著將自己“物化”為商品而帶來的精神上的迷茫感;而在社會中有一定經濟話語權的中產階層女性,也仍要與由男性建構起來的強大消費邏輯保持某種平衡或某種解脫。而無論哪種向度的敘事,身體、欲望及性都是支撐其文本背后的歷史語境。正如汪民安所說:“今天的歷史,是身體處在消費主義中的歷史,是身體被納入消費計劃和消費目的中的歷史,是權利讓身體成為消費對象的歷史,是身體受到贊美、欣賞和把玩的歷史。身體從它的生產主義牢籠中解放出來,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陷入消費主義的陷阱。”[6]雖然此類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都市女性的精神癥候,對都市文學的發展及成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文學本身處在消費市場的現實處境,又使得文學文本本身具有潛在的商品屬性,尤其在市場巨大的經濟誘惑之下,作家們迎合消費文學市場的傾向也比較明顯,也使得文本存在著諸多問題。如過于巧合的情節設計及性場面、性心理的不節制描述,降低了文學本身的審美性與批判精神。同時,普遍存在過度釋放都市女性的小資情調,迷戀于營造一種無邏輯的“感傷”情緒,這種“感傷”情緒的過度敘事,也使得寫作價值立場比較迷茫。
二、想象、出走與留守:鄉村底層女性的困境
在魯迅的筆下,鄉村是承載國民愚昧性的“鐵皮屋子”,而在沈從文的筆下,鄉村是寄托原始、美好詩意想象的挽歌。以魯迅、沈從文為核心,形成了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兩大類型女性形象:一是愚昧落后封建的,如祥林嫂;二是詩意美好的,如翠翠。新中國成立初期,伴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女性擁有了與男性同樣的集體勞動的機會,但是在1985年改革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之后,女性又被迫從鄉村這一大的集體退場,重新回到了穩定傳統的家庭制(男權制)小單位,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政策,但由于傳統觀念、養育子女及男權壓制等原因,鄉村女性并未獲得平等的生存狀態。新世紀以來,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浪潮下,鄉村必然也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變化,且呈現出與城市諸多不同的質素。從總體而言,雖然“三農”問題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國家也出臺了“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政策,但是除了毗鄰城市或城中村這樣的鄉村得到了經濟發展紅利外,大部分偏遠村落仍然處于城市化帶來的負面效應中。可以說,市場經濟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偏遠鄉村長期穩定封閉的結構,催生出一批批進城打工者,即社會的底層群體。“鄉村女性”在這一城市化浪潮中,其生存命運也發生了復雜的變化:選擇(或被迫)進城打工的鄉村女性要面對流入城市底層的種種挑戰;獨守鄉村的女性則要應對男性出走后的更為復雜的生活狀態。作家們自然很早就察覺到了這一新興的底層群體的存在,并用文學的方式加以呈現,縱觀此類小說文本敘事,呈現出三個向度的特征。
向度一:對于具有傳統美德的“完美”女性形象的敘事。市場經濟的發展造成鄉村長期以來形成的穩定文化結構的解體,鄉村女性也一定程度脫離了家族長者及丈夫的權威束縛,鄉村總體呈現出秩序失范的混雜狀態。面對如此鄉村現狀,一些男性作家便在文本中塑造出一個與現實相反、更符合傳統文化并接近完美型人格的女性形象。如賈平凹《秦腔》中的白雪,年輕貌美的她在清風街是數一數二的存在,與其他言語粗俗、不知廉恥的鄉村女性相反,白雪天性善良單純,幾乎不拒絕別人的任何求助。可以說,她代表了傳統文化的一切美好品質。更重要的是,白雪熱愛秦腔藝術,并持之以恒地堅守付出。但是這樣“完美”的白雪,卻落得愛情與事業的雙重失意,她的命運就像終將失去傳播空間的秦腔一樣,成為一曲挽歌。為何如此“完美”的女性白雪只能走向如此慘淡的命運呢?可以從賈平凹創作《秦腔》的意圖來尋求答案。王彪就曾指出,《秦腔》的寫作“是一次尋根的過程……當代農村在急速走向荒涼,隨著父輩的消逝,我們與故土的關聯會越來越少。這是你心頭的隱痛,尋根的過程其實也是失去根的哀嘆,就像一曲絕唱”[7]。從這一角度分析,作為文化守成主義者的賈平凹塑造的“白雪”這一女性形象,顯然代表著在城市化沖擊下日漸衰落的傳統文明,白雪的人生悲劇就是傳統文明的悲劇。莫言的《蛙》則批判的是在市場化進程中“重男輕女”思想給女性所帶來的生命悲劇。鄉村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使得許多家庭冒著生命危險與違抗政策的風險生二胎,“陳眉”就是在計劃生育的高壓政策下僥幸出生的,但其僅是作為“女孩”的這一身份,就受到了父親陳鼻的冷眼對待,遭遇毀容后的她為了償還父債,又成為代孕的工具,本身善良美好的陳眉,在強大的父權制家庭結構與市場化社會的雙重壓迫下,身心備受摧殘,成為時代悲劇的一個縮影。再如劉慶邦的《葦子園》中純情天真的少女小青,僅由于父親固守女兒不能嫁給眼皮子底下的人的習俗,就強行拆散了小青與愛慕者之間的情緣,在嫁給一個外鄉男性之后,由于一直生的都是女孩,婆家人強迫其必須生出兒子來,小青也淪落為生育孩子的機器。綜上所述,此類文本通過對“完美”女性形象的敘事,暴露出背后潛藏的邏輯:一方面,是一種文化守成心理,是對消費社會文化的冷峻思考及抵觸;另一方面,消費文化帶來的秩序失范催生出男性對于傳統“柔順服帖”的女性形象的想象。“‘柔順服帖的女性身體形象,不僅表達了男權制對女性身體的欲望和想象,而且直接成為對女性身體的行為規范。在這種想象和規范背后,是男性對女性身體徹底占有和控制的權力關系。”[8]
向度二:書寫鄉村出走女性的生存困境。此類文本多視角敘述鄉村底層女性或主動尋求或在迫于壓力的情況下進入城市后的不同遭遇或艱難的生活狀態。賈平凹的《極花》與嚴歌苓的《誰家有女初長成》都關注“拐賣鄉村婦女”這一社會熱點事件。《極花》中的鄉村女孩蝴蝶跟隨母親進城尋求生活,卻在一次意外中被拐賣到陜北一個叫圪梁村的窮地方,經歷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蹂躪,幾年后終于獲得了解救的機會回到了母親身邊,但城市并未給予蝴蝶可以重新生活的空間,最終因為思念還留在圪梁村的孩子她又重回到了被拐賣的地方。《誰家有女初長成》中生長在偏遠村落黃桷坪的女孩潘巧巧,懷著對大城市深圳的憧憬,跟隨一個叫曾娘的人踏上了她的進城之路,但還未來得及看到燈紅酒綠的城市,就被騙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站,成為兩名工人兄弟花錢買來的媳婦,在身體飽受蹂躪,自尊被現實完全撕碎之后,她舉起了菜刀……為何鄉村女性走入城市的代價要如此之大?為何鄉村女性總容易成為金錢交易下的犧牲品?兩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進行了深入思考,并試圖找出問題的源頭或解決的方案。賈平凹將問題落腳到城市化發展中的城鄉問題上,如其在《極花·后記》中所說,“我關注的是城市在怎樣地肥大了而農村在怎樣地凋敝著……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還活著的一群人是懦弱還是強狠,是可憐還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樣常年駐雪的冰冷,還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9]而嚴歌苓似乎將問題的解決方法落到“教育”上,小說中的潘巧巧在知道自己這一生已經沒有退路的情況下,說出了這番話:“我要再活一回的話,就曉得要讀書了。讀書,考大學,然后到哪個單位去工作。”[10]還有許多小說文本呈現了鄉村女性在進入城市后,想要生活得更好就只能依靠出賣肉體來謀生的現實困境。如吳玄的《發廊》中從鄉村走入城市開發廊的女孩們,暗里卻與不同男性進行著肉體交易;劉慶邦的《天涼好個秋》中有著色情服務經歷的鄉村女性看云,回到家鄉后受到了鄉親們的集體道德譴責和非議等。
向度三:書寫鄉村留守女性的生存困境。市場化的浪潮打破了鄉村傳統的男性與女性的角色分工,許多家庭男性集體出走,形成了“候鳥式”的打工潮,而留守在鄉村的女性,其生存命運又會有何困境?孫惠芬的《歇馬山莊》《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歇馬山莊的兩個男人》是這一向度敘事的典型代表。如《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剛結婚就留守空房的女孩潘桃、李平,由于寂寞無聊走在一起成為好朋友,這一再平常不過的行為卻遭受了來自各自家庭長者的非議和阻撓,認為她們沒有遵守“媳婦”該有的本分,而當兩個女孩沉浸于友情帶來的虛幻想象中時,男人打工歸來的現實又讓她們陷入說不清、道不明的困惑中:一方面是對于丈夫的陌生感;另一方面是友情割裂后,對于回歸鄉村傳統女性角色的無所適從。除此之外,這些留守女性們在照顧家庭、孩子的同時,還要承擔起本屬于男性的耕作勞動,甚至會遭受村里男人的性騷擾等。
綜上所論,這些對于不同鄉村女性形象的文本敘事,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被消費社會豐富的物質與過剩的經濟遮蔽下的農村(主要是偏遠地區)日益凋敝的現實,同時也將“鄉村女性”面臨的困境推到了時代浪潮風口之上,這種寫作的“人民性”意識是值得被肯定的。但不可否認,在消費經濟市場下,作家們的集體中產化使得他們普遍缺乏底層“直接式”的體驗,有的作家更是通過新聞、報紙等媒體來間接“體驗”底層,這也就使得作家的底層創作是否真的能代表底層而成為一個問題。
三、歷史的隱退:“文革”女性形象敘事的日常世俗化
縱觀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文革”題材一度成為許多作家選擇的寫作向度之一。新時期初,傷痕、反思小說的宏大敘事,揭露了“文革”給人們帶來的殘害與傷痛,“災難性質、創傷記憶、歷史反省”[11]是這一時期“文革”敘事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消費文學的興起催生出一種以新歷史主義為其主要歷史觀的小說創作思潮,代表作品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及余華的《活著》等,消解了歷史宏大敘事的一貫傳統技巧。21世紀以來,消費市場的全民化、生活化,使得文學敘事不斷地走向了世俗化的傾向,這一傾向同樣適用于“文革”題材小說創作。縱觀此類文本,多呈現出“去歷史化”而突出日常生活碎片的寫作特征。而“女性”通常作為此類小說日常敘述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以女性在“文革”中的成長變化為線索,主要呈現出三個向度的敘事特征。
向度一:對于女性青春浪漫純情的放大書寫。從王朔“躲避崇高”論的論爭及《動物兇猛》等一系列的創作起,此類敘事方式就成為一股流行風潮。新世紀以來,擁有“文革”經驗的作家們無疑也順應了世俗化創作趨向的潮流,許多小說剔除掉“文革”特殊時期帶來的苦難及懺悔意識,以及“文革”帶來的傷痛反思,取而代之以女性青春浪漫純情的放大書寫,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敘事向度。莫林格爾說:“創作就如同做夢,并且像做夢一樣,它被看作是沖突的一種解決方式。”[12]作家們回憶重塑了青春的記憶,并美化了青春自由浪漫的一面,以應和當下的消費文學市場。王安憶的《桃之夭夭》娓娓敘述了上海市井之間一個叫郁曉秋的女子半生的經歷。作者用了大量細膩的筆調描述了郁曉秋少女時期充滿青春氣息的美麗,她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尋找一切資源打扮自己,感受著外貌變化帶來的欣喜與忐忑,憑借自身的才藝在弄堂之中成為被眾多同齡人欽慕的對象。嚴歌苓的《陸犯焉識》中傾其一生守望著丈夫陸焉識的馮婉喻。《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女子小菲對丈夫歐陽萸無條件的愛與守候。蔣韻的《隱秘盛開》中的鄉村姑娘潘紅霞在與萍水相逢的知青發生了關系后,用自己的一生無條件單戀著這個男人等。這些女性的浪漫純情與當下社會物欲膨脹、愛情稀缺的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定程度上對消費時代下的愛情模式產生了一種補充與彌合作用。
向度二:對于女性性欲望的放大書寫。從性欲望的角度入手,揭示“文革”對人的身體及精神帶來的畸形折磨,其實新時期起就有這樣的創作先例。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新世紀以來與“文革”有關的小說敘事,似乎強化了這一寫作路徑。此類文本,主人公的革命行動通常伴隨著不同的性欲望和性方式。葉兆言的《我們的心多么頑固》通篇敘述的是男主人公與不同女性之間的性愛史。畢飛宇的《平原》中還敘述了女性吳曼玲與狗交媾的情節等。但此類文本過于夸張、頻繁的性描寫在豐富了“文革”題材的敘事同時,迎合市場、滿足讀者獵艷獵奇的意圖也非常明顯,這無疑降低了文本的審美價值和精神深度。正如汪民安所發出的疑問:“到處都是性和身體,但到處都是空洞的身體……這是性的解放,還是以解放的手勢對性的掏空?”[13]
向度三:對于日常生活中女性小資情調的敘事。此類文本,“文革”僅作為敘事的背景,尋常日子中的瑣碎感受、片段體驗才是作家重點敘事的向度。而“小資情調”似已成為消費社會普遍追求的潮流,“在這個仿真的世界中,藝術與大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庸常的日常生活事物戴上了藝術和審美的面具,生活即審美,審美亦是生活。”[14]此類文本在敘事時,有意遮蔽了特殊時代物資匱乏、精神貧瘠等客觀因素,放大了女性對于精致優雅及生活細節的追逐享受等。如魏微的《一個人的微湖閘》中通過“我”的童年記憶,講述了“我”與爺爺奶奶在微湖閘一起生活的片段,過往的美好像流水一般自然流淌,“文革”的痕跡幾近消失。黃蓓佳的《沒有名字的身體》用特別細膩、平實、清麗、溫婉的語言,講述了一場跨越30年的師生戀情的故事。唐穎的《初夜》用細膩的筆觸敘述了同學俞海嵩母親優雅精致的上海女人派頭等。誠然,此類文本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時期傷痕、尋根小說忽略日常普通化敘事的缺憾,但是為了迎合消費文學市場與消費時代的審美趨勢,而過度美化“文革”記憶的寫作方式,在喪失了“文革”寫作的嚴肅性與反思性的同時,也難以找到一個清晰的價值立場。
四、結 語
在消費社會文化強大的歷史語境下,無論是都市女性的修羅場、鄉村底層女性的困境,還是“文革”女性形象敘事的日常世俗化,無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吸收了大眾文化的文學觀念與審美趣味,“文學的世俗化精神和日常化敘事,在歷史之手的撥弄下不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極有可能在文化轉型的消費時代躍升為文學實踐的一種主體精神和寫作范式,影響乃至支配著文學在全球化消費時代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15]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文學適應新的文學浪潮的積極嘗試,通過選擇創作大眾讀者接受的閱讀方式,建立起文學的讀者群,部分作家的文本創作更是有著很高的審美價值水準。或許,文學與商業的互動是文學在當下社會生存、發展的明智之舉,但“關鍵在于,文學不能放棄自己的審美自主權和崇高的人文主義理想,不能割讓和收縮自己的領地和邊界。”[16]凡是如此,文學才能在消費語境之中,擁有創造經典敘事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邵燕君.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小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2.
[2][3][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20,63.
[4][8][15][16]向榮.消費社會與當代小說的文化變奏:1990后的中國小說批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110,137,112,65.
[5]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96.
[6][13]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21,40.
[7]賈平凹,王彪.一次尋根,一曲挽歌[N].南方都市報,2005-1-17.
[9]賈平凹.極花·后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207.
[10]嚴歌苓.誰家有女初長成[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2.
[11][14]雷鳴.論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革”敘述的話語形態[J].南京師大學報,2016(03):153—160.
[12]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39.
作者單位:武警工程大學烏魯木齊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