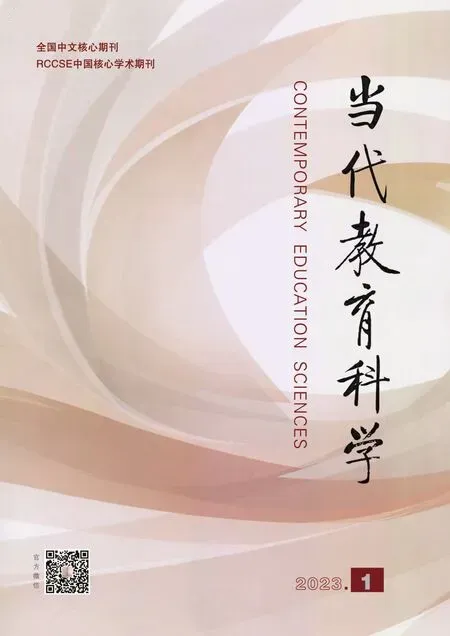重識“教育普及化”
——走出教育規(guī)模普及化的認識誤區(qū)
● 段會冬
改革開放以來,“教育普及化”(以下簡稱普及化)不僅作為我國教育發(fā)展中的重要任務,也成為社會各界關(guān)注的焦點話題。198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提出“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發(fā)展導向,明確了在初等教育階段推進普及化的工作要求;1985 年,《中共中央關(guān)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了“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政策要求,將普及化工作從初等教育延長到整個九年義務教育階段;2010 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出“基本普及學前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戰(zhàn)略目標,將普及化工作延伸到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可以說,在不到半個世紀的發(fā)展歷史中,普及化已經(jīng)成為多個學段政策制定的核心話題。
隨著關(guān)于普及化的教育政策在多個學段的推進,各個學段的普及化目標也被陸續(xù)宣布實現(xiàn):2011 年,我國向世界莊嚴宣布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化工作在義務教育階段率先實現(xiàn);2019 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許多媒體相繼報道了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1]。2022 年,教育部明確確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jīng)進入“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2];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布的《2021 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可知,學前教育毛入學率達88.1%,基本實現(xiàn)了普及學前教育的戰(zhàn)略目標,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91.4%,實現(xiàn)了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戰(zhàn)略目標[3]。
按照媒體報道和相關(guān)部門的表態(tài),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我國教育發(fā)展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普及化的戰(zhàn)略目標。然而,我們依據(jù)什么判定普及化目標已經(jīng)實現(xiàn)?為什么在論及普及化時,我們總是關(guān)注毛入學率?為什么一些學者在對許多國家教育發(fā)展的分析中習慣于從規(guī)模的角度理解普及化?[4]普及化只是意味著毛入學率所代表的發(fā)展規(guī)模達到了對應的指標,還是有著其他的發(fā)展訴求?如果確實存在其他的訴求,那么這些訴求又指向什么?普及化是否真的與質(zhì)量無關(guān)?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教育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作為國家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普及化之后教育發(fā)展的價值追求,還是本就是普及化的應有之義?
回到普及化的概念,仔細審視這個被多次提及但又缺乏解釋的概念,是當前我國教育發(fā)展無法回避的關(guān)鍵問題。要完成這一工作,必須重新梳理“普及教育思想”的來龍去脈,在歷史線索中重識普及化的含義。
一、模糊的普及化:普及教育思想的提出
有學者認為,普及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夸美紐斯。[5]實際上,近代普及教育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的教育理念。莫爾在書中提到烏托邦“所有兒童都被引導讀有益的書”,而且“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總是把體力勞動后的剩余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6]在那個資產(chǎn)階級瘋狂壓榨勞動人民以實現(xiàn)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階段,勞動人民連健康都難以得到保障,受教育權(quán)更加無從談起。莫爾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思想喊出了民眾希望獲得教育權(quán)的心聲。這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作為普及教育思想重要的倡導者,莫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尤其是他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思考對于我們理解“什么是普及化”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在莫爾的普及教育思想中已經(jīng)開始含有規(guī)模的思維。盡管在莫爾的筆下兼有“所有”“大部分”等表述,這意味著莫爾并沒有確定普及是否意味著全體,但他至少認為只有少數(shù)人有受教育權(quán)的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普及教育。模糊的規(guī)模思維已經(jīng)在莫爾的思想中萌生。另一方面,莫爾并沒有停留在規(guī)模上思考普及教育,而是用烏托邦人的口吻表達了自己心中關(guān)于普及教育內(nèi)容的思考。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學科甚至勞動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都被作為普及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被提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爾筆下的烏托邦人學習了許多學科,但唯獨沒有強調(diào)神學。對于科學教育的重視與對于神學的弱化充分體現(xiàn)了莫爾與經(jīng)院主義教育針鋒相對的立場,這在教育史上不僅略早于拉伯雷,更早于培根一個世紀。[7]
莫爾的普及教育思想雖然帶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但相比于前輩學者們更多關(guān)注社會統(tǒng)治階層的訓練上,他的確與他們有著明顯的不同。[8]有學者甚至認為普及教育思想是莫爾超越人文主義教育學家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9]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他關(guān)于普及教育規(guī)模和內(nèi)容的認識仍然略顯模糊,但他不從單一規(guī)模層面理解普及教育的思想開啟了普及化概念的多維思考。
如果說莫爾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思想還帶有鮮明的空想主義色彩,稍晚于莫爾的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則回答了落實普及教育無法回避的兩個關(guān)鍵性的問題:一是普及教育何以必要;二是普及教育如何實現(xiàn)。
路德認為普及教育之所以必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普及教育是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的需要。他認為:“德國政府是以羅馬帝國法為基礎的,這給我們國家?guī)砹酥腔酆屠碇恰<偃缥覀儾荒軋猿诌@些法的話,那么我們的國家將無法維持。那么誰來堅持呢?暴力統(tǒng)治和權(quán)勢都做不到,必須用知識和書來達到這個目的。為此,人們必須學習,并懂得我們帝國的法律和智慧。”[10]路德甚至認為,不送孩子去上學是一件“像個魔鬼”的事情,因為“你每天享受國家的好處,但作為回答卻搶劫了你的孩子,讓他去貪婪,使你不能全力維護政府、法律與和平。雖然通過世俗的權(quán)力保障了你的人身、生活、財產(chǎn)和榮譽,但是你破壞了社會秩序”[11]。由此可知,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帶有鮮明的國家和法治的視角,而非從個人發(fā)展的層面思考普及教育,而是更強調(diào)國家和法治的視角。再者,普及教育是宗教改革的需要。路德認為,盡管上帝給了每個人以機會,但魔鬼對塵世的侵擾,往往使得民眾極易陷入敗壞、不軌的狀況。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的教會非但沒有幫助民眾承接上帝的福音,反而在迫使每一個公民不得不承受購買贖罪券等各種形式的敲詐和掠奪。因此,改革教會、促使上帝的福音傳到全世界就成為宗教改革的當務之急。將上帝的福音傳到全世界必須人人皆能讀《圣經(jīng)》,然而,民眾受教育狀況不佳,加之一些教父對于《圣經(jīng)》語言的解讀冗長難解,因此,“要想學習《圣經(jīng)》就應該致力于語言”[12]。這種借助語言實現(xiàn)上帝的福音傳到全世界的期望,成為路德心中普及教育的重要理由。畢竟要做到人人皆能讀《圣經(jīng)》,就需要普及教育,以確保民眾都能夠理解《圣經(jīng)》的語言。因此,無論從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的角度,還是從宗教改革的角度,路德都認為普及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路德普及教育思想的另一個方面指向如何實現(xiàn)教育的普及。他從經(jīng)費來源和受教育義務兩個角度論述了關(guān)于如何普及教育的設想。在《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中,路德指出:“每個城市每年都會支出大量經(jīng)費修建道路、加固城墻、購買武器、裝備戰(zhàn)士。為什么我們不能支出同等經(jīng)費去維持一兩所學校呢?一個城市的繁榮,不僅僅取決于它的自然財富、城墻的堅固、建筑物的優(yōu)美以及軍隊武器的充足。城市的安定和強大更重要的是取決于良好的教育。”[13]路德強調(diào)了市政當局在普及教育中的責任,明確了普及教育需要充分依托市政當局的財力支持,而不能寄希望于普通民眾的投入。與此同時,路德還認為應當勸導父母們明確讓孩子接受教育的義務,因為這不僅是父母的道德責任,也是公民的義務。[14]經(jīng)費保障輔之以義務教育觀念的確立,為教育普及工作的有效推進提供了頗具可行性的思路。
路德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兩個關(guān)鍵性問題的思考和論述推動了普及教育思想的發(fā)展。然而,筆者認為,長久以來,對于路德普及教育思想的理解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潛在的意義,即對于“什么是普及化”的回答。盡管路德并沒有正面回應究竟“普及化是什么”,但他的思考延續(xù)了莫爾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兩個維度。一是普及離不開對規(guī)模的要求。如果宗教改革不是針對某一個社會階層而是指向社會的各個階層,如果讀《圣經(jīng)》是宗教改革中每個信徒獲得救贖的方式,我們就有理由相信,路德心中的普及應當是指向每個人的。路德始終強調(diào),上帝對于每一個人是平等的。所謂的貴族,并不是天生的,是“憑筆達到貴族地位的”[15]。即便路德所想的普及不是“必須”涉及全體,至少也是“可以”涉及全體。這種并未言明的對“普及”的理解并不應該因其潛在性而被人忽視。二是普及教育不能回避對內(nèi)容的思考。如前所述,作為宗教改革家,路德非常強調(diào)民眾對于《圣經(jīng)》的閱讀,而這勢必牽涉語言的學習。這意味著路德心中的普及教育不僅是量的問題,還包括了對于內(nèi)容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盡管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擺脫模糊的印象,但已然勾勒了包括但不限于規(guī)模思維的普及化概念雛形。
作為宗教改革家,盡管路德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他也同時開啟了普及教育的世俗轉(zhuǎn)向。畢竟路德對于普及教育必要性和舉措的思考,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國家和社會的視角。因此,我們不能將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看成是宗教思想的附庸,而應當承認這一轉(zhuǎn)向更加符合教育的近代轉(zhuǎn)型需求。當然,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仍然有許多問題未能充分論述。例如,路德雖然意識到語言在宗教改革和普及教育中的重要性,但他仍然將目光聚焦于拉丁語,而并沒有充分意識到民眾掌握的語言才是普及教育的基礎,因此,他的思想并沒有促使初等學校從拉丁語學校中分離出來。[16]真正完成這一任務的學者是夸美紐斯。夸美紐斯對于普及教育的論述使得普及教育思想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
二、制度化的設想:夸美紐斯普及教育思想的提出
在普及教育思想的發(fā)展史上,夸美紐斯做出了兩個方面的重要貢獻。首先,夸美紐斯將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從國家和宗教的視角延伸向了人的視角。夸美紐斯認為:“只有受過恰當教育之后,人才能成為一個人。”[17]他不相信“一個沒有學會按照一個人的樣子去行動,即沒有在組成一個人的因素上受到訓練的人,真正能成為一個人”[18],因此,“一切生而為人的人,生來都有一個同樣的目的,就是他們要成為人,即要成為理性的動物”[19]。夸美紐斯關(guān)于教育之于人意義的論斷不僅作為他思想的標簽被廣泛提及,也是普及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題。這個論斷也成為夸美紐斯給出的、簡明扼要的普及教育必要性的理由。
與路德非常強調(diào)從國家、法治等角度理解普及教育不同,在夸美紐斯的論述中,我們隨處可見的是從人的視角出發(fā)理解普及教育之必要。當然,作為路德思想重要的繼承者,夸美紐斯的思想并沒有脫離與宗教的聯(lián)系。之所以強調(diào)教育之于人的意義,歸根結(jié)底,還是因為他認為教育是幫助人理解上帝的重要方式。然而,我們不能據(jù)此就將夸美紐斯的普及教育思想視為一種宗教思想。必須承認,在夸美紐斯思想中的確存在著世俗與宗教的雙重性。但擺脫了原罪論束縛的夸美紐斯深受康帕內(nèi)拉等人文主義思想家的影響,對于人和現(xiàn)世生活的重視已經(jīng)成為其思想的重要支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夸美紐斯的普及教育思想已經(jīng)超越了單純的宗教目的,向著世俗世界邁出了堅實一步。
夸美紐斯并不是唯一的從人的視角理解教育普及必要性的學者。與他同時代的笛卡爾曾提出了理性均等思想。笛卡爾認為,理性是“使我們成為人、使我們異于禽獸的東西”,因此,理性“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不折不扣的”。[20]簡言之,理性是“人間分配得最均勻的東西”[21]。然而,推崇理性的笛卡爾并未迷信地認為單單擁有理性賦予的聰明才智就能夠必然帶來人的發(fā)展,而是強調(diào)必須“正確運用才智”[22],這恰恰為每個人接受教育預留了充分的空間。
可以說,在那個“重新發(fā)現(xiàn)人”的時代,夸美紐斯與笛卡爾一樣都從各自的角度論述了如何將人的視角融入普及教育思想,呼應了那個時代的理論訴求。相比于笛卡爾更強調(diào)運用自由探究和反思推理探索世界,夸美紐斯則將感覺主義推至前臺,強調(diào)了它對于人的發(fā)展的意義,而這顯然對于后世思想的發(fā)展意義深遠。無論是洛克關(guān)于“平常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教育造成的……”[23]的觀點,還是愛爾維修提出的“得到多少感覺,他們就受到多少教育”[24]的主張,無疑都表現(xiàn)出鮮明的夸美紐斯感覺主義思想的延續(xù)性。而洛克的白板說和愛爾維修的教育萬能論被視為西方近代初等教育普及重要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夸美紐斯不僅自己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思想,而且與同時代的學者共同啟迪了后世學者關(guān)于普及教育的思考。這在普及教育思想史的發(fā)展中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
其次,夸美紐斯對于普及教育的整體思路進行了較為完整的制度設計。作為“第一個對初等教育做了明確定義的人”[25],夸美紐斯的普及教育思想并沒有停留在“為什么要普及”上,還回答了他心中理想的泛智教育與學校理想該“如何實現(xiàn)”。之所以如此關(guān)注“如何實現(xiàn)”的問題,是因為他深知好的思想并不必然轉(zhuǎn)換為實踐。他曾對路德普及教育的思想給予了肯定,但他同時提出:既然路德已經(jīng)提出了很好的設想,為什么依然“在較小的村莊和村落中,并沒有設立學校”?為什么“設立了學校的地方,學校也不是為整個社會設立的,而只是為富人設立的”?為什么“教導青年的方法通常都是非常嚴酷的,以致學校變成了兒童恐怖的場所,變成了他們的才智的屠宰場”?[26]這些問題的提出反映了夸美紐斯對于理想與現(xiàn)實關(guān)系的深刻思考,也促使他不得不回答“如何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問題。
夸美紐斯對于普及教育“如何實現(xiàn)”問題的回答是系統(tǒng)的。他不僅設計了由母育學校、國語學校、拉丁語學校和大學在內(nèi)的完整的教育系統(tǒng),而且非常關(guān)注學校內(nèi)部的制度設計。他曾經(jīng)說:“學校的長處全在于制度……制度才是一切的靈魂。通過它,一切產(chǎn)生、生長和發(fā)展,并達到完善的程度……”[27]沿著這一認識,他不僅探討了眾所周知的、也給他帶來長久學術(shù)聲譽的學年制、班級授課制等諸多重要問題,也系統(tǒng)論述了泛智學校關(guān)于“教什么和學什么”“人員”“教材”“地點”“時間”“課程”“課間休息和假期”七大方面制度的總體設想,這為近代公共教育體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盡管夸美紐斯自始至終并未直接給出他心中關(guān)于普及化的界定,但他的系統(tǒng)論述為理解普及化的含義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例如,他提出“把一切事物交給一切人”[28],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課程體系,還強調(diào)“各個年級應規(guī)定適合于中等智力的全年級教學內(nèi)容”[29],這意味著普及化無法回避內(nèi)容維度;他提出“各年級應在同一時間……開始和結(jié)束學年課程”[30]“每節(jié)課緊張的腦力勞動以后,要有半小時的休息……”[31],可見普及化還要顧及時間維度;他提出“有多少年級,就有多少教學用房”,且“每一個教學房間必須進一步劃分”[32],這表明普及化還必須考慮空間維度。總之,普及化不單要解決“有學上”的問題,還要解決“學什么”“怎么學”等系列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普及教育發(fā)展史上,夸美紐斯的思考推動了普及化內(nèi)涵的豐富化。
夸美紐斯對于普及教育的整體思考并未擺脫宗教因素的影響,然而,作為“最早建議突破狹隘小圈子而為更多學生提供教育的教育家之一”[33],夸美紐斯的確在普及教育思想發(fā)展中作出了不容否認的重要貢獻。他一再強調(diào)在他所希望建立的“泛智學校”中,“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教育”[34]。這是他普及教育理想的最簡明表達。
三、普及化的理論化:教育發(fā)展階段論的形成
盡管路德和夸美紐斯的思想給出了普及教育的必要性,但他們始終未正面回應該“何謂普及化”的問題。從宗教改革或者“一切生而為人的人”的角度出發(fā),普及化似乎是指向全體。然而,普及化究竟是“一個都不能少”,還是“涉及大多數(shù)人也可以”?可以說,初等教育的普及并未引發(fā)學界對于普及化含義的深入探討。社會意義、宗教意義以及教育意義的闡釋始終無法給出一個更具操作性的關(guān)于普及化的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世界高等教育邁向普及化的進程以及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學家馬丁·特羅(Martin Trow)的研究才使得“何謂普及化”的問題得到了正面的回應。
二戰(zhàn)后,歐洲高等教育獲得了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相繼進入了恢復發(fā)展階段。恢復與發(fā)展帶來了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張,例如,1947 年,瑞典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shù)僅為1.4 萬人,到1960 年這一數(shù)字已經(jīng)翻了一番,達到3.5 萬人。而1965 年,這一規(guī)模再次翻番,達到7 萬人。[35]法國、丹麥、英國等歐洲國家高等教育在20 世紀60 年代都經(jīng)歷了相似的規(guī)模擴張。1973 年,馬丁·特羅發(fā)表了《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轉(zhuǎn)換中的諸問題》(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一文,在系統(tǒng)梳理和回顧了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發(fā)展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被廣泛引用的高等教育發(fā)展階段論,即高等教育發(fā)展大致可以劃分為精英化、大眾化、普及化三個階段。自此,普及化成為描述教育發(fā)展階段論的重要概念。
總體來看,馬丁·特羅對于普及教育的研究圍繞階段論展開,在其中強調(diào)了規(guī)模思維、整體思維、系統(tǒng)思維以及時代思維四個理解普及化的重要維度。首先,馬丁·特羅的研究使得普及化有了明確的規(guī)模概念。按照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階段論,毛入學率達15%和50%是劃分三個階段的重要臨界點。這為我們研判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階段提供了非常重要又極具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也直接啟發(fā)了其他學者對高中教育發(fā)展階段的思考。例如,在馬丁·特羅的文章發(fā)表幾年后,日本學者藤田英典便借用了馬丁·特羅的規(guī)模思維,分析了日本高中教育發(fā)展的三個階段,這可以說是高中教育研究歷史上較早嘗試對高中教育發(fā)展階段進行劃分的嘗試。[36]我國推動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時采用了毛入學率達90%的規(guī)模指標,這從根本上看依然是將普及化視為一種規(guī)模概念的基本認識。
同時,馬丁·特羅又提醒我們不要從單純的規(guī)模思維理解教育的普及化。馬丁·特羅認為,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發(fā)展的諸多問題都源自增長(growth),因為規(guī)模的擴張勢必改變學生的同質(zhì)性。過去,建立在同質(zhì)化基礎上的精英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對學生基礎、需求、興趣等多個方面的差異而采取與之相適應的應對措施,所以增長還會帶來了包括財政投入、學校管理、學生選拔、課程設置與教學形式、團隊成長、學術(shù)標準的維持、考試等高等教育的各個方面改變,甚至還會對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37]在此基礎上,馬丁·特羅認為應當從教育觀、教育功能、課程和教學形式、學生經(jīng)歷、領(lǐng)導與決策、學術(shù)標準、入學與選拔、學術(shù)管理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高等教育發(fā)展的綜合狀況,以此來判定高等教育所處的發(fā)展階段。[38]
馬丁·特羅高等教育階段論的整體思維既是對規(guī)模思維反思,也是對規(guī)模思維的重要補充。它使得我們不得不將普及視為一個“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維度都需要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而且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維度未必會齊頭并進。規(guī)模的擴張可能會面對課程建設的滯后,課程建設的改進又可能會面對師資隊伍的滯后,師資隊伍的提高又可能會面對管理制度的滯后……總之,走向普及化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qū)崿F(xiàn)的。即便我們現(xiàn)在達到了毛入學率的要求,也未必意味著我們完成了“化”的過程。
此外,馬丁·特羅的教育發(fā)展階段論還強調(diào)了教育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思維。系統(tǒng)思維關(guān)注從橫縱關(guān)系的角度理解普及化階段的到來。從橫向關(guān)系來看,普及化必須正視普職關(guān)系的存在。很顯然,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張,不得不對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所需的經(jīng)濟、技術(shù)等精英人才的需求作出回應。[39]這種回應不僅意味著精英人才的外延從學術(shù)性人才不斷擴展到技術(shù)性高端人才等行列,而且意味著發(fā)達國家普及高等教育的歷程不可能單純由學術(shù)性高校完成,應用型大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少學術(shù)性高校在規(guī)模擴張的過程中不得不適當調(diào)整自己的辦學定位與培養(yǎng)體系,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表明過分強調(diào)普職二分與普及化的總體導向并不一致。從縱向關(guān)系上看,普及化還涉及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關(guān)系。例如,學校教育本應成為推動社會公平的重要力量。當入學問題在階層間等維度上差異較大時,民眾自然會首先將質(zhì)疑的目光聚焦于初等、中等教育。然而,當初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后,高等教育就會成為民主化所關(guān)注的核心領(lǐng)域。[40]換言之,民眾已然將整個教育視為一個系統(tǒng),在論及教育公平問題時,自然而然地選擇從系統(tǒng)的視角討論學校的作用。因此,在討論高等教育入學規(guī)模擴大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話題不僅涉及高等教育自身,還事關(guān)基礎教育的規(guī)模與公平問題。當我們思考高等教育發(fā)展階段的轉(zhuǎn)換可能對基礎教育產(chǎn)生影響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種影響反之也可能存在。
最后,馬丁·特羅并沒有固守于30 多年前提出的高等教育階段論的論述,而是不斷反思曾經(jīng)的理論是否適應30 多年后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實際情況。[41]他敏銳地意識到包括信息技術(shù)等新技術(shù)模糊了公益性與贏利性大學之間的界限、教學與研究之間的界限、學科之間的界限、大學和學院的界限[42]……可以說,新技術(shù)對大學的影響是全面且深刻的。由于網(wǎng)絡也可以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進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學生完全可以在更加個性化的時空借助網(wǎng)絡平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普及化的話題不得不面對新技術(shù)時代的到來,不得不重新思考實體的學校和虛擬的網(wǎng)絡空間之間的關(guān)系。這實際上是將普及化的話題從實體的學校機構(gòu)帶入了更為廣闊的虛擬空間。由此,普及化過程中的虛實關(guān)系也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成為普及化領(lǐng)域不容忽視的重要關(guān)系。
馬丁·特羅關(guān)于普及化的論述,對于我們理解普及化有兩個方面的重要貢獻。一是他發(fā)展了普及化的內(nèi)涵,使得今人可以較為清晰地理解普及化究竟所指為何,而不至于在朦朧模糊的狀態(tài)下猜測哪些話題屬于普及化而哪些話題已經(jīng)超越了普及化的邊界。二是他使得規(guī)模與其他維度之間的關(guān)系更加清晰。盡管路德、夸美紐斯等學者的普及教育思想都包含了規(guī)模之外還有其他的基本認識,但他們并未深入剖析規(guī)模與其他維度之間的關(guān)系。然而,馬丁·特羅的論述使得二者的關(guān)系更為清晰。規(guī)模不僅是最為直觀的觀測指標,也可以作為引發(fā)其他維度發(fā)生變化的重要誘因。正是甲學段規(guī)模的擴張導致原有的體系內(nèi)諸要素(例如課程、管理等)不得不作出調(diào)整,而乙、丙等學段作為臨近體系(如職業(yè)教育、高中教育等即作為高等教育的臨近體系)的發(fā)展也勢必因甲學段招生規(guī)模的擴大而受到連帶影響。因此,馬丁·特羅的分析使得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規(guī)模對于普及化的重要意義。
四、普及化釋義:一個指向教育形態(tài)整體變革的改革過程
從莫爾嘗試提出普及教育思想開始,教育普及化的話題已經(jīng)跨越了六個世紀。從路德、夸美紐斯最初關(guān)于普及教育必要性與舉措的思考,到夸美紐斯對于普及教育所指的拓展,再到馬丁·特羅明確提出規(guī)模思維、整體思維、系統(tǒng)思維以及時代思維四個理解普及化的重要維度,關(guān)于何謂普及化的問題已經(jīng)逐漸清晰。在普及化不斷被提及的當下,我們必須更加冷靜地意識到它既是一個認識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且認識問題可能直接影響實踐層面的改革思路和舉措。因此,今天重識普及化,必須立足于認識和實踐兩個層面,力求實現(xiàn)認識與實踐的有機統(tǒng)一。
從認識層面來看,普及化是一個兼有多維性、過程性和發(fā)展性的概念。
其一,普及化是一個多維概念。規(guī)模是普及化的應有之義但并非普及化的全部含義。普及必然涉及規(guī)模,如果仍然只是少數(shù)人享有受教育權(quán),而大多數(shù)人仍然無法接受教育,那么這種教育無論如何與“普及”無關(guān)。即便是不同學段達到普及化的規(guī)模臨界值有所不同,我們也毫不否認規(guī)模的確是理解普及化的重要指標。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盡管從普及教育思想提出之始便與規(guī)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單一的規(guī)模思維顯然距離真正的普及化尚遠。即便我們的規(guī)模達到了相應的數(shù)值,我們依然無法認定我們實現(xiàn)了普及化,必須充分考慮與之相關(guān)的課程、教學、管理、評價等多個維度的指標。簡言之,多維性意味著必須從教育發(fā)展的整體形態(tài)著手才能真正理解普及化的含義。
其二,普及化是一個“化”的過程。當宣布實現(xiàn)普及化時,我們似乎更加關(guān)注作為結(jié)果的普及化,但沒有過程的結(jié)果是虛空的。多維性告訴,我們普及化涉及多維指標,但不意味著這些維度是靜止不變的。如果說多維性展現(xiàn)了普及化的橫切面,那么,過程性則展現(xiàn)了普及化的縱切面,即突出強調(diào)以動態(tài)的視角理解多維度的改變。橫縱視角的結(jié)合,才能真正呈現(xiàn)更加完整、更加立體的普及化。必須強調(diào)的是,在這個“化”的過程中,沒有哪一個維度可以置身事外,且各維度的變化并不是單擺浮擱、各自為戰(zhàn)的。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滯后或脫節(jié)都會對全局造成影響。規(guī)模獨自改變,而其他維度并未跟進,教育發(fā)展也并未完成普及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普及化過程的復雜性與系統(tǒng)性。
其三,普及化是一個發(fā)展性的概念。回顧普及教育思想的發(fā)展歷史,不同時代的學者給出了各自的回答。我們與其簡單地將其視為關(guān)于普及化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倒不如從教育與社會關(guān)系層面更加深刻理解不同時代認識差異背后的社會因素。在宗教改革時代,普及教育被視為實現(xiàn)宗教改革目標的重要手段,因此,那時對于普及教育的理解自然離不開宗教的色彩。而與路德不同,生活于宗教改革末期的夸美紐斯更加關(guān)注普及教育的現(xiàn)實意義和實現(xiàn)路徑,因此,他的普及教育思想更為系統(tǒng),也更具世俗性。到了馬丁·特羅的時代,科技的進步、經(jīng)濟的發(fā)展已經(jīng)與宗教改革時期有了巨大的不同。社會的變革催生了更加復雜的教育體系,因此,在這個時代討論普及化必須充分考慮內(nèi)外部存在的諸多聯(lián)系,必須充分考慮新的技術(shù)手段對于教育發(fā)展的深遠影響。整體思維、系統(tǒng)思維、時代思維等維度的提出,正是對于時代發(fā)展的教育影響的理論化思考。按照這一思路,在未來的教育發(fā)展歷程中,尤其是信息技術(shù)等新手段不斷深度卷入教育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我們對于普及化的理解仍然存在巨大的發(fā)展空間。可以想象的是,隨著新技術(shù)手段的廣泛使用,未來的普及化將無法回避實體與虛擬的關(guān)系,我們可能會進入更加個性化的普及化狀態(tài)。總之,論及普及化,不僅要跳出規(guī)模普及化的舊有局限,還要擺脫已有認知對我們的束縛,用發(fā)展的眼光理解社會發(fā)展可能帶來的新的變化。
從實踐層面來看,普及化應當是一個教育綜合改革的過程。
概念的闡釋,不僅給予普及化一個更加立體、清晰的界定,對于普及化目標的實現(xiàn)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很顯然,普及化不會憑空實現(xiàn)。誠如夸美紐斯所憂慮的那樣,好的思想并不必然帶來與之相應的實踐。即便我們對于普及化的認知到位,也不必然實現(xiàn)普及化。因此,“如何做”與“知道是什么”同樣重要。
我們強調(diào)普及化應當是一個改革過程,但并不是有了過程就必然帶來理想的結(jié)果。不斷致力于擴大招生規(guī)模,增加辦學場地,充其量帶來規(guī)模的擴張,而對于師資的培養(yǎng)、課程的建設、評價的改革等顯然助力有限。沿著多維性和過程性認識的思路,除了“有學上”,普及化還應當充分回答“學什么”“怎么學”“誰來教”“學得怎么樣”等諸多問題。因此,任何一個學段的教育普及化必定涉及教育形態(tài)的整體而非局部,必定是一個教育綜合改革的過程。
在普及化的綜合改革中,我們必須明確質(zhì)量的核心地位不容動搖。馬丁·特羅等前輩學者對于課程、師資等諸多維度的闡述,不僅表明沒有質(zhì)量的規(guī)模擴張,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及化,而且強調(diào)了質(zhì)量的提升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沒有管理、評價等一系列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改革,沒有配套經(jīng)費、政策的支持,質(zhì)量的提升只能是空想。簡言之,普及化本就是一個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圍繞質(zhì)量核心,將課程改革、評價改革、管理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囊括其中并整體推進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普及化。倘若其中某些維度與其他維度不相匹配,例如評價跟不上規(guī)模,或者師資跟不上課程,那么普及化也勢必難以實現(xiàn)。“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式的改革,看似各個維度都進行了改革,但目標之間缺乏關(guān)聯(lián),舉措之間缺乏呼應,政策推進缺乏協(xié)調(diào),這種改革顯然無力破解困擾質(zhì)量提升的許多瓶頸性問題。于是,改革日復一日,問題依舊存在。巨大的資源投入始終難以真正推進普及化。既然是綜合改革的過程,問題的解決過程必須相互協(xié)調(diào)。
盡管馬丁·特羅告訴我們規(guī)模的擴張可能成為其他因素的誘因,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可能性并不必然發(fā)生。或者說,規(guī)模的擴張并不必然帶來其他維度的改變。我國高中教育發(fā)展的歷史表明,規(guī)模的擴張并未帶來階段的轉(zhuǎn)換。我們非但沒有真正實現(xiàn)普及化,連大眾化階段是否存在都尚存疑問。[43]因此,我們不能寄希望于擴大規(guī)模之后,其他相關(guān)維度的變革會自然發(fā)生。這也意味著將資源過多投放于規(guī)模領(lǐng)域,而對于課程、師資等支持力度不夠,可能“等不到”普及化的實現(xiàn)。更為重要的是,馬丁·特羅所闡述的規(guī)模與其他因素的關(guān)系,是對西方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歷史性回顧,并不意味著改革的步伐必然完全再現(xiàn)這段曾經(jīng)的歷史。換言之,推進普及化的改革并不必然規(guī)模擴張優(yōu)先,等到規(guī)模達到了新階段的臨界值再推動包括課程在內(nèi)的其他維度的改革。多個維度的改革究竟是齊頭并進,還是次第進行;究竟是規(guī)模當先,還是課程先導,所選擇的步驟與節(jié)奏完全需要根據(jù)不同學段教育發(fā)展的現(xiàn)實情況來決定。一味強調(diào)規(guī)模先行,無視改革的系統(tǒng)性,或者簡單照搬照抄他國經(jīng)驗,往往只會帶來問題的復雜化,而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因此,普及化也是一個本土化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基于自己的問題、立足自己的基礎而推進的一場整體性變革。
總之,盡管以馬丁·特羅為代表的前輩學者已經(jīng)給出了普及化的理論闡述,但對于普及化的認識并未終結(jié)。對于普及化認知的歷史已經(jīng)充分表明,單純重視規(guī)模不足以實現(xiàn)普及化。在推進普及化的過程中,我們只有跳出規(guī)模思維的局限,努力推進教育形態(tài)的整體變革和教育綜合改革,充分理解社會發(fā)展帶給普及化的新手段以及提出的新要求,才能真正實現(xiàn)普及化的戰(zhàn)略目標,推動教育實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