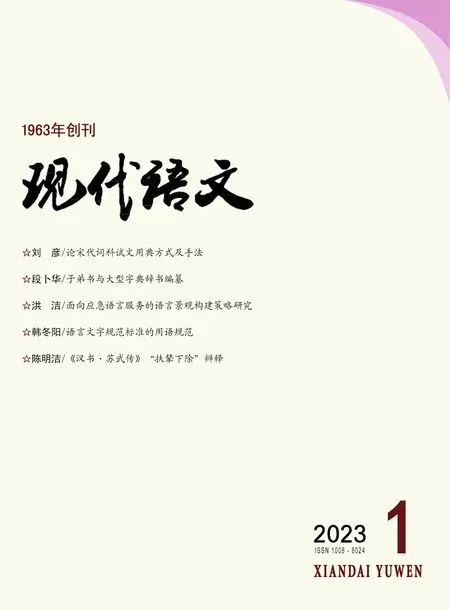“威脅”的名詞化及漢語詞典收詞釋義考察
劉智賢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中文分社,北京 100089)
一、引言
英語語言學界對名詞化(nominalization)的研究起步較早,其中,以韓禮德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派的研究最為深入,該學派分別從語義功能、語法功能、語法類別三個方面,對名詞化進行了系統分析。從語義功能來看,名詞化是指把某個過程或特征看作事物,動態過程轉化后實體屬性得到凸顯;從語法功能來看,名詞化主要能使謂詞從及物系統轉換到物質種類;從語法類別來看,名詞化通過詞性轉換的方式得以實現[1]、[2]。
國內語言學界也較早注意到“名物化”現象。朱德熙等學者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出發,將這一現象的研究觀點歸納為:主賓語位置上的動詞、形容詞已由行為范疇或性狀范疇轉入事物范疇;用作主賓語的動詞、形容詞具有一系列的名詞語法特點;主賓語位置上的動詞、形容詞失去了動詞、形容詞的全部或部分語法特點[3]。朱德熙等學者同時批判了以上的“名物化”觀點,認為主賓語位置上的謂詞不一定表示事物范疇,表示事物范疇也不一定由名詞完成,并且認為主張“名物化”的學者混淆了指稱與事物本身的性質差別[3]。不過,據其例證可見,他們反對的是將一切主賓語位置上的謂詞或謂詞短語一律視作名物化的絕對性觀點,并承認名物化中的所謂“事物”,在心理學上確有根據。
從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法位置對于名詞化來說并非決定性因素,名詞化是實現語法隱喻的有效手段,是創造概念隱喻的最常見方式。在由音系層(phonology)、詞匯語法層(lexicogrammar)、話語意義層(discourse semantics)組成的三層符號系統中,名詞化將含有動詞、形容詞的小句改變為名詞或名詞短語,用名詞體現過程本身,打破語言系統的一致式(congruent form)常規,使詞匯語法層所承載的表層意義和話語意義層所承載的深層意義變得不一致,從而增加單位小句的信息密度,體現內在的邏輯關系,適應特定的交際功能[2]。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古代漢語語料均來源于中國基本古籍庫V8.0;現代漢語語料均來源于北京大學CCL語料庫。
二、“威脅”的名詞化
名詞化現象在科技、新聞文體中大量存在,是漢語語法歐化的表現之一[4]。動詞或形容詞漂移為名詞后,能夠幫助其所處結構有效縮減句子或分句,同時包含大量信息,從而體現相關活動的客觀性和嚴肅性[1],并發揮促進語義連貫的語篇功能[5]。需要指出的是,漢語詞匯系統中的某些動詞正在經歷或已經完成向名詞的漂移。不過,由于漢語缺少狹義的形態變化,因此,對這些動詞是否已經成為兼類詞的考察,需要在語法功能的基礎上進行,即考察詞與詞之間的語法關系,判斷這種漂移是否已經相對穩定。如果一個動詞的語法搭配能夠同時符合以下特征:能直接受名詞修飾,能直接作“有”的賓語,能直接受前置動量詞修飾,那么,可以將該詞視作動名兼類詞[6]。此外,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在同一句法槽中具有并列關系,可由已知詞的類別推知其他詞的類別;若連續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其所處句法環境與句法結構相同,也可由已知詞的類別推知其他詞的類別[7]。
(一)“威脅”的名詞化特征
“威脅”是施事對受事施加的一種動作,可以用于表現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中的某種對立狀態,也可以用于表現客觀物質世界中某事物的變化對另一事物的存續造成危險的狀態。近些年來,在共時語言系統中,“威脅”的語法性質發生了變化,在表示動作的同時也能夠表示事物,具有了一系列名詞的特征和功能。
1.“威脅”直接受名詞修飾
(1)他們認為地區形勢雖有緩和,但外部威脅依然存在。
(2)反戰人士強烈呼吁英國政府立即停止對伊拉克進行的軍事威脅。
在例(1)和例(2)中,“外部”“軍事”為名詞,作定語修飾“威脅”。除此之外,“環境”“戰爭”“武力”等名詞也可以與“威脅”組成定中短語后,出現在主語、賓語的位置上。在CCL語料庫中,出現定中短語“軍事威脅”322次,“戰爭威脅”239次,“武力威脅”153次,“外部威脅”31次,“環境威脅”31次。
2.“威脅”直接作“有”的賓語
(3)科威特隊射門兩次,有一次較有威脅。
(4)不論是地球的追捕還是三體的追殺,我們都逃脫了。兩個世界對我們都不再有威脅。
在例(3)和例(4)中,“威脅”都作動詞“有”的賓語。在CCL語料庫中,“有”和“威脅”作動賓短語共出現643次。
3.“威脅”直接受前置動量詞修飾
(5)在偵查此案過程中,證人和辦案人員受到過多次威脅。
(6)這番威脅免不了又令泰勒冷汗涔涔。
動量詞表示動作次數或發生的時間總量。抽象名詞大多不能直接受一般名量詞的修飾,但能受前置動量詞,特別是“次”的修飾。因此,如果一個詞在能直接受名詞修飾、能直接作“有”的賓語的基礎上,還能直接受前置動量詞的修飾,那么就可將它視作動名兼類詞[6]。例(5)和例(6)中,“威脅”作為一種動作,可以受前置動量詞“次”“番”等的修飾。
4.“威脅”的并列同現成分
(7)由于科技的非人道化使用,它也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威脅。
(8)這種壓力一旦受到外界的壓力與威脅,就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民族凝聚力。
在例(7)和例(8)中,出現在連詞“和”“與”前后,與“威脅”構成并列關系的兩個詞是“災難”“壓力”,二者只有名詞詞性,因此,可以推知“威脅”也是名詞。
5.“威脅”的同境語法結構
(9)此后,開始進行[消除北方威脅]、[統一北方地區]的戰爭。
(10)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嚴重]。
例(9)中,“威脅”和“地區”相繼出現在[V+X]和[X+V]的格式中,其句法環境相同,因此,“X”的詞性也一定相同。因為“地區”只有名詞詞性,所以“威脅”也是名詞。同理,例(10)中“問題”和“威脅”相繼出現在謂語之前,“問題”只有名詞詞性,所以“威脅”也是名詞。
(二)“威脅”的名詞化隱喻功能
詞匯語法層是話語意義層的體現,而語法隱喻的產生依賴于打破一致式的常規,在詞匯語法語法層與話語意義層之間形成一種張力,使表層意義與深層意義產生錯位[2]。從隱喻功能的角度來看,“威脅”的名詞化隱喻功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增加句子信息量。在信息量相同時,非一致式所包含的詞匯數量往往少于一致式。如例(3)可用一致式表達為:“科威特隊射門兩次,有一次威脅到了我方球門。”一致式在此需要點明“威脅”的對象,非一致式則通過過程的事物化而承載了相等的信息,凸顯了名詞化在濃縮信息、增加信息量方面的顯著作用。
第二,模糊施事。名詞化將動態的過程變為靜態后,可以對施事進行虛化,如例(1)中,“外部威脅”的發出者隱藏在語境中,而一致式則必須交代出誰是“威脅”的發出者。
第三,增強語篇客觀性。科技、新聞文體中名詞化出現的頻率最高,語篇作者往往通過名詞化的使用,來保持自身客觀敘事的地位。久而久之,名詞化的使用也逐漸成為衡量語篇專業程度的標準之一。“威脅”在科技、新聞文體中的名詞化,正是增強語篇專業性的有效手段。
三、漢語詞典中“威脅”的收詞考察
語文詞典主要用來歸納詞類、解釋語義、指明用法,承擔著在語言發展中客觀反映詞匯現實面貌的任務。因此,語文詞典應根據詞語的發展演變,對其穩定下來的詞性、義項、用法進行精確記錄、及時反饋。外向型詞典主要供有漢語學習需求的外國讀者學習使用,也是國際中文教師教學的重要工具。這里首先梳理“威脅”一詞的產生及演變,之后從語文詞典與外向型詞典兩方面,對“威脅”一詞進行考察。
(一)“威脅”的產生與演變
所謂“詞匯化(lexicalization)”,一般是指大于詞的、自由組合的句法單位逐漸演變為詞的過程[8]、[9];所謂“跨層詞匯化”,是指兩個相鄰的卻不在同一句法層次、不形成直接句法關系的語言成分,通過脫離其原有組合層次,凝固為一個詞的現象[10]。非句法單位形式演進為一個詞匯單位的現象,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漢語詞匯雙音化。完成跨層詞匯化的兩個語言成分,通常都經歷了由獨立的單音成分演變為雙音韻律詞的過程,體現出漢語兩個音節構成一個音步的傾向。其次是語法化。一般來說,實詞的虛化、弱化會使其能產性急劇降低,逐漸成為附加成分,附著在其相鄰成分之上,起到韻律作用或標示一定的句法關系。再次是高頻共現。兩個語言成分共同出現的頻率高是雙音詞衍生的關鍵條件之一,兩個非直接句法成分需形成一定的句法構式,而后經過原組成成分意義與構式義的整合,在語用推理的基礎上形成新詞[11]、[12]。
在古代漢語中,“威脅”起初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詞,而是作為線性緊鄰的兩個詞同時出現的。例如:
(11)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史記?刺客列傳》)
(12)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晉書?王敦傳》)
(13)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魏書?崔延伯傳》)
例(11)中,“威”是名詞,作非施受主語,在語義上表原因,意為“勢力、威勢”;“脅”是謂語動詞,語義為“挾制、脅迫”。例(12)中,名詞“威”是介詞“以”的介引成分;“脅”是謂語動詞,“脅”的賓語可由名詞充任,其結構語義為“用威勢來脅迫”。例(13)中,“威”為名詞,作動詞“揚”的賓語;“脅”為動詞,作后一動賓結構中的謂語核心。
可見,“威”和“脅”并不處于同一個句法結構中,(X+威)+(脅+Y)是其前后語言成分的常見組合關系。在語言使用過程中,“威”和“脅”由于長期連用,伴隨著中古時期單音詞向詞素轉化的趨勢[13],單音詞素配對構成雙音新詞,遂逐漸凝固為一個常項AB,同時,X和Y的句法語義變化并不影響AB的繼續出現。其跨層詞匯化模式為:(X+A)+(B+Y)→X+(A+B)+Y→A+B。
在跨層詞匯化的整合過程中,“威”由表示具體概念轉為表示行為動作進行的方式,“脅”表示相關行為動作。“威脅”成為一個獨立的偏正式雙音動詞,相關句法結構被重新分析為“X威脅/Y”。例如:
(14)曇朗既殺死文育,復威脅/文育部曲,令他從順……(民國蔡東藩《南北史演義》第六十九回)
跨層結構與組合之前的結構在語義上具有繼承關系[14](P379-380),具體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兩個組成成分語義基本不變,形成語義雙重心;第二,其中一個組成成分語義弱化乃至消失,形成語義單重心;第三,兩個組成成分語義均弱化乃至消失,形成語義超重心[11]。就我們的考察來看,“威脅”屬于語義雙重心結構,在跨層詞匯化后,單個成分的語義基本不變。它的主要變化是在于“威”由于在語法上作方式狀語,因此,其語義有所虛化,不再實指武力,而指一切能使個人或群體產生敬畏或畏懼心理的情勢。
(二)語文詞典中的“威脅”
《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與《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以下簡稱《現規》),是國內當前兩部影響較大的詞典。“威脅”在《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的釋義是:“動①用威力逼迫恫嚇使人屈服:~利誘。②使遭遇危險:洪水正~著整個村莊。”[15](P1358)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第4版)》的釋義是:“①動用權勢或武力恐嚇脅迫:武力~。②動(某些因素)造成危險或危害:環境污染~著人類健康。”[16](P1424)
在《現漢》和《現規》中,動詞“威脅”的兩個釋義體現出兩種語義特征:第一,施事動作發出的主動性(義項①)。這時,施事一般由擁有主觀意志的人或組織充任,對受事施加壓力,使他作出符合施事意愿的動作。第二,受事所處狀態的客觀性(義項②)。這時,施事一般由不具有主觀意志的物質或抽象事物充任,因此,“威脅”的動作也不具有主觀性,句子凸顯的是受事處于危險狀態。不過,二者在釋義、示例方面均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就釋義方面而言,《現漢》義項②并未點明“威脅”的施事,與義項①的區分度不高;《現規》義項①的釋義只關注了“威脅”動作本身的方式和進行,未能體現出動作的目的是“使人屈服”。因此,《現漢》應加強區分兩個義項的側重點,《現規》則應對義項①進行補充,表明動作的目的。
就示例方面而言,《現漢》義項①所舉示例是一個連動短語,《現規》義項①所舉示例是一個偏正短語,二者均未體現施事以及受事如何屈服。對此,更適合使用兼語句以體現各成分的句法語義關系。例如:
(15)歹徒威脅他把錢交出來。
例(15)中,“歹徒”是施事,“威脅”是動作,“他”是受事,“把錢交出來”是釋義中“使人屈服”的具體表現,四者構成了一個信息完整的行為過程,便于讀者準確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現漢》與《現規》均未收錄“威脅”的名詞義項。基于本文的考察,“威脅”已經具備了名詞全部的句法功能,并且穩定地出現在主流語言生活中,應在今后的修訂中對其名詞地位予以確認。
(三)外向型詞典中的“威脅”
1992年,國家漢語水平考試委員會辦公室考試中心出版了HSK考試大綱——《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將漢語詞匯分為甲、乙、丙、丁四級常用詞。其中,要求中等漢語水平學習者掌握甲、乙、丙三級常用詞,“威脅”收錄于丙級詞中。2021年,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了《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將學習者的中文水平分為“三等九級”,并以音節、漢字、詞匯、語法等語言基本要素構成“四維基準”。“威脅”收錄于六級詞匯表中,即位于中等水平的最高級。可見,“威脅”應為中級漢語水平學習者所掌握。
《商務館學漢語詞典》(以下簡稱《學漢語》)是以生成句子為主導功能的積極性詞典,引導學習者了解詞語的意義和用法,從而產出符合規范的句子,主要面向中級水平以上的漢語學習者[17]。《漢語教與學詞典》(以下簡稱《教與學》)是為漢語教學專門編寫的中型工具書,主要服務對象為漢語教師和中級及以上水平的漢語學習者。兩部詞典在收詞范圍、收詞數量、難易程度上大體相當,并且都主要面向中級及以上漢語水平的學習者。兩部詞典在外向型漢語詞典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業內評價較高。
《學漢語》對“威脅”的解釋是:“(動)①用巨大的壓力迫使別人屈服:公開威脅丨不怕威脅丨他用死來威脅她丨我沒有錢,你威脅我也沒有用丨他用刀子威脅她丨我不止一次地受她威脅。②某種情況使人覺得不安或感到會受到傷害:構成了威脅丨嚴重地威脅著丨經濟危機正在威脅著國家的發展丨傳染病威脅著人們的健康丨火災威脅著森林的發展丨地震時刻威脅著這一地區人民的生命。”[18](P726)《教與學》對“威脅”的解釋是:“①(動)用使人害怕的行為或語言,迫使人屈服:解決矛盾不能用武力相~丨不管敵人怎樣~,他始終不屈服丨你不要以這種手段~我,我知道該怎么做丨你不要用~的語氣說話丨敵人的~嚇不倒我們。②(動)使人遭遇危險:大火~著周圍鄰居的安全丨過多使用農藥~人們的健康。”[19](P1093)
《學漢語》的收詞以《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甲、乙級字詞為主,《教與學》的收詞以漢語水平(考試)大綱和教學大綱中的初、中級常用詞為主,在解釋詞義時從中級語言水平讀者的角度考慮,采取較為通俗淺近的說法。需要指出的是,這兩部詞典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釋義與示例不相匹配、示例存在著搭配不當等。
就釋義與示例不相匹配而言,《學漢語》中“威脅”的義項與《現漢》《現規》基本相同,問題是在于義項②的釋義重點為“某種情況作用在人身上時,給人造成不安的感覺”,但部分例句的施事和受事并未涉及到人,而是呈現出客觀的社會情況,如“經濟危機正在威脅著國家的發展”。可見,義項②的釋義存在以窄釋寬的問題。同樣,《教與學》中“威脅”的義項②也強調“使人遭遇危險”,而忽略了人以外的其他客體。今后外向型詞典的編纂應避免相關問題。
就示例中的搭配不當而言,“火災威脅著森林的發展”是《學漢語》中“威脅”的義項②的例句,它在句法上并無問題,但在語義上,“森林的發展”顯然不能作“威脅”的賓語。在CCL語料庫、BCC語料庫及主流新聞媒體平臺上,也均未檢索到“森林的發展”這種表達,應刪除該條示例。同時,《教與學》中“大火威脅著周圍鄰居的安全”的表達也缺乏地道性。“威脅”在表示“使遭遇危險”時,經常出現在新聞報道中,語體正式程度高。在用作缺少具體語境的詞典例句時,應優先考慮其常用語境中的搭配,以符合讀者的認知。“周圍鄰居”的敘述者應是當地居民之一,不符合“威脅”常用的第三人稱敘述視角,該句應改為:“大火威脅著附近居民的安全。”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學漢語》《教與學》均未收錄“威脅”的名詞義項。與語文詞典一樣,今后外向型詞典也應對“威脅”的名詞地位予以確認,從而便于外國漢語學習者區分詞類、掌握搭配規則。
四、結語
漢語詞的兼類問題與隨之產生的詞典中的詞類標注問題,在語言學界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論。目前,根據詞的語法功能劃分詞類,即考察一個詞在語法結構里能夠穩定占據的語法位置,是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的主流觀點。在此基礎上,諸多學者試圖建立多重標準,從語義或表述功能出發劃分詞類[5]。語言是人類對精神和物質世界的描述,而事物與動作之間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二者在共時層面處于一個連續統的兩端,因此,在二者中間難免會存在模糊地帶。對于兼類詞的處理,語文詞典編纂者更關注共時層面中的詞匯發展,從詞典體量和實用性、讀者需求等角度出發,認為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詞的全部兼類標出,只需標出其常用的類別即可[16],而外向型詞典對詞類的標注往往參考權威語文詞典。不過,即使以常用性為原則,如何作出判斷同樣需要建立相應的標準。本文基于系統功能語言學視角,對“威脅”的語法功能和名詞化特征進行了考察,證明其名詞義項在科技、新聞等語域具有常用性,有必要在詞典中予以體現。總之,在常用性的標準下,還有多少兼類義項未被詞典收入?不同類型的詞典對詞語兼類是否應建立不同的標準,以服務于不同的讀者?這些問題今后仍需要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