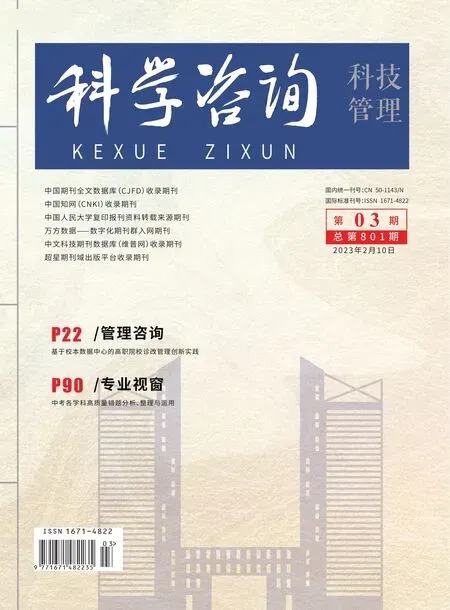“信息繭房”作用下“00 后”高校學生職業價值觀現狀及對策研究
趙康,劉若曦,陶敏,王樂樂
(安徽大學商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海量信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多元的網絡空間變得更加紛繁復雜。互聯網在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的同時,其衍生出的問題如“信息繭房”[1]也隨之而來。“信息繭房”入木三分地描繪了這樣的畫面:在信息極為開放和便捷的時代,人們卻主動蜷縮在像“繭”一樣的信息“繭屋”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00后”大學生作為互聯網最忠實的受眾,他們的思想認知和價值體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繭房”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基于此,他們會對客觀世界產生自己獨特的理解,他們會將自己對客觀世界的獨特理解遷移至對職業的認知、理解、判斷和選擇中,這就會使他們產生自我認同的職業價值觀。“00后”大學生即將走入新的人生階段——就業,然而,當前的就業形勢仍然較為嚴峻。在宏觀形勢變化的前提下,彌補“00后”大學生在職業價值觀上的缺陷就變得很有意義。本文擬從“信息繭房”的視角出發,深刻探究“00”后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現狀,并針對其職業價值觀的綜合表現從多個層面提出可行性建議,凝聚各方力量共創“破繭之策”,解決“信息繭房”的難題。
一、背景概述
互聯網的發展使信息數量和網民數量迅速增加,信息獲取的成本空前降低,但也出現了信息過載等問題。由于用戶感知、處理信息能力的相對有限性,為降低自身的認知負荷,用戶通常會表現出選擇性接觸和從眾心理。用戶通常會選擇自己感興趣、能使自身輕松愉悅或對自身有利的信息,長此以往,用戶會將其限制于像“繭”一般的封閉環境中,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繭房”現象[2]。“00后”大學生盡管具有一定的信息篩選和判斷能力,但他們也會在自我選擇和算法推薦下陷入信息窄化和觀點極化的怪圈。
“00后”高校學生是指在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正在接受基礎高等教育但仍未走入社會的青年群體。時光飛逝,最早的“00后”迎來了他們人生的成人禮,他們即將走入社會。根據形成期理論,成長環境對個體價值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為: 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趨于穩定時,價值觀的傳遞也相應呈現出平穩的特征;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發生異化時,價值觀也會發生變化,甚至可能會出現價值觀的割裂。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從這一層面來看,人的思想行為深刻反映著一定社會環境中的各種關系。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生產力大幅提高,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狀況和行為表現。互聯網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21世紀初,中國互聯網快速發展,中國跨越式進入網絡社會,中國的網民數量迅猛增長,位居世界第一。因此,互聯網的發展已經成為在改革春風吹拂下的“00后”高校學生成長的最鮮明底色。
職業價值觀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學者Super提出的,他認為“職業價值觀是指個體追求的目標、個體的內在需要和從事活動時所追求的工作的特征或屬性”[3]。職業價值觀在傳入中國后,國內大部分學者在國外學者定義的基礎上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論:竇運來認為職業價值觀是評價工作行為及其后果的內心尺度,綜合反映了個體的內在追求及偏好[4];姚輝認為職業價值觀是個體基于工作行為及其后果的價值判斷[5];欒貞增認為職業價值觀綜合反映了個體對工作場所中事物對與錯的價值評價[6]。筆者綜合各種文獻發現,中外學者并沒有對職業價值觀的內涵達成一致共識,但是他們都認為職業價值觀會影響個體的工作行為、態度和選擇偏好。本文以西南交通大學寧維衛教授的《職業價值觀問卷》提供的維度進行現狀的歸類,較為綜合地分析“信息繭房”下“00后”高校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現狀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信息繭房”效應下“00 后”高校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現狀
(一)缺乏主流價值認同
主流價值觀折射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價值共識,青年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群體之一,青年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與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休戚相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尚處建設之中、西方外來文化猛烈沖擊的背景下,青年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關系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影響深度和廣度。
在互聯網時代,為了迎合部分年輕人所謂的反叛精神,網絡信息的娛樂性因素層出不窮,“娛樂至死”已然成為社會不良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碎片化、淺薄化和庸俗化的信息在不斷侵蝕著青年的思想,荼毒青年的未來。“信息繭房”以個人議程設置取代公共議程設置,這極大地窄化了大學生選擇、接受和傳播信息的渠道。很多重要的社會公共性議題也被有選擇地忽略和遺漏,這使主流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和權威性也在不斷地被削弱[7]。身處“信息繭房”的“00后”高校學生對自己所處的“信息孤島”狀態并不自知,高度發達的網絡掩蓋了他們真正的認知水平,異化了他們的認知傾向,使他們沉湎于自我愉悅的信息“奶糖”,極力排斥陽春白雪的主流價值,他們全然不知自己已經處于危險的境地。
(二)畏懼現實生活交往
21世紀初以后出生的“00后”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會因為學業、情感和經濟等方面的問題而面臨困惑和心理壓力,這些問題可以通過開展談話、轉移注意力、發泄精力和自我鼓勵等合理的方式來解決。但一些學生卻沉浸在“信息繭房”塑造的“此心安處”,開啟自我防衛機制,與造成這些困惑和壓力的根源——現實世界相隔絕,拒絕與人溝通交流。從這一方面來看,“信息繭房”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學生產生厭世心理,消極避世,不愿走入社會、走入職場。
在“00后”大學生虛擬社交空間中存在著這樣一句經典的話:“現實中我唯唯諾諾,網絡中我重拳出擊”。這句話生動形象地描繪出部分大學生在現實世界中表現出的“見光死”的懦弱姿態,而在虛擬世界中,他們如魚在水、如鳥在空。虛擬的社交空間的喧鬧代替了現實世界的繁華,一方面,“00后”大學生可以在網絡空間高談闊論、口若懸河,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給陌生人以自己最柔軟的溫情,也能嫉惡如仇、針砭時政,對于自己所不能認同的觀點報以最大的冷意;另一方面,部分“00后”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唯唯諾諾,他們樂于貼上“社恐”的標簽,社交能力下降,社會黏性減弱。“信息繭房”為大學生逃避現實交往、有意忽略現實的磨練提供了借口和機會。“信息繭房”成為大學生存在習慣性逃避、選擇性漠視等思想的理由,使大學生在走上社會后,其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會大大下降[8]。
(三)較強群體極化傾向
群體成立的原因之一是成員遵循共同的行為準則,形成了內部認同的價值觀。群體組織因群體成員有相似或共同的知識效應而形成,群體成員擁有共同的認知結構和價值觀念。由于群體內部有內部信息的發布、群間交流的封閉、意見領袖、沉默的螺旋等因素的存在,這些因素既可能會促進群體內部團結,也可能造成群體感染和群體極化[9]。在網絡群體繁盛的時代,互聯網空間上涌現了大量的虛擬社群。
部分“00后”高校學生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社會圈群中,他們在享受社會圈群帶來的精神支持的同時,也要受到圈群規則的限制。為了維護圈群的獨立,“00后”高校學生要遵守圈群的秩序,這也是圈群得以正常運轉的條件。在這樣的圈群中,“00后”高校學生往往會為了成員的身份而壓抑自己的個性,以達到真正融入該圈層的目的。同時,為了表現出對圈層的認同,在圈群間出現觀念相悖的情況時,本圈群的成員會盲目信從自己所在圈群的觀點,由此構成了圈群的主流輿論力量,持有少數意見的人出于害怕被孤立的心理通常保持沉默。長此以往,他們不再愿意持有個性化觀點,只能隨波逐流、屈從群體。
三、基于現狀的對策研究
(一)推進主流價值傳播的創新
主流意識形態的層次一直以來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其傳播形式呈現出拘束化和單一化的特征。媒體要精準定位“00后”大學生的興趣愛好與價值訴求,并給“00后”大學生推送有針對性的信息內容。因此,主流媒體應當積極推進主流意識形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主流意識形態理論在網絡圈群中的有效供給,從而增加“00后”高校學生與主流媒體推薦內容的觸網時間,不斷弱化“信息繭房”給“00后”大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強“00后”大學生對主流價值的認同。高校可以鼓勵和引導大學生更多地關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央視和新華網、微博、公眾微信和高校主流微信平臺等權威媒體,以此規范大學生接觸的主流權威媒體,使大學生能通過主流媒體及時了解國內外的重大時事[10]。
(二)重視自身媒介素養的提高
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11]。不可否認,數字化媒介在“信息繭房”的影響擴大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信息繭房”重要的技術誘因。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大部分“00后”大學生存在媒介素養較低的問題。因此,“00后”大學生不僅要學會如何解讀紛繁復雜的信息洪流,更要學會如何取舍信息,這要求他們要切實了解“信息繭房”的負面影響,同時要重視理論知識的學習,強化自身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00后”大學生要重視專業知識的學習,以便于自己在面臨信息洪流時,可以抽絲剝繭地建立自己的理論據點,在大潮之中擁有自己的立足之處。在日常生活中,“00后”大學生要重視與老師和同學的交往,積極在觸媒中進行反思與總結,以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三)促進良好信息環境的營造
近年來,高等教育出現了“片面重視網絡信息而忽略了其他信息來源渠道”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于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12]。在虛擬世界中,大學生“醉生夢死”“樂不思蜀”,忽視了通過社會實踐獲取最真實的信息,感受社會生活的力量。因此,高校要為學生提供信息獲取的多元渠道,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社會現實生活的機會,幫助學生拓寬視野,走出舒適圈。此外,高等教育的精準化、個性化依然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高校教師要深入學生群體之中,加強與學生的交流,從而及時地了解學生的需求,并鼓勵學生進行積極的自我探索。高校更要營造深度學習的信息環境,加大信息資源建設,建立個性化服務體系,幫助學生認識更加多彩的社會生活,突破“信息繭房”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