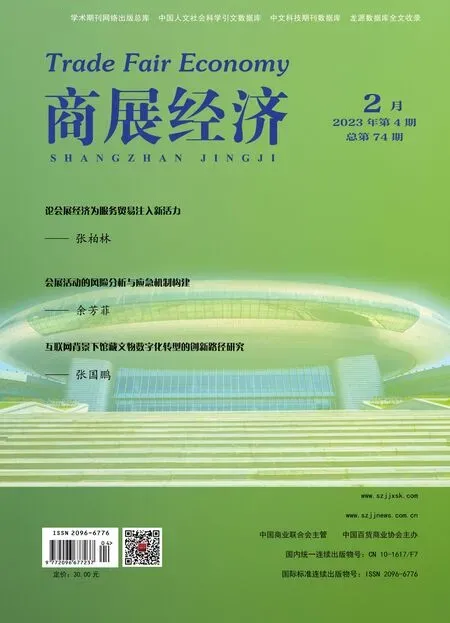互聯網背景下館藏文物數字化轉型的創新路徑研究
張國鵬
(貴州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貴州貴陽 550025)
2021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文件提出要推動我國實現從文物資源大國向文物保護利用強國的歷史性跨越,要全方位提高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數字化水平。在互聯網背景下,數字藏品(NFT)的創造和發展不僅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且加快了文化遺產和文化產業價值的傳播,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擁有更廣闊的未來,建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
1 社會背景
1.1 傳統文化與媒介
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人們對文化和精神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傳統文化展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數字藏品憑借其稀缺性、唯一性、平民化等優點,已成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新載體。
在這個“萬物皆媒”的時代,數字藏品不僅發揮著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而且作為數字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其在不斷地發展和演進,從單一走向多元化:從傳播學的角度,數字藏品作為一種文化傳播載體,是一種新型傳播媒介,具備傳播強媒介屬性;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數字藏品重要的IP打造來源,是數字藏品創作的依據與發展的基礎。
1.2 數字藏品文化傳播現狀
數字藏品作為數字文化產業的首要代表,不僅是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現中國形象的“窗口”,也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數字流動文化博物館”。
隨著近年來傳統文化數字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的博物館逐漸意識到傳統文化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相繼推出與傳統文化緊密結合的數字藏品,如“越王勾踐劍”“蕭何月下”等。但由于數字化建設在時間上有先后,我國博物館在數字藏品的打造上仍然存在整體的滯后性和區域的不平衡性,各博物館在傳統文化數字化傳播方面水平各異,問題普遍體現在三點:第一,數字藏品內容缺乏設計感和藝術感,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第二,數字藏品形式單一,霸權式的文化滲透,使受眾缺乏參與感;第三,數字藏品的內涵挖掘不夠深入,難以在情感和精神上打動受眾,阻礙了傳統文化的深層次傳播。
2 研究意義
2.1 緊密貼合國家政策精神
為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的重要指示精神,每個博物館都應最大限度地結合自身特色,對“數字藏品+傳統文化”進行深層次挖掘,更好地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2.2 促進數字文化產業發展
挖掘一件文物、一個故事及其背后的文化表現與傳承,為目前發展不均衡的數字藏品領域提供策略建議,為提升人民傳統文化的滿意度探索核心動力。思考如何將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數字藏品創作之中,促進數字文化產業發展,對數字藏品建設水平各異的中國博物館具有重要意義。
2.3 傳播與保護傳統文化
數字藏品的形式不僅可以讓更多年輕人便捷地了解傳統文化,改變中國傳統文化漸漸被國民所淡忘的局面,讓傳統文化重新“活”起來,而且能有效促進傳統文化以適應時代的方式進行創造性轉變與創新性發展,避免傳統文化在時代潮流中被淹沒。
3 應用場景
就傳播內容而言,數字藏品文化傳播內容在時間上可劃分為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現代文化以城市宣傳文化、商業文化為核心,而傳統文化則以民族文化、藝術作品文化為重要內容。豐富的傳播內容背后,反映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不斷跟進。
3.1 以現代文化為主的應用場景
數字藏品+城市文化得到人們的青睞,目前北京、上海、成都、衢州、青島等,包括地級以下城市都已經發布了與城市相關的數字藏品,用數字藏品宣傳推廣城市文化,發展城市旅游,相互賦能,相互融合,已經成為城市宣傳的一種新途徑。如山東省推出的互聯網傳媒集團聯合山東文交所推出的山東省首個城市風光主題系列數字藏品“青島印象”上線“海豹數藏”,包含“五月的風”“匯泉浴海”“魚山覽潮”“嶗山觀海”“青島大學”“山海之間”6件藏品,每件藏品在各自的發售時段均被搶購一空,在“文旅”和“數字”兩個圈層之間成功“破圈”,并且有效提升了城市的辨識度、知名度和美譽度。
3.2 以傳統文化為主的應用場景
數字藏品和傳統文化的融合,是目前博物館推動傳統文化傳播的主流方式,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館、敦煌研究院、貴州省博物館等都相繼推出了館內相關藏品的數字藏品。眾多珍貴文物,正在以一種虛擬的形式被大眾所了解和收藏。2022年初,20余所博物館與支付寶平臺小程序鯨探合作推出數字藏品,用戶可通過福卡兌換等方式獲得,兌換到的數字藏品可以在鯨探存放及使用。通過數字藏品的方式,讓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從象牙塔走出來,擴大了文物知識的傳播面。
4 傳播特征
根據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提出的傳播學研究5W模式即控制研究(Who)、內容分析(Says what)、媒介研究(In which channel)、受眾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s)。數字藏品總體的傳播特征應從數字藏品文化傳播內容、傳播媒介、接受者、傳播效果及受眾反饋這五個方面進行分析總結。
4.1 傳播內容
在傳播內容上,雖然目前數字藏品所展現的文化豐富多樣。無論是河南博物館的“婦好鸮尊”數字藏品,還是舞劇《只此青綠》數字藏品……推出后都受到普遍歡迎。但數字藏品仍存在傳播路徑趨同等問題,傳播形式包括數字形式的圖片、音樂、視頻、3D模型等,部分形式的數字藏品并沒有收到預期的傳播效果。例如,在內容效果上,創新創意性和趣味性方面仍凸顯不足;數字藏品創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4.2 傳播媒介
新媒體環境下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影響力大的傳播特性同時也成為傳統文化數字化建設呈現的重要方向。網絡數據挖掘結果顯示,不同城市的博物館傳播傳統文化在微信表現差異較大,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征。從運營績效來看,截至2022年11月15日,排名前3的分別為故宮博物院(1488.29)、國家博物館(1041.36)和陜西歷史博物館(628.18)。從運營內容來看,在更新頻率和更新內容上都呈現出相對薄弱的特征,存在泛娛樂化和時政化問題。
4.3 接收者
從深度訪談情況來看,不同年齡人群在獲取數字藏品信息方式上呈現出差異性,具體體現在新型線上媒介和傳統線下媒介兩類渠道:青年受訪者更偏好選擇新型線上媒介(如抖音、微博、微信等),而 45 歲以上的中老年受訪者更偏好傳統線下媒介(如博物館內、親朋好友)。數字藏品傳播媒介的探索需考慮不同人群的觸媒習慣及時代發展的變化,構建兼具個性化和普適化的傳播矩陣勢在必行。
4.4 傳播效果
各博物館發行的數字藏品就特色文化及古今歷史在一定程度上都進行了重點展示。傳播推廣傳統文化,既要講“靈魂吸引”,又要講“雙向奔赴”。但目前數字藏品的傳播過程呈現為簡單的線性傳播模式,沒有考慮到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是由多方力量共同締造的,是由博物館發起的單向傳播,以自我為中心。這意味著以數字藏品為媒介的文化傳播效果難以得到充分體現。
4.5 受眾反饋
以傳統文化為核心的數字藏品進行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必要性。但絕大多數人沒有參與到數字藏品的互動中來,文化接受具有被動性,也沒有關注到數字藏品的深層次文化價值,如缺少征集了解受眾意見的反饋渠道。“合民意、聚民心”是推動數字藏品創作和發展體系不斷完善的必然要求。
5 策略建議
國務院《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因此,要實現前沿科技和傳統文化的深度融合,在滿足人們情感需求和物質體驗的同時,進而推動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5.1 增強人與藏品間的“情感連接”
5.1.1 打造Z世代喜聞樂見的數字藏品,滿足文化需求
在信息過載的新媒體時代,館藏文物因為束之高閣,其背后的文化現象難以被理解,往往不被年輕人喜愛,所以博物館需要用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文物背后蘊藏的歷史文化,數字藏品的運用正是讓文物“活”起來和文物年輕化的一種嘗試。2022年3月“區塊鏈芝士”公布了中國數字藏品的相關調研分析報告,報告對數字藏品買家用戶畫像維度實現了更為精準清晰化的定位:數字藏品的消費者整體年齡結構較為年輕化,其中“18~30歲”的消費者占比49.1%,成為數字藏品的消費主力軍。數字藏品與傳統文化的結合,在無形中將傳統文化的形象進行拆解,注入“時尚”“潮流”“科技”等元素,也激活了數字藏品的社交屬性,并通過數字藏品讓年輕人認識和了解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5.1.2 構建虛實結合傳播體系,提升文化互動
對于數字藏品的展現形式過于扁平化的問題,可引入AR/VR實景展示、3D模型的展現形式等來提升創新創意性,給人們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并融合城市歷史和文化品牌,深層次地挖掘文化內涵,讓人們主動了解城市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才能收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如在數字藏品中“附著”文化講解視頻,聯系具體的歷史文化內容來達到深層次傳播文化的效果。推動受眾對于數字藏品作品的深刻理解以及其背后文化內涵的了解認同,改善人們的文化體驗。
5.1.3 多元玩法與激勵,實現文化體驗
體驗為王的當下,技術創造出的新潮感和體驗感給游客重新審視博物館、文化景點的可逛性帶來了可能。如2022年4月,山東水泊梁山景區發行首款數字門票——好漢令。此次發行的“好漢令”不僅具備收藏價值,而且還可作為終身游覽景區的通行證。這類數字化玩法將傳統人工購買門票的繁冗操作簡化,門票變成了具有收藏價值的“寶藏”,游客的游逛趣味得到了提升,也進一步提升了景區的曝光度。
5.2 增強人與藏品間的“互動設計”
5.2.1 “創作人、服務平臺、消費者”三位一體,營造一體化創作環境
數字藏品的主要參與者呈現為創作人、服務平臺和消費者三方面,統籌三者將使之發揮乘數效應。目前我國很多博物館的館藏文物數字藏品實踐雖已快速發展,但較多停留在館藏文物單一的還原設計層面,存在形式趨同問題。對于創作人而言,博物館要充分保障作者權利,激發創作積極性,數字藏品創作在保證文化性和歷史性的前提下,適當增加趣味性。對于服務平臺而言,依靠數字藏品的逐漸普及,可以不斷發展自身經營規模,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成為數字藏品界的“淘寶”。對于消費者而言,數字藏品具有一定的社交屬性,但普通用戶由于技術門檻難以參與其中,無法滿足其個性化需求。因此,建議數字藏品設計從三方面進行一體化改進,推動各種主題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呼應,實現文化要素的立體化、綜合化表達。
5.2.2 深層次挖掘文化元素,加強整體設計環節
文化元素是控制數字藏品文化表達的重要影響因素,人們對數字藏品文化的感知同時關聯其對既有文化元素的整體解讀。因此,數字藏品設計應遵照文物原型的文化元素,通過對文物信息的挖掘、提煉與重組,有機融入設計作品,維持與協調數字藏品文化表達的完整性。2022年6月,貴州省博物館聯合百度百科博物館發行“守護神系列——蝴蝶媽媽”系列數字藏品,結合貴州省博物館多件刺繡類一級文物,以“生命”為主題進行藝術創作。從文物中提取蝶花紋飾,以高級定制服裝櫥窗的展現形式進行3D渲染,從多方位呈現。將民族服飾的神秘與現代時裝相融合,讓人們愛上中國傳統民族服飾。
5.2.3 學習與創新相結合,突出特色文化
近年來,各城市博物館在數字藏品的建設上,逐漸從學習者轉變為講授者。如貴州省博物館數字藏品建設在開展初期,向北京、南京、西安等城市的博物館進行深入學習,結合自身特色展開數字藏品建設,在獲得一定效果后,把建設效果和經驗分享給其他博物館。參照數字藏品建設表現突出的博物館,學習一些可復制、可推廣、可借鑒的技術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同時也應堅持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結合本博物館的特色文化,在傳統文化呈現維度上集中展現當地的文化主題與內涵,發揮數字藏品作為媒介在傳統文化形象構建層面的積極意義。
6 結語
相較于傳統文創產品開發,少而精的數字藏品更容易集中力量,打造出更具影響力的“館藏IP”,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探討數字藏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應用,并分析總結數字藏品在中國傳統文化傳播中的途徑,讓館藏文物真正“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