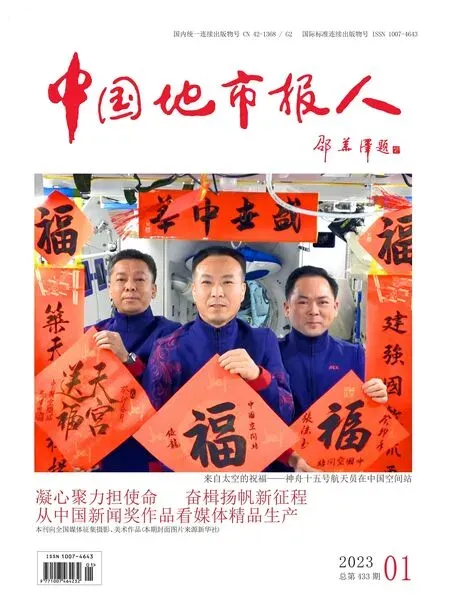“吃播”走紅的傳播學原理分析
——以嗶哩嗶哩為例
李雨隆
近年來,“吃播”受到年輕受眾喜愛,“吃播”即直播吃飯。“吃播”在韓國出現較早并得到蓬勃發展。“吃播”這個詞最早出現于韓國的一個綜藝節目,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直播開始興盛,“直播吃飯”的內容也吸引了大量觀眾觀看,越來越多的“播客”憑借“直播吃飯”走紅,隨后韓國獨特的“吃播”文化也逐漸被中國人關注。
隨著人們物質與信息都逐漸得到滿足,“吃播”模式還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衍生。一方面,不計其數的“吃播”進駐我國各大直播平臺,一些主播憑借獨特的風格與特色的內容脫穎而出,擁有眾多粉絲并成功實現流量變現,其中“大胃王”類型的吃播較為流行;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逐漸走向短視頻時代,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的“大胃王”吃飯直播開始轉型,衍生出了“錄播”這一形態,也就是說主播吃東西的過程提前錄制完成,再通過剪輯與后期處理形成更加凝練的內容,最后上傳到視頻平臺與觀眾見面。嗶哩嗶哩(又稱bilibili,以下簡稱B站)作為年輕人聚集的文化社區與視頻平臺,就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吃播UP主”進駐,并上傳了許多精美有趣的“吃播”視頻。
由于發布的視頻內容能夠通過剪輯變得更加有趣多樣,因此B站的“吃播”視頻內容不僅僅局限于“大胃王”風格,而更傾向于向百花齊放的“吃播”風格轉變。通過分析大量的吃播內容,“吃播”視頻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類:“挑戰型”吃播、“日常對話型”吃播、“ASMR”吃播。
一、理論回溯:使用與滿足
“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開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轉折點,也是受眾研究的主要理論框架之一。在該理論中,受眾被看作是有著特定“需要”的個人,而受眾的媒介接觸活動是滿足受眾特定“需求”的過程。[1]美國社會學家E·卡茨被認為是“使用與滿足”說的“現代時期”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將媒介接觸行為概括為“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的因果連鎖過程。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興盛,視頻成為新型傳播媒介,“吃播”作為視頻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廣泛受眾,因此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研究“吃播”受眾的心理需求與觀看動機是較為合適的。從長遠眼光來看,“吃播”以其“低門檻”的優勢吸引了眾多主播的加入,從受眾的角度研究其特點與傳受雙方的關系,不僅能夠使“吃播”從業者與視頻平臺深入思考如何提升用戶體驗,以此提升視頻質量、增強用戶黏性,還能在激烈的競爭當中一馬當先,從而促使整個行業也能得到良性發展。
本文將采用參與式觀察法和主題分析法,對B站的“吃播”視頻進行分析。具體研究方法是:首先,在B站“美食區”展開沉浸式體驗與觀察,觀看視頻并參與互動,感受作為受眾甚至粉絲的心理狀態,分析內在動因;其次,抓取B站具有代表性的“吃播”視頻彈幕與評論進行分析;最后,在互聯網論壇或知乎問題中搜尋有關B站吃播的相關內容作為進一步的補充。
二、“沉浸式”體驗:“吃播”受眾的需求滿足
(一)虛擬陪伴:緩釋現實孤獨
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化社會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當代年輕人承受著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特別是對于已完成學業在城市中獨自打拼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被工作填滿,努力拼搏,想在大城市站穩腳跟,工作之余無暇社交但卻渴望親密關系來緩解現實的孤獨。這種需求在現實生活中是矛盾的,但是科學技術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種矛盾。互聯網的出現與移動設備的更新換代使得遠距離社交成為可能,足不出戶就能與遠在千里之外的人進行心靈上的交流,真正實現“距離不是問題”。[2]
對于中國人來說吃飯絕不是簡單的“進食”,“飯桌”文化已經浸潤了人們的生活,“飯桌”一直都是人們社交的場所。但是部分年輕人因為難以承受面對面交流的壓力而對于現實生活中的“飯桌”社交顯示出反感的情緒。與之相對的是,“吃播”所呈現的“虛擬飯桌”是一種“無壓力”社交,想交流時發出彈幕,不想交流時就沉默,還能夠隨時退出,幾乎沒有任何社交成本;關閉彈幕時變成了自己與UP主一對一的交流,打開彈幕時感覺變成和許多朋友一起吃飯和交流,社交體驗是非常自由的。
“日常對話型”吃播就模擬了現實生活中的“飯桌”,此類UP主在錄制視頻時通常把攝像機想象成他們的觀眾甚至朋友,不僅訴說自己生活中的趣事還會進行互動,詢問觀看者的狀況,觀眾會通過彈幕進行互動。比如“就是氣氣”是B站擁有七十多萬粉絲的吃播UP主,視頻風格主要是“一人食”,在吃飯時會與屏幕前的觀眾進行互動,比如提起自己才下班,詢問觀眾今天上班的情況,這時彈幕內容多為對于詢問的回答,仿佛在跟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吃播”UP主的視頻是錄制剪輯的,因此與用戶的互動不是同時進行的,但是也能達到互動的目的,增強虛擬的陪伴感。比如在“Anna智賢”的視頻中經常出現“感謝智賢陪伴我每天的晚飯時光”“哇,今天智賢家吃炸雞,我也買了炸雞,四舍五入我和智賢一起吃飯啦”。這種“社會臨場感”雖然缺乏“身體的在場”但也增強了人們心靈上的距離,獲得滿滿的陪伴感。
(二)虛擬體驗:代償性云進食
“吃播”熱潮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與受眾心理的“代償性”滿足有關。所謂“代償性”滿足就是人們通過觀看UP主幸福、滿足地吃東西的場景,感覺自己同樣品嘗到了美食,獲得美妙的感覺。人們“代償”心理產生的原因在彈幕中能夠窺見一斑。通過整理分析“Anna智賢”點擊量最多的五個視頻的彈幕,發現每個視頻中的彈幕都有與“減肥”相關的內容,最多的一個視頻中有二十多條彈幕提及。因此可以看出,為了保持身材,許多人對于食物的攝取有所節制,但這樣不能滿足對美食的渴求,轉而通過看吃播進行云進食獲得“代償性”滿足。
“吃播”視頻中的畫面與聲音是受眾身臨其境的重要因素。B站吃播視頻畫面精致,食物誘人,對應的彈幕都顯示出對食物的夸贊,當UP主吃東西發出咀嚼音時,有彈幕表示“仿佛我自己也吃到了”“我好像聞到了食物的味道”。[3]聽覺也是刺激受眾產生“飽腹感”的一個因素。專業的“吃播”UP主所使用的收音設備能夠清晰地記錄咀嚼食物的聲音,通過接收的設備播放只有很少的失真,因此將受眾的虛擬體驗無限放大,把受眾帶入一個三維的世界。幾乎零失真的咀嚼音使得“ASMR”型吃播區別于其他類型的吃播,這類吃播選取的食物咀嚼音清脆悅耳,通過專業的收音設備將聽覺的元素放至最大。
人的感官是相互關聯的,對于一種感官的刺激會引起其他感官的聯動反應。所以觀看吃播視頻,在視覺和聽覺的雙重刺激下引發了味覺甚至嗅覺反應。換句話說就是,人們在誘人的食物和咀嚼音的刺激下產生心理反應,獲得“吞咽”和“飽腹”的快感與滿足感。
(三)真人表演:好奇心的滿足
“吃播”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網絡真人秀,主播們在節目中扮演真人秀演員,進行吃東西的表演,這種表演在特定的環境中進行,并且能夠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吃播”與電視真人秀節目相比較更加貼近受眾的生活,畢竟“吃飯”是每個人每天都會進行的日常動作。學者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可以看作是一種表演,而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又能夠被分為前臺表演和后臺表演。[4]對于個人來說,“吃飯”屬于一種私人行為,應該在后臺進行。然而“吃播”主播進一步弱化了自己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界限,將原本應該在后臺表演的私人生活展現在了大眾面前。當UP主展現自己的私人空間時,有受眾會通過彈幕提出自己的評價甚至對環境布置提出自己的意見,進一步拉近了自己和主播之間的距離,實現了“缺席的在場”。
人們觀看吃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能吃”和“吃不到”。世界食物種類繁多,一部分受眾由于時間、金錢和地域的限制,即使對許多食物充滿好奇也沒有條件品嘗;還有一部分觀眾由于身體原因、飲食習慣或者心理障礙不敢嘗試,但是又充滿好奇,因此“吃播”視頻中對于食物的展示以及“UP主”進食的反應彌補了受眾未能品嘗食物的遺憾。[5]比如B站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吃播”UP主,主要向觀眾呈現當地的特色美食,引起了許多受眾的關注,在展現不同于國內烹飪做法和常見食物時,彈幕顯示出驚訝與好奇:“原來你們還吃駱駝肉”“西紅柿竟然還能烤來吃”……“挑戰型”吃播在B站也擁有高超的人氣,比如UP主“記錄生活的蛋黃派”的100元系列,包括“加100元料的珍珠奶茶”“加100元料的手抓餅”的主題,食物的類型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但是以數量為賣點,完成普通人一般不會選擇的挑戰,也能夠極大滿足受眾的好奇心。
(四)娛樂消遣:精神的調節與放松
當代年輕人在高壓的工作與學習的環境中生活,催生了一系列負面情緒,一部分人不想通過閱讀書籍、觀看電影等高度耗費精力的方式來調節自我,而選擇只需要耗費少量精力、利用碎片化時間就能達到娛樂效果的、看似毫無意義的消遣方式。觀看“吃播”就是這樣的解壓方式,觀看視頻時不用進行思考,只用直接接收視覺和聽覺等帶來的感官刺激。在up主“Anna智賢”的評論區有觀眾表達:自己在下班之后每天都會準時觀看視頻,實在是太解壓了,工作的壓力一掃而空。也有彈幕顯示:在寫作業時會打開視頻當作背景音,不僅沒有打擾我學習反而提高了效率。對此可以看出,許多人觀看“吃播”并沒有特定的目的,只是想讓自己“開心一下”,使精神得以放松。
三、結語
在互聯網高速發達和社會加速現代化的雙重影響下,人們熱衷于線上圍觀吃飯這一日常事務。從受眾研究的角度來看,“吃播”之所以被許多人接受和喜愛,是因為這一方小小的“虛擬飯桌”滿足了現代年輕人的心理需求,使得緩解孤獨、代償心理、好奇心理、精神調節需求等都得到了滿足。在受眾主動選擇觀看“吃播”的背后,我們也要思考這些由社會心理需求變遷所引發行為的負面影響。
現代社會是“功績社會”,也就是說人們會成為自己的雇主,不斷提升自我,使自己變得更加美好。因此,分析代償心理產生的原因,一部分是源于女性對于自身身材的焦慮,“吃播”中帶有肥胖因子的食物,與進食者完美形象的對比會加大對身材的心理焦慮,而且“云進食”也會加大受眾對于美食的渴望,當渴望不能在現實中得到滿足時,可能會造成暴飲暴食的后果。人們麻木地觀看著同質化的視頻時,接收的是空泛的內容,雖然能夠獲得短暫的快感,但正如尼爾·波茲曼所說的“娛樂至死”,過度的娛樂只會漸漸讓人喪失思考的能力,弱化向上的精神。加之如若人們沉溺于虛擬的陪伴,那么現實的生活必將被影響,反而會加重孤獨的程度,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基于此,一方面,“吃播”主播應避免低俗化內容的生產,應制作兼具畫面高質與內涵美好的視頻;另一方面,“吃播”受眾在享受“吃播”所帶來的快感時要避免沉溺其中,切忌用虛擬世界代替真正的現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