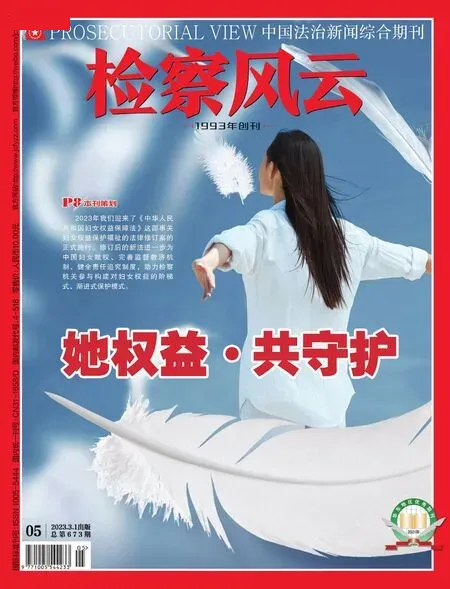徐冰:更珍惜自己文化的價值
說現在是讀圖時代,其實中國人讀了好幾千年了。今天出現的很多標識,其實都是“象形文字”,就像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識“五環”已經成為了一種符號,如今是新一輪“象形文字”興起的時期。
“天書”與“地書”
《檢察風云》:古元先生也是您的老師吧?
徐冰:古元先生是我很喜歡的一位老師。他沒有直接在教室里教過我,但私下里,我和他有一些接觸。我早期的東西受他影響比較大。我最喜歡的中國藝術家有兩個,一個是古元,一個是齊白石。這兩個人真是非常了不起。簡單說,誰畫中國人畫得過古元?當然我對古元的偏愛可能帶有性格上的原因,可能有過高的評價,但我是這么認為的。你看古元木刻里那么丁點的小人,畫得那么像中國人,骨子里透著中國人的感覺,那種大棉襖、腿部彎曲的程度和那種動作及感覺,完全是我插隊時村里的農民。這種對中國人的刻畫,入木三分,一般的藝術家是很難達到的。雖然后來中國繪畫的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真正把中國人、中國農民骨子里東西畫出來的,我覺得沒有人比得上他。
《檢察風云》:安迪·沃霍爾復制瑪莉蓮·夢露的畫像,您當時的復制有沒有受到安迪·沃霍爾的影響?
徐冰:毫無疑問是受到他的影響的。在一期《世界美術》上,我看到了安迪·沃霍爾的一幅作品,黑白的,也就一塊小豆腐干那么大,是安迪·沃霍爾做的肯尼迪夫人像,以重復出現的形式表現出來。看了以后,我就對重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張小的發表物對我的影響其實很大,這件作品讓我琢磨了很長時間,結果這成了我研究生畢業的論文題目,后來也導致我對版畫的“復數性”概念進行了一系列研究。那時關于西方當代視覺文化的信息很少,文化的“胃”的吸收能力極強,有一點東西,你都先吃下去,然后再慢慢咀嚼消化,一點都不浪費。
《檢察風云》:解構漢字,是不是暗示漢字在走向死亡?
徐冰:漢字在走向死亡?不會。漢字其實沒有走向死亡,而是在發展,事實上,在這個時代,漢字與當代數字技術和電腦網絡時代的關系優于其他的文字。比如說漢字的打字速度,就比其他字母文字要快,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再一個,漢字的象形性在今天這個讀圖時代,優勢正慢慢被體現出來。我后來不是做了一個作品叫“地書”嗎?“地書”和剛才提到的這個主題是有關系的,為什么我做“地書”?它是一個很當代的作品,作品的靈感來源于我們象形文字的傳統,說現在是讀圖時代,其實中國人讀了好幾千年了。今天很多標識的出現,其實都是“象形文字”,就像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志。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識“五環”已經成為了一種符號,要我說呢,如今是新一輪象形文字興起的時期。因為整個數字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使人類的生活方式和關系都在變化,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新的,而且有太多新技術出現,每天都有新的、以前沒有經歷過的事物。我們面對這些東西,就像原始人面對世界一樣新奇,我們的生活其實和幾千年以前截然不同,但是我們使用的文字還是一樣的。
《檢察風云》:對于一個不懂漢語的西方人來說,看到“天書”和看到中國古籍中的文字并沒有太大的區別,您覺得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于“天書”的感受是否會不同?
徐冰:會不一樣,但是失去一部分,也會獲得一部分。反過來講,“天書”對誰都很平等,它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不管你懂不懂漢字,反正誰都不認識。
《檢察風云》:做“地書”時為什么增加了與觀眾的互動?
徐冰:你說的沒錯,“地書”增加了與觀眾的互動。這個作品實際上是從現實生活中來的,它本身和社會進程有很密切的關系。比如這個作品其實開始很早,但沒法結束,為什么呢?因為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標識、表情符出現。在網絡上,在生活的環境中,我走到哪都會把一些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的標識照下來,它們太豐富,而且隨時在出現。最早我們展示這個作品,是把我工作室中這個作品的工作區搬到展廳中去,實際上是在表達我們對這個作品的認識。其實它是沒完沒了的,不可能結束的。
另外,在我的這個作品中,我最早做的是書,寫一本誰都可以讀懂的書,后來我們又開發了電腦軟件,打字進去以后,能轉成標識性的語言,有英文也有中文。這樣的話,如果輸入的中文和英文是同樣的內容,會出現同樣的標識,懂中文和懂英文的人都能理解它。于是,它有點像是不同語言的中間站。我們展示時有兩臺電腦,可以互動,觀眾可以參與。現在把它放在展廳里,要我說是不滿意的。它不應該在展廳里,因為它應該被人們帶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其實觀眾根本沒有必要走到美術館的展廳里,但這不是我作品的問題,而是整個網絡藝術、高科技藝術至今尚不能解決的問題。
出國與回國
《檢察風云》:20世紀90年代,你移居美國,在美國的時候是不是也看了許多當代藝術的作品?做了一些極端的實驗?
徐冰:在美國我做了很多很極端的實驗。去美國主要還是想去試一試,當時搞不明白的就是,為什么這些邊緣文化的藝術家,進入美國中心藝術區或者西方的藝術系統這么難?這到底怎么回事?帶著很強的好奇心,我來到美國,盡可能地參與到當代藝術的系統中去,基本上那些年我都在東村、SOHO(蘇豪區)和現在我的工作室布魯克林的維廉斯堡,這些地方都是紐約最具實驗性的藝術區,18年來像是跟隨最具試驗性的藝術家群體在遷移。
《檢察風云》:就像古元到了北方以后有了新的感受一樣,你到了美國之后,是否也對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感受?
徐冰:一開始并沒有,開始是希望融入西方。我帶去的很多舊作品,我都沒拿出來過。看上去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很具實驗性的藝術家,但事實上,現在回過頭來看,你不管怎樣“去身份化”,但是事實上,真正屬于你的,它總是在你的創作、思維線索中起作用。時間長了以后,這么多年在美國,真正的收獲,我覺得是對自己的文化真正有價值的部分有了認識,比過去更加珍惜它們。
《檢察風云》:我看西川和您的訪談里談到你的工作室像書房,是不是你的工作室里也放了很多書?
徐冰:我的工作室里書和畫冊特別多,而且各種文件資料都在那里堆著,空間其實不是很大,給人的感覺不像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室。我做的東西非常多,而且這些作品很少能在工作室完成,它們有的要焊接,有的要裝玻璃,有時候需要印刷,工作室不可能有這樣的條件。我們在工作室做各種實驗和設計,再找到合適的工廠和專門的部門來加工。工作室是一個思維的環境。
《檢察風云》:后來又是怎么回國并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職務的呢?
徐冰:中央美術學院聘任我,我就回來了。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新的進程和變化吸引了我,使我看到了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實驗性,以及其他地區沒有的特殊性。我在美國待了18年,作為獨立藝術家在世界各地做展覽,一直是以一種非常獨立的狀態存在的,回國以后情況不同了。我其實比較喜歡這種遷移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讓我過去的經驗變得更加清晰,反差會對人的思維空間有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