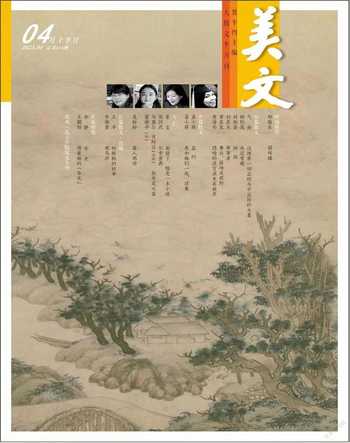鴻儒白詩(shī)朗

何云燕 壯族,廣西天等人,文學(xué)博士。廣西民族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副教授。2012-2013年美國(guó)波士頓大學(xué)“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訪問(wèn)研究員,2016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jì)念館(Yad Vashem)訪學(xué)學(xué)者,2018-2019年英國(guó)劍橋大學(xué)訪問(wèn)學(xué)者,曾發(fā)表數(shù)篇散文作品。
一
歷史上,特別是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學(xué)術(shù)思想界曾經(jīng)有過(guò)非常著名的“波士頓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當(dāng)年生活工作在美國(guó)波士頓學(xué)界的三個(gè)人:哈佛大學(xué)的杜維明,波士頓大學(xué)的南樂(lè)山(Robert C. Neville)和白詩(shī)朗(John H. Berthrong)。當(dāng)時(shí)南樂(lè)山任波士頓大學(xué)神學(xué)院的院長(zhǎng),白詩(shī)朗是副院長(zhǎng)。不少人將曾長(zhǎng)期執(zhí)教于美國(guó)夏威夷大學(xué)、近些年活躍于海外漢學(xué)界并受聘為北京大學(xué)人文講席教授的安樂(lè)哲(Roger T. Ames)誤稱為“波士頓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和代表,大概源于他和南樂(lè)山的中文名字中都有一個(gè)“樂(lè)”字,還有一個(gè)可能的原因是因?yàn)榘矘?lè)哲現(xiàn)任世界儒學(xué)文化研究聯(lián)合會(huì)會(huì)長(zhǎng)、國(guó)際儒聯(lián)副主席,這個(gè)身份容易與“波士頓儒家”的“儒”字重疊而令人產(chǎn)生聯(lián)想。
說(shuō)到誤解,可能國(guó)內(nèi)很多人對(duì)“神學(xué)院”也多有誤解,往往一聽(tīng)“神學(xué)院”就會(huì)聯(lián)想到教會(huì)和修道院之類教牧和修道場(chǎng)所,這樣的認(rèn)識(shí)主要是受到過(guò)往一些文學(xué)作品或電影作品的影響。的確,最初的神學(xué)院是教會(huì)設(shè)立的,但最初的大學(xué)、醫(yī)院也都是與教會(huì)有關(guān)的,很多大學(xué)、醫(yī)院都是教會(huì)設(shè)立的,而且與國(guó)內(nèi)大學(xué)、科研和醫(yī)療機(jī)構(gòu)等廣泛開(kāi)展合作交流,關(guān)系非常密切。比如,美國(guó)威廉瑪麗學(xué)院,泰國(guó)易三倉(cāng)大學(xué),意大利米蘭圣心天主教大學(xué),等等。簡(jiǎn)單講,如今國(guó)外的神學(xué)院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獨(dú)立于大學(xué)之外的神學(xué)院;另一類是與綜合性大學(xué)一體的神學(xué)院。前者如美國(guó)戈登康威爾神學(xué)院、紐約神學(xué)院、普林斯頓神學(xué)院等,后者如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神學(xué)院、耶魯大學(xué)神學(xué)院、波士頓大學(xué)神學(xué)院以及英國(guó)牛津大學(xué)、劍橋大學(xué)的神學(xué)院等。前者主要培養(yǎng)教牧人士,與綜合性大學(xué)的關(guān)系有的疏遠(yuǎn)有的親密;后者主要培養(yǎng)與人文宗教及社會(huì)科學(xué)相關(guān)的研究型人才,學(xué)科方向設(shè)置與大學(xué)其他院、系、所類似,遵循同一模式。這種情況下,前者和后者的關(guān)系也是有的疏遠(yuǎn)有的親密,這主要取決于前者的態(tài)度和傾向,比如許多較為保守的獨(dú)立神學(xué)院就認(rèn)為哈佛大學(xué)、耶魯大學(xué)的神學(xué)院過(guò)于自由和世俗化。其實(shí)中國(guó)國(guó)內(nèi)情況也大致類似,為教會(huì)培養(yǎng)教牧人員的獨(dú)立神學(xué)院如北京的燕京神哲學(xué)院(天主教)、燕京神學(xué)院(基督新教),南京的金陵神學(xué)院等;與之相應(yīng),伊斯蘭教有自己的經(jīng)學(xué)院;佛寺則有佛學(xué)院,等等。而國(guó)內(nèi)高校則沒(méi)有神學(xué)院,卻有類似于宗教文化研究院的相關(guān)機(jī)構(gòu),這些機(jī)構(gòu)除了不培養(yǎng)教牧人士之外,其基本功能跟國(guó)外與大學(xué)一體的神學(xué)院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功能相當(dāng)。
所以,盡管白詩(shī)朗長(zhǎng)期執(zhí)教于神學(xué)院并榮任副院長(zhǎng),但實(shí)際上他是一位學(xué)者,一位儒家學(xué)者,或者說(shuō)是一位海外漢學(xué)家,一位鴻儒。可以以他出版的著作為證:《普天之下:儒耶對(duì)話中的典范轉(zhuǎn)化》(1994)《論創(chuàng)造性:朱熹、懷特海和南樂(lè)山比較研究》(1998)《儒家之道的轉(zhuǎn)化》(1998)《簡(jiǎn)明儒學(xué)導(dǎo)論》(2000)《過(guò)程的擴(kuò)展:中西方哲學(xué)與神學(xué)轉(zhuǎn)化的探索》(2008)等等。當(dāng)然,白詩(shī)朗的學(xué)術(shù)著作遠(yuǎn)遠(yuǎn)不止這些。2011年初,白詩(shī)朗在將受聘為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客座教授前,曾提供給該校一份長(zhǎng)達(dá)25頁(yè)的簡(jiǎn)歷,其中主要列述了自己的教育背景,所受獎(jiǎng)勵(lì),學(xué)術(shù)著作和學(xué)術(shù)論文清單等,均與海外漢學(xué)、中國(guó)學(xué)密切相關(guān)。這次來(lái)華訪問(wèn),應(yīng)該是白詩(shī)朗在2010年9月應(yīng)邀參加第一屆世界尼山論壇會(huì)議后,緊接著再次來(lái)華與中國(guó)大陸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學(xué)者近距離大范圍地接觸。
白詩(shī)朗生于1946年3月美國(guó)威斯康星,于美國(guó)堪薩斯大學(xué)獲得學(xué)士學(xué)位,研究方向是中文和哲學(xué);后于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獲得碩士和博士學(xué)位,研究方向分別為中國(guó)哲學(xué)中的道家和宋代新儒家。經(jīng)歷了完整、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之后,白詩(shī)朗一直從事著與中國(guó)哲學(xué)有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事業(yè),直到2022年8月在加拿大去世。
二
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宗教學(xué)專業(yè)留校任教的教師,應(yīng)邀到美國(guó)夏威夷大學(xué)參加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當(dāng)他看到參會(huì)者當(dāng)中有不少在讀博士生,非常活躍地發(fā)言、點(diǎn)評(píng)和主持會(huì)議主辦方安排的小組討論時(shí),很受吸引和鼓舞,隨即萌生了到美國(guó)讀博士的愿望。于是,他向前來(lái)參會(huì)的一位美國(guó)學(xué)者詢問(wèn)申請(qǐng)到美國(guó)讀博士的途徑,這位美國(guó)學(xué)者就推薦了當(dāng)時(shí)并未出席這次會(huì)議的白詩(shī)朗,并留下了白詩(shī)朗的聯(lián)系方式。北京大學(xué)這位教師會(huì)后給白詩(shī)朗寫(xiě)信表達(dá)了自己的愿望,很快即收到白詩(shī)朗的回信。回信表示愿意接受這位北大教師赴美跟隨自己攻讀博士,并詳細(xì)介紹了申請(qǐng)、簽證、赴美和入學(xué)程序。當(dāng)年,北大教師順利入讀波士頓大學(xué)跟隨白詩(shī)朗攻讀博士學(xué)位并于1992年畢業(yè)獲博士學(xué)位。在讀和畢業(yè)之后,他均受到白詩(shī)朗先生多方面幫助和鼓勵(lì)。那個(gè)時(shí)候,美國(guó)學(xué)習(xí)中文的人很少,但波士頓大學(xué)卻有專門印有漢字校名的文化衫,白詩(shī)朗先生專門買來(lái)送給北大教師,他很自豪地穿上在校園向大家“炫耀”,至今仍保留著作為美好紀(jì)念。
經(jīng)這位北大教師介紹和推薦,白詩(shī)朗在二十世紀(jì)末10年和本世紀(jì)初10年的20年間,陸續(xù)邀請(qǐng)并支持國(guó)內(nèi)十幾位學(xué)者赴波士頓大學(xué)學(xué)習(xí)和訪問(wèn),有的是讀博士學(xué)位,有的是作訪問(wèn)學(xué)者。一位清華大學(xué)的學(xué)者在讀書(shū)年代學(xué)習(xí)的外語(yǔ)是德語(yǔ),在她拿到邀請(qǐng)前往美國(guó)駐華大使館簽證時(shí),美國(guó)簽證官發(fā)現(xiàn)她英語(yǔ)交流有困難,就用中文問(wèn)她到美國(guó)后如何克服語(yǔ)言上的障礙時(shí),她跟對(duì)方講述了“波士頓儒家”的“故事”,簽證官很高興地就批準(zhǔn)了她的申請(qǐng)。
2011年11月中下旬,受聘為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客座教授舉行儀式時(shí),白詩(shī)朗應(yīng)時(shí)任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研究生院執(zhí)行院長(zhǎng)張華教授邀請(qǐng)到北京進(jìn)行了為期一周的講學(xué)、訪問(wèn),學(xué)校還專門舉辦了“儒學(xué)傳習(xí)與中西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白詩(shī)朗先生講授了他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與西方文化對(duì)話的經(jīng)歷與思考,分享了許多中西人文學(xué)術(shù)交流的心得。也是在這次活動(dòng)中,白詩(shī)朗答應(yīng)從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接收幾位在讀博士到波士頓大學(xué)進(jìn)行聯(lián)合培養(yǎng),首批共三位,王雅鴿、娜仁格日勒和我。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國(guó)內(nèi)外研究生聯(lián)合培養(yǎng)基地2009年掛牌以來(lái),支持舉辦了眾多碩士博士參加的赴外國(guó)際會(huì)議和碩士層面的聯(lián)合培養(yǎng)項(xiàng)目,我們這一批是一次派出博士最多的。白詩(shī)朗先生此前接收過(guò)不少來(lái)自中國(guó)大陸的訪問(wèn)學(xué)者,但同時(shí)接收多位博士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訪問(wèn)學(xué)生”還是第一次。
因?yàn)榧磳⒁ゲㄊ款D大學(xué)參加“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項(xiàng)目的訪學(xué),我有幸作為白詩(shī)朗教授北京之行的陪同翻譯。白詩(shī)朗到北京后第一站探訪之地是五道口邊上的萬(wàn)圣書(shū)店。彼時(shí)我是一個(gè)初入京城的壯族女子,對(duì)偌大的北京還不是很熟悉。白詩(shī)朗教授熟門熟路地步行把我?guī)У饺f(wàn)圣書(shū)店。路上他一直跟我強(qiáng)調(diào),萬(wàn)圣書(shū)店在很多中外學(xué)者中頗具名氣,之前他的朋友也帶他來(lái)過(guò)幾次。有一次美國(guó)東西海岸的幾位儒學(xué)學(xué)者到孔子故里曲阜開(kāi)會(huì),還專門停留在北京一日,為的就是到萬(wàn)圣書(shū)店找中國(guó)學(xué)者的最新儒學(xué)研究成果。“可見(jiàn)萬(wàn)圣書(shū)店多么了不起!”白詩(shī)朗不禁感嘆。聽(tīng)罷,我對(duì)北京作為中國(guó)政治與文化中心的好感倍增。
到了萬(wàn)圣書(shū)店,白詩(shī)朗很認(rèn)真地找尋他曾經(jīng)坐過(guò)的位置,并找到那個(gè)最喜歡的靠墻座位,坐下來(lái)打開(kāi)電腦,然后一臉俏皮地輕聲告訴我:“每次我們來(lái)總是有人盯著我們看,中國(guó)人對(duì)外國(guó)人來(lái)北京書(shū)店可能是比較好奇,可能是怕我們做壞事。但是我可是好人哦!為了避免尷尬,我就躲在這角落里,這樣就不太容易引起別人注意了。但不是每次來(lái)都能遇上這個(gè)角落空著。如果有人坐著,我就希望他或她能快點(diǎn)走。今天沒(méi)有人跟我搶這個(gè)座位,我真是太高興了,能請(qǐng)你陪我一起坐下來(lái)看書(shū)嗎?我想整理一下明天的講座稿。”邊說(shuō)邊露出憨憨的笑容。沒(méi)有想到一個(gè)國(guó)際大學(xué)者竟然這么平易近人,讓我初見(jiàn)他的緊張情緒一下就放松了。
接下來(lái)的數(shù)日,除了在北語(yǔ)做講座和開(kāi)會(huì),我還陪同白詩(shī)朗走訪了清華、北大,并有幸見(jiàn)到了剛剛從哈佛大學(xué)回國(guó)到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擔(dān)任院長(zhǎng)的杜維明先生。赫赫有名的杜維明先生攜家人和同事宴請(qǐng)了白詩(shī)朗,并專門為他點(diǎn)了烤鴨。白詩(shī)朗像孩子一樣,饒有興趣地看著廚師在餐桌邊上切鴨肉薄片,又興致勃勃、略帶笨拙地自己用面皮卷烤鴨片,然后很自豪很滿足地品嘗起來(lái)。我們所到之處,只要有孔子像,他就會(huì)挨著站,像中小學(xué)生一樣挺直腰、雙手合于腹前,神情莊重地跟孔子像合影。白詩(shī)朗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喜愛(ài)是溢于言表的,更是根植于內(nèi)心的。他總是不遺余力地尋找時(shí)機(jī)推動(dòng)、促成中美學(xué)者尤其是中美青年學(xué)子的交流與合作。
在短暫的相處中,我對(duì)這個(gè)即將成為我“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項(xiàng)目”的外方導(dǎo)師充滿了敬意,也消除了我人生中首次出國(guó)學(xué)習(xí)的諸多憂慮。我最難忘的是我們那次在圓明園迷路的“事故”。由于那時(shí)我們都還沒(méi)有智能手機(jī),我只能靠地圖和問(wèn)行人來(lái)確定路線,結(jié)果陰差陽(yáng)錯(cuò)繞了很遠(yuǎn)的路。本來(lái)腿上有舊傷的白詩(shī)朗在半道上突然扭到了腳,加之他身材比較高大、年歲稍高,使得他走路變得艱難了起來(lái)。眼見(jiàn)天色漸暗,路上行人稀少,找不到任何援助,我急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他看出了我的焦急和恐懼,不停地安慰我,還特地講了很多故事和笑話,硬撐著走了很久。到達(dá)目的地之后,見(jiàn)到了他的朋友和學(xué)生,他哈哈大笑,說(shuō)看到我急得快哭了,讓大家不要責(zé)備我。后來(lái)我們到了美國(guó),他也不忘記時(shí)不時(shí)拿這事來(lái)調(diào)侃我。
三
白詩(shī)朗對(duì)學(xué)生的關(guān)愛(ài)是頗具中國(guó)傳統(tǒng)風(fēng)范的。王雅鴿、娜仁格日勒和我沒(méi)有到波士頓之前,就介紹他的幾個(gè)中國(guó)學(xué)生給我們認(rèn)識(shí),希望她們協(xié)助我們租房。等我們搭乘飛機(jī)過(guò)來(lái)的時(shí)候,他考慮到我們?nèi)松夭皇欤瑢iT請(qǐng)一個(gè)中國(guó)來(lái)的博士生到機(jī)場(chǎng)迎接我們,把我們帶到預(yù)定好的住地。他說(shuō)是因?yàn)椴ㄊ款D的公交系統(tǒng)不發(fā)達(dá),出行基本靠貫通大波士頓區(qū)的鐵路,但是鐵路系統(tǒng)又比較復(fù)雜,擔(dān)心我們拿著沉重的行李走迷路。得知我們順利到達(dá)并安頓好之后,他專門在辦公室等我們,為我們大致介紹了波士頓大學(xué)(BU)的基本情況,并為我們引見(jiàn)了兩三位老師,歡迎我們?nèi)ヂ?tīng)他們的課。
隨后他開(kāi)車帶我們到波士頓學(xué)院(BC)參加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希望我們?cè)缛杖谌氩ㄊ款D的學(xué)術(shù)研究環(huán)境。路上,他告訴我們,波士頓學(xué)院雖然名稱是“學(xué)院”但是其排名在很多方面比波士頓大學(xué)強(qiáng);波士頓大學(xué)和哈佛大學(xué)、麻省理工隔著一條查爾斯河,我們有機(jī)會(huì)也可以去對(duì)面的大學(xué)看看,如果需要去旁聽(tīng),可以寫(xiě)信去問(wèn)問(wèn)任課的老師,得到允許之后就可以去了。“大部分美國(guó)人都很熱情大方的,你們直接問(wèn)就好,很多人喜歡自己的思想和知識(shí)被別人認(rèn)可。就算有老師拒絕你們,那也沒(méi)有關(guān)系,大波士頓區(qū)好的大學(xué)和老師多得很。還有中國(guó)學(xué)者云集的燕京學(xué)社,那里有很多中美文化交流活動(dòng)和會(huì)議。” 臨了還教我們用波士頓口音讀“Boston”,并不忘戲謔美國(guó)各地口音的巨大差異。白詩(shī)朗就是這樣,總是提供給我們希望和動(dòng)力,鼓勵(lì)我們積極樂(lè)觀應(yīng)對(duì)機(jī)會(huì)和挑戰(zhàn),給我們示范如何輕松幽默地面對(duì)各式各樣的境況。
我們到達(dá)波士頓兩個(gè)月之后,美國(guó)的大學(xué)基本進(jìn)入漫長(zhǎng)的暑假,意味著接下來(lái)的兩三個(gè)月就沒(méi)有課可以去旁聽(tīng)了。白詩(shī)朗帶著幾個(gè)波士頓大學(xué)的碩博研究生開(kāi)起了一門課,讓我們都去旁聽(tīng)并參與討論。我們到了之后發(fā)現(xiàn),除了一個(gè)年近60的白人女博士生,其余基本都是中國(guó)人。他指導(dǎo)的一個(gè)中國(guó)碩士生跟我比較熟悉,她悄悄地告訴我,美國(guó)教授幾乎沒(méi)有人用自己的假期補(bǔ)課、開(kāi)課的,白詩(shī)朗很明顯是專門為了你們仨才暑假開(kāi)班的。聽(tīng)罷我很感動(dòng),下課之后趁著沒(méi)人在旁邊就此問(wèn)他,他沒(méi)有直接回答而是說(shuō):“你們?nèi)绻蔷旁路萜鹗迹涂梢耘月?tīng)很多課。四月份到就很快遇上暑假,有點(diǎn)可惜,因?yàn)槟銈儾庞惺畟€(gè)月的時(shí)間。但你們也不得不考慮中國(guó)那邊的學(xué)習(xí)期,早來(lái)就可能早點(diǎn)拿到博士學(xué)位。”我說(shuō),少聽(tīng)課沒(méi)有關(guān)系,放假我也正好可以全天泡圖書(shū)館,因?yàn)槲覀兌奸_(kāi)題了,可以充分利用波士頓大學(xué)圖書(shū)館收集博士論文材料、撰寫(xiě)初稿。當(dāng)他得知我對(duì)波士頓大學(xué)圖書(shū)館的圖書(shū)編排和開(kāi)放安排很滿意時(shí),喜笑顏開(kāi)。
在美國(guó)教授一般很少跟學(xué)生到飯館聚餐,但是為了照顧我們的風(fēng)俗習(xí)慣,白詩(shī)朗每隔一段時(shí)間就利用中午陪我們到中餐館吃簡(jiǎn)餐。美國(guó)中餐館有一個(gè)不成文的習(xí)俗,就是給每個(gè)到來(lái)的客人一個(gè)福餅(fortune cookie,也稱幸運(yùn)餅干或簽語(yǔ)餅),即菱角狀的小脆餅,里面有一條小紙片,印著一句溫暖美好的話。白詩(shī)朗經(jīng)常跟著我們興高采烈地拆福餅,輪流讀出自己得到的吉言良語(yǔ),在歡喜中相互開(kāi)玩笑。另一個(gè)有趣的事是,每次白詩(shī)朗跟我們出現(xiàn)在公共場(chǎng)所的大門前,我們幾個(gè)女生中總有人習(xí)慣性地?fù)屩退_(kāi)門,他基本是順從地配合通行并表示感謝。這樣的情形在美國(guó)很容易引來(lái)異樣的目光,他就會(huì)訕訕一笑,然后向周圍人解釋:幫忙開(kāi)門是中國(guó)人表示尊重的一種方式,無(wú)論男女,這是中國(guó)的一種禮儀。
無(wú)論在哪里,白詩(shī)朗總竭力給予我們最大的扶助、理解和包容。遇到這樣的老師,我們都深感幸運(yùn)。文章標(biāo)題用“鴻儒”一詞,來(lái)自我和老師們?cè)趫A明園風(fēng)和樓的一次聚會(huì),餐廳正中的匾額上清人所書(shū)“鴻儒”兩個(gè)大字。白詩(shī)朗乃一代異國(guó)“鴻儒”,言傳身教讓我們體悟到什么是儒學(xué)、什么是儒者。我把自己對(duì)儒學(xué)的跨文化傳播與接受寫(xiě)進(jìn)了對(duì)美國(guó)經(jīng)典作家梭羅的研究之中。2014年我博士論文答辯通過(guò)之后,彼時(shí)還在清華任教的王寧教授感慨地對(duì)我說(shuō):幸虧你去一趟波士頓,受波士頓儒學(xué)的熏陶,要不然這論文你沒(méi)有辦法寫(xiě)好。我誠(chéng)懇地點(diǎn)頭贊同,想起白詩(shī)朗親筆簽名送給我的幾本書(shū)。
2013年初回國(guó)之后我再也沒(méi)有跟白詩(shī)朗見(jiàn)過(guò)面,但是一直保持通訊聯(lián)絡(luò)。2018年我到英國(guó)劍橋大學(xué)訪學(xué),在網(wǎng)絡(luò)上跟他匯報(bào)了在英的學(xué)習(xí)情況。他告訴我,他退休之后離開(kāi)了波士頓,搬到加拿大的溫哥華。疫情期間我給他發(fā)過(guò)問(wèn)候電子郵件,但是不知何故沒(méi)有收到回復(fù)。疫情還沒(méi)有消散他就去了天國(guó)。
想起白詩(shī)朗先生,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會(huì)深深印刻在腦海里的,至少兩點(diǎn):一是他對(duì)學(xué)術(shù)的認(rèn)真執(zhí)著態(tài)度。他對(duì)神學(xué)研究是如此,對(duì)儒學(xué)研究是如此。這儼然已經(jīng)化成他的個(gè)人風(fēng)格。做一件事,就堅(jiān)定不移地去做,去做好。二是他的儒雅和豁達(dá)的性格。一想到白詩(shī)朗先生,腦海里就出現(xiàn)他溫暖的笑和幽默的話語(yǔ)。在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面前,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diǎn)。他愛(ài)智慧,保持包容、博大的胸懷。和南樂(lè)山一樣致力于探尋全球現(xiàn)代思想的豐富資源,世界多元主義的支持者。中美學(xué)界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是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重要力量。白詩(shī)朗先生離開(kāi)我們遠(yuǎn)行了,我們會(huì)認(rèn)真讀他的書(shū),永久懷念他。只要有書(shū)在,他就是常留在我們身邊。
(責(zé)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