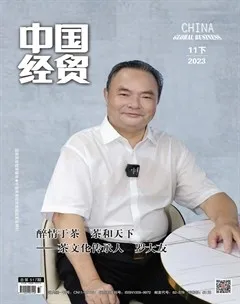中國地區飲食失調的理論探索及治療新方法
陳琳 劉小青 王欣
飲食失調是一種異常的飲食習慣和食物成癮,嚴重損害心理生理健康的一種精神疾病。近五年飲食失調的發病率在我國城鎮地區不斷上升,心理治療需求也在不斷擴大。本綜述的主要目的是結合認知行為理論對于疾病的患病機制的解釋,探索飲食失調治療的新方法認知行為的音樂療法和音樂治療飲食障礙的相關技術。
飲食失調是一種嚴重影響心理、身體健康或功能的飲食模式(DSM-5,2013)。根據上海精神衛生中心(SMHC)的臨床記錄,在過去五年中,門診病人中患有飲食失調的人口幾乎翻了一番(Chen et.al.,2021)。然而,中國對飲食失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 (Lau et al., 2006; Lee et al., 2003; Lee et al., 1998; Leung et al., 2004),可能是因為飲食失調更常見于中等高收入的發達國家,而中國的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這表明對該疾病的研究和關注嚴重不足。
關于飲食失調的患病機制,目前認知行為理論被廣泛接受,根據這一理論,還發展了認知行為療法(CBT)用于飲食失調的治療。然而,關于CBT治療飲食失調的有效性,研究者們得出了矛盾的結論。Gro Trondalen(2016)提出了飲食失調音樂治療的理論框架,該治療方法基于心理治療和認知主義取向,將音樂視為連接內在世界和外部客體的橋梁,建議音樂可以幫助飲食失調患者探索個人潛能。因此,認知行為音樂治療(CBMT)技術也被應用于飲食失調的臨床治療中。
飲食失調
根據2013年第五版美國精神學會的定義,飲食失調是一種進食或進食相關行為的持續障礙,它會導致食物攝入或吸收的改變,并嚴重損害身體健康或心理社會功能。DSM-V將飲食障礙分為異食癖、反芻障礙、回避或限制性飲食障礙(ARFID)、神經性厭食癥(AN)、神經性貪食癥(BN)、暴食癥(BED)和其他特定的飲食失調(OSFED)(APA, 2013)。異食癖和反芻障礙出現在生命的早期階段,此外,非典型性飲食障礙(UFED)適用于飲食失調的特征性癥狀為主的表現,會導致臨床上顯著的痛苦或社會、職業等其他重要功能的損害,但不符合任何疾病的全部標準。飲食失調在一些研究中被定義為神經性厭食癥和貪食癥的總和,在其他研究中被定義為神經性厭食癥、貪食癥和未被分類的飲食失調的總和。未被分類的飲食失調(EDNOS)是DSM-IV(APA,2000)中總結出來在DSM-V被刪除,以更加細致的劃分取而代之,比如被劃分在EDNOS中的暴食癥就在DSM-V中被列為重要的飲食失調類別。
中國城鎮地區的發病率 根據DSM-V,回避或限制性飲食在男女比例中的發生率接近,智力障礙、自閉癥、焦慮癥、抑郁癥患者為易感人群。厭食癥的發病率約為0.4%,死亡率為5%,臨床上男女的發生比率為10:1,而在貪食癥患者中這一比例正好相反。貪食癥的女性發病率為1%-1.5%,青少年晚期和青年早期是貪食癥的高發期。暴食癥通常發生在18對以上的人群,女性和男性的發病率分別為1.6%和0.8%,暴食癥存在種族和民族特征,研究發現尋求減肥的白人女性更易發現暴食癥。
全球報告的飲食失調的患病率各不相同,從 2012 年的 0.1% 到 2013 年的 3.8% 不等(Qian et al.,2013)。2012年調查顯示,飲食失調在我國各類精神疾病中占0.1%,其中青少年和大學生是最常見的飲食失調診斷人員,大學中飲食失調的患病率為 3.3%(Liang et al.,2008)。
患病的機制研究
認知行為理論 認知行為理論起源于1986年的構想 (Fairburn, Cooper, & Cooper, 1986),最初的構想認為特定進食行為的發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為了改變目前的情緒狀態,暴食行為對情緒調節起到了中和作用,使患者短暫地擺脫困境,得到了強化(Fairburn, Cooper, & Cooper, 1986)。認知行為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貪食癥(bulimia nervosa)的維持機制,一方面該理論認為自我評價系統的失衡是維持貪食癥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人對于自身的評價來源于生活領域感知到的表現,比如工作、社會和家庭關系等,而飲食失調的人評價自身很大程度或者獨一無二的取決于他們的飲食習慣、身材體重以及他們控制這些的能力(Fairburn et al., 2003)。這也讓患者更容易陷入暴食中,然后再進行嚴格的控制,以此來減少暴食造成的體重增加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此,認知行為理論認為,對飲食、身材、體重以及自控力的過度評價是持續性暴食的重要因素。神經性貪食癥的臨床特征包括嚴格的體重控制,比如食物攝入、自我催吐、濫用輕瀉劑和利尿劑以及過度鍛煉,多種形式的身型檢查或回避直視身體,大腦充斥著關于被體重、身材食物的想法。這些臨床特征被理解為源于“核心精神病理學”(core psychopathology)(Fairburn et al., 2003)。認知行為理論還認為暴食癥(binge eating)是摒棄實際攝入熱量赤字的一種特殊形式飲食控制,是一種極端的、獨特的日常飲食規則。自控力的缺乏也使得暴食癥患者對于這種病態進食規則的消極抵抗,所以暫時摒棄節食模式以暴飲暴食取代,并表現為對自己控制進食、體型體重能力的懷疑 (Fairburn et al., 2003)。另一方面,清除(purging)如自發的嘔吐行為和濫用瀉藥、利尿劑是一種補償行為,也是神經性貪食、暴食癥的維持機制。患者相信通過清除可以減少體重增加從而低估暴食帶來的后果。除此之外,患者有著一套極端的自我評價系統,他們會設置嚴苛的標準并通過進食、 身材、體重和自我控制來評估自己的成敗,如果沒有達到設置的標準,則將錯誤歸咎于自身的失敗而他們設置的嚴格的標準。
認知行為療法由(Fairburn, 1981)第一次提出,該理論認為,病態的完美主義傾向(clinical perfectionism),核心低自尊(core low self-esteem),情緒縱容(mood tolerance),人際交往困難(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是維持神經性貪食癥的四個主要機制。進一步來說,這四種維持機制可以概括為,神經性貪食癥患者的自我評價和自我價值取決于為之奮斗的目標和是否取得想要的成果,無論客觀原則和外部環境的艱巨,這種自我評價不是簡單的對自己無法控制進食、身材體重的消極評價,而是對自己所有品質的無條件的永久的消極評價,這使得患者無法正確處理特定的情緒狀態,例如抑郁、焦慮等,形成“情緒調節行為的功能性失調”(dysfunctional mood modulatory behaviour),此外,外部環境對與身材的壓力和家庭中患有飲食失調的人會造成人際困難,從而維持對于進食、身材體重的病態控制。
治療方法新探索
認知行為音樂療法治療飲食失調 認知行為理論解釋了飲食失調的患病機制,認知行為療法也被廣泛使用。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有一家專門為飲食失調女性提供住院治療的醫院開展了認知行為音樂療法(CBMT)。認知行為音樂療法的技術包括唱歌、打鼓、歌詞分析、音樂創作,治療目標集中在三個層面:行為問題、認知扭曲和飲食失調的根本原因 (Hilliard, 2001)。同樣的,Bonilin(2006)認為音樂治療的主要目標是提供情緒表達的出口和增加認知功能,包括形成對飲食失調的認識,洞察潛在風險和由他們引起的問題,并識別扭曲的過程。使用認知行為音樂療法治療是一個三階段的連續過程,在治療的初級階段,針對由于排斥治療產生的壓力,Justice (1994)建議,音樂強化的放松技術放在飯后音樂治療小組中使用,可以幫助轉移飲食失調者的強迫性想法。結構性的即興作曲,包括預先準備好促進即興創作的鋼琴音階和和聲進行,在初級階段也可以幫助客戶建立安全、自由表達的環境,并且可以通過回聲模仿、增加或減少節奏的型,對主題進行和聲,使用音樂主題進行對話的方式將病人的音樂反應作為一種評估手(Nolan,1989)。
再教育階段的目標是對飲食失調造成的感覺和認知混亂進行辨別。(Hilliard, 2001)描述了使用歌曲討論的技巧治療飲食失調時的情況。治療師讓客戶將某一句歌詞與自己的想法聯系,歌詞可以投射他們的內心想法,并且間接的表達過程減少了緊張和焦慮感,在治療師的指導下,可以使他們聯系到與飲食失調相關的失控、焦慮和完美主義有關的不舒服的感覺。這一技術讓病人了解他們的心理病理學。
在治療飲食失調的康復階段,當事人對障礙背后的核心問題已經有了深刻的認識,并且致力于解決過去的人格發展沖突,重建新的人格結構(Goodsitt,1997)。Justice(1994)描述了在飲食失調的康復中可以使用音樂想象技術。
音樂放松和想象技術 邦尼引導想象和音樂法(Bonny Method of Guided Imagery and Music, GIM)是用于第一階段的有效技術,GIM通過使用音樂和語言交流,引導自我圖像的生成從而獲得無意識的信息,目的是幫助當事人獲得內省能力和洞察力,發現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案。GIM由Helen Bonny在1970年代創建,是一種以深度為導向的音樂心理治療方法,需要有資質的心理治療師施行。GIM的前提是音樂可以揭示意識領域,喚起意向,促進身心發展(Clark,2002),治療的過程從音樂輔助的深度放松過渡到改變當事人的意識狀態,為感覺、意向的產生做鋪墊,在體驗這兩種內在感受的同時聆聽預先選擇好的音樂,聆聽結束后,治療師幫助當事人回到普通的意識狀態,治療師通過經驗分享,在治療中發揮引導作用 (Bobilin, 2006)。
臨床即興創作技術 音樂治療中的臨床即興創作是在治療環境中運用音樂基本要素、樂器等使參與者進行音樂創作(Wigram ,2004)。在音樂治療文獻中,大多數案例研究使用心理動力學理論框架討論了即興創作作為飲食障礙患者的干預措施。但是也有研究者采用自由創作策略的結構化經驗對飲食失調進行探索,這種方法允許每個人根據他們各自選擇的樂器進行自由地即興創作,樂器的選擇可以投射他們的情緒。正如Bauer (2010)指出,患有神經性貪食癥的人喜歡用木管或鋼琴上演奏響亮而刺耳聲音的音樂,治療師將此解讀為患者尋求關注的一種的內在聲音并且可能夾雜著憤怒和失望。
即興創作在治療方面的時間維度影響治療效果,由于飲食失調患者有著不穩定的自尊和完美主義傾向,隨著治療時間的推移,對內在感覺的音樂探索會提高與由于飲食失調引起的情緒問題,加強對身心聯系的認識 (Trondalen & Sk?rderud, 2007),并且即興音樂創作沒有正誤帶給他們一種掌控感,這對于恢復完美主義傾向具有積極作用 (McFerran & Heiderscheit, 2016)。此外,即興創作可以作為交流個人信息、增強情緒和飲食失調患者獲得肯定的方法 (McFerran & Heiderscheit, 2016)。
歌曲討論技術 對歌詞的意義探索和音樂要素,如音調、節奏的解讀可以稱為音樂治療中的歌曲討論。 Gardstrom和Hiller(2010)在飲食失調的治療中,將歌曲討論作為一種投射方法提出,認為音樂治療師根據突發事件、治療階段和心理過程與客戶一起聆聽預先選定的曲目,然后討論歌曲意義和與客戶生活的相關性 (Gardstrom & Hiller, 2010)。激發被飲食失調壓抑的情緒反應,歌曲的選擇至關重要。討論完全陌生的歌曲需要專注力,這種專注可以幫助提高客戶在治療過程中的意識和參與(Punch, 2016)。
歌曲討論可以喚起飲食失調者的口頭表達,這是減少患者對于不斷壓抑的痛苦記憶帶來的不健康的應對機制的一種方式,從而減少飲食障礙患者需要共同面對的焦慮問題 (Susanne, 2010)。正如音樂治療目標是讓飲食失調患者學會以健康而不是破壞性的方式應對憂慮或壓力(Justice, 1994)。歌曲討論作為一種表達性的治療方式,作為連接進食后出現的負性情緒,可以安排在飯后進行。所以說,歌曲討論提供了一種間接途徑用來表達和投射焦慮、恐懼和消極情緒(Pasiali et al., 2020; (Gardstrom & Hiller, 2010)。例如,研究者使用被試喜歡的音樂作為歌曲討論的材料,并在歌曲討論的音樂治療后測量了飲食失調者餐后的焦慮水平,結果表明焦慮情緒有了明顯好轉 (Bibb et al., 2019),證實了歌曲討論可以減少飲食失調者焦慮的間接投射作用。
總結與展望
當前,中國地區飲食失調的研究和治療仍存在一些挑戰。盡管飲食失調在中國的患病人數呈增長趨勢,但對其患病機制的認識尚不明確。認知行為理論在飲食失調治療中被廣泛應用,但對其有效性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因此,建立更準確的飲食失調患病機制模型,并開發創新的治療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未來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中國地區飲食失調的患病機制,例如考慮文化、社會和心理因素的綜合影響。此外,還可以通過整合跨領域的研究成果,建立更為綜合的認知行為模型,以更好地解釋飲食失調的維持機制。
在治療方面,可以考慮引入音樂治療作為一種創新的方法。研究顯示,音樂治療在心理治療中具有潛力,并能夠幫助飲食失調患者探索個人潛能。因此,進一步研究飲食失調音樂治療的效果和應用范圍,將有助于提供新的治療選擇和改善患者的康復效果。
總之,深入探索中國地區飲食失調的患病機制,并發展創新的治療方法,對于提高飲食失調的診斷和治療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加深對該疾病的理解,并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干預措施,以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