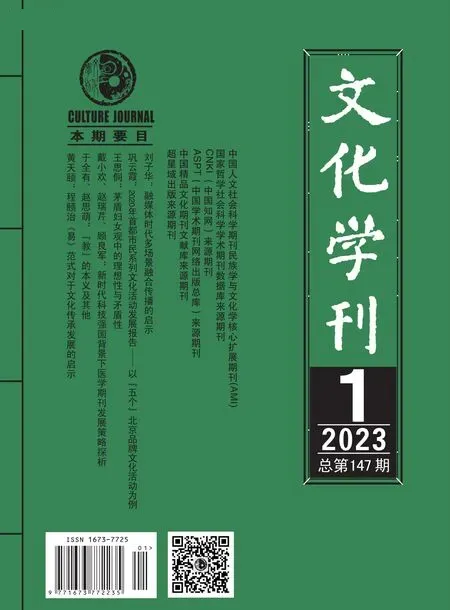吳冠中散文及張培基英譯版中模糊修辭的運用和翻譯賞析
汪 洋 王宏志
一、引言
運用模糊語言是文學作品的特點之一,散文作品亦是如此。中英文模糊修辭的研究與翻譯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吳冠中先生以精湛細膩的繪畫技巧和一生忘我的藝術探索精神,名震中外藝壇,在揮毫作畫之余又常提筆為文,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他的散文“洗練雋永、風格卓異,比許多名家的作品毫不遜色”(洛丁1995)[1]。張培基教授的譯著《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囊括了“五四”運動以來一大批杰出作家寓意深厚的作品,對西方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朱曼華2000)[2]。該譯著收錄了吳冠中若干篇散文,隨處可見模糊修辭的巧妙運用,塑造出一個特色鮮明的藝術世界,值得文學愛好者細細品味。而張培基教授對其散文的英譯本,語言自然流暢,尤其對原文本中模糊修辭的翻譯處理更是雅俗得當,力求保留原文的神韻,完美地再現了原文的藝術意境,堪稱我國文學作品外譯本的經典代表,更值得翻譯愛好者學習和模仿。通過對吳冠中先生散文中模糊修辭的梳理以及從語言差異、文化差異、效果對等角度賞析張培基英譯本中對模糊修辭的翻譯處理,以期總結相關的翻譯經驗,為進一步研究模糊修辭的翻譯方法,以及我國文學作品的外譯實踐奠定基礎。
美學意義上的模糊語言,是指“詞語具有朦朧而又廣遠的語義外延”(毛榮貴、范武邱 2005)[3]。散文旨在傳達作者的自我感悟,通過寫景、敘事等方式表達出自己的情感,在行文上往往運用大量的模糊語言,使不同范疇的事物產生亦此亦彼的關系,使本有瑕疵的事物得以遮丑藏拙而趨于完美,留以讀者無限的回味與遐想。韓慶玲(2006)指出:“模糊修辭指通過對語言系統固有的或是在語言特定組合關系中臨時產生的模糊性的利用,使言語的語義具有不確定性的語言應用活動。”她認為模糊修辭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常式模糊修辭及變式模糊修辭兩種。常式模糊修辭主要是指語言系統的固有模糊性,也可認為是詞語的模糊性,而變式模糊修辭主要關注語言在組合過程中產生的臨時模糊性[4]。簡言之,常式模糊修辭的研究對象是模糊詞語。模糊詞語的所指對象具有不確定性和外延性,這類詞通常是表示情感狀態、時段、色彩、數量等等。而變式模糊修辭中,句子模糊性并不是語言系統內固有的,而是使用修辭格使得言外有義,借代、比喻是這類修辭格的經典,用典、比擬、夸張等也屬于這類修辭現象。
二、 吳冠中散文模糊修辭的運用
吳冠中的散文風格自成一派,在面對任何風景時,總離不開畫家的本行。如《漁村十日》中“暮色昏黃了,天際緋紅了,海波蕩漾著紅的、紫的、烏藍的色塊,船的墨黑厚重的身影在壓迫這些色塊,畫家們說這是油畫。”[5]大量顏色范疇詞的運用體現出他對色彩豐富性的極致追求,塑造出幅五彩繽紛的海景落日圖。吳冠中筆下的顏色詞不僅用于描繪風景,更能用之敘寫自己的人生軌跡,如《三方凈土轉輪來:灰、白、黑》中“青年時期喜用淺灰色調,總覺人生灰暗苦澀;中年進入白色時期,白墻、雪峰、羊群皆是畫中常客;暮年跌入、投入了黑色時期,愛黑,強勁的黑,黑得強勁,黑是視覺刺激之頂點。”[6]74-75灰、白、黑三種色調分別對應吳冠中人生三個階段,即青年、中年和暮年,體現了他對顏色的感悟已深入骨髓。
吳冠中深受魯迅的影響,他的散文情感濃烈、簡練坦誠,在行文中往往使用借代的辭格抒發感情。如《哭》中“哭它太偉大了,哭老鷹的后代不會變成麻雀吧?[7]206”將“老鷹”指代為“實力雄厚的祖國”,將“麻雀”指代為“祖國的后代”,抒發了作者熱烈的愛國情懷以及對民族的深切憂患;《鴕鳥·孔雀·老鷹》中將“孔雀”指代為“可憐的女人”,暗諷了那些徒有其表而無其實的人。吳冠中的散文呈現激情豪放的風格,如《風光風情說烏江》中,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格,將“長江”和“烏江”分別比喻為“老虎”和“獵豹”,突出“烏江”流水湍急、驚濤駭浪,十分險峻。吳冠中也會在行文中借用典故,增強文章感染力,如《雪》中“東風梳弄柳絲,已是桃花季節,當屬虢國夫人游春的時光了”[6]139,借用“虢國夫人游春”的典故,委婉含蓄地表達出五月京郊百花山如詩 如畫的風光,正是觀賞桃花的好時機。這些描寫均屬于變式模糊修辭的范疇,作者將意圖蘊含在言辭之外,使言外有義,弦外有音,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語言藝術的魅力。
由于文化差異性,語言的模糊性往往給譯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擾。吳冠中的散文運用了豐富的模糊顏色詞和數量詞,委婉含蓄、余音裊裊;又巧妙地運用大量的辭格,塑造出模糊朦朧的藝術意境。張培基對于模糊語言有著深刻的見解和獨特的審美風格,又以高超的翻譯技巧保留原文的神韻,完美地再現了原文的藝術意境。下面就吳冠中散文中的幾個實例,探討張培基對于不同類型模糊修辭翻譯的獨特鮮明領悟。
三、常式模糊修辭的翻譯
(一) 模糊數量詞
數量詞作為一種數量文化,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英漢中都存在豐富的模糊數量詞,張培基對于模糊數量詞的翻譯策略也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了不同文化賦予數量詞的不同內涵。
1. 而她總離人群遠遠的,常盤旋于高空,遠看她只是短短的線之一劃。
原文中的模糊量詞“一劃”形容老鷹身手敏捷,像一根細線那般劃過天際。張培基抓住了其特點,采用以模糊譯模糊的翻譯策略,將“短短的線之一劃”譯為“disappear way up like a flash”[7]217-218,在贊嘆老鷹速度之快的同時,也為讀者營造出了朦朧模糊的意境,留以無限的遐想。
除此以外,吳冠中在散文里提及每一次能去上海的時間“多半是匆匆三五天,只有很少幾次是超過一星期的”。“多半”和“很少幾次”存在邊界不明的情況,張培基采用了以模糊譯模糊的翻譯策略,巧妙地將多半譯為“often”,將“很少幾次”譯為“seldom”,符合了英文簡潔精煉的特點,也使得譯句前后結構達到平衡。[8]175
(二) 模糊顏色詞
在漢英文化中,表示顏色的詞語都屬于模糊詞語。但由于文化的差異以及各國人民感受的不同,不同語言的顏色詞也深刻打著不同文化的烙印,這種差異性在漢英語言就得到充分的反映。
2. 灰褐色的老鷹從未意識到打扮自己的羽毛。
形容老鷹的“灰褐色”是一種中性色,有適中的暗淡和適度的淺灰,況且“灰色”屬于一個模糊集,還包括“淺灰、中灰和深灰”等等。“grayish”在英語中指的是“slightly gray in colour”,即“淺灰色”。張培基將“灰褐色”譯為“grayish brown”,既忠實地傳達出該模糊顏色詞的色彩特點,又保留了原文的模糊性。在另一處,“鬢發斑斑”指的是“斑白的頭發”,由于英語文化中有“白發”——“grey hair”的表達方式,故張培基將原文代表“斑白”的模糊顏色詞歸化為“grey”,使譯文更容易被讀者所接受。
翻譯模糊顏色詞時,既要在整體上把握并再現原文色彩,又要在細節上進行微觀調控。原文中的“香云紗”是一種珍貴的絲綢紡織品,傳統上的香云紗顏色深暗,張培基并沒有把“黑色的”直譯成“black”,而是將其巧妙地譯為“dark-colored”[8]175,表面上看似不如“black”忠實于原文,實則更加契合香云紗的顏色特點。
四、變式模糊修辭的翻譯
(一) 借代
借代(Metonymy) 是中英共有的修辭格,指不直接把所說的事物 (本體) 表達出來,而是用與之有聯系的事物 (借體) 來稱呼,突出事物的本質特征,增強語言的幽默性和感染力,以達到言在此意在彼的修辭效果。吳冠中的散文風格深受魯迅的影響,語言濃烈、豪放坦誠,通過對某個事物和某個事件的描寫以抒發自己的情懷。
1. 開始屠殺生靈了,屠殺自己的孩子……
這是吳冠中對于自己的某些劣畫曾招搖過市而感到不滿,于是下定決心毀掉所有不滿意的畫作。其關鍵的藝術效果,即將“屠殺生靈、屠殺孩子、刀下留人”等詞語指代“毀畫”,使得語言更加鏗鏘有力,也從側面表達出畫作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屠殺生靈”和“屠殺孩子”所指的是同一個動作,張培基采用了直譯,將其譯為“butcher my own babies”,單從這個句子看似不知所云,但后文的“problematic paintings”解釋了“babies”的所指[7]203,既忠實再現了原文的韻味,又使得語言表達更加簡約鮮明。原文句末“一次次淘汰、一次次刀下留人”反映出吳冠中在毀畫過程中矛盾的心情,其內容與前文的審查有所重復,故張培基采取了零翻譯的策略,降低了譯文的模糊性。
2. 她頭鉆進沙堆……人笑這是鴕鳥心態。
委婉曲折是漢語的特色,其中“鴕鳥心態”喻指逃避現實的心理,亦指不敢面對問題的懦弱行為。張培基并沒有翻譯成“orstrich mentality”,而是譯成今用英語中現有的“orstrichism”(有自我陶醉之意)[7]217,更加符合語境。
(二) 比喻
比喻是一種常用的辭格,即用本質不同但又有相似點的事物(喻體)來描寫或說明另一事物 (本體),從而使得事物生動形象,以此引發讀者聯想,并使文采斐然,增強語言的感染力。
3. 雖相距不遠,但上海對他們而言恐怕只是一個遙遠的天國。
“天國”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意象,指圣人靈魂的安居之所,亦指上帝居住的地方。將“上海”比喻成“遙遠的天國”看似矛盾,但恰是合理的:矛盾在于上海這座大都市確實存在,而“天國”這一意象卻是虛構的;而合理的地方在于,中國疆土之遼闊,而在那個年代,能感受到上海繁華氣息的人卻屈指可數。張培基將“遙遠的天國”譯成“inaccessible paradise on earth”[8]175忠實地再現出原文的韻味,上海大都市真切存在卻又遙不可及,其模糊特點與原文一一對應。
4. 我時而順著大車道,時而踏著羊腸小徑前往趕路。
“羊腸小徑”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格,將喻體“羊腸”的特征來修飾“小徑”,形容小徑蜿蜒曲折,張培基采取意譯的方法,將“羊腸小徑”譯為“narrow footpath”[7]207。雖然語言的文學色彩有所丟失,但干脆利落地表達出小徑之狹窄,降低了譯文的模糊性。
(三) 用典
用典即引用古典中的故事或詞句,以豐富而含蓄地表達有關內容和思想。用典增強了吳冠中散文的藝術表現力,使得行文更具有生命力,其所蘊含的文化意象也折射出了中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底蘊。
5.多少富豪人家在此舉辦過婚嫁喜筵!梁園日暮……
“梁園日暮”出自岑參七言絕句《山房春事二首》(其二)中的“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9]。吳冠中借此典故描述了自己所住的會仙堂往日富麗堂皇、門庭若市,而如今蕭條冷清、輝煌不再,委婉而含蓄地表達出作者的感慨之情。張培基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將“梁園日暮”譯為“like a run-down royal palace”[8]183,即“破敗的皇室”,雖然在原文的韻味上有所欠缺,但忠實地揭示了其含義,實現了意象的轉化,使讀者更易于接受。
另一處,“衣冠沐猴”指猴子穿衣戴帽,究竟不是真人,比喻虛有其表,如同傀儡。吳冠中借用該典故,看似批判古代官僚和皇帝的虛偽,實則是嘲諷當今社會偽裝已成為了一種風氣,言在此而意在彼。“衣冠沐猴”這個典故對于很多漢語讀者都不曾接觸,英文讀者對此更是陌生,張培基將其譯成“dress up as such”[7]213,舍棄了陌生的意象而保留其含義。
五、結語
散文的藝術特點是“形散而神不散”,行文中塑造大量朦朧而又模糊的審美意象。吳冠中的散文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運用模糊修辭的范例,增強了語言的感染力,同時也加深了讀者對原文的理解。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傳遞方式,對于模糊修辭的翻譯,重點在于能否再現原文的模糊信息和模糊意境。而張培基教授對于模糊修辭的處理無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典范,通過以上譯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在翻譯文藝性散文時,譯者必須對原文進行深刻透徹地挖掘,通過各種翻譯技巧和手段以保留原文的模糊特點,再現原文的韻味;但由于漢英文化差異性,必要時也不惜舍象而留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