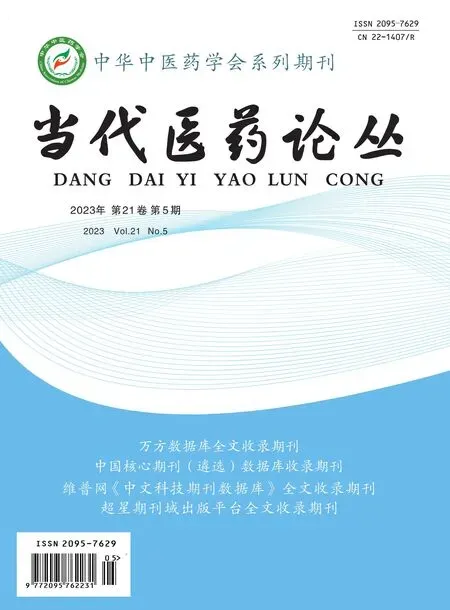基于玄府理論探討風藥在肝纖維化治療中的應用
李 雪,高永翔,李雪萍
(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 成都 610075)
肝纖維化是肝臟的一種病理生理過程,是指在各種致病因子的作用下,肝臟細胞外基質合成與降解失衡,導致間質膠原及其他基質成分在肝組織中異常沉積,進而引起肝臟纖維結締組織異常增生的一種病變。肝纖維化若持續加重,可進展成肝硬化。肝纖維化屬于中醫學中“臌脹”“脅痛”“黃疸”等范疇。本病的病機包括疫毒濕熱侵襲、正氣不足、氣機郁滯、瘀血內停等。玄府是人體內各類物質代謝的微小通道,玄府理論與肝臟的生理病理有著密切的聯系。風藥是指味辛質輕薄藥性升浮,具有祛風解表等功效的一類中藥。風藥與肝同性。本文基于玄府理論探討風藥在肝纖維化治療中的應用。
1 玄府與肝玄府理論
玄府理論最早見于《黃帝內經·素問·水熱穴論篇》:“所謂玄府者,汗孔也。”《黃帝內經·素問·調經論》中也有相關論述:“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可見古人最早認為玄府為排泄汗液的通道,常以“氣門”“腠理”形容玄府。到金元時期,劉完素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中提出“玄府者……皆升降出入之通利也”“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間萬物,盡皆有之,乃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府也”。劉完素在前人的基礎上拓展了玄府的概念,總結出玄府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玄府即指汗孔,廣義的玄府指人體各處細微的孔竅,具有溝通全身水液、氣血、神機等功能。他認為,玄府通利,則氣血津液運行通暢,人體安康;若玄府郁閉,氣機血脈凝滯,則百病由生。
現代醫家基于古人對玄府的認識,拓展了玄府理論,經現代醫學證明玄府為人體內各種物質代謝的微小通道。王明杰[1]教授在《玄府論》中提到玄府的特性有廣泛分布、結構細微、貴開忌闔,認為玄府為氣血及營衛精神升降出入的通道,也是氣血灌注、津液布散及神機正常運轉的保障。羅再瓊等[2]與王明杰教授的觀點相似,在劉完素的基礎上,總結玄府具有廣泛性、微觀性、開闔性及通利性,是機體溝通三焦、腠理,構成內外生理物質交換的微觀孔竅與通道。開通玄府為中醫基本治則之一,可瀉火、潤燥、補虛、達神等,如辛溫宣通之藥輔助散熱,辛散之藥活血、行津潤燥,辛溫走竄之藥輔助補益之品行至全身各處,可通過補益運轉神氣。常富業等[3]認為玄府是氣血津液及神機運行最微小的通道,是氣血津液及神機的道路,與現代醫學的微循環、離子通道、細胞間隙等結構有一定關聯,有維持氣血滲灌及津液輸布流暢的功能。楊麗等[4]總結了國內外對肝竇結構的相關研究,認為肝竇內皮細胞過窗孔數量及直徑的變化調節肝臟內的微循環,肝竇內皮細胞結構異常將導致肝臟微循環功能受損,這是肝纖維化的主要病理表現。孫學剛等[5]認為肝臟調暢氣機的生理功能與肝臟調節糖、蛋白、脂肪等物質代謝相類似,并闡述了肝篩結構可能是肝調節氣機、疏通氣血、代謝毒物的超微結構。黃文強等[6]也認為肝玄府與肝竇內皮細胞窗孔結構形態及功能相似,肝玄府為肝臟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的微觀通道。可見,在古人的基礎上,現代醫家對肝和玄府的生理結構及病理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豐富了肝病治療的理論基礎。
2 肝纖維化的發病機制及治療
肝纖維化在西醫學中是各種慢性肝病過程中的病理改變,如酒精性脂肪肝、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寄生蟲感染、內分泌疾病等引起的肝細胞損傷,具體病理表現為肝臟內細胞外基質中的間質膠原及其他基質成分在肝組織中異常沉積,造成肝臟組織被大量纖維瘢痕替代,破壞肝臟正常的結構及生理功能。肝纖維化進一步發展可引起肝硬化、肝功能衰竭、肝癌等,嚴重影響患者的健康及生命安全。有研究表明,肝纖維化的過程是可逆的。因此,進一步優化肝纖維化的中西醫治療對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及預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西醫對肝纖維化的治療主要以病因治療為主,治療方案有抗纖維化治療、抗病毒治療、免疫治療等,但臨床療效仍不理想,且有較明顯的毒副作用。肝臟生理結構損傷后的修復過程十分復雜,目前的抗肝纖維化藥物多為單一靶向藥物,其療效有限。中藥具有多靶點、多途徑的治療特點,且目前中醫藥治療肝纖維化在臨床上已顯示出療效好、副作用少、價格低廉等優勢[7]。因此,研究中醫藥治療肝纖維化的作用機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醫理論中沒有肝纖維化這一病名,但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于肝病中“癥瘕”“積聚”“脅痛”“鼓脹”“黃疸”等范疇。中醫古籍中有大量關于肝病生理、病理及治療的論述,如《備急千金要方》中提到“肝脹者,脅下滿而痛引少腹”。《四圣心源》中記載:“積聚者,氣血之凝瘀也,血積為癥,氣積為瘕。”《諸病源候論》中說:“……陰陽傷損,血氣凝澀,不能宣通經絡,故積聚于內也”“諸臟受邪,初未能成積聚,留滯不去,乃成積聚”。《古今醫鑒》說:“脅痛者……或痰瘀留注于血,與血相博。”《金匱要略》中論述酒精性肝病的證候:“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太平圣惠方》中提到鼓脹的病機:“夫水氣心腹鼓脹者,由肝脾二臟俱虛故也。”中醫認為肝體陰而用陽,肝藏魂,主藏血,主疏泄,具有調暢氣機、調節情緒、疏通經脈的生理功能。肝病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稟賦不足、七情內傷、飲食不節、久病體虛或外感六淫邪氣等原因,致氣滯、血瘀、痰飲等病理產物形成,從而導致肝失疏泄。病位主要在肝,易影響脾、腎。肝氣郁結,情志不暢,則見急躁易怒、胸脅脹悶;氣滯血瘀,則見脅肋刺痛;肝氣橫逆犯脾胃,導致脾胃虛弱,運化失職,水濕停聚,痰濕內生,故見納呆、惡心欲吐,痰濕日久生熱,痰瘀濕熱互相影響,進一步傷肝;肝氣郁結,日久化熱傷陰,最終傷及腎陰,可見耳鳴健忘、腰膝酸軟等虛實夾雜之證。
現代醫家總結肝纖維化的中醫證型多為氣滯血瘀證、肝郁脾虛證、濕熱疫毒證、肝腎虧虛證等,中醫治療以開通玄府為法,有活血化瘀、養血柔肝、化瘀消癥、疏肝健脾、清熱利濕、補益肝腎等治法,代表方劑有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湯、大黃蟄蟲丸、茵陳蒿湯、龍膽瀉肝湯等。王龍等[8]提出肝纖維化的基本病機為玄府郁閉,其邪氣由淺入深,初在氣分,病久則入血絡,故認為治療肝纖維化應靈活運用開通玄府之法,初起氣分階段應在清熱化濕的同時配合調暢玄府氣機;血分階段,應重在化痰、活血通絡;后期痰瘀與肝臟生理功能受損相互影響,當滋養與開闔同時進行。其結合玄府理論系統論述了肝纖維化的病因病機及中醫治法,為肝纖維化的中醫治療提供了理論支持。張聲生等[9]認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主要病機特點為肝生理功能失調,引起脾腎虧虛,導致痰濕熱瘀等病理產物形成,并進一步損傷臟腑,其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中醫證型分為濕濁內停、肝郁脾虛、濕熱蘊結、痰瘀互結、脾腎兩虛,治療上以祛濕化濁、疏肝健脾、清熱化濕、活血化瘀、補益脾腎為法,常用胃苓湯、逍遙散及中成藥化滯柔肝顆粒、護肝片等,并可配合針刺治療,以調節臟腑功能。呂文良教授認為肝纖維化的根本病機為氣血不和,而肝脾與氣血生化和運行密切相關,治療上應注重調和肝脾,以益氣健脾、和胃化濕、行氣化濁為治法,對于肝氣不舒、血瘀肝絡者,酌情予疏肝解郁、柔肝養血、活血化瘀等法,可用柴胡、郁金、白芍等,黃疸者可加用茵陳、大黃清利濕熱[10]。王憲波等[11]總結到,中藥復方可多環節、多途徑、多層次治療肝纖維化,且多從瘀血、濕熱、疫毒方面辨治,常用活血化瘀之桃仁、川芎,清熱利濕之黃芩、茵陳等。
3 風藥在肝纖維化治療中的作用
“風藥”一詞最早見于《外臺秘要》:“冷加熱藥……風加風藥。”在《神農本草經》中,記載了89味祛除風邪的藥物。金元時期,張元素在《醫學啟源》中提到“藥類法象”,認為風藥具有“風生升”的特性。《黃帝內經? 素問》中提到“風氣通于肝”。可見,風藥與肝臟之風同氣相求,具有升散的特性。張元素的弟子李杲在此基礎上于《脾胃論》中提及:“如脈弦者,是風動之證,以風藥通之”,并論述了風藥有勝濕、行經、生陽等功效,如論述防風:“防風治一身盡痛……乃風藥中潤劑也”。清代醫家徐靈胎在《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中提到“凡藥之質輕而氣盛者,皆屬風藥。”風藥味辛甘,質輕薄,性升浮,被認為是開通玄府的關鍵藥物。風藥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風藥指具有疏散風邪、平肝熄風、祛風濕功效的藥物,廣義的風藥還具有升散宣通、升陽除濕、行氣活血、疏肝解郁、通瘀散癥、化痰散結、引經報使等功效。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辛味藥多富含揮發油、苷類及生物堿油,有較強的擴血管、改善微循環等作用[12]。常用的風藥有升麻、柴胡、羌活、防風、藁本、葛根、川芎、獨活、白芷、荊芥、細辛、蔓荊子、麻黃、薄荷等。劉完素認為玄府為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風藥辛散體輕,宣發透達,與玄府生理功能相應,因此風藥可用于開通玄府,使全身津液營血流行通達,氣機出入升降有序,如麻黃、桂枝、細辛、柴胡等風藥,可開泄腠理,祛邪外出。
肝纖維化初期,多為肝郁氣滯,肝玄府病在氣分,氣機運行受阻,使津液運行不暢,再有肝病傳脾,脾胃虛弱,運化不行,則濕邪內生。劉完素提出以辛苦寒藥清熱化濕,通利玄府,以辛藥升散,以苦藥燥濕,以寒藥勝熱,可達通利玄府之功效。李東垣認為苦寒及淡滲之藥損傷陽氣,故常用燥濕行氣化濕之風藥,取風能勝濕之意,創立了升陽除濕之法[8]。氣滯日久,玄府不通,則郁而化熱,可配伍柴胡、蟬蛻、薄荷等風藥調達木氣,升散郁熱。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提到:“瀉陰火,以諸風藥升發陽氣,以滋肝膽之用。”他常用升麻、柴胡、羌活等藥,于升發陽氣中瀉陰火,調暢肝膽氣滯。錢乙在《小兒藥證直訣》中運用瀉青丸配伍風藥羌活、防風以升散肝火。除了升散氣分郁熱,風藥還能使營血之熱向外透達,起到通利玄府、條達肝氣的作用,如連翹、薄荷等風藥有透熱轉氣之功[13]。隨著肝纖維化的進展,肝玄府不通,氣血不暢,水液代謝受阻,痰濕內生。風藥溫燥,性升散,可行氣、燥濕、化痰,能使氣機通利,津液輸布順暢,促進肝玄府恢復正常的生理功能,如羌活祛風化痰,獨活化痰散結。肝纖維化多見氣滯血瘀證,氣血運行不暢,則肝絡阻塞,瘀血內生,治療上多用活血化瘀之法。風藥辛散性燥,可暢行氣血,能疏利玄府氣機,對于血瘀痰凝等病理產物有宣散作用,蟲類風藥更有走竄經絡之功效,可深入絡脈,因此臨床多用風藥化痰散結,活血祛瘀。例如,膈下逐瘀湯中配伍丹參、赤芍、紅花,鱉甲煎丸中使用土鱉蟲。白芷、藁本、葛根等中藥均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川芎、獨活及僵蠶、全蝎、蜈蚣等蟲類藥均具有通絡散結之功效。黃淑芬[14]認為,風藥能直達血分,活血通絡,對瘀血有發散祛邪、開郁暢氣、辛溫通陽、走竄通絡等全身性的整體調節作用。現代藥理研究也顯示風藥具有擴血管、改善微循環、抗炎、抗血栓等作用[15-16]。肝纖維化后期,肝腎不足,風藥升散溫通,可在補益藥的基礎上配伍風藥,以達補而不滯之功。也可用風藥助正氣化瘀,使氣血運行順暢,以通為補,如柴胡、葛根、防風等。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獨活、附子、木瓜、天麻、防風、葛根等19 種風藥均能提高人體免疫力,獨活、葛根、苦參、牛黃、川芎等36 種中藥均具有抗腫瘤的作用[17]。通過補益肝腎,可增強肝的疏瀉功能與腎陽的溫煦之力,從而扶正祛邪,調暢肝絡。風藥不論在衛氣營血還是氣血津液方面都有各個層次的具體運用,可隨證加減用藥治療肝纖維化。但需要注意的是,風藥耗氣傷陰,在臨床辨證時當明確寒熱虛實,用藥有度,配伍適當,注意中病即止。
4 小結
通過總結肝玄府理論及風藥的運用,可見風藥在臨床治療肝纖維化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風藥的行氣化瘀、祛濕通絡、補益肝腎、清熱利濕等功效,可以更有效地通利肝玄府,從整體上調節全身氣血津液的運行,使肝臟的生理功能得到改善,延緩肝纖維化進程。對于各類慢性肝病進展過程中的肝纖維化,合理運用中藥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病情,提高其生活質量。目前,風藥的基礎研究正逐步深入,在臨床的運用也日益廣泛,未來對風藥的運用將更加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