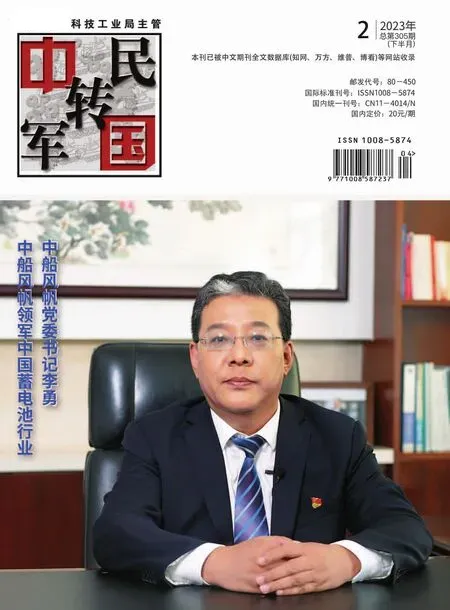《論持久戰》書寫邏輯及其當代啟示
■ 張治家
克羅齊曾講:“一切歷史皆當代史”。毛澤東在20 世紀30 年代撰寫的《論持久戰》為國民指明了抗戰的前途和方向,提供了具體的實踐指導,中國軍民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在持久戰戰略方針的指引下經過浴血奮戰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時光荏苒,在中美斗爭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重讀重思《論持久戰》,從中汲取經驗與智慧,為打贏新時代“持久戰”提供助力便成為應有之意。
一、廓清迷霧:一篇統一思想的雄文
1938 年5 月,在陜北延安鳳凰山的窯洞里毛澤東利用8 天8 夜的時間揮筆一蹴寫就《論持久戰》這篇曠世佳作。毛澤東為什么要寫作《論持久戰》?《論持久戰》為什么在抗戰10 個月后才問世?
持久戰的方針在全面抗戰前已被提及、論述,但如何具體操作則是困擾毛澤東的難題。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在如何使用安排八路軍進行抗戰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思路看法是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當中,其軍事戰略思想是伴隨具體實踐展開而不斷成形。共產黨領導發動的游擊戰在山地、平原地區的成功實踐[1]為毛澤東持久戰的戰略戰術提供了現實依據,為其《論持久戰》中的理論闡述夯實了的基礎。
縱覽《論持久戰》全文并結合歷史背景,毛澤東的言說對象[2]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共產黨內存在的對游擊戰持懷疑、否定態度的同志;第二,仍然采用錯誤、消極片面抗戰戰略戰術方法的國民黨友軍;第三,國內絕大多數愛國卻還未找到正確抗戰方法的民眾。針對不同的言說對象,毛澤東的敘述重點也會不斷變換,以便吸引對方思考理解進而支持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1937 年底懷揣莫斯科指示歸國的王明,通過先后發表“游擊戰不能戰勝日本”“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于統一戰線”等觀點,對毛澤東“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構想造成了嚴峻挑戰,王明的觀點還一度獲得了黨內部分同志的支持。為了同各種錯誤觀點做斗爭,為了廓清黨內同志的思想迷霧,掌握正確克敵制勝方法,在八路軍成功于山地、平原敵后戰場站穩腳跟這一實踐基礎上,毛澤東揮筆寫就了《論持久戰》,統一了黨內思想認識,解決了全黨全軍進行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問題。那么毛澤東又是如何來分析正在進行的中日戰爭呢?
二、時代定位:把準戰爭的性質及發展走向
采用客觀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分析中日戰爭的邏輯起點,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3],戰爭的性質決定了雙方必然要分出勝負,絕無和談的可能。其對中日矛盾雙方的四個基本特點及抗戰三個階段的劃分都是此一邏輯的自然展開,后來的歷史走向也驗證了毛澤東思路的正確。
汲取《論持久戰》中的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交織,在中美斗爭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如何對中美雙方的競爭關系進行時代定位與研判,成為我們能否取得競爭勝利的關鍵!那中美競爭的實質是什么呢?通過長時段歷史觀察可以發現,美國用200 多年的時間,在經濟領域逐漸構建了貿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撐的世界體系,在政治領域構建了暴力—盟友—規則相互支撐的帝國霸權,在文化領域構建了英語—基督教—人權相互促進的終結型意識形態,三個領域耦合形成了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任何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地位更遑論不服從美國安排的國家都會受其全方位打壓。
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始終希望通過接觸政策將中國納入到由其主導的“主—從”結構關系當中,而中國從平等地位出發的“新型大國關系”建構顯然不符合美國的認知與預期,兩國不同的未來圖景模式決定了雙方競爭的不可避免,而美國基于基督教一元化傳統的思維方式又決定了競爭的零和性,也即中美競爭必然決出勝負,試圖通過讓渡部分經濟利益以促美和談的觀點是行不通的。
美國以“新冷戰”思維建構的唯我獨尊的“新羅馬帝國”與中國主張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4]理念之爭是世界政治競爭的暴風眼,中國除了全心努力打贏這場“持久戰”外別無他路可走,而這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考驗。這場新形勢下的中美“持久戰”又包含哪些特點呢?
三、總體戰:軍事角逐背后的斗爭更加激烈兇險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黨政軍民一體化的總體戰是共產黨最終帶領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下,毛澤東并不尋求同敵人的直接正面作戰,而是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后方通過自身頑強的發展、生存,抑制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進而達到持久削弱敵人的目標。敵后游擊戰開展的同時也是共產黨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重新整合改造農村的過程,在抗戰過程中通過政治動員,共產黨將一盤散沙、粒子狀的個體凝聚成具有民族主義觀念的新式國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對社會結構進行重塑,最終完成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雙重使命。
隨著時代的發展,戰爭的形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類似抗日戰爭樣式的國家間全面戰爭逐漸消失,核武器的出現使得大國間較量很難再直接訴諸軍事手段來實現政權更迭,各國轉而探尋除軍事外的其他手段。大國通過小型的、局部可控的軍事沖突,采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混合式的總體戰達到顛覆敵方政權的目的。這種總體戰雖然沒有硝煙,卻同樣冷酷與激烈,由于其隱蔽性反而會使人缺乏危機意識、喪失警惕,在總體戰中落入敵人的圈套進而招致失敗。蘇聯解體就是最深刻的教訓!美國和平演變的邏輯思路在于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必然導致市民社會的崛起和文化價值的自由化,最終演變為追求政治的民主化與多黨制,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新思維政策恰恰與美國和平演變的頻率同步,因激進的經濟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失敗。
我們要時刻以蘇聯為鑒,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深刻意識到美國對我們的和平演變從未停止過。當下持續的中美全方位競爭、全面的總體戰只不過是將原本隱蔽的斗爭公開化、白熱化。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飛速發展在帶來國力提升的同時也為和平演變提供了更深厚的土壤,值得我們警惕。
在經濟領域,市場化的發展培植出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買辦階層,他們與西方資本有著深度的勾連,高度依附西方金融資本階層,他們崇尚西方文化、認同西方價值理念,利用金融資本、裹挾政府權力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他們滲透到教育、媒體領域,不斷傳播西方意識形態,同時試圖通過市場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攫取更多的財富和權力。
在政治領域,改革開放市場化的過程不可避免地使得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變化,部分官員理想信念動搖,沒有經受住糖衣炮彈的考驗而走向貪腐墮落,官商之間通過尋租形成裙帶利益集團,對黨和國家的利益、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在思想文化領域,美國通過長期的滲透已經培養出一個穩固的親美的文化階層,他們熱衷于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通過歪曲、丑化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來解構、動搖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試圖從意識形態領域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尤其是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碎片化、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不斷充斥著網絡,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動搖。那么我們該采取何種辦法應對美國的“和平演變”,打贏中美斗爭博弈的“持久戰”呢?
四、致勝密碼:黨的領導、統一戰線與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堅持黨的領導
《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5]。
在中美斗爭博弈的“持久戰”中,黨的領導依舊是我們能夠克敵制勝的法寶。面對市場經濟浪潮下社會上存在的缺乏政治思維,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利益化、技術化的傾向,共產黨能夠主動“刮骨療毒”,開展黨的建設和和思想政治教育,高壓反腐,進行思想、作風、組織建設,為黨注入政治活力,重塑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領導不僅通過黨規黨法納入到國家法治體系中,而且通過修憲方式明確寫入憲法的正文中。縱觀黨的歷史,我們能夠取得一次又一次偉大的勝利,根本原因都在于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二)開展統一戰線
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曾指出:“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就要使我們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敵人”,要在多方斗爭博弈中壯大革命的力量、削弱反動的力量。共產黨正是依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起救亡圖存的偉大合力,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偉大勝利。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統一戰線繼續參與、服務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發展壯大國家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持續增添著動力。我們要想打贏中美斗爭博弈的“持久戰”,就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充分調動、發揮全體中華兒女的聰明才智與創造力。
疫情之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同時還伴隨著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加速拓展,這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和地位帶來了極大挑戰。黨中央、習主席審時度勢,及時提出要促進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指出要充分發揮國內市場的主體地位,充分激活民眾的生產、消費動力。另外,中國成功踐行的制度方式也為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與西方日益極化、民粹思潮泛濫、政黨攻訐不斷的劣政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發動人民戰爭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一旦喚醒動員了民眾,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之中”。正是通過植根于人民、發動人民戰爭,共產黨得以不斷發展壯大并帶領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
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每在關鍵時期,總是人民群眾匯聚迸發出驚人的能量。近代以來中國先后錯過了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早班車,最終趕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末班車。改革開放以來,20世紀70 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全球產業資本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也順勢向西方開放引進外資,但因此產生了財政赤字進而引發經濟危機,是農村率先開展的制度變革使得國家走出了經濟危機。80 年代農村釋放的活力與動力,創造的繁榮穩定支撐了城市步履維艱的改革。90 年代依舊是農村提供的人口紅利使沿海得以引進勞動力密集的低端產業,再加上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渡過了席卷東南亞的經濟危機。進入21 世紀,2007 年次貸引發西方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使得外需再度下降。依舊是國家憑借“三駕馬車”,對農村大量投資以及農民的內需消費挽救了中國。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觸發了全球危機,結合歷史經驗,中國的制勝之道依舊在農村、依舊在人民[6]。若能借機推動國家的生態文明轉型,促進生態資源資本化和城鄉融合發展,我們就能轉危為安,再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當下中美“持久戰”中人民依舊發揮著柱石作用,是黨的執政基礎和力量之源。比較中美兩國對待人民的態度與方式,前者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通過高質量發展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后者則服務于資本,打著民選政府的旗號卻無視民眾的利益。中美兩國的斗爭博弈是民心向背的比拼,我們將進一步地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發動人民,努力打贏新時代的“持久戰”。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贏下這場“持久戰”只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手段,我們在發展提升自身的同時還要帶動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共同發展進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的共同富裕貢獻力量。
五、結語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美國試圖憑借科技與軍事霸權主導建立的單極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雙重矛盾:一是,美國的世界帝國模式與以中國為代表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模式的沖突;二是,美國坐享帝國體系帶來的利益卻拒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必然導致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序發展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美國為了維持其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勢必會對中國進行全面打壓與脫鉤,這將進一步加劇全球的沖突與震蕩,為世界帶來更多的危機與災難。我們在同美國進行“持久戰”的同時還要建構出更加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未來世界格局的中國方案,要化“歷史終結”為“貞下起元”,要化文明沖突為文明交流,要從文明的源頭出發,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目標,通過開放與合作,為更美好的人類未來貢獻屬于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