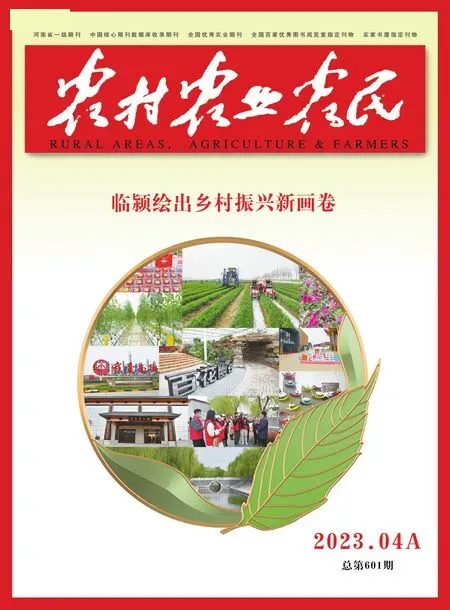第一粒玉米
王佳慧
(中國農業博物館)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這句廣為人知的唐詩似乎向人們展現了一個春華秋實、累累碩果的景象。然而,無論是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農耕,還是高科技的現代農業,即使忽略氣候、溫度、水分等給作物帶來的不可控的影響,土壤也并不能如古人所愿,將一粒粟供養出萬顆子。事實上,在我們熟悉的禾谷類作物中,如果按比例換算的話,一粒小麥種子能結大約40 顆麥粒,一粒水稻種子能結大約100 顆稻米,而一粒玉米種子則能產出大約600顆籽粒。較之水稻和小麥,玉米產出巨大。因其產量優勢、功用繁多,加之生長周期較短,玉米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糧食作物,同時也是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多年來,我國玉米產業已歷經6 代品種,包括以中單2 號為代表的第一代和以丹玉13 號為代表的第二代等(圖1)。玉米產業的升級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人們的生存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一粒玉米”來到中國
玉米并不原產于我國。據考證,玉米應在明代后期傳入我國。從文獻來看,明正德六年(1511 年)的《潁州志》一書在對農作物的品種進行分類記錄時,在“蜀秫”類目中提及的“珍珠秫”疑指玉米,是最早的國內對玉米有記載的文獻。而玉米在我國最早的明確記錄源于明嘉靖年間的《襄城縣志》,書中將玉米稱為“玉麥”。但有學者認為,明朝方志中所記載的“玉麥”并不指玉米,而是指更接近小麥的一種穬麥。比較確認的記載玉米信息的最早文獻是成書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的《南畿志》,其中記載道:“花果園在城南,姜菜園散在城隅,香稻田、番麥廠并在城東,以享宗廟。”玉米在書中被命名為“番麥”。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趙時春在《平涼府志》中記載:“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從其對植株性狀的描述來看,這種“番麥”應當就是我們所說的玉米。這是我國至今保存下來的對玉米形態最早的記錄。“番麥”之后,玉米又被稱為“御麥”,嘉靖末年,杭州學者田藝蘅在其《留青日札》中記載:“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種于西苑,故曰御麥……干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須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真異谷也。”與此同時,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及玉米時,改“御”為“玉”,同音轉書,并依據自己的科學判斷,重新將玉米命名為“玉蜀黍”,書中寫道:“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其后,各類文獻中記載了玉米的不同名稱,如“御米”“西番麥”“回回大麥”等。直到明末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圖2)中“玉米”這個名稱第一次被推出。可以看出,明朝記載玉米的文獻幾乎都將其傳入的源頭指向了我國的西北地區。明人所指的西番,指嘉峪關外傳統西域之地,因而普遍認為,玉米由中東地區經絲綢之路傳入(另一種觀點認為玉米經東南海路傳入)。我國的第一粒玉米應始種植于西北,后中原,繼而南下江南。相關資料顯示,東北地區的玉米應為移住東北的漢族民眾帶入,種植時間較晚。

圖2 《農政全書》(中國農業博物館)
“第一粒玉米”在墨西哥
若追根溯源,“第一粒玉米”的故事并不發生在中東或東南海外,而發生在約1 萬年前的墨西哥。玉米植株高大,雌雄花同株異位,莖稈挺直,葉尖細長。自然界內沒有任何一種植物與玉米形態相似,因此,一度被人們稱為“外星植物”。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尋找玉米的“祖先”。玉米的起源地曾經被認定為位于中南美洲的多個國家和地區。直到20世紀80 年代,分子生物學的證據將玉米的“祖先”指向了一種“野草”——大芻草(Teosinte)。據考證,大芻草最早馴化于墨西哥南部的巴爾薩斯(Balsas)河流域,至今尚存。盡管大芻草與現在的玉米形態不一致,人們很難相信它們同源,但以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撐,科學家們已經借助基因比對和考古記錄拼湊出了由大芻草到玉米進化的全過程。2022 年,我國的科學團隊(華中農業大學嚴建兵團隊)和美國的科學團隊合作,構建了玉蜀黍屬(玉米和它的“祖先”野生大芻草的7 個亞種)的遺傳變異圖譜,揭示了玉米及其“祖先”適應環境進化的分子機制。同時,植物考古學的證據也證明了“第一粒玉米”的起源地。在墨西哥的特瓦坎(Tehancán)山谷和位于瓦哈卡(Oaxaca)地區的吉拉納蒂茲(Guilá Naquitz)山洞里,考古學家們發現了最早的玉米遺存,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玉米”。這些玉米遺存包括3 個玉米芯殘塊(圖3),以及一些極其微細的玉米淀粉。無論是分子生物學和植物考古學的證據,還是存在于星羅棋布的中南美洲古代遺址里關于玉米的史前物證,都毋庸置疑地證明,“第一粒玉米”出現在約1 萬年前的墨西哥。

圖3 吉拉納蒂茲(Guilá Naquitz)山洞里出土的3 個玉米芯
如果說亞洲孕育了稻米文明,那么玉米文明應當歸于拉丁美洲。玉米崇拜是墨西哥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語言中,玉米被稱為“印第安谷”。玉米的“祖先”大芻草,其名字來源于阿茲特克語“Teocentli”,意思是“玉米的神穗”。從14 世紀至16 世紀,阿茲特克人居住在墨西哥的平原和高地上,阿茲特克文化是中美洲古老印第安文明的一部分。對于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代印第安人來說,玉米的存在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在瑪雅文明中,造物主用玉米做成了人的身體,玉米是神物,是生命之源。時至今日,人們仍然把當地的土著稱為“玉米人”。他們崇敬地將玉米的植株和果穗刻在器具、神像和廟宇上(圖4)。在印第安神話中,人們所崇敬的玉米神,同時也是豐收之神、雨水之神、森林之神。

圖4 玉米神像
就像他們崇拜的熱烈而充滿生命力的玉米,拉丁美洲人同樣精力旺盛、熱情似火。他們在9000 多年前馴化了大芻草,使其減去分枝,果穗增大,鋪滿籽粒。在大航海時代,玉米被哥倫布帶到西班牙,隨后傳入歐亞及全世界。在傳播過程中,玉米曾被稱為“土耳其谷”“羅馬谷”“埃及谷”等。除以各地名稱稱呼玉米,在印度次大陸,玉米的稱呼還與圣地麥加相關,如“Mecca”“Makka”“Makkaim”“Makai”等,均為麥加讀音的變化形式。各地人們以故鄉和圣地的名字命名玉米,對其不吝贊美。中國人則用最崇尚的玉、最依賴的米來稱呼玉米,寓意其如玉珍貴,如米飄香。
現今,除南極洲,其他六大洲都在種植玉米。在我國,玉米在各個地區都有種植(圖5)。我國主要的玉米種植帶從東北延伸至西南方向,經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12 個省、自治區。玉米種植帶產量占我國玉米總產量的85%。無論是種在東北黑土地上的春玉米,還是華北平原的夏玉米,或是長江以南的鮮食玉米,玉米從不排斥變換的環境,它總在克服不適,慷慨生長。

圖5 各地區農民畫中的玉米(中國農業博物館)
從最初的大芻草發展至今,世界各地已經孕育出數不勝數的玉米品種。從植株到籽粒,它們被食用、飼用,被用來制藥或作為工業原料。玉米見證了人口的激增和文明的發展。目前,世界上已有多家玉米專題博物館。在秘魯,“圣谷”玉米博物館里陳列了上百個玉米品種,向人們呈現著玉米豐富多彩的故事。2014 年,內蒙古通遼市成立了我國首家玉米博物館;2021 年,長春市雙陽區建成了黃金玉米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為我們講述著玉米文明,也講述著古往今來為玉米文明而發光發熱的人們。
“第一粒玉米”似乎只剩下留在中美洲的遺跡,但“第一粒玉米”的故事還在繼續。人們還在繼續培育下一個玉米新品種,孕育一個新顏色,創造一種新食物,合成一種新能源。在人們的不懈努力下,玉米產量還在不斷創新高。“第一粒玉米”還將滋養更多姿的品類,創造更廣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