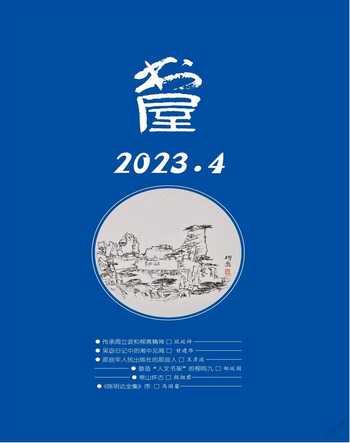人性善惡之辯
劉道玉
在中國古代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個被稱為“千古之辯”的爭論,即關于人性善惡的爭論。論辯的雙方都是儒家泰斗級的人物,一個是儒家二號人物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另一方是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他是儒家大師級人物,而且發展了法家思想。
《孟子·告子》分為上下篇,在上篇中有關于人性的論述。如果用白話文表述,其意思是: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低處流的。當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飛騰起來,能使它高過額頭;加壓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崗,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形勢迫使它如此。人之所以脅迫他做壞事,本性的改變也像這樣。孟子的人性本善論認定: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成也,我固有之也。因此,孟子的觀點是“人之初,性本善”。
什么是人性?人性即心靈性或人的秉性,人心決定人性。所以人性是生來具有的,是自然形成的。孟子也承認,在社會中,有人也有惡的表現,但他解釋那是違背人性的,是人性扭曲的表現。
荀子比孟子出生晚了半個多世紀,他們雖然都是儒家代表人物,后人常常把他們并稱為“孟荀”,但他們的學說卻分歧非常之大。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他們沒有可能直接論辯,而是超越時空的思想碰撞。后人發現,在《荀子》一書中,存有他對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評論,從這些評論中,可以窺見孟、荀二人在人性觀點上的對立。載在《荀子》一書的《性惡篇》中,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而孟子的性善論成了他主要的批判對象。在荀子看來,諸如貪財好私、妒忌憎恨、貪圖享樂等人性的惡性其實都是與生俱有的。
如果對這些惡性放任不管,任意放縱本性,就會出現互相爭奪,擾亂社會秩序,最終導致暴亂的后果。對待人的性惡表現,荀子也認為需要整治。怎么避免人性的這些弱點呢?怎樣使人向善呢?那就是建立禮儀、制定法度,用來整治、改變、馴服和教化,引導人們情性的改變。為了實現這種改變,人需要有動力,如果沒有,那也是沒有可能通過學習改變他們。這個約束,就是圣人們創立的禮儀教化,用它消除惡性。對于孟子認為人失去了本性才會產生惡的觀點,荀子也進行了反駁。
人們感到困惑的是,同為儒家的代表人物,為什么他們對人性善惡有著如此對立的觀點呢?我以為主要是三點:首先是他們的人生觀不同。孟子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信奉人性本善,認為只要統治者施行仁政,就可以建立國泰民安的社會,形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好民風。然而,荀子雖然也儒家代表人物,但他是現實主義者,認為人性本惡,所謂的善只能是后天的教化,統治者要想富國強兵,必須隆禮重法。
其次,二人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的環境不同。孟子雖然是魯國孟孫氏的后裔,但三歲喪父,其母仉氏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孟母三遷”和“斷機杼”,孟母教育和激勵孟子發奮學習是家喻戶曉的故事。孟母的慈愛之心感動了兒子,從此勤奮好學,終于成為我國古代四大圣人之一。同時,這種慈愛也在孟子的心中滋生了人性本善的種子。荀子是趙國人,家境殷實,經營著百多畝田產和桑園。他們二人的家境反差很大,對他們對人性的認識也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再次,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人是社會的人,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人群之中,這些人的政治態度和人性都會影響他們對問題的結論。如果他處在貪婪和為非作歹的人們中,他看到的是人性惡的方面;如果他處于善良的人群中,他看到的是人性的善。當然這些觀察都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帶有隨機性,并不能以偏概全。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中國這個“千古之辯”呢?在我看來,人性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完全以善或以惡,都不能完全概括所有人的人性。實際上,人性具有二重性,既有善良的人,又有品性惡劣的人;既有善良的人變為惡劣的人,又有惡劣的人變為好人;既有一貫潔身自好、樂善好施、永葆真善美的人性,也有冥頑不化、惡貫滿盈的人性;既有獨立自主的人,又有扮演角色的人(即偽裝)。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學者,他的名字是喬治·赫伯特·米德,在某些方面他有點像我們古代的孔子,終生沒有個人論著出版。但是,死后他的學生們根據他講課的記錄,整理出了幾本著作。他有一個最有影響的觀點,即人的自身是由“我”(Me)和“自我”(I)兩部分組成。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由其自身的角色(獨立行為)和扮演的角色(角色行為)所組成。因此,一個人的自身角色才是真實的“我”,而扮演的角色卻是偽裝的“我”。這種偽裝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例如,那些說假話、套話、空話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性也是一個悖論,有時候善的一面掩蓋了性惡的一面;也有些人雖然性情耿直、粗魯,但卻是善良的人。一個人如果掌握了辯證法和懂得了人性的悖論,就能夠辨別人性的善惡和真假。
我們討論人性的善惡,并不是為辯論而辯論,而是要廣泛宣傳人性真善美的美德,要重視教育對人的教化作用。我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畢生從事教育的工作,自認為并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在工作中既有成就,也有錯誤和失誤。曾子(曾參)是孔子的弟子,曾經被封為儒家五圣之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曾子在儒學學派中地位之重要。曾子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他曾說“吾日三省吾身”。
我是一個事必躬親、事求必成的人,抱著知錯必改、知恩必報的信條。我崇信曾子的名言,從“知天命”開始,我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即今日事今日畢了沒有?今日錯今日改了沒有?今日恩今日感恩了沒有?蜀漢昭烈帝劉備在詔書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我也把這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時時刻刻反躬自問,保持善良的美德,隨時去掉自己身上不良的習性,做一個正直、清廉和有利于人民的人。我已屆鮐背之年,但我依然堅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和筆耕不輟的信條,直至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