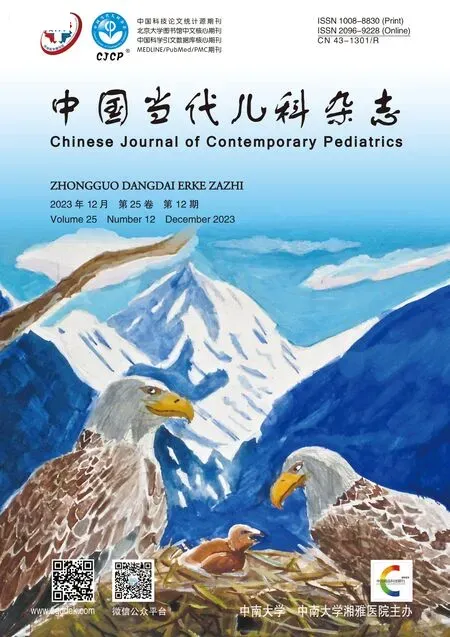免疫球蛋白A血管炎病因及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熱愛拉·加那提 劉細細 綜述 朱學軍 審校
(1.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江蘇南京 210029;2.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血液科,江蘇南京 210029)
免疫球蛋白A 血管炎(immunoglobulin A vasculitis, IgAV),又稱過敏性紫癜,多發生在細菌或病毒感染之后,是一種由免疫復合物沉積引起的小血管炎,通常會累及皮膚、胃腸道、關節和腎臟[1]。IgAV 多發于兒童,發病率約為20.4%[2],男性患病率是女性的近兩倍。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近年來人類對IgAV 的病因有了新的認識,如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3]、肺球孢子菌[4]等感染因素,以及SARS-CoV-2 疫苗[5]、人乳頭瘤(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疫苗[6]、其他生物制劑[7]等非感染因素可能與IgAV的發病有關。
研究表明,半乳糖缺陷型IgA1 (galactosedeficient IgA1, Gd-IgA1)及含Gd-IgA1 的免疫復合物在IgAV 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8]。除此之外,抗內皮細胞抗體(anti-endothelial cell antibody,AECA)和IgA1 的結合物(IgA1-AECA)及T 細胞免疫與IgAV 也存在一定相關性[9]。隨著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遺傳易感者對各種誘發因素所進行的免疫應答及表觀遺傳學也成為了IgAV 發病機制研究方向[9]。
本文將綜述IgAV 病因的新進展,并從Gd-IgA1、含Gd-IgA1 的免疫復合物、IgA1-ACEA、T細胞免疫等免疫因素及遺傳因素方面論述IgAV 的發病機制,以期為該病的預防和管理提供依據。
1 IgAV病因
IgAV 的具體病因仍未明確。既往研究表明,IgAV 的發病多與鏈球菌、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及某些食物、藥物等有關[1]。近期研究發現IgAV的病因可能還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
1.1 SARS-CoV-2及其相關疫苗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SARS-CoV-2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目前認為感染SARS-CoV-2 會觸發一系列自身免疫性疾病,IgAV 的發生也可能與之相關。對于由SARS-CoV-2感染引發的IgAV青少年及兒童患者,更容易出現發熱和腎臟受累,自愈率和完全康復率也低于其他原因導致的IgAV 患兒,提示COVID-19相關IgAV患兒的病情相對更嚴重[3]。
免疫系統的過度激活可能是SARS-CoV-2 引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IgAV 主要與SARS-CoV-2與血管緊張素轉化酶Ⅱ(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的結合有關。ACE2 會將血管緊張素Ⅱ(angiotensin Ⅱ, AT Ⅱ)轉化為血管緊張素-(1-7)(angiotensin 1-7, AT 1-7),從而刺激內皮細胞產生一氧化氮(nitrogen oxide, NO)。然而SARS-CoV-2 與ACE2 的結合會導致ACE2 表達降低,抑制AT Ⅱ轉化為AT 1-7,導致AT Ⅱ的增加,從而致使NO 產生降低。NO 有維持血管穩態及調節血管舒張的作用,NO減少使血管微環境更容易發生凝血和炎癥,導致IgAV的發生[10]。
研究表明,SARS-CoV-2 疫苗可以引發IgAV,且兒童較成人預后差[11]。SARS-CoV-2 疫苗相關IgAV 患兒初發與復發的臨床表現類似,最常見的表現是肉眼血尿(89.5%),而皮損相對較少[12]。Ramdani等[5]研究共納入來自24個國家的330例接種SARS-CoV-2疫苗后新發IgAV的病例,其中占比較大的是美國(58%)、英國(9%) 和法國(9%),這些患者從接種疫苗到發病的中位時間為7 d,且兒童IgAV 報告率顯著高于成人。330 個病例中可追蹤到最終結果的病例數有147例,其中95例痊愈,1例有后遺癥,2例死亡。
接種疫苗后自身反應性B細胞重新被激活分泌IgA,從而導致IgAV[13],因此IgAV 的發生可能與SARS-CoV-2 疫苗的成分有關。首先,由于SARSCoV-2 疫苗的結構與人類蛋白質的結構存在相似性,疫苗抗原也可能通過分子模擬途徑攻擊具有相似結構的人類蛋白質,從而導致自身免疫性疾病[14]。其次,疫苗中的佐劑可以與模式識別受體結合,動員天然免疫細胞并分泌大量細胞因子,誘導先天免疫反應[15];而不含佐劑的mRNA疫苗,也可以通過mRNA 本身經模式識別受體途徑刺激先天免疫反應,先天免疫反應激活后產生的大量細胞因子,通過旁觀者激活途徑誘發自身免疫性疾病[13]。
1.2 其他生物制劑及化學藥物
IgAV 常常出現在使用藥物治療某種原發病的過程中。首先是生物制劑,Desai等[7]報道了第一例維多珠單抗治療小兒潰瘍性結腸炎后出現IgAV的病例。其次是抗生素,如環丙沙星[16]、頭孢曲松鈉[17]等均可以引發IgAV,但由于抗生素抗感染的特性,其引發IgAV 的理論仍存在爭議。據報道可以引起IgAV的其他藥物還有丙戊酸鈉[18]、阿貝西利[19]等。以上藥物可能通過刺激抗體產生、對血管壁的直接毒性作用或激活嗜酸性粒細胞來誘導IgAV的發生發展[9]。
1.3 其他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也可以引發IgAV。研究表明,IgAV患兒EBV感染率為0.9%,其發病可能與EBV 直接激活體內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有關[20]。HIV 相關IgAV 的發病機制可能與HIV可以直接引起內皮功能障礙和針對HIV蛋白的免疫球蛋白生成有關[21]。近年來,隨著HPV 疫苗的接種率日趨上升,其不良反應也暴露出來,其中包括IgAV[6]。肺球孢子菌病是由球孢子菌感染導致的肺化膿性、肉芽腫性真菌感染。Archambault 等[4]報道了1 例感染肺球孢子菌后出現廣泛的出血性大皰性紫癜。以上感染引發IgAV的致病機制尚不清楚。
2 IgAV發病機制
目前已有2種假說分別解釋IgAV的發病機制。第一種假說認為,Gd-IgA1 和含Gd-IgA1 的免疫復合物的產生與IgAV發病有高度相關性,即Gd-IgA1的產生增加Gd-IgA1 和IgA1 特異性自身抗體結合,形成致病性循環免疫復合物并沉積在全身小血管中,從而引發一系列炎癥反應。另一種假說則強調IgA1-AECA 復合物誘導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從而激活中性粒細胞,最終導致全身性血管炎。IgAV 的致病過程還受到多種因素的調節,如細胞免疫微環境及遺傳學等。
2.1 Gd-IgA1的產生及其與IgAV的相關性
IgA 分為IgA1 和IgA2 兩種亞型,IgA1 的分子結構使其更易發生異常糖基化,導致IgA1 在IgAV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22]。IgA1 的糖基化過程受相關酶活性及基因表達的影響,而相關酶活性及基因的表達受某些細胞因子及相關信號通路的調節。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 IL)中的IL-6家族與Gd-IgA1生成的相關性最高[23]。研究表明,白血病抑制因子在與其相應的受體結合時可以通過白血病抑制因子-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1 信號通路介導Gd-IgA1 的過度產生,從而誘發IgAV[24]。黏膜免疫相關分子Toll 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也參與Gd-IgA1的產生,如TLR7可以刺激B細胞分泌IL-6 和IL-12 等細胞因子,并通過TLR7-N-乙酰半乳糖胺基轉移酶2 信號通路產生更多的Gd-IgA1[25]。TLR9則可以通過TLR9-髓樣分化因子88 信號通路誘導IL-6 及A 增殖誘導配體的產生,并與兩者協同促進Gd-IgA1的產生[23]。
除上述分子外,miRNA 也可以調節糖基轉移酶的表達。如miRNA-148b 的上調可以抑制C1GALT1基因的表達,從而使Gd-IgA1 水平升高[23]。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Gd-IgA1與IgAV發病有高度相關性。Neufeld 等[8]研究發現,Gd-IgA1 的致病性可能與其含量正相關。Zhang 等[26]也在IgAV 患者的組織中檢測到IgA1 的異常糖基化,并發現IgAV 腎炎(IgA vasculitis with nephritis,IgAVN)發生發展與Gd-IgA1相關性更高。
2.2 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與IgAV的相關性
Gd-IgA1 不是IgAV 疾病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有研究發現,IgAV 患者的皮膚小血管壁及腎臟系膜細胞中均有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沉積[8]。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通過血流進入腎臟后,其表面受體CD71 與腎系膜細胞結合后沉積在腎小球內。而腎小球系膜分泌的其他分子(如整合素和谷氨酰胺轉移酶2等)會上調CD71表達,對含Gd-IgA1 的免疫復合物在腎臟的沉積產生正反饋調節作用[27]。由此可知,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比重及分子量較大的患者可能大多為腎型IgAV。
2.3 IgA1-AECA與IgAV的相關性
由于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解釋IgAV 的全身癥狀,Xu 等[9]提出IgA1 與AECA 的結合在全身性小血管炎癥中起核心作用。IgA1-AECA可以與內皮細胞上的特異性受體結合并誘導IL-8 釋放[28],從而在體外募集中性粒細胞并促進炎癥的發生。同時,IgA通過與IgA的Fc受體結合促進中性粒細胞活化和趨化。IgA的Fc受體交聯會以多種方式引起內皮細胞的損傷,如吞噬作用、促進活性氧的產生、釋放含有乳鐵蛋白等有毒分子的顆粒、分泌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性作用及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的形成等[29]。
2.4 T細胞異常與IgAV的相關性
含Gd-IgA1 的免疫復合物還可以影響T 細胞免疫,表現為T細胞的數量、比例及功能的改變,使得T細胞免疫在IgAV的發病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Li等[30]研究表明,IgAV患者體內輔助性T細胞17(helper T cell 17, Th17) 及調節性T 細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的數量存在不平衡,表現為Th17 增加和Treg 減少。2021 年有研究確定了一種特殊類型的Treg,名為Tr1 細胞,其在急性期IgAVN的腎組織中表達明顯增加,而在外周血中的表達降低,且緩解期體內Tr1細胞表達低的患者復發率較高,提示Tr1細胞可能有預測IgAVN復發率的價值[31]。Imai 等[32]在IgAV 患者中發現循環細胞毒性T細胞激活,而腎小球中循環細胞毒性T細胞增加會導致IgAV 患者出現腎損傷。Audemard-Verger等[33]發現IgAV患者皮膚和腎臟中存在CXC趨化因子受體3陽性T細胞浸潤,且CXC趨化因子受體3陽性T細胞的數量與IgAV患者腎臟損傷嚴重程度呈正相關。
此外,異常T細胞亞群還會促進細胞因子的產生[34],驅動炎癥反應。同時,細胞因子還可以通過相關的分子信號通路作用于IgA,加劇Gd-IgA1的產生。
2.5 遺傳易感性及表觀遺傳學與IgAV的相關性
遺傳因素在IgAV 發病機制中也非常重要。IgAV 的遺傳易感性不是由單個基因決定的,需要多個基因協同工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與免疫應答及炎癥相關信號通路的基因多態性上[9]。
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是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HLA Ⅱ類基因已被確定為IgAV 最主要的遺傳易感位點,其多態性不僅影響不同人群對IgAV 的易感性,還影響疾病的嚴重程度和臨床表現[35]。Xia 等[36]的研究表明,HLA Ⅱ類基因中的HLA-DRB1基因與IgAV易感性密切相關。
多種非HLA 基因也被證實與IgAV 易感性有關。Carmona 等[37]通過大規模交叉疾病分析,確定位于NAGPA基因內含子區域的rs3743841 為IgAV 和川崎病之間共同的潛在風險位點,是迄今為止與IgAV 相關性最密切的非HLA 基因。Hui等[38]則發現ACE基因型中的D等位基因可能與兒童IgAVN的易感性相關。Balc?-Peynircio?lu等[39]的研究顯示,地中海熱基因突變會導致先天免疫系統的炎癥性改變,從而增加血管炎的易感性。
表觀遺傳調控是指DNA 序列尚未發生改變,生物表型發生了可遺傳性改變,主要機制包括DNA甲基化、組蛋白甲基化、非編碼RNA調控等,其在免疫性疾病中也發揮一定作用。研究發現,編碼組蛋白去甲基酶的KDM4C基因是兒童多發性血管炎的常見風險位點[40]。表觀遺傳調控領域的進展促進了IgAV 發病分子機制研究的深入,為治療IgAV提供了新思路。
3 結論
IgAV 的發生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近年來其病因的新發現主要體現在SARS-CoV-2 及其相關疫苗等方面。發病機制方面,大多研究傾向于感染等因素激活機體異常免疫反應,導致Gd-IgA1過度產生,形成含Gd-IgA1的免疫復合物,進而沉積在血管中導致IgAV。另一種則認為中性粒細胞的活化起核心作用,即IgA與IgA的Fc受體結合誘導中性粒細胞的募集和活化,引起全身血管炎癥,這更好地闡明了IgAV 的全身受累機制。遺傳易感性及表觀遺傳學可能是這兩種發病機制都密不可分的一環。深入探討IgAV 的發病機制,對于在分子水平上預防疾病、精準治療、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然而,IgAV的發病機制仍不明確,IgAV、IgAVN 和IgA 腎病之間的關系也未完全闡明。尚需不斷進行基礎研究,揭示IgAV 的核心發病機制。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