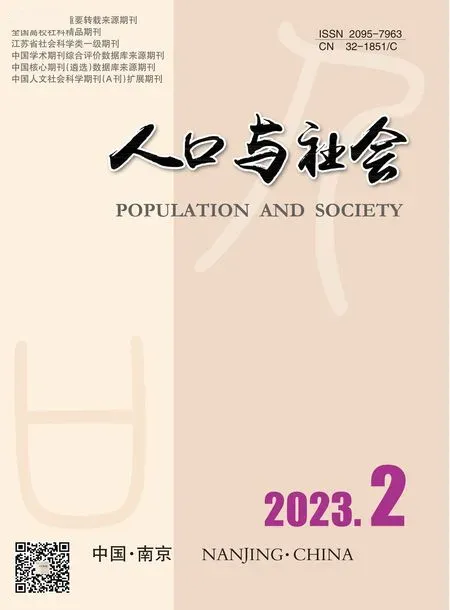農村青年戀愛與婚姻的適應性策略
黃佳琦
(武漢大學 社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問題的提出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個體需要依靠家庭獲得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婚姻締結是擴大家庭關系,實現家庭延續的必要條件。在傳統社會,個體婚姻與家庭形象、家庭發展緊密相關,婚姻締結的意義重大[1]。
學界對婚姻締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締結的方式以及影響因素兩個方面。首先,學者們普遍認為婚姻締結的方式正在發生轉變。齊亞強和牛建林認為,中國婚姻一直以來都是匹配型婚姻,隨著社會結構、制度和文化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匹配模式[2]。范成杰和楊燕飛提出“無媒不婚”的婚姻締結方式,認為婚姻締結在流動性社會中發生形式與內容的分離,形式上依靠媒人介紹實現婚姻締結,但實質是青年遭遇擇偶困境時的策略性應對[3]。施磊磊對青年農民工婚戀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發現,青年婚姻締結方式的變化并不是傳統到現代的線性過渡,而具有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復雜特征[4]。陳雯認為當代青年已經轉向通過戀愛締結婚姻,并且將戀愛方式分為本地婚戀、異地婚戀和邊緣婚戀三種類別[5]。其次,學界對婚姻締結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綜合性分析。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學者們普遍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與傳統生育偏好疊加導致部分地區性別結構失衡,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性別不均衡的問題尤為凸顯,所以從人口學意義上來說,人口性別不均衡是影響農村地區婚姻締結的根本原因。從中觀層面上來看,人口流動帶來的婚姻競爭對男性造成擠壓,在婚姻成本不斷提高的現實背景下,代際合力的強弱程度對婚姻締結的成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6],個體與家庭的綜合能力正在經受婚姻市場的考驗[7]。
在傳統社會,婚姻締結的主導權掌握在父代手中,是父代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展現,因此婚姻的社會意義成為婚姻的重要內涵。而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個體的主體性凸顯,個體逐漸獨立于家庭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在婚配過程中表現為個體之間“處得來”成為婚姻締結的關鍵[8]。婚姻含義中的個人價值開始超越社會意義,婚姻對個體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滿足逐漸成為現代婚姻的主要目的[9]。婚姻的含義已經發生不可逆的轉變,既有研究總結出的綜合性、結構化的影響因素并不能夠完全解釋新時代青年的婚姻現狀,這使得從微觀層面入手,對兩性互動過程的剖析更有助于理解婚姻締結過程中的現實問題。
基于此,本文將影響婚姻締結的結構性因素作為背景條件,引入性別視角,采用過程分析的方法,透析農村80后、90后青年男女之間的微觀互動過程,探尋兩性戀愛與婚姻締結的內在關聯,力求對新時代農村青年的婚姻有進一步的理解。
二、調查情況與本地婚偏好
(一)調查情況
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我國中西部多地農村青年男女的婚戀案例,重點以在安徽淮南L村展開的為期20天的調研為經驗基礎。期間筆者訪談了8位80后、90后青年男女,其中男性4位,女性4位,包含未婚、已婚以及離異三種婚姻狀態,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見表1。此外,筆者還進一步訪談了留守在村的父輩,輔以家庭視角理解農村青年婚戀問題。本文所指的農村青年是出生于八九十年代、非正規就業的群體,這一群體由于未接受過專業的技能或職業教育,就業狀態呈現出層次低、流動性強的特點,這使其難以建立起與城市之間的強連接關系,而不得不穿梭于城鄉之間。農村青年與鄉村的關系網絡斷裂,又難以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巨大的發展壓力使其對親密關系的需求和要求更高,加劇了婚姻締結的難度。

表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筆者調研的L村,具有較為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農民可以依靠土地滿足基本溫飽需求。村莊周圍有煤炭資源,到礦井工作成為當地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煤礦資源吸引人口集聚,圍繞礦井開店做生意也能獲得不錯的收入。隨著礦產資源逐漸枯竭,到2010年左右,青年一代開始離開村莊,進入全國勞動力市場,男性普遍從事建筑、運輸等體力勞動行業,女性在沒結婚之前會去東部發達地區的工廠里工作。
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使得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在城市生活發展是大部分農村青年的愿望。而在當地卻出現了反向流動的現象,青年男女到了適婚年齡會回到農村老家結婚生子,本地婚仍然是當地主要的婚配模式。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締結方式不同,新時代的本地婚姻是青年男女主動選擇的結果。男性締結婚姻離不開父代的支持,因此男性天然具有本地婚偏好。雖然女性在婚姻市場開放的背景下,擁有更多選擇的權利,能夠通過結婚實現城鄉身份轉化,但當地女性仍然傾向于通過親戚朋友介紹對象,與本地男性結婚。
(二)本地婚偏好產生的原因
1.受教育水平低與身份轉化困境
1980年到2000年左右,是L村的繁華時期,煤礦資源開發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先天資源優勢使本地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整體上來看,本地就業收入與外出務工收入差距不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之當地傳統租放式撫育觀念的影響,L村居民對讀書學習不以為意。“我們小學班里50個同學,上高中的不到10個,一個考上大學的都沒有,家門口就有掙錢的機會,根本沒人想讀書。”(小志,男,32歲,離異未婚)80后青年小志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勉強讀完初中,便去礦井工作了。落后的教育觀念和利益的吸引,使得本地80 后、90后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十分有限。
依靠煤礦資源和體力獲得經濟收入的男性受到教育水平限制的現象并不明顯,但對于女性來說,這一影響隨其進入城市就業立刻被放大。“沒見過世面,也不想那么早嫁人,當時有同村的人去溫州廠里工作,我就跟著去了。在外面的那幾年進過好多廠,大城市也看了不少,但感覺自己什么都不會,學歷也不夠。后來家里給介紹對象,我也到年紀了,回家結婚也挺好。”(小新,女,37歲,已婚)。現代市場賦予了女性更多機會,雖然女性能夠憑借自身努力實現身份轉化,但市場強調“能者為先”,受教育水平低使得農村青年女性的就業和發展受限,在城市中獨立實現身份轉化的難度較大。
2.社會支持與婚姻要價
在個體能力與市場要求不匹配的背景下,通過結婚實現由鄉到城的身份轉化可能會使女性產生依附性。受到現代觀念影響的女性,其個人感受凸顯使其不愿犧牲主動權來換取城市身份,她們更希望自己掌握選擇權和主動權。鄉土社會的優勢在于其基于血緣聯結而成的發達的社會關系網絡。本地婚使得女性不僅能夠與姻親建立聯系,激活社會支持網絡,獲得更多資源,而且能夠利用其在婚姻市場中的性別優勢獲得更多的婚姻選擇權和要價權。所以,對于面臨城鎮化困境的農村女性來說,本地婚成為她們的最優選擇。
三、農村青年男女的戀愛互動
在本地婚偏好的影響下,親戚朋友介紹依然是L村婚姻聯結的主要方式。但與過去的婚姻介紹不同,在現代婚姻締結過程中,介紹只是第一步,其后還要經過漫長的相處,男女雙方才能走進婚姻的殿堂。建立戀愛關系成為婚姻締結的先決條件。
(一)農村女性:主導戀愛與考驗對象
中國當前的性別結構和婚姻市場賦予女性在婚配過程中的優勢地位,使女性擁有更多自主選擇幸福生活的機會和權利,所以對于大部分情侶來說,戀愛環節是由女性主導的,女性成為兩性關系的主導者和戀愛規則的制定者。
過去,受到親代對整體利益考量的影響,女性的擇偶標準為男方經濟收入高和家庭聲譽好等[10]。而在個體訴求日益增長的今天,“對我好”和“處得來”成為女性的首要擇偶標準,女性在戀愛互動中強調個人感受,擇偶的側重點從客觀條件轉變為主觀感受,考驗方式從一次性考驗轉變為持續性考驗。從女性的戀愛特點出發,可以將女性在戀愛互動中的行為概括為制造需求與關鍵時間考驗。
1.制造需求
在女性看來,能夠為自己著想、包容和愛護自己的男性才值得托付終身。為了在親密關系中獲得確定感,女性會主動制造需求看對方能否滿足自己,以評判男性是否真心對自己好。通常這些需求最初要通過消費來滿足,比如雙方約會時,吃飯、看電影必不可少,有時還要逛街買東西,在特殊的日子要有禮物,等等。消費具有可計算性,消費的數額和頻率成為女性初期衡量親密關系是否可以建立的標準。
隨著兩性距離的拉近,女性在對男性產生依賴的同時,會提出更多情感需求。“談戀愛的時候我在溫州打工,他在本地開貨車,經常見不到面肯定擔心啊,我要求他每天都要給我打電話。他做到了,每次一打就是一小時,有時候各干各的沒聊天也不會掛電話。我發現我講了的話他都記得,我感覺他挺寵我。”(小新,女,37歲,已婚)對女性來說,男性能夠付出金錢和時間,為女性帶來持續的心理滿足和情感愉悅十分重要,良性互動會不斷加強女性對婚姻生活的美好想象,如果在戀愛過程中男性能夠符合女性對結婚對象的心理預期,女性就更傾向于結婚。
2.關鍵時間考驗
在L村,逢年過節是介紹對象的高峰期,年輕人從外地回家,有機會與異性見面和相處。但是返回就業地后,男女雙方大多數時間只能通過微信和電話聯系,所以對于長時間不在同一地方的青年男女來說,關鍵時刻的表現變得尤為重要。“女孩都要浪漫,生日是鐵定要過的,不在一起的時候要發紅包、送禮物,在一起的時候還要訂蛋糕、買鮮花,去年我還喊了她的閨蜜們一起吃飯慶祝她生日,吃完飯去唱歌,當然都是我出錢。”(小劉,男,32歲,已婚)生日、節日等都屬于關鍵時間,除此之外,一些對兩人來說有特別意義的日子也可以算作關鍵時間,被納入女性對男性的考驗范圍。“我倆剛處了幾個月,我爸去世了,我在外地,我老公(當時是男朋友)就經常跑到我家幫我媽干農活。我媽被他打動了,打電話跟我夸他,我心里當然高興啦。后來我倆結婚,我媽考慮到我老公家里有兩個弟弟,沒要彩禮,還給我陪(陪嫁)了不少東西。”(小新,女,37歲,已婚)
女性在戀愛互動過程中采用制造需求和關鍵時間考驗的方法對男性進行評價,同時不斷確認自己的主導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即便女性制造需求的行為始終貫穿戀愛過程,這在一定情況下是女性對理想親密關系狀態的訴求,有些要求雖然苛刻,但目的是為男性指明努力的方向。制造需求運用的是“加減法規則”,男性能夠做好當然加分,但即便沒有做好,也不會直接危及兩人的關系。而關鍵時間考驗運用的則是“乘除法規則”。在講述過程中,大部分女性對關鍵時間發生的事件都印象深刻。在關鍵時間,男性的表現如果能給女性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會對親密關系的推進有所助益,相反,如果男性在這些時候沒有表現好,則會對親密關系造成沖擊,導致女性對男性的好感直線下降,可能引發爭吵,甚至關系破裂。
(二)農村男性:底層危機與努力迎合
農村青年婚姻締結的種種表現反映出現代婚姻不再是簡單的外在條件匹配,擇偶標準更加個體化、細致化,配偶選擇變得靈活、主觀、多元,從而導致部分經濟條件、家庭背景、樣貌等方面較好的男性也有可能被“剩下”。
老陶今年72歲,共有四兒一女,老大、老二和老三都在外地買了房子,女兒嫁在本地,經常回來看他,老陶成為別人眼里“最幸福的老人”。但是老陶不這么覺得,他從來不參與村莊活動,也不串門、與人聊天,老兩口拼命掙錢:老陶種著好幾畝地,前幾年在農閑時還跑去浙江做綠化,這幾年在礦上做小工,前前后后掙了萬把塊;老陶的老伴經常去采茶,閑的時候還找各種零工。以老陶的條件,他每天的生活理應悠閑自在,但他總是愁容滿面,原來是因為今年34歲的小兒子還未結婚,這成為兩個老人最大的心病。
在農村,熟人社會環境下,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家族之間的競爭壓力強化了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感,只有兒子結婚,父母才覺得人生圓滿,家族才有面子[11]。在傳統觀念與現代社會發展的雙重影響下,農村青年男性一面承受著責任倫理的壓力,另一面承受著婚姻市場開放帶來的焦慮。他們稍有不慎便會淪為大齡剩男,被迫進入婚姻二級市場甚至退出婚姻市場。農村青年男性正面臨底層危機。
過去農村男性只要能滿足婚姻要價,基本就能實現婚配,所以只有經濟困難或有生理缺陷的男性才會陷入底層危機。而現在,主觀感受主導的婚姻締結方式使得農村男性的婚配壓力越來越大,女性對男性內在條件的要求更高了,農村男性想要結婚,就必須盡快作出調整。因此,男性在戀愛互動的過程中會采用主動出擊和形象塑造的方法,努力實現女性對兩性關系的期望,以提高親密關系的穩定性。
1.主動出擊
在農村男性處于劣勢的婚配環境中,表現主動的男性能夠最先獲得建立親密關系的機會,而被動等待注定難以破解婚姻困境。“我18歲的時候認識我老公,他比我大5歲,當時我倆都在浙江的服裝廠打工,他追的我,后來他就去工地干活了,掙得多些。我倆談了三四年,結婚后我老公才說,當時他去浙江服裝廠打工,就是為了找女朋友,要不然在工廠掙得又少又不自由他才待不住,不過他對我挺好的,我挺知足。”(小許,女,31歲,已婚)小許的老公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了小許的芳心,而小輝今年已經38歲了,還在等待自己的“緣分”。在第一段感情中,小輝比較木訥,不主動與女孩聯系,聊天也不會“起話頭兒”,反而是女方主動一些,一段時間后,女方覺得小輝無趣,便向小輝提出了分手。對于這段感情,小輝認為女方與自己性格不合,“她性格比較強勢,總是她要哪樣就哪樣,我不愿意圍著她轉。”(小輝,男,38歲,未婚)小輝在女友提出分手后就一口答應,也沒有嘗試挽回,覺得可以找到更好的。結果第二個女孩與他第一次見面后就表示不愿意繼續相處,小輝灰心了,一直單身到這個年紀。他講道:“我現在就想找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女孩,但還是要看緣分,實在不行二婚的也成。”(小輝,男,38歲,未婚)在L村,像小輝這樣被動等待戀愛的男青年還有好幾個,他們普遍有幾段短暫的戀愛經歷,被動和等待的態度是他們難以維持戀愛關系的重要原因。
2.形象塑造
當農村男性獲得與女性接觸的機會后,便進入到女性主導的戀愛之中。與女性借助戀愛確認男性是否適合結婚的目的不同,大多數農村男性戀愛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結婚,而只有通過女性考驗的男性才能順利結婚。當農村男性掌握這一要點后,便會在戀愛中處處留心,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塑造成女性心中所希望的形象。“我脾氣比較差,經常會因為一些小事發火,他脾氣好,在小事上還比較照顧我(筆者追問大事指什么,訪談對象想了想,回答是基本沒什么大事),都是先哄我,等我火氣消了之后再給我講道理,我倆現在吵得少了。”(小許,女,31歲,已婚)
與城市青年不同,大部分農村青年由于地理條件限制,一般都會先確定戀愛關系,然后開始相互了解和建立情感聯結,這使得農村青年可能并不是出于個體之間的相互吸引而走到一起,致使“男弱女強”的婚姻市場特征延續到個體互動過程之中,男性自我需求的表達成為“小氣”“計較”和“不包容”。在表達受挫后,男性為了避免產生沖突影響兩人的感情,開始選擇迎合,對于男性來說,讓步、說好話比講道理更容易化解二人之間的沖突。總體而言,當前農村青年男女在戀愛互動的過程中展現出“強勢女性”與“妥協男性”的特征,形成女性主導與男性迎合的相處模式。
四、適應性策略與婚姻締結
人口流動使傳統性別觀念發生轉變[12]。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收入,并逐漸提高了自我認同感,女性的權利意識覺醒。此外,社會資源的分配和流通賦予了農村女性更高的社會地位,現代觀念對農村女性的影響更為明顯,她們希望掙脫原生社會環境,融入城市生活,消費觀念和方式也在逐漸改變。但農村男性受經濟能力和戶籍身份的限制正逐漸被現代社會邊緣化[13],傳統社會的保護以及現代社會的排斥導致農村男性仍保持著傳統婚戀觀,自此兩性之間產生文化價值觀差異。
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婚姻締結具有必要性,對于男性來說,婚姻是家族延續的前提,對于女性來說,婚姻是社會身份的載體。基于婚姻對于個體的重要意義,男女雙方都具有強大的實現婚姻締結的動力。但由于文化價值觀差異,建立親密關系的過程存在較大困難,為了實現婚姻締結,男性率先妥協,在戀愛過程中運用適應性策略化解沖突。
適應性策略是男性為了達成結婚目的,按照女性的要求對自身進行調整的策略,體現在男方為了滿足女方的需求單方面調整自己,最終達成一種不平等的同步。在戀愛互動中,男性采用適應性策略,在資源、權力和空間上均對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讓渡,以維持親密關系并最終實現婚姻締結。
(一)經濟資源讓渡:消費觀念的適應性調整
訪談中,多位男性表示買鮮花和送禮物不實用;衣服不用經常買,夠穿就行;過節最好的方式就是兩個人一起吃頓飯。與此同時,女性同樣認為鮮花不實用,但她們收到鮮花時仍然十分開心,并且都記得自己第一次收到花的樣子;逛街(或網購)在女性看來很重要,把錢花在打扮上很劃算;節日需要有儀式感才能印象深刻。整體上,男性的消費觀念更偏實用,女性的消費觀念更主觀。
在戀愛過程中,女性為了在親密關系中獲得更多的確定感,會考驗男性是否愿意為其消費。男性雖然不贊同,但為了展示自己“不吝嗇”,也會讓渡自己的經濟資源支持女性消費,以獲得女性的好感。因此,兩性之間并沒有針對消費觀念的差異進行調試,而是男性單方面進行適應性調整,在形式上達成與女性消費觀念的一致。
(二)決策權讓渡:家庭角色的適應性調整
在中國傳統的父權文化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及其家庭,男性處于家庭的主導地位,掌握家庭資源的支配權,“男主外、女主內”是傳統家庭的主要表現形態。談及當家權,50后、60后男性直言都是自己當家做主。市場化發展使女性能夠參與就業從而獲得資源和收入,降低了女性對男性及其家庭的依附性,女性有了與男性平等對話的權利。在80后、90后男性的表達中,多有“小事她做主,大事商量著來”的表達。
在L村,男性的弱資源積累、弱就業能力以及半封閉社會環境造就了女性的強勢地位,男性“一言堂”的行為已無法與現實男女社會地位相匹配,男性在戀愛互動中對自身進行適應性調整成為必然。所以,在當地青年的戀愛互動中,角色的調整并非兩性博弈的結果,而是男性單方面進行的適應性調整。現代女性不僅能夠參與決策,而且在大多數時候起到決定性作用。這種情況下,女性獲得決策權并不一定有利于親密關系的發展,因為帶有一定的交換色彩,即通過男性讓渡決策權,女性才能提高自身對親密關系的掌控度和確定感。
(三)私人空間讓渡:生活方式的適應性調整
在L村結婚,房子雖然由男方購買(或建造),但裝修的決定權通常掌握在女方手中。訪談對象小新特意強調,她在十幾年前結婚的時候,沒要彩禮,但要求男方家里一定要把新房子鋪上瓷磚。從裝修這件事能夠看出女性對高質量生活的向往,然而現實能力不足以使其真正在城市生活。基于此,女性對男性是否踏實努力工作十分在意,男性不努力工作會使女性產生危機感,為了避免危機,女性會對男性的個人行為進行管束。比如,結婚后,小志的妻子要求他每周只能和朋友聚一次,并且不能和她認為是不正經的“狐朋狗友”出去喝酒。半城市化的就業方式使得農村青年男性的自律性不高,于是女性想要通過“管”來獲得安全感。訪談對象小志目前離異未婚,他提到結婚前都按照前妻的要求裝修房子,其他方面也遷就對方,但是前妻卻管得越來越多,這些約束在婚前都沒有。男性對個人生活方式的適應性調整,實際上是將其私人空間讓渡出來,換取女性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總而言之,農村男性對自身消費觀念、決策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適應性調整,實際上是用經濟資源、決策權和私人空間換取女性對親密關系的確定感、掌控感和信任感。適應性策略雖然能夠化解兩性沖突,延續親密關系,但并非雙向調試的結果,而是男性單方面妥協的表現,不利于兩性之間建立長期平等的關系。
五、總結與討論
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市場開放刺激主體意識覺醒,城市成為農村青年向往的歸宿,致使資源不足且能力有限的農村家庭被動參與市場競爭,農村家庭的脆弱性凸顯。婚姻締結作為完成家庭再生產的關鍵環節是父子兩代人的共同責任,主體意識加強使得兩性戀愛過程成為影響婚姻締結的重要因素。性別失衡使農村女性在婚姻市場處于優勢地位,可以選擇從農村流向城市,但激烈的市場競爭與有限的就業能力又導致部分農村女性選擇回流。理論上,女性回流給予農村男性更多的選擇機會,有利于緩解農村男青年的婚配壓力,但實際卻呈現出婚配難度提高、婚戀壓力加重的情況,一些條件還不錯的男性也可能遲遲不能結婚。
在當前女性“對我好”和“處得來”的擇偶標準下,能夠快速作出調整以適應女性要求的男性成為農村婚姻市場中的勝利者,而那些被動型男性在與女性的相處中沖突不斷,致使戀愛失敗。兩性相互調試以提高雙方的適配性在親密關系維持的過程中必不可少,但問題在于,現代文化對兩性的影響程度不同使得兩性婚戀觀產生差異,文化價值觀不同降低了兩性的適配性。與城市青年不同,對于農村青年來說,熟人社會環境將其婚姻與家族尊嚴聯系在一起,加之婚姻市場的開放性賦予農村女性更多的選擇機會,農村男性的婚姻處境更加艱難。
因此,在責任倫理和婚姻市場的雙重擠壓下,農村男性青年作出讓渡與妥協的策略選擇。單方面適應性調整是農村男性應對婚配困境,為盡快完成婚姻締結而作出的選擇,雖然能暫時延續戀愛關系,但其背后單方面的妥協與讓渡,加劇了性別不平等,不利于親密關系的長久和穩定。信任是兩性親密關系得以長久并走向婚姻的重要條件[14]。吉登斯認為理想的親密關系是純粹關系,是信任關系,歸根結底是情感交流的問題,在人際間平等的語境中與別人、與自己交流情感[15]。戀愛為兩性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時間和空間,青年應當在戀愛中展現出真實的自己、表達真實的想法,男女雙方要在相互調適的過程中建立起平等的情感關系。穩定且高質量的親密關系不僅能夠使家庭幸福,而且有助于社會安定和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