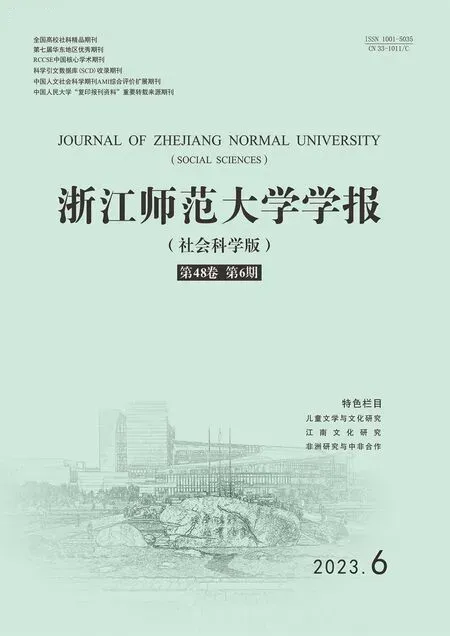實景轉向:《絲綢之路》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自我鏡像
周傳藝, 鄭 淏
(山東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58)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紀錄片的創作大多受到蘇聯的影響,在內容和理念方面都具有明顯的政治化特征。它主要以新聞報道的形式來向全國人民“通報”國家大事,制作內容較為單一,制作方式也比較僵化,被有的國內學者形容為“政治化紀錄片”(1958—1977年)。①1980年播出的《絲綢之路》具有轉折意義:它偏重大量的實景拍攝,改變了以往紀錄片的創作理念和實踐走向。此后,《話說長江》《話說運河》《望長城》等眾多紀實性影片相繼出現,標志著我國紀錄片攝制進入新紀元。這一“實景轉向”,實際上具有雙層指向:改革開放后的影像空間是一層指向,聚焦影片文本自身(主要以影片中的實景為主),偏向于中國的風景紀實;另一層指向則是風景背后蘊藏著我們重建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訴求。實景轉向成了創作者的一個修辭策略,用以表述特定的歷史需求。
米切爾(W.J.T.Mitchell)曾在《風景與權力》(LandscapeandPower)中指出了“風景”背后的罅隙。他認為,風景實際上是一個被建構的過程,準確來講,風景的形成是“社會和主體性身份形成”的過程。[1]在此,米切爾指出了風景與社會和主體身份之間的辯證關系。在他看來,風景只不過是以文化為中介的自然,它“是闡釋性的,其例證就是試圖把風景譯解成各種文本系統”,[1]而重要的是風景背后承載的文化意義編碼和意識形態表述。從這一層面來看,實景在某種程度上是自我的映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實景基于改革開放后的歷史語境具有什么樣的意義?我們緣何需要以“實景”記錄去填補自身的情感結構?實景作為一種“文化表述的媒介”是如何被表征和再現的,又是如何參與協調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認同的?
一、媒介語境:改革開放早期的影像創作
1980年5月1日,由我國中央電視臺和日本放送協會(NHK)合作攝制的《絲綢之路》首播。這部紀錄片一經播出便引發中日兩國的強烈關注。②該片雖以“合拍”的名義完成,但“合拍”僅限于雙方共同投資、組建聯合攝制組、膠片統一(在日本)沖洗、素材的共用,成片的剪輯卻是分開完成的,[2]311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日雙方影片創作的自主性。該片講述了長安至喀什的故事。片中呈現了我國的悠久歷史、大好河山以及獨特的風土人情等,對秦長城、兵馬俑、河西走廊、敦煌莫高窟、玉門關、沙洲故城、月牙泉、黑水城、樓蘭、米蘭遺址、尼雅古城、和田、吐魯番、蘇巴什古城等眾多歷史遺跡進行的“重訪”,有效喚起了廣大觀眾對祖國輝煌歷史和美麗自然風光的自豪情感。1983年,在第一部的基礎上又攝制了《絲綢之路2》,重點記錄走出中國境內后絲綢之路沿途的風景,最終將鏡頭戀戀不舍地停留于“羅馬”。
作為中外首次合作拍攝的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對我國紀錄片的攝制有著重要意義。從題材來看,1949年以來我國很少觸碰文化風光類——過去往往是以時事新聞、軍事政論、政策傳達、文化科技、藝術趣味等為表現內容,旨在宣傳國家的政治、文化、時事等訊息。雖然后期出現了文化風光類的創作,但大部分都僅僅是起點綴作用,并未形成“題材”的主流。從創作理念來看,長期以來,由于特定題材的表現需要,“格里爾遜”(Grierson)模式成為主導我國紀錄片創作的基本模式——其畫面加解說詞的影像形態很大程度上賦予了創作者絕對的話語權。雖然《絲綢之路》整體上還延續“格里爾遜”的創作模式,但開始使用一定篇幅將同期聲插入其中。這一細小的突破在中國紀錄電影史上有著顯著的意義,它意味著我們開始自覺使用實景/紀實的方式來攝制主流紀錄片。這一創新之舉呈燎原之勢,迅速作用于人文地理紀錄片攝制的實踐,并在此后數年間留下一系列較為經典的影像文本:由央視攝制的聚焦長江流域自然風光、風土人情以及沿岸人們生活場景的紀錄片《話說長江》(1983);聚焦運河沿線古跡風光、建設成就、文物存留等情況,并在《話說長江》基礎上增加大量人物采訪與同期聲的《話說運河》(1986);以主持人的視點切入敘事,使用長鏡頭的紀實手段考察長城的修建、變遷,以及記錄長城與當今自然生態與人口遷徙變化的《望長城》(1991)等。該類紀錄片的“紀實性”,賦予了其超過影片本身的價值與意義,它不僅讓我國的人文地理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現在大眾視野中,同時也引導人們關注祖國河山、認知祖國疆域及其背后的人文歷史知識。作為這一影響的“最初”源頭《絲綢之路》,其意義不止于此。基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媒介環境,該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20世紀80年代以降,電視媒介開始替代電影媒介并逐漸成為主流,這是《絲綢之路》橫空出世的媒介前提。20世紀80年代的廣播電視發展策略在“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建設方針指導下出現重要改變——“既要成為群眾獲得各種信息(首先是新聞和政令)的重要來源,又要成為進行教學和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的重要陣地”。[3]也就是說,在實現中央、省、市、縣的四級聯動覆蓋模式的傳播網中,“傳播文化科學知識”成為一個顯性的存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媒介趨向實際上就是由銀幕到熒屏的轉變——十年間,影院的觀影人次不斷遞減,已下降了20%,[4]而這正是電視機開始逐漸進入普通家庭的時期。中國電視機的普及與改革開放是基本同步的。
其二,紀錄片的長篇化、連續性的媒介特性保證了《絲綢之路》敘事的完整性。一方面,不同于電影的媒介形態,紀錄片《絲綢之路》實現了時間之“連續性”與敘事之“完整性”的統一。《絲綢之路》雖然有不同的剪輯版本(CCTV版和NHK版),但其長達數年的播放時間,共17集(CCTV版)的篇幅將跨越兩千多年的,有著厚重歷史感的風俗文化呈現出來。每一集都自成單元,且每個敘事單元都有一個核心的主題,從長安行至羅馬,繪制了一張媒介地形圖。另一方面,播放媒介的“家庭性”潛在地提升了《絲綢之路》的社群影響力。如日本學者藤竹曉所說:“電視使家庭成員團聚在一起,同時又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以電視為媒介,交流各自的經驗。”[5]62事實上,客廳里的電視營造了一種“家庭團圓”的氛圍,實現了家庭成員之間進行文化意義上“對話”的可能。
其三,影視作品的“跨地”拍攝是對既有創作模式的突破。影視作品,尤其是紀錄片的創作,很大程度上是被區域所“綁縛”的。從生產角度來看,紀錄片的攝制資本大都來自政府或個人,缺少商業化運作的社會(或民營)資本,這使其并非像故事片一樣具備較為顯著的大眾性和商業性。因此,區域性的主題表現,更能適應小眾化、個性化、作者性等“反市場”話語。當然,這種“跨地”創作的深層訴求是脫離地方感的“部分表達”而去追求更加宏大的“整體表述”,以適應改革開放后“表述中國”的內在要求。1983年,第一次全國電視節目對外宣傳工作會議通過的《全國電視對外宣傳工作會議紀要》是影視作品宣傳“重心”轉向的一個關鍵綱領,《紀要》中調整了電視外宣功能的指向。此后,中央電視臺首先調整機構,成立專門以對外宣傳為宗旨的節目制作、翻譯和發行部門——對外部。地方電視臺紛紛跟進,到1984年已有19個省臺成立了對外部或對外組。[5]310由“內”到“外”的策略調整,使得“內外”二元的關系結構中,“內部”被表述為一個整體。《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等紀錄片的攝制,都是橫跨多個省份或多個國家的“跨地”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一策略的適配。
由此可見,新時期的媒介環境在“新舊”媒介的交替、文本“內外”的革新中具有了新的接受空間,并產生了與之相應的審美需求。以此為基礎再來反觀《絲綢之路》及其所開創的實景轉向,便會了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改革開放后一代人的文化記憶。但問題在于,無論是對于絲綢之路歷史線路的追尋與重返,還是對線路上國家文化藝術的生動記錄,抑或是對相關考古發掘事業的追溯探訪,該片在新時期“外向型”社會轉型、憧憬未來的同時,卻都“內聚于”歷史悠久、綿延不絕的古老之路,而非當下之路。“實景轉向”于是乎面臨著一個自我的悖論:在面向未來的新時期語境中,“過去”作為一個反向維度卻成為我們尋找自身存在的坐標。因此,在“過去—未來”的時間張力中,我們為何選取“過去”作為表現對象,而不是未來?現實方面,改革開放后,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時代的核心議題,但文學與藝術學領域似乎卻背道而馳——鄉土文學(電影)、尋根文學(電影)、國學等成為書寫現代化的“另類”。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庫斯(Matei Calinescu)曾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了審美現代性(文藝創作)與社會現代性(現實)之間的對立、矛盾抑或分歧之處,作者分別以“歷史—社會學”和“美學—道德”兩種視角去分析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背后的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五個基本概念,[6]發現了“現代性”背后“反現代性”的美學表現。這種美學的獨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表述的需要。那么,改革開放后的現代性語境中,《絲綢之路》這種非現實的“實景”,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表述需要?它與改革開放后的意識形態關聯又是怎樣?
二、風景“深處”:重建民族共同體
《絲綢之路》的“實景”拍攝是中、日兩國合作的。雖然中、日兩個剪輯版本在對待“真實性”問題上的態度有些許差別,③但整體來看,其已顯示出對紀實性影像風格建構的努力。這體現在將紀錄片攝制過程,如貫穿全片的工作人員的測繪、對古代遺跡的探訪、工作人員的日常生活行為,以及考古發掘的實時記錄等畫面鏡頭挪至影像文本中,這一策略早在20世紀蘇聯紀錄電影中就已被嘗試——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創作的《持攝影機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中將隱蔽的攝影機放置到鏡頭中予以呈現。片中,創作者扛著攝影機不斷尋找莫斯科城市的最佳記錄視角,這一“自我暴露”的方式非但未影響到影片內容的敘述,還進一步增強了影片的真實性表述。導演將這一方式稱為“電影眼”(Kino-eye),即比人的眼睛更“真實”地觀看。此后,紀錄片中將攝制主體挪至影像文本中似乎成為“實景”背后更為真實的修辭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紀60年代出現在法國的“真實電影”。這一紀錄電影流派中,讓·魯什(Jean Rouch)等創作者將“在場性思維”進行了藝術性的使用:創作者的“介入”和表演者的“扮演”在銀幕內外的參與、互動、交流等張力中,有效地建構了“真實”(vérité)的內核。這一先鋒性實踐指明了建構真實性所基于的兩種“非真實”:作為再現的“扮演”,以及銀幕外攝制過程的“虛假/假定”。也就是說,“真實”的建構,很多時候需要在其對立面(非真實)中尋找合法性依據。這一策略不僅成為后來紀錄電影中反復使用的語言形式,同時也解決了歷史題材紀錄片中有關“再現”與“真實”的矛盾議題。在《絲綢之路》中,由于題材的特殊性,其拍攝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與歷史遺跡相關的人物與事件,在“再現”與“真實”之間出現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但即使這樣,創作者一般不用或謹慎地使用演員來進行扮演,以避免在歷史場景“再現”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不真實感”。在較少的幾次“扮演”中,也僅僅使用模擬音效等較為單一的手段來進行弱化,如《玄奘天竺天行》(第16集)中敘述玄奘西行的故事時,隨著音樂響起,畫面中出現一個戴著斗笠的騎馬人影,以及一匹馬正在行走的四蹄。創作者已經盡力避免對于人物細微特征的記錄,這樣的一種“再現”也僅停留在對于觀眾的暗示:歷史中的玄奘西行情景。隨著這段行走情景的繼續,紀錄片的畫面停留在了古龜茲遺址——蘇巴什國古城。
紀錄片拍攝自然風景與這一時期巴贊、克拉考爾等紀實電影理論的引進有著內在關聯。改革開放之后,國內影像創作掀起了紀實美學的浪潮。1979年,張暖忻和李陀在《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中,首次將“紀實風格”作為一個審美旨向引入國內。④此后,關于紀實美學的理論和創作迎來一個爆發期。作為國外電影理論譯介陣地的《世界電影》雜志,開始大量刊載紀實理論文章;⑤《沙鷗》《青春祭》《城南舊事》《沒有航標的河流》《大橋下面》等紀實美學的影片也大量出現。今天來看,雖然紀實美學并未持續太久(隨后被以第五代為主的影像美學所替代),同時也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誤讀”,⑥卻是時代選擇的結果。紀實性的美學追求,是對長期以來蘇聯理論體系下的蒙太奇觀念的修正,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我國電影現實主義創作的傳統。從更深層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后“實事求是”的時代要求,在影視創作領域掀起一股“求真之風”——包括這一時期對虛假性的批判、對戲劇性的遠離,都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紀實美學的內在邏輯。雖然實景拍攝是創作者們較為新穎、躍躍欲試的創新形式,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它逐漸被影像化美學所取代,僅成為一個實驗性的語言嘗試,在改革開放后的短期內承擔著某種歷史敘述的功能。
在世界電影發展史中,這一形式語言曾于不同階段相繼出現,如蘇聯“電影眼睛派”、弗拉哈迪(Robert J.Flaherty)和格里爾遜等紀錄電影創作、二戰后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等。需要反思的是,“實景”拍攝中的自然風景根植于一種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它與所處的時代之間是否有一種必然的關聯?較有代表性的是德國曾于魏瑪共和國時期大量出現以高山雄景象征自身“優秀”文化的高山電影(Bergfilm),該類電影的開創者是弗萊堡人阿諾德·范克博士(Dr.Arnold Fanck)“把懸崖與激情、無法接近的峭壁和無法解決的人際沖突結合在一起;每年他都會帶來一部高山上的新作。虛構的元素盡管離奇卻并不妨礙影片中大量高海拔寂靜世界的紀實鏡頭”。[7]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認為,這一類型不同于攝影棚搭建的場景,“如此壯美的鏡頭極力傳播的高山訊息成為許多德國人的信條”,這是階級關系和民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作者富有洞見地指出了風景的記錄與共同體想象之間的關聯。
風景與共同體之間的關聯不止于此。人類學家奧爾韋·勒夫格倫(Orvar Lofgren)曾在《度假》(OnHoliday)一書當中,較為深刻地探討了風景(landscape)在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的作用。日本地理學家志賀重昂,美國人類學家溫迪·達比等學者都論述過“風景”與“民族—國家”之間內在的關聯。再回到《絲綢之路》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發現,絲綢之路的“風景”是由攝制組“在路上”的鏡頭組接而成的——每一集都會出現攝制組工作人員所乘的專車在戈壁、公路、沙漠等環境中穿行的鏡頭,就是在這些鏡頭中,繪制出了長安、樓蘭、吐魯番、天山、帕米爾高原等媒介“地圖”。“地圖”原本就是共同體想象的重要介質,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年再版的《想象的共同體》中,增添了第十章——“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用以分析政府如何通過人口調查、地圖制定和博物館來建構民族主義的認同。[8]159據其論證,在19—20世紀東南亞(泰國、印尼等)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地圖充當了強有力的象征(map-as-logo),“經緯線、地名、河川、海和山脈的記號、鄰國,它們如今是純粹的記號,而不再是世界的指南針了。以這個形狀,地圖遂進入了一個可以無限再生產的系列之中,能夠被轉移到海報、官式圖記、有頭銜的報紙、雜志和教科書封面、桌巾,還有旅館的墻壁上。因其立即可以辨認與隨處可見的特質,作為識別標志的地圖深深地滲透到群眾的想象中”。[8]171在《絲綢之路》第一集《長安古城》中,創作者就已提綱挈領地呈現了整個絲綢之路的“地圖”——它不僅是整個紀錄片劇集和敘述次序的“目錄”,更深層的則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共同體想象的媒介坐標。此后,將地域(行政區域或地形)作為單集劃分標準的編排策略,將重要的城市、河流、盆地、山川等可視化為一張地圖插入每集的敘述,便成為創作者精心設計的“拼圖碎片”——天山南路、河西走廊、吐魯番盆地、交河故城、高昌古城等地貌空間,以及蘭州、武威、西安、張掖等重要的城市,由“碎片”建構絲綢之路完整“地圖”的過程,是紀錄片敘事完整化的過程,亦是圖繪共同體輪廓的過程。
三、自我鏡像:從現代化之路到全球化之路
戴錦華曾指出:“80年代中國知識界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文化策略……事實上成了新時期最有力的意識形態合法化實踐。具體到中國/世界、國家/民族的命題上,則是嘗試在話語實踐范圍內實現‘國家’與‘祖國’概念的剝離。‘國家’被用來指稱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社會主義體制,而祖國則指稱著故鄉家園、土地河山、語言文化、血緣親情與傳統習俗。”[9]這一轉變,是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強化的表現。再返回改革開放初期的影像,“風光”的展現恰恰標識著20世紀70年代末、20世紀80年代初的歷史轉型的結果——它通過強調共同的地緣關系來實現文化共同體的認同,同時修復階級話語曾經造成的創傷與悲情。從這一層面看,“祖國風光”實際上是民族主義寓言的寄托。這一時期,《廬山戀》《漓江春》《神秘的大佛》《大海在呼喚》《牧馬人》等“風光片”的橫空出世,不僅將鏡頭對準了祖國的自然風貌,同時在“風光”的背后有著大量的民族語言的書寫——包括跨國戀、國寶的守護、歸僑的渴望、華僑之子的選擇……自我與世界的關系,是風光片類型外衣下的思維內里。
當然,如果我們把絲綢之路的“路”還原成一個文化地理學概念,便可以發現絲綢之路的“路”有著“歧義叢生”的指向,它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我國改革開放后自我鏡像的真實寫照。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創作,大多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道路”。除《絲綢之路》之外,中央電視臺和青海電視臺聯合攝制的《唐蕃古道》(1987)聚焦唐代以來中原地區去往青海、西藏等地,甚至尼泊爾、印度等國的重要交通要道,該道路因文成公主進藏嫁與松贊干布而聞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紀錄片共包括20集,展現了西部雄渾壯闊、神秘古老的自然風貌和善良、淳樸的西部人民建設、開發家園的工作生活狀況。中央電視臺和黑龍江電視臺聯合攝制的《黃金之路》(1985)以清朝黃金運輸道路為題材,展現了從哈爾濱、大興安嶺到黑河、漠河、額爾古納河之間的地理風貌,探訪了四站、十二站、十八站等深具人文氣息的歷史遺址。中央電視臺同云、川、陜、鄂、渝等地方電視臺合拍的《蜀道》(1988)則從古代長安通往蜀地的必經之路,講述到現代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25集的長度涉及了長江纖道及川江支流的十三條古道、五條鐵路、八條公路干線,“蜀道”不僅成為古代的一個交通空間,更成為當下的映射。此外,以“道路”為主題創作的紀錄片還包括《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等。
在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反復訴說的“道路”,究竟通往何處?我們緣何需要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語境中,對道路的母題加以敘述?其背后的文化邏輯與思維內涵是什么?共性的地方在于,這些道路的時間指向大多是模糊的:既記錄歷史,又指向未來。在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絲綢之路與中國自身是互為指涉的:這條“路”是一條開放之路、面向世界之路。有學者認為:“改革之‘河’的對岸,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宏偉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10]20世紀80年代的響亮口號——“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之中,“現代化”與“世界”分別指向了現代中國之“路”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而“未來”則是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發展趨勢的判斷。《絲綢之路》在后期剪輯時有一處細節,即日本版本每天以黃昏落日作為片尾,而我們更傾向于使用朝陽。[2]312落日與朝陽,成為兩個相反的歷史維度與自我定位,在深層指向了中日兩國的當下處境。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有一被遮蔽的話語體系,即無論“現代化”還是“全球化”都可被定義為一種敘事,這一敘事的邏輯和根源在于歐美中心主義的世界體系及其背后的不對等序列。現代化理論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西方進步而非西方世界則停滯不前”,而這正是一個“深深植根于帝國歷史”的本源問題。[11]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或者說,為了抗衡“現代化”背后的歐美中心主義,“未來”的另一端——“歷史”成為一個可供挖掘的空間,以此凸顯中國的主體性與特殊性。
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作為連接中國東西方的交通要道被人們所熟知。自絲綢之路產生伊始,它就變成了中國的一種特殊符號并被世界所接納。重要的是,絲綢之路開辟了中外交流的篇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充當了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在中國與世界文化的“傳播—接受”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昔日強盛的光輝逐漸被西方世界所遮蔽,原發性的民族主義在時間與空間雙重維度上發生了“迷失”,尋找“出路”成為一個引人深思的議題。因此,絲綢之路成為一次意味深長的文化回溯。這一邏輯在后續翻拍作品中再次得到強化。
2003年,日本NHK電視臺再次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攝制《新絲綢之路》。這次拍攝,中日兩國在資金和人力資源配置等方面各占一半,但是最后呈現的剪輯版本卻截然不同。中國版本突出歷史的敘述,10集中,分別呈現了古代居民生存、考古文物、佛教文化等。⑦作為導演之一的谷大象曾作出解釋:“新版不同老版對絲路古道沿線的紀實報道,而是選擇十處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地方挖掘,每集各自成章,受益于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觀點來自被認可的學術支持,盡可能地還原歷史原貌。”[12]但從文本內容來看,《新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翻拍”。影視作品的“翻拍”一般都基于不同的生產邏輯而呈現——基于跨文化的邏輯,或經典文本再闡釋,又或是資本的商業邏輯等——但從兩個版本的制作團隊一致、文本重合、商業價值并不凸顯三個方面來看,其邏輯似乎并不屬于翻拍的任一序列范疇。雖然新版在技術手段、設備支撐等方面有所提升,但這并非主因。因此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緣何需要《新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紀錄片,雖然是對歷史維度的回溯,但更是對自身的指涉。兩個版本選材重合,卻時隔20余年——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發生轉變的重要黃金時間。1980年的鏡頭里中國境內各地區還是很原始的農耕游牧狀態,青山綠水民風淳樸;而2003年的鏡頭里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商業化帶來的轉變已非常明顯。實景記錄的背后,是中國自我成長之路,也是“面向世界”的全球化之路。中日兩國針對絲路題材的兩次合作,實際意義已超過影視文本本身。《絲綢之路》提供了一個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相互合作、共存的依托。中日兩國原本就是“一衣帶水”的鄰居,兩國人民有著深厚的友誼基礎。《絲綢之路》的攝制,雖然日本站在一個“文化他者”的視角來進行敘述,但歷史上絲綢之路的分支對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有著同樣深刻的影響。因此,這種跨地性能夠規避文化細節的差異,從而引起更廣泛的觀者認同。另外,在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的進程中,“全球化”成為一個愈加鮮明的概念。《新絲綢之路》拍攝時,中國已加入WTO,這一機遇伴隨著挑戰,對我國的發展之路是至關重要的。聚焦西部的“絲綢之路”,與“西部大開發”戰略在某種程度上是吻合的。不管是對于眼前立竿見影的市場,還是未來西部在全國發展戰略的走向,開發西部的經濟、政治意義重大。在這一時期,重拍“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全球化發展中的一個影像闡釋。
結 語
從“實景”到“歷史”再到當下的“現實”,絲綢之路的文本內外,映射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自我鏡像。進入新時代,“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被提出,這一起始中國、聯結亞洲、非洲、歐洲的古代商貿路線再次被賦予了時代意義。“一帶一路”倡議某種意義上是續寫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這一由各國人民歷經艱險、克服萬難開辟出的道路,承載著“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內核。新時代背景下,亞歐各國同樣在發展轉型過程中面臨著共同的訴求與使命,共同建設“一帶一路”成為一個必然選擇。曾經的駝鈴聲、舟楫往來的絲綢之路,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再次被繪制而出,并閃耀著歷史的光輝。
注釋:
①如學者何蘇六將我國紀錄片自1958年至世紀之交劃分為4個時期:政治化紀錄片時期(1958—1977年)、人文化紀錄片時期(1978—1992年)、平民化紀錄片時期(1993—1998年)、社會化紀錄片時期(1999至今)。詳見何蘇六:《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第1頁。
②“拍攝《絲綢之路》,不僅在中國電視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電視史上也是第一次。它的前數集在日本播出后,電視收看率猛增三倍,全國形成了‘絲綢之路熱’”。詳見裴玉章:《從〈絲綢之路〉談日本系列電視片的制作》,《新聞大學》1981年第1期。
③據記載,“渭城朝雨”“祁連山下”等一些片段在拍攝時,我方會對泥濘的路面進行打掃,使用文工團演員來“扮演瓜農”等。這些有組織的拍攝痕跡以及創作者的主觀介入程度,與NHK的“原生態”理念有些許不同。詳見方方:《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第312頁。
④張李二人認為,“世界電影藝術在現代發展的一個趨勢,是電影語言的敘述方式上,越來越擺脫戲劇化的影響,而從各種途徑走向更加電影化”,完成這一過程的重要途徑,就是采用“‘紀實’手法,使影片帶有很強的記錄風格”。詳見張暖忻,李陀:《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電影藝術》1979年第3期。
⑤如《世界電影》1981年第6期連續刊載巴贊的《攝影影像的本體論》《“完整電影”的神話》《杰作:〈溫別爾托·D〉》等。
⑥巴贊的紀實美學理論主要是對蒙太奇理論的顛覆,而蒙太奇理論體現著普多夫金、愛森斯坦等“蘇聯傳統”,并長期影響著我國的創作與觀念。巴贊紀實理論的引入,主要是暗合了我國電影理論界在新時期推翻舊有理論體系的內在需求,而當時并未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便急迫地運用到實踐創作的指導中。
⑦第1—10集分別記錄:羅布泊古代居民生存歷史、伯孜克里克文物的流失、草原民族的遷徙史、佛教文化的傳播、東西價值觀的差異、遺跡和文物保護工作、青海之路上的歷史、黑水城中的歷史、絲綢之路重鎮喀什、歷史上繁榮的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