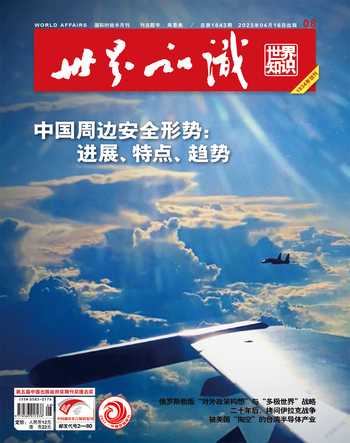國際合作助推全球“氣候適應”
胡玉坤

孟加拉國農民以漂浮農場應對氣候變化。該國可能會在20年內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大面積土地。
遏制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一場生死之戰。全球通力合作致力于深度減排,固然是遏制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而攜手提振“氣候適應”的雄心和行動也刻不容緩。世界各國共同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每個國家都必須審時度勢做出對本國和對世界負責任的明智抉擇。2022年11月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屆締約方大會顯著增強了“氣候適應”的元素和分量,并再次凸顯了團結合作的強烈信號,從而為全球適應努力續寫了新的篇章。
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對人類福祉和地球健康都構成了愈來愈嚴重的威脅。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布的《2022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報告揭示,全球年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0~2019年間處于歷史最高水平。若以世界各國迄今做出的減排承諾來考量,預計到本世紀末全球升溫的中位數將達到3.2攝氏度。但迄今仍沒有使全球變暖迅速停止的任何減排舉措,而溫室氣體的排放卻仍在持續攀升。如此一來,就像節能減排一樣,適應氣候變化的必要性已變得毋庸置疑。
由于各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自然稟賦各異,不同國家的氣候脆弱性及受氣候影響的程度也不盡相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處于氣候變化第一線、深受其害的特別脆弱國家,主要是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所負責任最小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它們有的已被不間斷的氣候災難無情推到了“懸崖”邊上。非洲一些國家仍深陷罕見的氣候災害的“泥潭”無法自拔。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去年底的統計數字,僅非洲之角就有約36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特別脆弱國家幾無能力和資源招架氣候惡變的沉重打擊。
即便是美國這樣實力雄厚的發達經濟體也不堪其苦。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21年逾40%的美國人所生活的縣蒙受過氣候災難。美國在2022年共發生了15起損失超過10億美元的天氣/氣候災害事件。就在圣誕節期間,美國許多州都受到了暴風雪的襲擊。其中紐約州遭遇了該地區幾十年來最致命的暴雪。極端天氣事件通常突如其來,美國也難保不需要外來的緊急馳援。2005年8月那次災難性的卡特里娜颶風襲擊了美國東南部幾個州,致使1800多人遇難,5000余人受傷,經濟損失逾1600億美元。包括聯合國、歐盟、中國在內的數十個國際組織、國家和地區都立即動員起來向美國提供了緊急支持。
不可遏制的全球變暖預示了世界各地的各種極端天氣事件將變得愈加頻繁、嚴重、令人震驚。更酷熱的天氣、更瘋狂的野火、更嚴重的水資源匱缺、更兇猛的風暴和洪災等將會疊加來襲。這就不難理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1年推出的第六份適應差距報告何以冠名為《風暴正在聚集》。這份報告令人信服地揭示,氣候變化影響增大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
不斷上演的各種極端天氣事件讓世界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所有國家都已受到并將繼續受到氣候危機的更大鉗制。凡此種種,既是全球合作遏制氣候變化不力的表現,也是其結果。各國共同面臨的巨大危機理應化作一股合力。大力增進國際合作無疑是對國際和各國政策制定者的一大考驗。
早在全球氣候治理開啟之初,國際社會就將多邊國際合作定位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主要全球機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1988年聯合創建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便是一個明證。作為氣候變化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多邊機構,它主要致力于牽頭開展定期的科學評估,以便為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提供氣候變化及其影響與風險的科學信息,并據此提出相應的減緩和適應策略。深耕30余載的這個多邊機構迄今已涵蓋了195個聯合國成員國,并先后推出了六份重量級的權威評估報告。
“氣候適應”的國際探索長期在迷霧中緩緩行進,已走過了30年歷程。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頗有遠見地設計了“減緩”和“適應”兩大戰略,但其主要囿于國家層面的行動。而且自從發軔之初,盡管兩者總被相提并論,但減排向來被當作頭等大事,在國際政策和實踐舞臺上長期唱主角。值得注意的是,“減緩”是一個舉世受益的全球性問題、而“適應”主要只給局部地方帶來益處的論調一直不絕于耳,至今還大有市場。這種失之偏頗的認知和敘事也使各國的適應行動各行其是,強有力的國際合作則姍姍來遲。

2022年11月6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COP27)在埃及海濱城市沙姆沙伊赫開幕。
由于極端天氣事件的不斷緊逼,全球適應行動終于提上了國際氣候治理的議程。2015年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的《巴黎協定》破天荒地確立了一個具有風向標意義的全球適應目標,即“提高適應能力,增強韌性并降低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以期對可持續發展有所貢獻”。這個新藍圖明確載明:“各締約方承認適應是所有人都面臨的一個全球性挑戰,具有地方、國家以下各級、國家、區域及國際的維度”。這個國際條約還圍繞全球盤點、透明度框架尤其是氣候融資等議題設計了相關條款。這些都為助推各締約方將承諾化作實踐鋪平了道路。
30多年來,在諸多推力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氣候治理的天平逐漸開始朝著“適應”端傾斜。在后《巴黎協定》時代,各級政策制定者都面臨向低碳和氣候韌性轉型的巨大挑戰。聯合國系統內外打“頭陣”的一些多邊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環境署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等,都不約而同開始瞄準適應干預,并撬動了一些可圈可點的探索性項目。形形色色的多邊適應項目正在醞釀或起步之中,呈現出良好的國際合作勢頭。“氣候適應”在國際發展舞臺上的政治能見度也大為提升。
不過,世界各國的適應努力很不平衡,其動機和雄心也不是鐵板一塊的。一些飽受災害蹂躪的脆弱國家得益于多邊或雙邊國際合作項目的助力,成為走在世界前列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例如,尼泊爾2021年出臺了《國家適應計劃2021~2050》。該國政府誓言,2030年之前它所有753個地方政府都將制訂并實施具有氣候韌性和性別敏感性(由于女性受氣候變化影響尤其嚴重,國際社會十分注重任何發展項目包括環境項目的性別敏感性)的適應計劃。中國于2022年6月出臺了《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展現了與世界同步共同推進“氣候適應”的雄心和藍圖。
從發展脈絡看來,國際合作盡管日漸增強,但仍是薄弱環節,也堪稱一個“瓶頸”。環顧全球,袖手旁觀者有之,“搭便車者”亦有之。諸多壓倒性證據也表明,全球適應方面集體行動的力度還遠不足以抵御全球氣候緊急情況。
大量國際經驗證明,國際發展合作是有效處理全球性重大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氣候變化愈演愈烈的新常態下,通力團結合作無疑是造福人類的一把“利劍”。其原因大抵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如氣候變化這樣極富挑戰性的全球事務需要有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人類同在惟一的星球上,誠如新加坡知名學者馬凱碩一語道破的:所有地球人生活在同一艘船的193個獨立船艙里。高度不確定的氣候威脅不分國界,沒有任何國家能置身事外。齊心協力的集體行動是降低氣候變化影響的最佳路徑。強化國際合作有利于優勢互補、經驗互鑒。
第二,發達國家為其長期碳排放負責并為此“買單”合情也合理。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等特別脆弱國家的碳排放最少,受害卻最為深重。有的國家已不幸“淪陷”,生計和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可持續發展也嚴重受阻。由于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最不具備應對能力的這些國家單憑自身資源幾無走出氣候變化陰霾的可能性。
第三,全球“氣候適應”和韌性上要取得突破,取決于發達國家攜手填補氣候融資上的巨大缺口。發達國家至今仍未完全兌現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幫助貧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經合組織的統計分析揭示,2019年發達國家總共提供了796億美元氣候資金,比2018年僅增長了2%。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資金總額中所占的份額分別僅為尷尬的15.4%和1.5%。彌合籌資缺口既是實現全球氣候公正的一個主要癥結,也是拯救生命和保護生計的關鍵所在。
第四,在全球互聯的現代世界,增強所有國家氣候適應的能力和韌性對每個國家都是利好之舉。撇開富裕國家援助貧窮受害國的道義責任不說,氣候危機正在顯著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現存全球經濟體系中內嵌的不平等。如果聽任“氣候適應”的鴻溝繼續擴大,勢必累及全球氣候治理的整體進步和人類的整體利益。提振氣候領域的國際合作也是實現“不讓一個人掉鏈子”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
第五,極端天氣事件的侵襲似乎看不到盡頭。新冠疫情的三年大流行昭示,攻克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系統性風險離不開各國的共同努力。正是全球科學家爭分奪秒攜手研發并及時推出了多種疫苗,加上普及接種的國際和國家努力,全世界才迎來了走出疫情的曙光。經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洗禮”,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切認識到同心協力拯救地球的共同使命。
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國際合作是增加勝算的最優抉擇,也是惟一出路。各國須彌合分歧、凝聚共識,明智而大膽地提振“氣候適應”的雄心和行動,打贏這場嚴峻的“生死之戰”,從而為地球也為人類自身創造一個可持續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