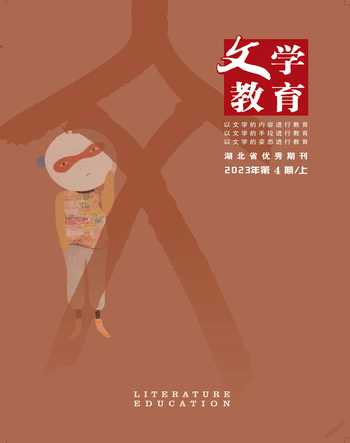梁曉聲《人世間》的工業化書寫
張海東
內容摘要:梁曉聲小說《人世間》以社會變革故事為基準,在現代小說寓意的探索和在工業小說書寫特色的開創方面彰顯了其獨特的文學價值。通過對中國當代歷史進行深廣描摹,立體地呈現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總體的發展演進狀況,并在其百萬字的篇幅中,對工業變遷中的人世沉浮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寫,其中既有人物的命運起伏,也有工業改革理性化的全景展示,這種真實的、時代性的工業書寫得益于作者的成長經歷,脫胎于個人思考,在文本中則表現為站在全知視角上,以時間為軸來從社會、民生、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角度對歷史進行復現,與此同時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獨具匠心,突出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總體性思考,彰顯出作品史詩性的恢宏。
關鍵詞:梁曉聲 《人世間》 工業化書寫
如果說在八九十年代中相繼發表的幾部知青作品構成了梁曉聲文學創作的基本底色,那么進入新的創作周期,面臨著如何為作品賦予更廣的視角和更深的內涵這一難題,作家給出了他獨特的思考:以工業城市五十年的歷史變遷為敘述場域,以普通工人周秉昆一家的命運為故事核心,將一個在歷史長河之中、民族行進歲月里的工業化改革勾勒出來,并予其深廣描摹、精心復現,力求講出半個世紀中最真實、最深刻的工業化變遷故事。
一.《人世間》中工業化敘事方法的選擇
東北地區的工業文學相較于其他地域的文人書寫會更多地受到歷史慣性的影響①,這種慣性由血緣作為紐帶,包含兩代甚至是三代人對整個東北工業區由盛轉衰的共同記憶,其中顯現著他們在大廠之中獨特的精神生活體驗。梁曉聲是在哈爾濱成長起來的作家,親身感受過改革開放后東北工業區中的生活,其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下崗潮勢必給他以及像他一樣生活在東北這塊土地上的平凡人留下眾多刻骨銘心的記憶,這種浮動于時代潮流之上,同時夾雜著個人記憶的題材是梁曉聲進行文學藝術加工的基礎[1]。作為工人子弟,勢必該為流逝的歲月做些紀念,于是那些下崗工人的子一輩開始直擊工業題材的創作,而梁曉聲的《人世間》則通過設置子一輩和老一輩、過去和現在的聯系,不去追求地域歷史文化中的生命形態與生活方式②,更加看重老中青三代人在當代東北社會的生活體驗,通過人物的精神狀態呈現出個性化的形象,如此讓讀者能夠一探站在歷史大潮之中的人們的所思所想。在作品的書寫中,作家力求全面展現出東北工業區的輝煌與衰落在個人記憶中的景象,在敘述方式上,選擇以不帶主觀情感的敘事、簡單直接的口語對話、白描的環境渲染以及對細枝末節的刻意避免,但同時《人世間》中的這種敘事語言因題材的原因導致其必會受制于歷史語境的影響,其中人物的生活思想狀態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變化,所以作品在選擇第三人稱敘事的同時又以各色人物為中心,讓作品中的語言深含個人化的意味:當時間浮動于上世紀60、70年代時,作品中的工人的形象是高大的,“大三線”工人周志剛驕傲地稱自己為“領導階級”和“新中國的第一代工人”,而那些工人之后則被譽為“紅五代”,他們在當時是國家光榮的建設者,同時也是有著“敢叫日月換青天”豪氣的勇士;八十年代之后,整個作品的基調為之一變,故事場景也遠遠不再局限于幾個工廠之內,開始更多地敘說各家之中的喜怒哀樂,這種書寫本身就回扣了全景的書寫布局,將目光進行播撒,觸角力求更廣地接觸到更多的人,正如將江邊的建筑民夫和拉小車的下崗工人融于敘事中,用他們來反映工業變革之下的普眾生活,意蘊更加深刻。除了在視角上進行時空變化,作品在情感的舒陳方面也有所思量,書寫帶有疼痛的歷史,本身的情感就將是冷淡的,梁曉聲將書寫的內容進行了“東北式”的加工,比如以東北地區的城市建筑為背景,人物對話上加入東北式的幽默語料,情節故事表現東北人民豪情的哥們義氣,如此調控,從而略微地減輕悲歡離合的文本故事中的殘酷和冷峻,展現出苦難歷史時期崇高樂觀的生命境界。但既然選擇以歷史為軸,那么在“真實的歷史”的約束之下,落在筆尖下的文字就要表現出工業轉折時期普通大眾的真實生活,90年代的東北工業城市是脆弱的,各種問題堆積,人民生活折戟,但更深刻的是在心理上有了在自我縱向歷史落差對比和了解了南北橫向經濟發展鴻溝現實之后的蒼涼與無奈,塑造出一種歷史的灰敗感。作品中的工業城市帶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標記,其中的某些場景在冥冥之中推動著故事的發展,使得文本的結局產生了些宿命的意味,如作家常常直接在文本里用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地名,如“共樂區”“光字片”“醬油廠”“人民電影院”(原型城市中曾經的真實地名)等,這些地名是工業時期的產物,脫胎于早期工業化,承載著一代人的記憶,但當市場經濟全面形成后,東北工業區一系列積重難返的問題相繼出現——原本的工業住宅區破敗不堪、國企工廠陷入發展泥沼、大批工人失業下崗、老年人的退休金和治病補貼得不到保障……,這些內容塑造的圖景就使得《人世間》中的文本表現出一種搖搖欲墜的“消亡感”和今非昔比的“哀嘆感”,最后的“光子片”拆遷或許就代表著這種過往歷史的徹底消逝。
二.工業化變遷下的平民社會建構
經濟制度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往往能夠深層次地影響到個人的生活和發展,而《人世間》中的社會建構則深深打上當代工業變遷的烙印,首先是家庭關系架構,以周家為例,周志剛身為新中國“大三線”工人,需要在政策的規劃下去往各地參加建設,這就使得在以父親為一家之主的年代里,周家的孩子往往缺少與父親的溝通交流,作品中幾次較為深刻的談心還多是以書信的形式來表現,而母親單一人又難以很好地對子女進行管束,對子女的情感變化更是難以揣摩,這或許也是周家三兄妹性格獨立而又特殊的一大重要原因,盡管周志剛日后退休重回故里,可隔閡已經產生,矛盾的爆發也常常在所難免。再就是社會人際關系的建構,當工業化的時間點落在改革開放之前時,計劃生產式的工廠和分配型的任人制度結合成一張無形的手,不僅安排了普通民眾的工作生活,同樣地也間接規劃好了人們的人際關系,舉例而言,1974年以前周秉昆以及他的父母在這座城市最大的友情來源就是同在工業區內居住的人物,這一現象在其他書寫東北工業化變遷的作家如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筆下則更為突出[2],除此之外,人物自身所工作的工廠環境更是自身友誼圈定性的重要因素,如還在木材廠工作時,周秉昆的社會人際關系最主要與同廠的肖國慶、孫趕超幾人相連,等到了醬油廠則有了與曹德寶、呂川和常進步等人的新聯系,并形成了“六小君子”的格局,故事才得以進一步發展。與此相同,時代變化造成工業變遷不斷,個人命運也會隨之不斷改變,周秉昆以后無論是進工廠,入報社,還是做小工,干“拉腳”,抑或是開飯店等情節都為他重新編織了新的關系網,沿著這些線索不斷生發出新的故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生的走向,正如書中所說——“對于底層青年們而言,友誼是必須認真對待的”,所以身在一個工業化元素特別飽滿的地域和時代里,與工業變遷緊密相連的親情友情的建構勢必為他們這些從集體工廠出來的人所珍視,從而展現出艱苦歲月下特殊的真情與忠義。另外,在情感認同方面作品則以情緒深境中的共鳴來架構,對當下時代有集體認同,這是梁曉聲賦予作品中大多數人物的特性,并且人物關系由此鋪設開來,舉例來說,當文本故事還停留在“文革”結束前時,書中大多數人物的故事集中表現出一種受壓抑的悲苦,在周秉昆家體現為周家人因各種政治原因四處流散,在木材廠和醬油廠的人們則表現為半工業化低效率的集體勞作帶來的身心壓力,在光字片其他人家中則因缺衣少穿和政治沖擊而普遍地遭受苦難,之后時期的人物故事也同理可推。人會因為相同的心理體驗而互相聯結,在這里作家的想象為他提供了一種表達立場的便利③,因為“真實的生活是浩瀚無邊的,一個人不可能了解整體和所有千差萬別的局部”[3],但書中所表現的苦難時代下各個階層人民的生活表明在時代的洪流中所有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內容沒有雷同,各家有各家的不幸,悲苦穿插不斷,那么如何來解釋《人世間》中的人物受難的普遍性,作家在敘述人物故事時又是作何思考?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眾所周知,《人世間》是一部描寫了當代中國五十年社會變遷的小說,那么作者適當地以旁白的方式對故事人物所處的時代進行一些客觀評論,或者直接通過人物的言論來對所處時代進行優劣圈點式的追問將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這在很多優秀的長篇小說如《平凡的世界》中也有所體現,但在《人世間》中,這種本該出現的語段卻難以尋見,筆者于此將兩個問題相連提出自身的思考:作者以工業變遷為軸,不直言紛繁的社會現狀,而通過各種工業化的元素來聯結人物,以普遍性的人世滄桑醞釀大致相同的情感,在這種情感抒發和故事敘事中來表達一個地域之下普通人與時代的共振,以書中描述的80年代后的故事為例,周秉昆、白笑川等人南下演出,雖得到了一定的經濟收入,但“似乎每個人都遭受了精神重創”;周秉義在任副市長時南下招商引資時的所見所聞,使得他更加堅定了改造城市的決心;周秉昆、曹德寶、常進步回到之前的木材廠,發現木材廠因為南方加工廠進駐東北而導致破產,此時他們有些人之間的階級已經大不相同,但都不約而同地因為某些經歷生發出相同的情感,即關照對比不同地區的發展而表現出對現實的感慨和追求現代文明的焦灼,從而催發出東北人自立自強的吶喊,這種情感使他們之間得以聯結,并由眾多個體情感反映出當下工業變遷中人們的難處與困境,由此匯聚成九十年代東北發展的現實圖景。
三.《人世間》工業化書寫的價值意義
《人世間》所描寫的時代之變包含著梁曉聲本人深切的生命體驗,其表達了作者對地域民族思想的深切社會關懷,《人世間》是一部描寫東北城市50年歷史變遷的作品,當我們將作品中不同年代的內容結合起來比較閱讀,并將工業化變遷視角作為凸透鏡對文章主旨進行放大,就能從作品的歷史敘事中察覺出人物共性話題正經歷著由隱到顯的波動,主旨也不再局限于當下,而延伸至更遠的地方——地域民族性。文本在1978年之前的主要內容以鄰里相睦故事和工廠勞作記錄為主,選擇不直言“文革”這場對人們生活有重大沖擊的政治運動,而是落筆于生活細微之處,真正地展現命運場中人物的生命律動。但身在動蕩的十年中,是不可能完全脫離“文革”話語的,這時作家選擇大篇幅地來對當地的工業化進行深廣書寫,將區屬的兩座工廠中的運作模式、工廠制度、生產流程、工人情義等內容進行了細致刻畫,這就反映出就算是在政治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里人民生活才是人世間的主題,從而彰顯出日常生活對政治革命的解構功能。但梁曉聲是一個追求真實的作家,他不可能對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視而不見,所以在兩大主要內容之外,他寫了真實的悲苦——周秉昆家親人之間的千里之隔、鄭娟家的貧窮無助、受冤韓偉的自殺、軍工廠工人的沉痛吶喊以及其他一瞥便可見的下層人民普遍的缺衣少穿,集中表現出人世間的悲苦,當故事發展到80年代時,這種局面就大大改變了,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本地工業的發展受阻幾乎影響了全市所有的人,以工業立城的城市出現了工業轉型的難題,這個問題牽扯甚多,解決甚難,沒有借鑒的前例,矛盾也逐漸擴大,由此人與城的特殊境遇引出傳統與現代、科學理性與主觀信仰、城市與鄉村、文化與習俗、價值與判斷、動與靜等多元存在,在這時各種反思、求進的思想開始在人物的意識中覺醒,同時真正體現作者創作主旨和文本意義的敘事就在這一時期開始逐漸顯現。此時文本的主要內容表現為深陷困境中的工業轉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大批次的工人下崗,本地工業不斷遭受到外地工業的侵襲,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這種現實境遇使得人們不得不去思考未來的出路,由此周秉昆所在的雜志社開始成立演出活動部擴展業務并進行部門制度改革,周秉義所任職的軍工廠開始嘗試改變經營方式尋求出入,孫趕超等人則開始擺攤、跑腿、拉貨自謀出入,其他涉及工廠員工生活的敘述也都在講述他們對現實的憂慮和對未來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社會矛盾沖突大大加劇的歷史敘述中,梁曉聲卻始終保持“平靜”的敘述,以娓娓道來的方式將深刻的求進意識展現出來,構造出了一種靜穆的張力[4]。此時人們只是痛感生活的艱難,還沒有進行深層次的反思,等到故事發展到中部第十章后,終于有人開始集中地對現實的慘淡加以思考了,這時白笑川與周秉昆就南下演出的經歷談論自己的感受,他將停滯的東北與快速發展的南方城市進行比較,在敘述過程中類似“精神創傷”一類的詞用了14次,但此時周秉昆還是有所不甘,準備物色演員、歌手發展新產業,但結果是“有才能的,十之八九都走了”,最后周秉義從周秉昆那知道了事情原委,道出了當下東北的境遇——“東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這種覺醒開始慢慢擴展到其他的人,到最后,就連鄭娟也為光字片愈加臟亂的景象而心生感慨,這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生活慘淡的原因,身陷囹圄的東北這時也真正開始進行變革。到了新世紀,這種欲求喚醒人們思想的主題意蘊已經是噴薄欲出了[5],一封《難道只有下崗工人心疼下崗工人嗎》的群眾來信能激起全市人民的探討,各種社會改良方案也通過對話的形式不斷展現,緊接著各種新事物不斷涌現:新的工作、新的住所、新的街道、新的社會……,每個人都在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他們跟上時代,在享受社會福利的同時創造紅利,故事的結尾,作家對A市的圖景進行了美好描繪,其中雖有主觀化的書寫意愿,但這卻也展現出了歷經苦難的人們最終過上幸福日子的理想情懷,鼓舞著我們不斷為美好未來而努力奮斗。由此通過將《人世間》中的三個年代中的人物故事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出以上幾個時間段的敘述中梁曉聲不斷凸顯民族生活和民族性,進而獲得一種呼喚地域民族精神覺醒的超越性價值。
參考文獻
[1]梁曉聲.我與文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124.
[2]何青志主編.東北文學通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8:129-134.
[3](蘇)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89.
[4]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55.
[5]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56-62.
注 釋
①②張浩,武兆雨.新東北作家群筆下的工業書寫[J].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22(05):110.
③譚天.現實主義寫作的特質和詩性呈現機制——以梁曉聲《人世間》為中心的考察[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04):110-111.
本文系黑龍江大學2022年度國家創新訓練計劃課題“梁曉聲小說《人世間》的工業化書寫研究”(S202210212173)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