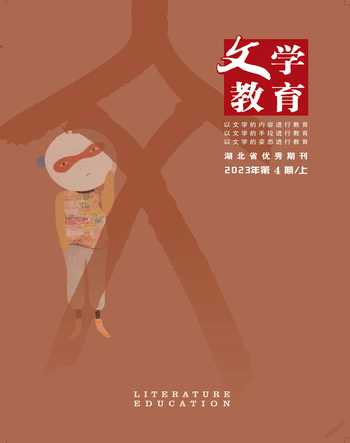沈亞之傳奇:純然的悲劇寫作
沈婧懿
內容摘要:沈亞之的傳奇作品被人誤解為“名檢掃地”“為文造情”“賣弄詩才”等等,本文對以上誤解提出反駁,指出沈亞之運用了十分高級的寫作手法,將其作品處理為純然的悲劇:在傳奇作品的內容編排和人物塑造上,寫幻而不重幻,著力于塑造詩意氛圍,渲染哀婉意境;在寫作手法上,淡化故事情節,模糊作品主旨,注重細部描寫,以獨特的敘述節奏完成純然的悲劇寫作。
關鍵詞:沈亞之 湘中怨解 異夢錄 秦夢記 悲劇
唐代文人沈亞之詩賦文俱佳,在唐代時,以詩顯名,其詩被稱為“沈下賢體”;時至今日,人們了解沈亞之多是通過他的傳奇小說,魯迅在《唐宋傳奇集》中收錄沈亞之三篇傳奇文《湘中怨解》、《異夢錄》、《秦夢記》,并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沈亞之道:“皆以華艷之筆,敘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i
然而從古至今,沈亞之卻是收獲許多誤解,且不提他在仕途上的歷盡磨難遭人毀謗,單看他的文學成就,也遭到一些惡評,古有劉克莊批評《秦夢記》:“唐人敘述傳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韋朗,無雙事,托之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敘,猶藉張生為名。唯沈下賢秦夢記、僧儒周秦行紀、李群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掃地。”ii到了現代,石昌渝說:“沈亞之夢中與弄玉成婚的奇幻之極。此篇大旨不在寫‘我’與弄玉的情愛,而在賣弄追到弄玉的這首詩歌,為文而造情,這情就像絢麗的紙花缺乏實感。”iii李宗為也認為:“沈亞之的傳奇,鑄詞用字不落蹊徑,與一般唐人傳奇文字的婉縟流麗異趣而頗有特色;但他的作品在情節發展上缺乏創造性的構思,思想內容和細節描寫也都比較貧乏,故其成就是遠不如李公佐的。”iv
筆者以為,沈亞之的傳奇其實受到了低估,其傳奇創作實則運用了十分高級的寫作手法,他將自己筆下的傳奇經營成純然的、唯美的悲劇,使其從始至終縈繞著惆悵哀婉的詩意氛圍,給人以美的享受、身心的滌蕩。
一.純然悲劇的故事內容
沈亞之的傳奇作品多以人神遇合、幻夢奇遇為主題,以得而復失為故事結局,類似的題材和故事發展脈絡體現出亞之在小說題材的選擇上的傾向。魯迅說亞之“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其實不然,通讀唐代傳奇便可以發現,唐代的傳奇小說中有許多鬼怪仙靈、死生夢幻的內容,這與時代風尚不無關系,并不代表亞之獨好此種題材,然而亞之的特點在于,他對于仙鬼復死題材的寫作,并不十分著眼于怪奇,而是更著重刻畫悲。
世間最悲,莫過于生離死別,不論是《湘中怨解》中的鄭生與汜人不復相見,還是《異夢錄》里邢鳳夢中的美人泫然辭去,又或是《秦夢記》中弄玉忽無疾卒,都給小說烙上了難以抹去的悲傷印記。然而亞之小說之悲遠不止存在于結局,若仔細品讀便可發現,其小說從始至終無不籠罩著惆悵氛圍。在《湘中怨解》中,天剛蒙蒙亮,洛橋下便傳來了女子的哭聲,凌晨出行的大學進士鄭生聞聲尋去,竟是一位美艷的女子在河邊要自殺,而她自殺的原因竟是遭嫂嫂虐待;誰能忍心見一位美麗的女子遭此不幸只得輕生呢,小說開篇即令人如見美玉蒙塵、嬌花受狂風摧殘一般心痛。鄭生的拯救當然是這位叫汜人的女子生命中的曦光,在隨鄭生生活的日子里,她可以誦著楚辭,寫著美麗的辭賦,鄭生作為有學識的男子,對于她的才華,流露出的是欣賞與驚嘆而非男權社會的指責與恐慌;對于鄭生來說,汜人的出現又何嘗不是生命中平添的一抹亮色呢?她不僅用美麗與才華為鄭生的生活驅走乏味,更用一匹奇珍織品換取千金,為鄭生解決了生活的貧困問題。可是愉快的生活是何其短暫,幾年后,鄭生帶著汜人來長安游玩,當天晚上兩人就經歷了離別,汜人對鄭生說:“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站在鄭生的角度,這一切該是多么的突然,多么的猝不及防,原來這些年與自己相濡以沫的竟非凡人,而他們愉快的時光就要這樣戛然而止了;站在汜人的角度,她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與鄭生的愛戀終有離別時候,但她忍著悲傷不斷地欺瞞,獨自在欺騙愛人的自責和等待別期的煎熬中度日。兩人相對垂淚,這一幕實在是令人不忍。鄭生再三挽留,卻無法阻止離別的發生。十幾年以后,鄭生的哥哥做了岳州的刺史,在某年的上巳節,鄭生與家人們在岳陽樓上參加哥哥的宴席,雖然從文中無從知曉鄭生這幾年的經歷,但從字里行間不難發現,鄭生仍是不如意的,況且現在的他已沒有了知心愛侶的陪伴,哀怨應該更勝從前,所以在這歡飲之時,只有鄭生愁容滿面,如當年的汜人一般吟出了楚辭:“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此時奇幻發生,汜人在華美隆重的排場中登場,在水面之上一邊起舞,一邊唱著楚辭,再度以楚辭訴說哀怨。鄭生與汜人隔水相望,從此以后,不復再見。故事戛然而止,徒留無限惆悵,叫人回味。
寫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的《異夢錄》中,邢鳳夢見的美人也因離別而傷感落淚,但這與汜人和鄭生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是全然不同的。邢鳳作為一個“無他能”的“帥家子”,面對忽然出現的古典美人,雖“大悅”,卻不懂欣賞,面對動人的《春陽曲》和“弓彎”舞,邢鳳顯得呆滯無感,說不出什么有內容的贊賞之詞,也沒有什么受觸動的表現,顯然,他欣賞不了美人之美,只是單純地迷戀聲色,所以一覺醒來,他甚至一度忘了自己曾在夢中有過這樣一段神奇經歷,絕不似鄭生那般戀戀不舍。而對美人來說,她在舊宅中孤寂度日,難得見到的男人只是為她的容貌和這夜的艷遇感到欣喜,面對表達少女思春孤獨等候的動人詩篇,也只是問一些毫無內涵的內容:“何謂弓彎?”于是,美人在向邢鳳展示了弓彎舞之后“泫然浪久,即辭去”。
而《秦夢記》更是徹頭徹尾的悲劇了,亞之于現實生活中無法求得的大展宏圖的機會,在夢中入古秦國得以實現,但榮華富貴,出入禁衛,全仰仗公主弄玉才能得到:在弄玉的夫婿蕭史死之前,縱亞之為秦穆公立下汗馬功勞,也不見什么大的賞賜,文中“居久之”三字便概括了亞之奪下五城后的結果;蕭史一死,秦穆公就為公主另覓駙馬,這才想起了亞之,亞之這才得以“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住到了皇宮里,然而“民間猶謂蕭家公主”,亞之也仍“備位下大夫”,只“由公主故”,才能夠“出入禁衛”;公主生日,亞之也拿不出什么珍貴禮物贈送,足見亞之地位之微。弄玉“忽無疾卒”,對亞之而言無異于晴天霹靂,一方面,亞之與公主雖不似尋常夫妻如膠似漆,卻也堪稱持重和睦,公主之死,令亞之悲痛欲絕,接連寫下數篇悼亡之作;另一方面,秦王很快就以見到亞之便會思念女兒的理由將亞之遣送出國。而亞之直至夢醒仍悵然若失,自問“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這三篇亞之的代表作使人讀完悵然若失,郁郁難平;文中大篇幅的詩詞文辭婉轉哀怨,余韻悠長,即便不懂詩文,也要被亞之渲染的詩意意境所打動。結合亞之生平,更能深刻理解這三篇傳奇中的悲劇所在,亞之雖出生吳興望族沈氏,但卻困厄終生,生活上,貧困使他不得不向他人乞食(“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托其食給。旦營其書,書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仆馬不以恙,即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勞,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埇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上壽州李大夫書》);仕途上,三黜禮部v,二敗制科vi,貶謫南康vii,歷盡艱難還不為人所理解,生前與死后都遭人非議(“郢崖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下:詰之既深,焉得默默已也?”《上九江鄭使君書》);情感生活也十分悲涼,與他恩愛互持的一妻一妾分別死在了他進士及第的前后,他孤苦伶仃地過完了艱難的余生。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初,科考已三次受挫的亞之總算進士及第,可他的愛妾盧金蘭卻死在了幾個月前的冬天,也是這一年,亞之寫下了《異夢錄》,那個讀著《春陽曲》、跳著弓彎舞的夢中美人,是否有著善跳“綠腰”“玉樹”viii、美麗聰慧的盧金蘭的影子?元和十三年(818),亞之的妻子姚氏因病去世,這一年,亞之寫下了《湘中怨解》,鄭生隔江遙望汜人,終不能改變仙人殊途的結局,不也正如失去妻子姚氏后的亞之獨自在人間受苦嗎?更毋寧說,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寫就的《秦夢記》里,亞之在古秦國的短暫輝煌,正如他在現實中以為自己打通了向上途徑、可以大展身手的錯覺一樣,終是幻夢一場。
二.刻畫悲劇的寫作手法
亞之的傳奇作品自古以來面臨著不少爭議,有觀點認為亞之的傳奇是“為文造情”,“缺乏實感”,也有觀點認為亞之的傳奇“在情節發展上缺乏創造性的構思”,“思想內容和細節描寫也都比較貧乏”,筆者擬在此為亞之做一辯解。在筆者看來,亞之的傳奇小說寫作方法非常高級,甚至對于悲劇的編排和塑造頗有西方現代派的意味。
亞之的傳奇小說有意淡化情節,甚至連主旨也十分模糊,而且常常進展直接,有時會給人以撲朔迷離的突兀之感,無怪乎會被解讀為游戲好奇之作。比如《湘中怨解》中的汜人在和鄭生在長安游玩時忽然道出自己的真實身份,隨即離去,令讀者與鄭生一樣錯愕,《秦夢記》中既沒有交代駙馬蕭史的死因,對弄玉的死也全無鋪墊,一句“公主忽無疾卒”,無比突然,速度極快地將故事情節向前推進,《異夢錄》的故事情節極其簡單,一位古代美人在邢鳳夢中忽然出現又忽然離去,人們不知她究竟經歷過什么,凡此種種令亞之傳奇收獲了“缺乏實感”的評價。
細讀這三篇傳奇便可發現,亞之對主線情節的推進所花筆墨極少,在情節的關鍵轉折點上敘事節奏極快,而對于諸如汜人的歌賦、鄭生與汜人再次相見時的場面描寫、邢鳳夢中美人的妝容服飾、夢中出現的詩詞、弄玉與亞之相處過程中的一些細節等等,卻很愿意花筆墨去描摹刻畫,這些內容對故事情節的推進作用不大,但對于營造畫面,渲染情緒,調動氣氛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亞之傳奇中往往有許多詩篇,因此他的小說被稱為“詩化小說”,包括楚辭在內的大量舒緩、哀怨的詩詞也將小說的節奏拉得緩慢。于是,亞之的小說呈現出獨特的快慢交疊、錯落有致的敘事節奏,給人以獨特的審美體驗。
在內容的編排上,亞之傳奇中的歡樂情節少之又少,他不會詳細交代鄭生與汜人相守的溫馨平和,也不會細說亞之在古秦國尚公主時的榮華愉悅;他有意將歡樂略去,徒留悲傷,于是反復皴染傷感的細節、凄迷的意境和悲愁的氛圍,因此,讀完水中仙女貶謫凡間與窮苦書生相戀的《湘中怨解》,人們記住的是愛而不能相守的苦命戀人和一首首凄美動人的歌辭,讀完夢中遇古代美人的《異夢錄》,人們記住了《春陽曲》、“弓彎”舞和一位哀愁的美人,讀完奇幻詭譎、一波三折的《秦夢記》,人們記住了亞之痛徹心扉的詩篇。歡樂是那么的短暫,悲愁是那么的綿長。在這樣充滿詩意和哀愁的氛圍中,讀者的身心也受到了哀愁之美的滌蕩。若亞之著力描寫仙凡相戀的獵奇、夢中艷遇的旖旎、夢游古秦國的刺激、尚公主的得意,那亞之傳奇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將會大打折扣。
亞之以悲為美的藝術追求深受楚辭的影響,想來亞之的命途坎坷與屈原的滿腹離騷頗有共鳴,更何況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亞之任郢州掾,郢州在歷史上是楚文化中心所在,因此亞之有意無意地接受了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的影響。不論是以悲為美的審美取向、人神遇合的故事題材、作者以自身歷幻的情節設計、唯美意境的營造,還是湘水、香草美人、楚辭這些元素的加入,都足見亞之小說中楚文化的印記。
對于“缺乏實感”、“內容貧乏”這類的評價,筆者以為,那是因為部分評論者的閱讀期待和亞之的傳奇并不吻合,他們期待看到情節緊湊、內容新穎的傳奇,期待像看寓言故事一般從故事中看到什么顯而易見的哲理,可亞之并不致力于給讀者留下什么跌宕起伏的奇幻故事或是發人深省的哲理寓言。而這也正是亞之傳奇的高級之處。當讀者隨亞之的文筆一起陷進“白楊風哭兮石鬣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的凄迷意境中,一起為“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的悲傷而慨嘆,亞之的傳奇也就實現了其藝術追求。至于弄玉何以忽然死了,秦穆公為何忽然就要遣送亞之離開等等故事邏輯問題,對于亞之的傳奇而言,刨根問底是毫無意義的。
宋代劉克莊對亞之的《秦夢記》以自身敷衍故事甚為鄙夷,在此也對這一看法做一簡要說明。劉氏之所以這般認為,一方面是由于時代觀念的限制,在小說地位低下的年代,文人士子普遍將它視為雕蟲小技,而其內容也多為風流逸事、煙粉靈怪,自命清高的讀書人怎會“攬歸其身”?這顯然是不符合儒家的傳統價值取向的。另一方面,許多人沒有讀出《秦夢記》背后的深意,以為是亞之對“尚公主”的憑空想象和對自己詩才的賣弄。在筆者看來,亞之此文之所以不避諱自己的身份,是因為那入古秦國歷幻之人不會是他人,只是亞之自己。大和元年(公元827年),亞之再度游歷了熟悉的秦國故地(亞之的青少年時期在隴州、商州一帶度過),面對童年熟悉的風物,剛剛經歷了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失敗、授櫟陽尉、轉福建等州為福建都團練副使、任殿中侍御史等一系列變故的他寫就了杰作《秦夢記》。對躊躇滿志又命途多舛的亞之而言,尋常詩文已難以傾瀉他的痛苦與困惑,他不可能在詩文中直抒胸臆,質問君王為何不重用才德兼備的自己,他也無法去質問蒼天為何處處與他為難,使他失去摯愛孤獨飄零,他弄不清生死是否真的有命,富貴是否真的在天,于是他開始懷疑,開始創作,開始如屈原“天問”一般發問,“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就其儒家信仰而言,他不信‘仙鬼復死’,弄玉既‘仙’又‘死’了,并由此導致了他一生命運的逆轉。言下之意他一生奉行積極入世的原則,汲汲于功名,仕途竟如此坎坷,命運又這等多舛。他對信念的懷疑,正如他對仙鬼不死的懷疑一樣。”ix若說亞之小說的情節荒誕,那亞之空有抱負卻終不得志的一生又何嘗不荒誕;金蘭陪伴亞之風雨同舟,卻死在了亞之中進士的前夕,又何嘗不荒誕;亞之立下戰功,本以為苦盡甘來,卻反遭貶謫毀謗,又何嘗不荒誕呢?
總而言之,亞之寫奇幻卻不重奇幻,全心全意地塑造著悲劇的人和悲劇的事,為此,他淡化了情節,模糊了主旨,敷衍著故事,刻畫著細節;最終,在凄迷哀怨的詩意氛圍中,故事的主人公泫然離去,作者亞之抒發著難以明說的哀愁,而幾百年后的讀者還在為之扼腕嘆息。
參考文獻
[1]魯迅校錄、曹光甫校點:《唐宋傳奇集全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唐]沈亞之:《沈下賢集》,四部叢刊,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3]李世進:《中唐作家沈亞之研究》,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
[4]楊勝寬:《也談沈亞之及其<秦夢記>——兼與程毅中先生商榷》,《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第48—52頁。
[5]楊勝寬:《論沈亞之及其文學創作》,《樂山師專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2期,第10—15頁。
[6]陳建平:《怨郁凄艷的無韻之詩——論沈亞之的抒情小說》,《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999年,第1期,第57—60頁。
[7]張清華:《沈亞之行年考》,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九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20—632頁。
[8]李世進:《沈亞之的生平與創作》,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9]周加勝:《唐沈亞之事叢考》,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10]汪卷:《唐人沈亞之的詩化傳奇》,《文教資料》,2006年,第3期,第46—47頁。
[11]陳才訓:《古文風貌與楚調悲歌——論沈亞之的文學素養與其小說創作之關系》,《中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4期,第24—27頁。
[12]高禎:《唐代寫夢小說的敘事時間探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第37—41頁。
[13]張同利:《少女踏春陽——沈亞之<異夢錄>的小說史意義》,《殷都學刊》,2011年,第4期,第54—57頁。
[14]葛成飛:《凄怨、幽迷的“沈下賢體”——沈亞之夢作品論略》,《長春工程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105—107頁。
[15]馬俊紅:《中晚唐傳奇詩性特質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16]周承銘:《夢與現實疊加的怨憤——<秦夢記>思想主題新論》,《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26—32頁。
[17]周承銘:《論唐人小說<異夢錄>思想主題》,《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17—24頁。
注 釋
i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74頁。
ii (宋)劉克莊《后村居士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卷一七三。
iii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三聯書店,1994年版,174頁。
iv 李宗為《唐人傳奇》,中華書局,1985年版,70頁。
v 元和五年八月(公元810年),沈亞之從家鄉吳興(湖州)出發應貢舉,獲解,在鄉飲酒禮后上京城,參加進士科考試。次年春,他在長安的省試落了第,此為“一黜禮部”。元和七年初(公元812年),亞之省試再次落第。元和八年初(公元813年)的省試中,亞之依然無緣得中,是為“三黜禮部”。
vi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沈亞之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失敗,是為“一敗制科”;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亞之再次回到長安參加制科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再告失敗,是為“二敗制科”。
vii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沈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隨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柏耆到滄州,助柏耆平息了從寶歷二年(公元826年)至此的兩河叛亂,因柏耆押叛將李同捷回京途中突生變故,柏耆專斷,不聽亞之勸告,斬殺了同捷,而文宗又聽信讒言,在柏耆、亞之尚未歸京詳情時就下了貶謫詔旨,將柏耆宣慰德州,取為判官,亞之受其牽連,貶南康尉。《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九:“李佑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耆欲襲誅之,亞之謂:‘恐生諸將心,且殺降不詳。’耆不聽,竟誅同捷。諸將嫉其專冒,攢詆之,文宗貶耆,亞之亦貶南康尉。”亞之的《上九江鄭使君書》,便是為此辯誣。
viii 沈亞之《盧金蘭墓志銘》曰金蘭“為《綠腰》《玉樹》之舞”。
ix 楊勝寬:《論沈亞之及其文學創作》,《樂山師專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2期,第10—15頁。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