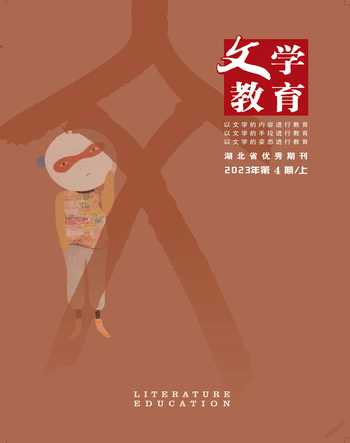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臺階》中父親形象的美學意蘊和情感密碼
蔡育峰
內容摘要:李森祥小說《臺階》中的父親,是一個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具有復雜而豐富的審美內涵。從“農民”身份切入,從“農民”形象的文化結構,解讀父親作為中國傳統農民典范的美學意蘊;從“父親”身份切入,從兒子視角解讀父親形象確立與崩塌的普遍性心理結構;從“老人”身份切入,從自然人的角度解讀父親面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時的無力感與絕望感,引發生命哲學層面的深刻思考。本文將父親作為“農民”“父親”“老人”三重身份分別剝離而又糅合,闡釋三種身份蘊含的普遍性文化結構、心理結構,以此揭示父親形象背后藏著的人類普遍性的情感密碼和美學意蘊。
關鍵詞:李森祥 《臺階》 三重身份 父親形象 文化結構 心理結構 美學意蘊
李森祥的小說《臺階》1988年發表在《上海文學》[1],入選人教版和蘇教版語文教材,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為什么《臺階》中父親形象能有這么深廣的情感力量?本文將父親形象分解為“農民”“父親”“老人”三重身份,闡釋這三種身份蘊含的普遍性文化結構與心理結構,以此解讀《臺階》父親形象的情感密碼和美學意蘊。
一.農民:中國傳統農民的美學典范
父親身上具備中國幾千年傳統農民的普遍性美德,是中國傳統文化滋養培育出來的農民形象的美學典范。父親作為農民形象的美學意蘊,契合了中國人關于農民形象的美學想象,因此具有廣泛的情感力量。
父親具有農民勤勞的美德,彰顯了農民形象的勞動美。父親為建造高臺階的新屋所做的準備,從“一塊磚”“一片瓦”開始,是非常瑣碎而漫長的。這種準備工作是低效率的,是農業的生產方式,但這勤勞奮進的精神,某種程度上卻與中國傳統文化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契合的。
父親具有農民吃苦的精神,彰顯了農民形象的堅忍美。父親在生活苦難面前所展現的堅忍,構成了中國傳統農民美學形象的一部分。父親從不畏懼辛苦,為了砍柴賣錢,起早貪黑,雞鳴時出發,黃昏后才回,一個冬天穿破底的草鞋就堆得超過了臺階。然而其中的辛苦疲累,從未將父親擊倒。
父親具有農民的淳樸謙卑,彰顯了農民形象獨特的人格美。新屋建成了,這是父親勞苦一生的高光時刻,父親要放四顆大鞭炮以示隆重。但是父親“居然不敢”放鞭炮,只讓“我”來點火。在鞭炮聲中,在被炸起的鞭炮碎紙中,父親不知所措,“父親的兩手沒處放似的,抄著不是,貼在胯骨上也不是”,只好露出“尷尬的笑”。當新屋建成,父親坐在九級臺階上,舉止失措,令人啼笑皆非!有人從門口過,問父親“晌午飯吃過了嗎?”明明已經吃過了午飯的父親,卻因為謙卑而下意識地回答沒吃過。這種淳樸的謙卑,既是中國傳統農民社會經濟地位的體現,也構成了中國農民形象獨特的人格審美。對生活的逆來順受,深刻到骨子里的謙卑,使得中國傳統農民形象具有一種令人悲憫憐愛的特質。
建造九級臺階的新屋,是父親作為農民對生活樸素而美好的熱望,也是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尋。父親一輩子與土地糾纏,在目光所及的狹窄世界里執著追尋生活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父親終其一生的理想,就是擁有一所有高臺階的新屋,因為在父親的世界里,高臺階是地位的象征,是尊嚴所在。王君認為父親用盡一生的力量建造九級臺階的新屋是一種精神冒險,并且盛贊“這篳路藍縷的追求充滿了神話式的傳奇色彩和寓言式的精微深意”[2]。
父親以建造九級臺階的新屋作為其人生價值的追尋,具有歷史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國傳統農民的宿命。父親以外在于生命本身的“高臺階的新屋”作為其精神追求和人生價值的確認,注定是荒誕而悲劇性的。九級臺階新屋建成了,父親也老了,腰也閃了,生命也進入了枯竭。父親的一生,由最初的雄心勃勃而始,由“若有所失”而終,令人深深感傷遺憾。這樣的結局,論者眾說紛紜。楊先武贊揚了父親堅毅執著的精神,但認為父親把人生價值寄托在高臺階的新屋上是可悲的[3]。王君從教學價值的角度出發,認為“必須要講出父親的偉大”,不必去批判父親的精神境界還不夠高,用“精英階層”的意識去嘲笑父親的“臺階意識”是荒謬的。她認為父親是艱苦創業的草根階層的典型代表,是中國的筋骨與脊梁[4]。論者眾說紛紜恰恰體現了這一結局復雜而豐富的審美意蘊。在漫長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除了生兒養女,中國農民終其一生的價值就是建造一棟新屋,這是他們一生最重要的光輝事業。現實生活中,老一輩農民的個人幸福和尊嚴就是與一棟新屋聯系在一起的。令人不能不深思的是,作家李森祥在小說《臺階》最后卻并沒有讓父親獲得這種幸福與尊嚴。這體現了李森祥對農民命運與生命意義的思考。
《臺階》發表于1988年,正處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時期。農民這一身份及其族群的生活方式、生活觀念正在發生潰敗和革新。如果以今天的視角看,《臺階》中的父親作為農民所具有的勞動美、堅韌美、謙卑的人格美,及其對生活樸素而美好的愿望,依然具有普遍性的美學意蘊,但是其中的具體方式,如“一塊磚”“一片瓦”的建造方式,逆來順受的堅韌謙卑,以“高臺階的新屋”為精神追求與人生價值確證等,是有其時代的局限性的。《臺階》發表至今三十余年,父親作為農民的美學形象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但也正在遇到新一代讀者的挑戰,尤其在城市里長大的一代,早已失去了理解其美學意蘊的生活基礎。但正因為如此,《臺階》具有了社會學史料的價值,讓今天的新一代年輕人能由此窺見中國傳統農民曾經的生存境況與人生追求。
二.父親:“父親”形象的確立與崩塌
關于《臺階》中父親的形象,論者多從農民的身份言說。部分論者雖題為探究“父親”形象,但其實質依然在探究父親的“農民”形象,如蘇寧峰《精神困境中的父親形象——人教版課文<臺階>教參解讀指瑕》認為《臺階》主旨在追問農民的精神存在和轉型時期農民的精神生活[5]。蔣云斌《“坐著”的父親——淺談<臺階>的“父親”形象》實質上依然從“農民”身份言說,認為父親與“世世代代的中國農民”一樣,“一輩子都坐在兩樣東西上——一是土地,一是傳統”[6]。也有人注意到了父親作為“父親”這一角色,但其論說多局限于父親的人物形象本身,如胡丹《“兒子”的崇敬與傷感,“我”的理解與感恩——<臺階>文本細讀》從“兒子”的視角論述了小說中“我”作為兒子對父親形象的理解,但其側重點在闡述“兒子”視角的意義,且未從普遍性角度探究父親形象的確立與崩塌[7]。
筆者以為,《臺階》從兒子視角為我們講述了一個關于父親形象的確立與崩塌的普遍性寓言,一個父親形象接受史。
作為“父親”形象,父親在“我”的情感建構、人格建構和理想建構中都曾承擔起“父親”光輝偉岸的角色。
像絕大多數中國傳統父親一樣,父親沉默寡言,小說關于父親的語言描寫極少。但從僅有的語言描寫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父親的溫情。童年的“我”是頑皮好動的,“我”喜歡在三級青石臺階跳上跳下,有一次“我”想一步跳到門檻上,結果狠狠地摔了一跤,父親拍拍我的后腦勺說:“這樣會吃苦頭的!”這里用極瑣碎的文字描述了三級臺階給“我”的童年快樂,以及父親對“我”頑皮好動的包容與理解。父親“拍拍的我后腦勺”,動作如慈母般溫柔。有人卻認為父親說話的語氣太過剛硬,語氣中透露著復雜的信息:既有辛酸,也有警示,還有夸大苦難的意味,而年幼的“我”根本不體會父親的心理,因此推斷父親有人格障礙,因為父親與最親近的家人之間也沉默寡言無法有效溝通,情感上比較疏遠[8]。筆者以為這樣的觀點稍顯偏頗,有過度闡釋之嫌。父親提醒“我”“這樣是會吃苦的”,恰恰承擔著父親教誨的職責。而每到過年,母親端水給父親洗腳的場景是溫馨而柔軟的。事實上,在父親主導下,《臺階》向我們呈現了一個典型的嚴父、慈母、孝子的溫情家庭結構。父親用愛與責任為“我”構建了一個溫情的情感世界。
父親的堅忍豁達,曾為“我”樹立人格榜樣。父親坐在臺階上洗腳,“要了個板刷沙啦沙啦地刷”。這個印象深深地印在“我”心里,讓“我”感受到父親的農民本色與豁達的性情。父親和泥水匠們抬青石板時腰閃了一下,卻依然一手按著腰堅持著。父親挑水時閃了腰,倔強而粗暴地推開了想要幫忙的“我”。這些細節,讓“我”銘記于心,因為其中有一個父親最倔強的堅強。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里,父親始終扮演中與母親不同的角色,在兒子的精神世界里,父親必須表現出男性的力量、堅韌、頑強,面對苦難始終不低頭的倔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父親用他堅韌倔強的一生完成了對“我”的人格塑造。
父親終其一生建造九級臺階的新屋,為我樹立理想建構的典范。為了實現理想,父親從“一塊磚”“一片瓦”開始,用大半輩子來完成,這種面對理想的堅韌執著的追求,令我震撼。而更重要的是,父親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那快樂自足的態度,認我著迷。父親從早忙到晚,晚上只睡三四個鐘頭。“我”擔心父親身體會垮掉,可父親卻很興奮,臉上總是含著笑,仿佛有使不完的勁兒。這樣的細節讓“我”明白了心中有夢想的人是最快樂的,讓我感受到了夢想的偉大力量。
父親形象從最初的高大、充滿力量美到衰弱、頹廢,經歷了父親形象的確立與崩塌的過程。小說一開始極寫父親的高大強壯,“三百來斤重”的青石板,“父親一下子背了三趟,還沒覺得花了太大的力氣”,這是極度張揚的力量美;父親坐在三級青石板臺階上時屁股在最高一級而兩只腳板在最低一級的樣子,令“我”印象深刻。此時的父親偉岸如山,映射在兒子的心理,產生了無限崇拜的熱情。后來的父親,和泥水匠們一起抬青石板,卻閃了腰,在挑水時又一次閃了腰,母親在父親閃腰的部位刺九個洞,用竹筒拔火罐,從父親的腰里吸出“一大攤污黑的血”,然后父親迅速衰老和頹廢了下去。在李森祥極度感傷的抒情化描寫中,藏著一個父親的衰弱與頹廢,也藏著一個兒子面對父親形象崩塌時的感傷與失落。
“父親”形象的確立與崩塌,都具有普遍性。在父與子的代際傳承中,兒子由弱到強,而父親由盛到衰。每一個長大的“兒子”,眼里都有一個由盛而衰的“父親”,這是人類共同的心理結構,也是《臺階》中“父親”形象具有深廣的感發力量的深層次情感密碼。
三.老人:人生終極意義的追問者
敘事時間的起點與終點的選擇,將深刻影響小說的主題。引導讀者關注小說敘事的時間結構,將有益于深化對小說主題的理解。《臺階》講述了父親為了修建九級臺階的新屋奮斗了大半輩子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敘事,完全可以在父親實現建造九級臺階夢想這樣的高潮部分結尾,由此我們將看見一個高大的、充滿力量美的強壯父親、一個年幼的充滿童真快樂的兒子、一個由嚴父、慈母、嬌兒構成的溫馨之家;我們將看見一個中國傳統農民“愚公移山”般充滿神話式傳奇色彩的奮斗史;我們還將看到一個中國傳統農民在達到事業與人生頂峰時的幸福與喜悅。可是李森祥沒有在父親實現建造九級臺階夢想這樣的高潮部分結尾,而是花費了不少筆墨去寫父親圓夢后的失落。
語文統編教材七年級下冊選錄的課文《臺階》,采納了“怎么了呢,父親老了”這個結尾。查閱《臺階》原來發表的《上海文學》和語文統編教材選用的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小說集,小說結尾是有這句話的。可是作者在2007年將此文選入小說集《臺階》時刪除了這個結尾[9]。楊鳳輝主張“怎么了呢,父親老了”這個結尾宜刪,認為只有去掉“怎么了呢,父親老了”這個結尾,小說才更具美學價值、思想價值,也才能避免讀者把父親的人生看成是個人的悲劇[10]。筆者認為,恰恰是結尾這種悲劇色彩,使得父親形象更具有普遍的抒情性,也使《臺階》在追問人生終極意義上走向深刻。
父親作為“老人”這一身份,使其天然成為人生意義的終極追問者。“老人”一般有兩個焦慮,一個是死亡焦慮,面對衰老和死亡產生的恐懼;一個是回顧、總結一生的焦慮,即對自我人生價值的終極追問。這兩種焦慮是交織在一起的,正是因為有了死亡,我們才需要在短暫的人生中努力創造,實現人生價值。父親用大半輩子的人生實現了建造九級臺階的人生理想,可他卻突然發現,他并沒有獲得期望中的幸福感與尊嚴感。父親必須要有新的人生目標來提供新的動力,可是“老人”臨近死亡的現實,使這種新目標很難建構。他每天都“若有所失”,陷入巨大的失落與虛無,因為他不再年輕,不再健壯,體力迅速衰減,也不再有人生目標和前進的動力。
但這種失落與虛無,或者父親老了的悲劇性結局,并不是消極的。如果《臺階》在父親實現建造九級臺階夢想這樣的高潮部分結尾,無疑是一個更加樂觀且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結尾。但這種樂觀與浪漫主義是危險的,遮蔽了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和精神處境,也將使小說《臺階》失去主題的深刻性與普遍性,而流于淺薄。筆者認為,正是父親人生理想的悲劇性,提供了一種震撼心靈、凈化心靈的作用,提醒讀者以現實主義的視角去思考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的價值追尋,深刻理解他們生存與精神困境,也因此獲得了書寫的真實性與普遍的情感共鳴。
如果我們將父親諸如“農民”“父親”等社會身份全部剝離,僅僅將其作為單個的“老人”來審視,父親的失落與虛無,其實是人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面前的無力感與絕望感。這種無力感與絕望感是人類共有的生命體驗,是超越了身份與文化而存在的,抵達了生命哲學的層面。郭躍輝認為,應該將“父親”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社會、文化、思想因素全部剝離,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父親形象。[11]筆者認為,我們并不是要剝離附著在父親形象上的社會、文化、思想等因素,而是要將父親作為“農民”“父親”“老人”的三重身份融合、糅合在一起來看,從而更深刻地理解父親這個人物形象復雜而豐富的美學意蘊。
注 釋
[1]李森祥《臺階》,《上海文學》1988年第6期。
[2]王君《從<臺階>看人生的困境》,《語文教學通訊》2008年第3期。
[3]楊先武《可敬而又可悲的父親——<臺階>意蘊新探》,《中學語文教學》2007年第8期。
[4]王君《必須要講出父親的偉大——<臺階>意蘊新探》,《中學語文》2009年第1期。
[5]蘇寧峰《精神困境中的父親形象——人教版課文<臺階>教參解讀指瑕》,《中學語文》2012年第10期
[6]蔣云斌《“坐著”的父親——淺談<臺階>的“父親”形象》,《語文教學通訊·初中》2015年第1期。
[7]胡丹《“兒子”的崇敬與傷感,“我”的理解與感恩——<臺階>文本細讀》,《語文教學通訊·初中》2019年第4期。
[8]向浩、童慶杰《<臺階>中“父親”人格障礙分析》,《中學語文教學》2019年第11期。
[9]李森祥小說集《臺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10]楊鳳輝《真的是父親老了嗎——<臺階>的結尾段宜刪》,《中學語文教學》2021年第5期。
[11]郭躍輝《“怎么了呢,父親老了”是畫蛇添足嗎?——小說<臺階>的一處細節解讀》,《語文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