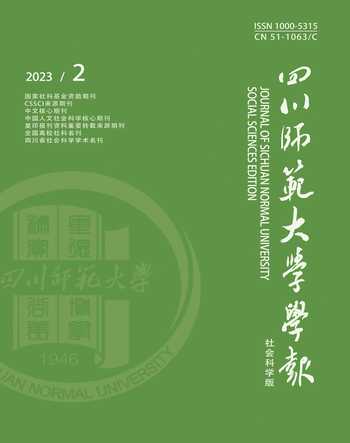陰翊王度:“張三豐入蜀見蜀王”傳說新考
摘要:明初皇室的“異人”慕求對“張三豐”神仙信仰的成立與傳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張三豐入蜀見蜀王”一事最為重要,但學界對其內涵意義并沒有認識清楚。新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蜀獻王朱椿《獻園睿制集》所收《與全弌老仙書》五篇、《張豐仙像贊》、《懷仙賦》,可以清楚地證明“張三豐入蜀見蜀王”實屬朱椿的建構。朱椿此舉是以太祖與周顛仙故事為樣板,利用道教異人張三豐塑造自身賢王形象,化解岳父藍玉謀反引發的政治危機,避免重蹈兄長潭王朱梓身死國除之覆轍。朱椿借此不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賢”之名,“后入蜀,見蜀王”情節亦得以成功躋身張三豐傳說系統,成為“三豐復生”神話的官方證明。
關鍵詞:蜀獻王;朱椿;《獻園睿制集》;張三豐;藍玉案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21
收稿日期:2022-12-28
作者簡介:白艷波,男,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E-mail: baiyanbo2011@163.com。
一引言
“張三豐”是明以降道教及社會一般宗教信仰和民間傳說中著名的仙真,與此前仙話、傳說中的仙真不同,其產生、型塑和傳播、接受都具有非常鮮明的特點。關于張三豐的當代研究已經頗為深入,但在根本上存在一個重要闕失,即對“張三豐”的“建構性”缺乏深入的認識。這里所謂“建構性”,是指無論歷史上是否存在著人物原型,“武當繼武真君張三豐”及其各種形象都是逐漸被人為構造出來的結果。此一建構過程相當漫長,可以說從明初一直到清代李西月重編托名之作《張三豐先生全書》為止。其中,明初皇室關涉此事甚深,不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主導力量。
任自垣(?-1431)《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6載,自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明太祖即已開始搜訪“張三豐”:
張全弌,字玄玄,號三豐。……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長往,不知所止。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張玄玄可請來。永樂初太宗文皇帝慕其至道,致香書累遣使臣請之,不獲。后十年敕大臣創建宮觀一新,玄風大振。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成書于宣德六年(1431),編者任自垣曾任太和山提點,并參與《道藏》的編纂,相關記載應非空穴來風。故,此一說法也被正史采納。《明史·張三豐傳》即云:“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又載,此前一年,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之子、湘王朱柏(1371-1399)親至武當山朝謁玄帝,尋訪“張玄玄”,訪之不遇,乃作《贊張真仙詩》:
張玄玄,愛神仙。朝飲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巖之紫煙。好山劫來知幾載,不與景物同推遷。我向空山尋不見,徒凄然!孤廬空寂大松里,獨有老獼松下眠。張玄玄,愛神仙。匪抑乘飆游極表,茅龍想馭游青天。
朱柏本人篤信道教,封地在荊州,是諸王中離武當山最近者,對明初張三豐的各種神異傳說應該并不陌生。結合朱柏此行邀請武當元和觀高道李德囦住荊州長春觀之舉,其尋訪“張玄玄”事可信度較高。
綜上可知,盡管不一定能夠確證明太祖朱元璋曾經遣使尋訪,但可以肯定的是,至洪武后期,“張三豐”的聲名已經朝野皆知,對他的搜訪已經成為明代皇室的一項重要舉措。
除卻本文將要重點討論的《獻園睿制集》和上引《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外,目前已知社會層面關于張三豐的最早記載是楊溥(1372-1446)的《禪玄顯教編》:
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后入蜀,見蜀王。……永樂中,命胡忠安濙馳傳遍索于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乃為憶仙宮以待之。
稍晚即天順五年(1461)初刊的官方文獻《大明一統志》亦載:
張三豐。居寶雞縣東三里金臺觀。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豐復生。后入蜀,見蜀王,又入武當山,或游襄鄧間。永樂中遣使尋訪不遇,為宮以待之。
于此可見,早期張三豐傳說具有三個核心因素:一是死而“復生”;一是“后入蜀,見蜀王”;一是洪武時“拂袖長往,不知所止”,“永樂中遣使尋訪不遇”。“復生”是仙話的基本母題,洪武、永樂時均尋訪不獲,也是傳說中原型往往退場的慣例,均可置而不論;“入蜀見蜀王”有所不同,涉及到具體的人、地、事,體現出濃厚的“歷史”意味,顯然屬于某種消息透露。
蜀王朱椿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四年(1371)生,十一年被封為蜀王,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永樂二十一年(1423)薨,謚曰“獻”。關于洪武后期“張三豐入蜀見蜀王”一事,雖有前引文獻之記述以及《明史·張三豐傳》之繼承,但因材料來源不明、內容歧異,以致當代研究者觀點不一,信從者有之Anna Seidel, “ ,斥偽者亦有之。面對相同的材料,研究者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近年來,隨著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原內閣文庫)藏《獻園睿制集》的發現,為學界研究張三豐及其入蜀見蜀獻王朱椿事迎來了新契機。《獻園睿制集》乃明朝第一代蜀王朱椿的文章匯編,在明清書目中雖偶有著錄,但流通有限。清初,蜀王府遭張獻忠兵燹,宮室被焚毀一空,《獻園睿制集》遂在國內失傳。因此,《獻園睿制集》一經發現,即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文集卷四《與全弌老仙書》五篇、卷五《張豐仙像贊》、卷十二《懷仙賦》與張三豐直接相關,似乎可印證其“后入蜀,見蜀王”事,使蜀獻王朱椿與張三豐存在確實交往得到了落實。
然而,本人深究《獻園睿制集》后認為,其相關文本無一不出于有意識的杜撰。亦即洪武后期“張三豐入蜀見蜀王”事,實出于蜀獻王朱椿本人的建構。以下即以《獻園睿制集》為中心,梳理文獻內外的線索,嘗試還原明初蜀獻王朱椿建構“張三豐入蜀見蜀王”的過程,并考察此舉的政治背景、動機與實際效果,以推進學界對《獻園睿制集》文本價值和“張三豐”神仙信仰的認識,尚祈海內外方家批評指正。
二《獻園睿制集》所見“張三豐入蜀見蜀王”辨析
《獻園睿制集》,“獻園”指蜀獻王朱椿,“睿制”乃表明作者藩王身份的敬辭。全書凡17卷,黑口,雙魚尾,正文每半葉10行,行23字。由朱椿曾孫、第六代蜀王朱申鈘(1448-1471,謚曰“懷”)于成化二年(1466)三月命蜀藩教授葉著編集,成化三年(1467)五月刊刻。其中,卷四《與全弌老仙書》五篇、卷五《張豐仙像贊》和卷十二《懷仙賦》的寫作對象都是“張三豐”,對于判定二人的關系性質至關重要。本節以這三類作品為中心,梳理“張三豐入蜀見蜀王”詳情。
在《獻園睿制集》所收三類共七篇以“張三豐”為中心的作品中,以卷四的五篇《與全弌老仙書》(后文提及,簡稱為《書一》、《書二》、《書三》、《書四》、《書五》),內容最豐富。其中,《書一》篇幅最長,為方便分析,略分段落并加序號如下:
(1)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敬問通玄觀妙先生全弌老仙:(2)夫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異人而有異聞異見者也。若黃帝之于廣成子、張良之于黃石公、曹參之于蓋公、漢文帝之于河上仙翁、宋太宗之于希夷先生,以至于我皇上之于周顛仙人,古今具載,班班可考。或以之而致清靜之化,或以之而成將相之略,或以之而開太平之運,或以之而輔圣體之康,是皆有大功德于國家者也。(3)予以幼沖之年,分封于蜀,切念蜀中乃太上降生之地,漢天師得道之所,必有異人出乎其間,得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有以發其愚蒙,諭以道德。然求之切切,得之寥寥,不能無所感焉。(4)乃聞全弌老仙,襲神明之裔,佩全真之教,留形逾于百歲,蹤跡半于天下。睹異人,得異傳,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大父”。短褐長絳,來游陜右。(5)予遂起敬起慕,齋戒彌月,遣一介奉瓣香,致尺書,以寓惓惓。乃蒙不鄙,惠然肯來,遠近聞之,莫不驚喜。及其至也,相見靡時,請叩非一,卻乃韜光晦美,若無以異于人者。予不能無所疑焉。相與半載余,乃時露一斑半點,尚未傾其懷抱,究其底蘊。(6)今年春季,謂予曰:“天國之山,仙人所居止也,茲行必欲造玄真之境,求長生之藥,持獻左右,以報知己之遇。秋來方可會也。”去后,嘗附至山筍、仙李、崖蜜,一味一感。(7)邇來形于夢者二,虬髯之狀,依稀而矚乎目;藥石之言,仿佛而聆乎耳。精神所格,昭昭若是。爰命使者存問起居,颙俟數日,欲見無由。使者回報,予心惕焉,再命之往。其至之夕,俄聞呼其從者之名,從者隨而呼之,亦應,及其秉燭四顧,則杳乎其無人也。僉曰:“老仙往矣,不知其所之矣。”(8)予則嘆曰:“老仙與予雅有夙昔之好,飄然長往,有道之士所不為也。吾意其入天國,會群仙,從容乎道德之場,超出乎喧囂之俗,其樂可知矣。然樂則樂矣,其如秋來之約何?此予心之所以懸懸而不置也。”用是,謹遣成都左護衛千戶姜福,偕釋道弟子原杰、吳潛中等奉書虔請,以達衷情。惟望速駕云軿,早班鶴馭,復予以前言,告予以奇遇,以嘉惠予而罔予棄,則予永有賴焉。臨風以俟。
第(1)段是作書時間“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和奉書對象“通玄觀妙先生全弌老仙”。《書一》標題為“與全弌老仙書”,“通玄觀妙先生”的尊號未見于他處,而“全弌老仙”之名則可與《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所載“張全弌,字玄玄,號三豐”相對應。第(2)段是蜀王朱椿自述訪尋異人的緣起。第(3)段是自述訪求異人以諭道德的心志。第(4)至第(7)段是回述此前與“全弌老仙”建立關系的過程,可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包括久聞其名、遣使禮請、應邀來訪和“相與半載余”,后一階段主要包括老仙辭別、蜀王對老仙的日思夜夢和多次遣使入山尋訪未果。第(8)段是書信的宗旨:令成都左護衛千戶并僧道弟子奉書虔請。后面四篇書信基本上是對《書一》主旨的重申,表達了蜀王對“秋來之約”已過而全弌老仙未返的悵然以及盼其早日采藥歸來的殷切期望。而卷五《張豐仙像贊》和卷十二《懷仙賦》又分別為《與全弌老仙書》的贊體和賦體表達,具有明顯的同質化特征。
《與全弌老仙書》及《獻園睿制集》所載其他材料,關于“異人張三豐”及其“入蜀見蜀王”的信息極其豐富,遠過于前后他書所載。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是前面提到的洪武后期尋訪“張三豐”,與明太祖征訪異人有直接的關系。不過,《與全弌老仙書》均沒有提到明太祖直接征訪“張三豐”,這和《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說法有異。二是世俗流傳張三豐“襲神明之裔,佩全真之教”(《書一》),表明其出身非凡與全真道士身份。其中,“襲神明之裔”與《懷仙賦》“繄留侯之仙裔兮,亦云異乎尋常”呼應,稱贊張三豐為張良后裔,出身非常;“佩全真之教”與《張豐仙像贊》“復續派于瓜王”呼應,指明張三豐為全真道士身份。三是此時張三豐已年過百歲,曾云游多地。如《張豐仙像贊》所謂“南游閩楚,東略扶桑,歷諸天之洞府,參化人而翱翔”。四是張三豐道行高深,受人景仰。“是謂瀛洲之客,實為王者之師”(《書二》)。“睹異人,得異傳”一句,與《張豐仙像贊》“既受訣于散圣”呼應,謂張三豐曾得異人指授。“茲遇全弌仙翁……所言必應,其于事會則周知”(《書二》),與《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事事皆有先見之理”的描述一致,乃道教異人的重要特征。凡此,都是目前所見對張三豐的最早描述。
以上所述,只是《與全弌老仙書》及《獻園睿制集》所載其他有關“張三豐”材料的基本內容或曰“字面意義”。其所蘊含的豐富內涵,則需要展開更深入的分析。
首先,五封書信在文體上均屬于帝王對有道高人的“征召書”,由使節訪求時攜帶前往,即所謂“奉書虔請”。它們顯然不是一般的書信,而是一種儀式性的文書。可以想見,當使節從蜀王府邸出發或到達高人異士所止的仙山洞府之時,必然存在著當眾宣讀或公開展示的儀式情節。征召使節除“成都左護衛千戶姜福”,尚有僧道原杰和吳潛中。后者未見于《獻園睿制集》他處,但文集中有多篇與僧人原杰相關的作品,可大致勾勒其生平。原杰,法號“性空”,禪宗曹洞宗僧人,本籍燕趙,曾云游吳越等地,禮南京天界寺宗泐為師,曾三度出任蜀地佛寺住持,能力出眾,晚年被蜀王任命為青城山飛赴寺住持,終老于此。與蜀王關系十分親近的僧人原杰,應當就是主持儀式并對外宣傳征召書內容的主事者。
前代類似這樣的征召書遺存不少,但征召對象皆實有其人。就明初而言,至少有《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所載“成祖征召書”: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豐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范,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誠愿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云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永樂十年二月初十日
此當與《漢天師世家》所載永樂六年(1408)成祖《命邀請真仙張三豐敕》“敕真人張宇初:今發去請張真仙書一通、香一炷。真仙到山中,爾即投此,教邀一來,以慰朕企佇之誠”中之“書一通”,同屬一體。對比二書,可以明顯看出,和成祖的征召書相比,蜀王的《書一》在很多方面與征召書的文體頗不相類。第一,《書一》第(2)(3)段用不少文字敘述緣起、吐露心志,帶有強烈的展示意味。盡管蜀王不是太祖、成祖那樣的皇帝至尊,但至少也是維屏大邦之藩王,像成祖征召書那樣寫上“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范”,即足夠恭敬,實無必要如此自陳胸懷,特別是重點提出了明太祖訪求周顛仙的“故事”,表明追摹父皇的態度;同時又表述自己訪求異人,在于“致清靜之化”、“成將相之略”、“開太平之運”、“輔圣體之康”,唯恐人之不察。第二,《書一》的后半段主要是在敘述一個故事,情節頗有跌宕起伏,生動描述出自己與“全弌老仙”相見又相別的過程。尤其在敘事上,既有實景對話,又有托夢傳語,近乎小說家筆法。此更不符征召書之體。因為這個故事明顯不是寫給“全弌老仙”,而是寫給儀式的“觀眾”聽的,或是編入文集時給天下讀者看的(當然,蜀王生前沒有來得及編刊文集)。
蜀王在《書一》中明確地宣稱自己已經成功征召到了“全弌老仙”,只是因為其人“若無以異于人者”,“予不能無所疑焉”,導致了老仙的離去。但書信卻沒有明確說明自己為什么后來改變了看法,并且重新開始汲汲訪求,務請老仙再次駕臨。而從文本上看,前文說“相與半載余,乃時露一斑半點,尚未傾其懷抱,究其底蘊”,而后面又說“藥石之言,仿佛而聆乎耳”,“老仙與予雅有夙昔之好”,明顯矛盾。如前文已論,在蜀王朱椿之前,至少有湘王朱柏親至武當山尋訪張三豐,但無所獲;然而,一向行蹤飄忽的張三豐,“短褐長絳,來游陜右”,就迅速被蜀王所知;且面對蜀王的禮請,“惠然肯來”,并在王府逗留半年以上,對待皇室的態度前后判若兩人;而辭去后,又屢訪不獲,與入蜀時的積極應召,形成強烈反差。在這些方面,《與全弌老仙書》所述二人關系完全不相吻合。
在老仙辭別的時間上,五篇《與全弌老仙書》和《懷仙賦》所述亦頗多抵牾,具體表現在年份和季節兩方面。(1)洪武二十七年與二十八年的矛盾。《與全弌老仙書》前三篇有題署時間,《書一》“洪武二十七年”,《書二》、《書三》“洪武二十八年”,但根據內容,這三篇書信應作于老仙春季辭別之同一年。(2)春季和夏季的矛盾。《書一》曰:“今年春季謂予曰:‘……秋來方可會也。”與《書二》、《書三》及《懷仙賦》的季節信息皆一致。但《書五》則曰:“乃去夏六月二十八日,使告于予曰:‘……旋歸之日,以秋為期。”明確提到老仙辭別日期,屬夏季。全弌老仙與蜀王朱椿相處半年后辭別,未再相見,因此,辭別只有一次,但“春季”和“去夏六月二十八日”相差甚遠,自相矛盾。
相關文本中矛盾的地方還有很多。如“張三豐”名號及年齡的歧異。在《與全弌老仙書》和《懷仙賦》中,稱張三豐為“全弌老仙”或“全弌仙翁”,且內容多有呼應;而在《張豐仙像贊》中,卻改稱“張豐仙”。又如年齡的歧異。《書一》明確提到“留形逾于百歲”;《張豐仙像贊》卻說“吾不知其甲子之幾何”。這樣明顯的差異,出現在同一文集中,令人費解。因為既然確實已經見到過“張三豐”,蜀王朱椿所撰(或詞臣代筆)《與全弌老仙書》本應為實錄文獻,但實際情形卻正相反,其中連張三豐名號、年齡和辭別時間等基本信息都自相矛盾,這顯然存在極大的問題。
最后,尤令人奇怪的是,《書一》中蜀王宣稱當其他人皆不知老仙所往時,自己已經斷定其必在天國山中。天國山乃蜀中道教名山青城山第五洞,與鶴鳴山相連。明代蜀王府距離鶴鳴山僅約70公里,蜀王在這里是想表明自己與老仙神有遇合,還是意在宣揚“張三豐”與蜀地張天師的淵源?抑或表示必能訪獲老仙?既然近在天國山中,但又為何數訪不遇呢?或許天國山只是僧人原杰等公開宣讀征召書的合適場所?
經過以上分析,蜀王朱椿在《書一》中宣稱的所謂“全弌老仙”,“乃蒙不鄙,惠然肯來”,可以肯定為蜀王的一面之辭;整體“張三豐入蜀見蜀王”,無疑更出于一種有意識的建構。也許不能否認洪武時期確實有某一位“異人”上聞帝閽、下播人口,但其能死而復生并出現在蜀地,與當時正陷于某種境地的蜀王建立起一定的關系,毫無疑問是蜀王一力營造的結果。
三賢王與異人:建構動機及其策略
那么,蜀王朱椿如此不遺余力地建構“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并大張旗鼓地宣揚其與道教異人張三豐的關系,有何目的?綜合《獻園睿制集》和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考察,此舉應與化解藍玉案引發的政治危機直接相關。
《書一》所署時間為“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相與半載余”、“今年春季”老仙辭別等表述可知,朱椿宣稱與“張三豐”在蜀地初次會面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夏秋之際,而著名的藍玉案即發生在本年初。當時的蜀王妃藍氏,為藍玉之女。更為不同尋常的是,藍玉案爆發時,蜀王恰好從成都趕到京師。據《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蜀王椿來朝。并長沙護衛于越州衛。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丁亥,蜀王椿還國,其從官侍衛賜予有差”。乙酉為二月初十,丁亥為十二日,蜀王來朝與返國僅相隔一天,行程緊湊。藍玉案詳情,還可參考藍黨供狀《逆臣錄》。由丁僧兒、蔣義等人的供詞可知,藍玉案事發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兩天后藍玉伏誅。藍玉案牽連甚廣,藍玉本人伏誅,被夷滅三族,連坐論死者15000余人。藍玉之女、蜀王妃藍氏也于次年二月去世。朱椿本人雖不在連坐之列,但來朝當日就親見岳父伏誅,王妃又因此早逝,年輕蜀王內心的驚懼沉痛不難想見。
其實,蜀王并非唯一因姻親關系而被卷入政治風波的明初藩王。據《明史·潭王梓傳》記載:
潭王梓,太祖第八子……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初為寧夏指揮。二十三年坐胡惟庸黨,顯與琥俱坐誅。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與妃俱焚死。無子,除其封。
在這場政治風波中,潭王朱梓并非胡黨,卻因王妃於氏的父兄牽連其中而驚懼過度,與王妃自焚而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促使潭王“大懼,與妃俱焚死”的,恰恰是太祖“遣使慰諭,且召入見”這一表達善意之舉,由此可見朱元璋平日行事之嚴酷。
同為藩王,朱椿與朱梓關系如何?對此事又作何反應?《獻園睿制集》卷4有兩篇《與潭府書》,可以佐證二人的親密關系: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十日,弟端肅奉書兄潭王殿下:小弟自十月十有一日陛辭,至正月二日之國,仰巫峽之高,歷瞿塘之險,間關萬里,幸獲平安,無非吾兄親庇之所及也……且疇之夜,魂夢之相接,精神之交孚,非其平日友愛之篤誠于中而形于夢者耶?
在該書信中,朱椿首先詳述了就藩行程之艱險,并將自己平安抵達歸結為兄長的庇佑;該書信中還提到夢中相見,可作為平日友愛的印證。第二通書信則追憶了少年時代的共處之樂,并表達問候。凡此皆可證明二人關系較為親近。對于王兄的遭遇,年初就藩時尚有書信往來的朱椿,一定十分惋惜與悲痛,同時對政治的殘酷留下了深刻印象。
從臨行前“其從官侍衛賜予有差”來看,太祖對朱椿還是信任的。朱椿在京城僅逗留一天,這一反常舉動應與藍玉案有關。謀反伏誅前,藍玉曾兩次在四川擔任總兵官,與蜀地關聯匪淺。《逆臣錄》即收錄了四川都指揮周助之子周鑒等蜀地高層武官及其親屬的供詞,可見藍玉案對當地政局的巨大震蕩。由此推斷,朱椿之緊急返國,是為了應對藍玉謀反伏誅的余波,穩定政局。因此,盡管此次得以順利返國,但藍玉案帶給蜀地和朱椿本人的政治危機遠未解除。
洪武二十六年初的藍玉案,與朱椿宣稱的本年夏秋之際“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是否有關?通過梳理朱椿自藍玉案爆發至與“張三豐”會面的行程,可以更直觀地發現兩個事件的關聯。如前所述,朱椿自稱與“張三豐”初次會面不晚于洪武二十六年夏秋之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朱椿從京師出發返回蜀地,到達蜀地的具體日期已不可知。但據前引《與潭府書》,朱椿從京師到成都就藩,耗時80天。以此為參照,則洪武二十六年朱椿返回成都當在五月初三前后,時值仲夏。據《書一》,遣使致書前,蜀王還作了“齋戒彌月”等準備,“離京還國”與“禮請老仙”兩項活動的銜接更為緊湊,朱椿幾乎是剛返回成都就立即采取了行動。由此可以進一步佐證此前的判斷:洪武二十六年,蜀王朱椿從京城返回蜀地不久即成功召至“張三豐”,這并非歷史巧合,而是當事人朱椿主動營造的結果。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建構“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與化解藍玉案所引發的政治危機有何邏輯關聯?為何選擇這種方式?個人認為,總體上說,朱椿的這一選擇乃是對歷史上“圣賢得異人”政治傳統的繼承,其中明初太祖朱元璋與周顛仙的關系起到了關鍵的示范作用。
朱椿建構“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首先是對歷史上“圣賢得異人”政治傳統的繼承。《書一》第(2)段是對歷史上圣賢與異人關系的總結,其中“黃帝問道于廣成子”事見于《莊子·在宥》,“張良受《太公兵法》于黃石公”事見于《史記·留侯世家》,“曹參求治道于蓋公”事見于《漢書·曹參傳》,“漢文帝受經于河上公”事見于《神仙傳》,“宋太宗問道于希夷先生”事見于《宋史·陳摶傳》,“明太祖問計、受仙藥于周顛仙”事見于《御制周顛仙人傳》。這六組人物中,前者(受命于天的圣君賢相)的“致清靜之化”等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者(作為天命化身的道教異人)的傳道或輔佐,因此朱椿盛贊廣成子等“是有大功德于國家者”。
上述六組人物關系所代表的“圣賢得異人”政治傳統,本質上正是當時或后世之人所建構的政治神話,目的在于借助道教異人來美化君王或名臣的形象。在此意義上,《書一》開篇之鋪敘傳統,恰恰是在為后文建構與異人張三豐的關系尋求歷史淵源和理論支撐。相較于“黃帝之于廣成子”等歷史典故,“我皇上之于周顛仙人”作為本朝典范,對蜀王朱椿建構與張三豐的關系,具有更直接的示范作用。
作為明初著名異人,周顛仙在朱元璋崛起過程中的神異表現,經過明太祖本人與明初文臣的大力渲染,在當時已廣為人知,對烘托受命于天的圣君形象、增強其帝王正統性發揮了重要作用。朱椿從小耳濡目染,對此自然不會陌生。洪武二十六年七月,朱元璋與周顛仙的關系又有新進展: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顛仙姓周……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卻之。至是,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砂之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為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周顛仙遣進藥”延續了此前傳說的神異特征,“覺有菖蒲丹砂之氣,是夕疾愈”暗示了太祖所服為道教仙藥。其間,洪武癸亥(十六年,1383)以來,赤腳僧多次求見,而太祖“以其虛誕,卻之”,此次“上不豫,飲藥未瘳”卻仍“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的情節鋪墊,其實都是為了證明“周顛仙遣進藥”并非“虛誕”,可謂欲蓋彌彰。而太祖之為周顛仙撰文勒石,遣使往祭廬山,主要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意在烘托自身受命于天、神靈庇佑的圣君形象。
太祖“親為文勒石紀其事”,即廣泛流傳的《御制周顛仙人傳》。遣使立碑事發生于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二十八日),而所謂“周顛仙遣進藥”及朱元璋親撰《周顛仙人傳》都在此之前。朱元璋圍繞周顛仙的這一系列政治操作,距離蜀王宣稱與“張三豐”的初次會面(洪武二十六年夏秋之際)不遠。這一時間點上的再度“巧合”,為追溯“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的建構提供了新線索。
從《書一》“或以之而輔圣體之康”(對應“我皇上之于周顛仙人”)的描述來看,蜀王在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制作第一篇《與全弌老仙書》前已知曉“周顛仙遣進藥”事,而信息來源應該就是太祖《御制周顛仙人傳》。《書一》引入“我皇上之于周顛仙人”時事,正是蜀王對效法太祖、建構與異人關系的自我坦白。“周顛仙遣進藥”與“張三豐入蜀見蜀王”這兩個情節,不僅在建構時間上前后相繼,在建構動機(烘托帝王/藩王形象)和建構手法(撰文、遣使)上也一脈相承。由此可以斷定,蜀王之建構與張三豐的關系,是以太祖與周顛仙的關系為樣板。《與全弌老仙書》等張三豐入蜀“實錄”之撰作,正是受太祖《御制周顛仙人傳》的直接啟發,目的在于增加“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的可信度并擴大其政治影響,以化解此前藍玉案引發的政治危機。《書一》開篇特意將“我皇上之于周顛仙人”加入古今“圣賢得異人”之列,還包含了稱頌太祖比肩黃帝等古代圣君之意。
為進一步增加可信度,蜀王在作品中對封地蜀中悠久的道教傳統特別予以強調。除了前引《書一》第(3)段,這一地域優勢在《書五》開篇被再次提及:“嘗聞尹真人親受太上之經,張天師親傳太上之道,皆得之于蜀中。余也分封茲土,竊有喜焉,意謂必有有道之士生于其間,得聞《道德》之言。而玄教寥寥,可為太息。”太上老君和張天師都是道教史上的核心人物,蜀王標舉二者與蜀地的因緣,正是利用其權威地位,為“張三豐入蜀”及后續“見蜀王”、“求長生之藥”等情節提供歷史依據,這一鋪墊反證了情節本身的建構性。而《與全弌老仙書》中“張三豐”入天國山后“不知所之”的情節設置,也使得對“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的解釋權牢牢掌控于蜀王朱椿一人之手。
總之,以上諸多策略成功地構建出唯一曾與異人張三豐“相與”的藩王,朱椿的賢王形象無疑得到了極大的凸顯。
四“宗室最賢”與“三豐復生”:建構的政治效果與歷史影響
從后續歷史進程來看,蜀王朱椿的確成功化解了藍玉案引發的政治危機,避免了此前兄長潭王朱梓身死國除的悲劇,成為明初藩王中難得的善終者。除了在洪武、建文、永樂三朝變幻莫測的政局中保全自身,朱椿還受到了太祖、成祖的特別褒贊與優待,并在去世后收獲“宗室最賢”之名。
據《太宗實錄》記載,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丁酉,蜀王椿辭歸。賜敕諭曰:‘賢弟天性仁孝,聰明博學,聲聞昭著,軍民懷服……賜椿鈔二萬錠,其從官賜鈔有差。”永樂三年(1405)二月,“戊寅,蜀王椿辭歸。宴如初至,賜賚甚厚。并賜其從官鈔有差。” 這兩次辭歸皆在成祖登基之初,此時政局未穩,成祖的多次褒賜帶有明顯的拉攏之意,因此敕諭可能含有褒美成分;但其中“聲聞昭著,軍民懷服”的描述當有現實依據,極有可能得益于“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的烘托。
永樂二十一年(1423)三月,“戊申,蜀王椿訃聞。上哀悼之,輟視朝七日,賜祭,謚曰‘獻……王性惇厚慈祥,孝友篤至,循執禮法,表里惟一。潛心儒術,旁及佛老,讀書為文,苦志不懈。喜延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游畋之事。王府官屬能進善言,厚禮之,終身仍恤其后。喜扶植名教,遇古書可以表范厚俗者,刊印以惠后學,大書‘忠孝維藩四字于燕居之所以自勵。太祖皇帝嘗稱椿曰‘蜀秀才,蓋在宗室為最賢。”本段是蜀王椿訃聞、成祖賜祭定謚時的評述,具有官方傳記性質,值得重視。這份小傳對朱椿評價極高,呈現的是一個典型的儒家賢王形象。其中,“太祖皇帝嘗稱椿曰‘蜀秀才,蓋在宗室為最賢”,概括了蜀王朱椿在洪武一朝的表現。“蜀秀才”是明太祖對朱椿博學善文的認可;“蓋在宗室為最賢”則直接將朱椿置于“明初第一賢王”的地位,應是《太宗實錄》編纂者的評定。雖帶有揣測口吻,但亦可見朱椿的賢王形象在當時已深入人心。“宗室最賢”這一定位也被后世朱椿傳記所繼承,成為蓋棺之論。
然而,洪武后期蜀王朱椿苦心建構的“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并未出現在上述傳記中,僅在《大明一統志》和《明史》“張三豐”條目之下被一筆帶過。不僅如此,官方文獻幾乎完全抹除了蜀王生平中的道教因素,轉而將其塑造為儒家賢王典范。這樣的記述,顯然是官方表述進行某種選擇后的結果。
其實,朱椿在就藩之初即因地制宜地確立了扶植佛道以“陰翊王度”的宗教政策,頗得太祖真傳。據《大慈寺題名記》載:
且夫奸臣賊子,其氣焰足以涂炭夫人,其視綱常之道,何有于己?而聞釋子之說,懺悔修省,舍惡趨善。昔賢以陰翊王度,詎不信然?稽諸載籍,我西土雜居羌戎,勇悍善斗,雖死不厭,惟僧可化,是我蜀人,奉之為甚……迨夫我朝混一,崇教安僧,始有復其舊觀。
此記作于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朱椿就藩兩月,尚處在探索治蜀方針的階段。奸臣賊子無視儒家綱常之道,卻在聽聞釋子之說后崇信佛教、舍惡趨善。這一描述深刻地揭示了傳統儒家在現實政治中的局限。“陰翊王度”是對佛教與王權關系的精妙總結,與太祖“(二教)暗理王綱,于國有補無虧”(《釋道論》)和“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三教論》)相映成趣,具有明顯的繼承性。“崇教安僧”作為明初太祖確立的國策,與蜀地“雜居羌戎,惟僧可化”的特點正相契合,因此,在朱椿就藩后得以繼續貫徹。相關討論,雖為佛教而發,但全篇多處“僧道”并稱,實際可視為對蜀地佛道政策的總體論述。《祭北極真武》亦載:“眷茲蜀地,實是邊城。匪依人力,賴神之靈。”精準地概括了蜀地區域政治特點。此文作于洪武二十九年三月,朱椿就藩六年,對封地已有較多了解和認識,即蜀藩偏居邊地,借助當地佛道神靈信仰能有更顯著的治理效果。
由此不難看出,歷史上朱椿在治理蜀地時,仰賴更多的是佛道教,而非傳統儒家的禮樂之教。但是,蜀王朱椿對佛道二教與蜀地政治關系的認識和實踐皆被排除于官方文獻之外,一如“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之失載于朱椿傳記。在儒家知識分子所主導的官方文獻傳統中,這樣的情形并不稀見。
雖然朱椿所著力建構的,對其成功化解政治危機、烘托賢王形象曾發揮關鍵作用的“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被中央朝廷官方文獻刻意屏蔽,但若轉向民間文獻,仍能發掘出不少信息。在此方面,清道光年間李西月重編《張三豐先生全書》,保存了不少明清以來與蜀獻王朱椿和張三豐相關的文獻,可供參考。其中,“顯跡·見蜀王椿”在鋪敘“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后總結道:“或曰:其后諸王如谷王穗、遼王植,多有不保其封,而蜀王得以居安樂土者,皆祖師教之云。”通過對比永樂年間被改封長沙、后因謀逆而被廢為庶人的谷王朱橞和被改封荊州、后被削去護衛的遼王朱植,可以進一步凸顯出“張三豐入蜀見蜀王”對蜀王朱椿“居安樂土”的關鍵作用。
同書“古今題贈”中的《三豐樓懷古》詩,亦可佐證張三豐對蜀王朱椿的歷史影響。此詩基本是對《明史·張三豐傳》的復述,其中“前不見洪武,后不見永樂。緣何獨謁蜀獻王,秀才奇遇增輝光”四句與朱椿直接相關,句末原注“洪武呼獻王為‘蜀秀才”。在作者的認知中,相較于同為皇室且地位更為尊貴的太祖、成祖先后尋訪“張三豐”而不得,“張三豐入蜀見蜀王”一事確曾對烘托蜀獻王朱椿聲名發揮了重要作用。
前引《張三豐先生全書》中的情節描述、按語、題詩在主題上高度一致,是明清兩代有關“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的歷史記憶殘存,“秀才奇遇增輝光”基本可視作明清以來蜀地民眾對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關系的普遍認識。官方所主導的評價,雖然成功抹除了朱椿賢王形象中的道教底色,轉而將其塑造為儒家賢王典范,但在民間文獻傳統中,“秀才奇遇增輝光”的歷史記憶卻流傳不絕。
除了成功烘托蜀王朱椿的賢王形象,洪武后期“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對“張三豐”神仙信仰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與“三豐寶雞復生”傳說結合,促成了明初“真仙張三豐”的誕生。
在歷代神仙傳說中,“復生”(或曰“尸解”、“陽神出游”等)是神仙異人的重要特征。“復生”故事通常由兩大情節單元構成:(一)眾人見證此異人于某時某地去世;(二)某官員稱曾在異地見到此人,目擊時間與其去世時間一致。這樣的設置,一方面可以達到突破時空的超自然效果,突出復生情節的神異性;另一方面,異地目擊者的身份通常為朝廷官員,從而增加了情節的可信度。在此方面,明初鐵冠道人張中的“復生”故事就很典型。明都穆(1459-1525)《都公談纂》載:“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道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后潼關守臣奏:有鐵冠道人者,以某日過關。計之,即投水之日也。蓋異人云。”鐵冠道人張中“復生”的目擊者是潼關守臣,核心情節是“投水之日”(南京大中橋)即“過關之日”(陜西潼關)。
以此視角考察明初“張三豐”神仙信仰,洪武后期的“入蜀見蜀王”情節在這兩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三豐復生”神話得以成立的關鍵。明代文獻在提及“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之前,往往會鋪敘“三豐復生”一事(見前引《禪玄顯教編》等):民人楊軌山等親眼見證張三豐于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辭世而后“復生”,構成第一個情節單元;“后入蜀,見蜀王”則構成第二個情節單元。但是,由于楊軌山等并不具備足夠的公信力,真正發揮目擊者作用并體現傳說神異性的是“后入蜀,見蜀王”情節。一方面,明代前期文獻《禪玄顯教編》、《大明一統志》等所載張三豐在寶雞金臺觀的去世時間為“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為《書一》所稱朱椿與“張三豐”初次會面時間(洪武二十六年夏秋之際)之下限,常人根本無法從陜西寶雞“瞬移”到四川成都,由此就達到了與鐵冠道人張中“復生”傳說中“投水之日”即“過關之日”相同的超自然效果。另一方面,作為張三豐“后入蜀,見蜀王”情節的“親歷者”蜀王朱椿,其社會地位僅次于皇帝,其尊貴的政治身份和在《與全弌老仙書》中的虔敬態度,極大地增加了張三豐“寶雞復生”、“后入蜀,見蜀王”這兩個連續情節的可信度。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蜀王朱椿是明初“三豐復生”神話得以成立并流行的關鍵人物,其所建構的洪武后期“張三豐入蜀見蜀王”情節是“張三豐”神仙信仰在明初的一次大發展,實乃永樂年間聲勢浩大的尋訪“真仙張三豐”活動之前奏。
New Research on the Tale of “Zhang Sanfeng Went into Shu and Met the Prince of Shu”
Bai Yan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Royal familys searching for “the Unusual”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the belief in the immortal “Zhang Sanfeng”, among which the event “Zhang Sanfeng went into Shu and met the prince of Shu” happened in the late Hongwu era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wever, the academia didn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notation. With the “Yu Quanyilaoxian Shu”, “Zhang Fengxian Xiangzan” and “Huaixian Fu” in Xian Yuan Rui Zhi Ji by Zhu Chun, Prince Xian of Shu, foun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recently, it can be clearly proved that “Zhang Sanfeng went into Shu and met the prince of Shu” was actually fabricated by Zhu Chun himself. Taking the story of Taizu and Zhou Dianxian as template, Zhu Chun made use of the Taoist immortal Zhang Sanfeng to shape his own image of a wise prince, to resolve the political crisis caused by the rebellion of Lan Yu, his father-in-law, and to avoid repeating the same tragedy as the death of his elder brother Zhu Zi, the Prince of Tan and abolishment of the Tan Kingdom. As a result, Zhu Chun survived the crisis, and won the title of “the wisest in the imperial clan”; the plot “(Zhang Sanfeng) then went into Shu, and met the prince of Shu” was also successfully absorbed into the legend of Zhang Sanfeng, becoming the official proof of the myth that “Sanfeng resurrected”.
Key words: The Prince Xian of Shu; Zhu Chun; Xian Yuan Rui Zhi Ji; Zhang Sanfeng; the case of Lan Yu
[責任編輯:凌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