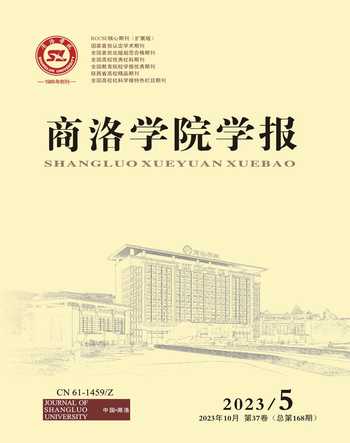論仇重的兒童文學創作
收稿日期:2023-06-04
作者簡介:劉景嘉,女,湖南株洲人,碩士研究生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23.05.009
摘 要:浙江籍作家仇重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被蔣風 稱為“三四十年代重要的童話作家”。他的文學語言天真浪漫,擁有民族性的藝術氣質。抗戰期間仇重未曾間斷的創作實踐,不僅為抗戰時期東南地區的兒童文學創作填補了空白,也使他成為戰后中國兒童文學復蘇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向當時兒童提供了珍貴的精神食糧。在政治、教育童話盛行的時期,仇重的創作雖沒有脫出主流創作思潮的藩籬,但他始終堅持兒童本位的創作觀念,立足現實日常生活關注兒童身體,結合中西各類元素,從“游戲”和“幻想”出發,尊重孩童的基本生命形式,對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有獨特的開拓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仇重;童話;兒童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7.8?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4-0033-(2023)05-0061-06
引用格式:劉景嘉.論仇重的兒童文學創作[J].商洛學院學報,2023,37(5):61-66.
On Qiu Chong's Children's Literature
LIU Jing-ji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Abstract: The Zhejiang-born writer Qiu Chong wa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nd was described by Jiang Feng as "an important writer of fairy tal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His literary language is naive and romantic, and he possesses a national artistic temperament. Qiu Chong's uninterrupted creative practice during the war not only filled in the gap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during the war, but also made him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post-war children's literature revival movement in China, and provided precious spiritual food to the children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fairy tales were prevalent, Qiu Chong's creations did not break away from the mainstream creative trend, he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child-oriented creation,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daily lif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ildren's bodies, combining various element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and respecting the basic forms of life of childr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ames" and "fantasies," which is uniquely pioneering and influential in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Qiu Chong; fairy tales; children's literature
仇重(1914-?),原名劉顯啟(劉重),曾用筆名仇重、柳一青,浙江黃巖塘角橋人,“三四十年代重要的童話作家”[1],曾任團中央出版委員會出版科副科長、黃巖師范學校校長,在《中學生》《小朋友》等重要兒童文學雜志擔任編輯。1946年,仇重經賀宜介紹出任上海兒童書局編輯,參加了“中國兒童讀物作者聯誼會”。1949年,他就職于團中央出版委員會,負責管理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1957年后被下放至長治師范教書,后借調到晉東南地委編史辦公室工作,此后下落不明。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界,仇重是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其兒童文學作品活躍于《小朋友》《兒童世界》《現代兒童》《中國兒童時報》等重要兒童文學刊物上。在戰亂頻發、中國兒童文學屢遭中斷的時期,仇重的兒童文學創作多經波折,但也造就了他豐富的人生經歷。由于其接觸報刊多、活動范圍廣,仇重的創作歷程甚至可被看作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一個縮影。與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文壇頗受關注相比,目前學界對仇重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由于歷史問題,仇重的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被低估的狀態。1984年,賀宜在編纂《兒童文學研究》時將仇重編入其中,文集中收錄多篇對仇重的評價和回憶。此后仇重開始作為三四十年代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回到蔣風等兒童文學評論家的視野。黃衣青曾這樣評價仇重在兒童文學史上的地位:“在當時兒童文學比較荒蕪的園地上,他也算是一個開拓者。”[2]汪習麟惋惜地將其稱為“早年為兒童文學園地作過除棘刈草的作家”[3]。本文試圖立足仇重生平,分析其兒童文學創作的文學觀念及審美特征,以仇重的創作為中心,分析仇重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各類刊物、兒童文學群體的互動,探索仇重在推動現代兒童文學運動發展中的意義。
一、承前與啟后:現代兒童文學視野中的仇重
仇重的兒童文學創作,大致可以分為1932—1937年、1937—1949年、1949—1957年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仇重于1932年開始以《小朋友》《兒童世界》雜志為主要陣地,發表中篇童話《蘋兒的夢》、短篇童話《管家婦》《猴子的墳》《荒蕪了的花園》及寓言《盆景的受難》等,自費出版長篇童話《殲魔記》。第二個階段,仇重于《中國兒童時報》上發表抗戰兒童小說《從風吹來的地方》《海濱小戰士》《祖母的鈔票》等。1948年,他回到上海后,又陸續發表短篇《金牛銀犁》《小木橋》《熊夫人辦學校》《稻田里的小故事》等。第三個階段,由于工作和時代原因,仇重創作的作品較少,僅有《半邊樹》和《哪吒父子》兩部童話。縱觀仇重的文學生涯,其創作從1932年持續到1957年,但創作數量眾多,質量較高。仇重在三四十年代未間斷地創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文學的發展和戰后兒童文學的承接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仇重的創作承接了前期兒童文學運動的發展,有著顯著的恒長性。他在創作高峰期不間斷的創作填補了東南地區兒童文學因戰火而中斷的空白。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動蕩和戰火急速中斷了二十年代剛剛起步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創作,“在戰爭期間,一些兒童文學出版機構被炸毀;《小朋友》《兒童世界》等最有影響的兒童文學刊物被迫陸續停刊,作家、編輯隊伍也迅速星散。中國兒童文學在進行了艱難的抗爭之后一度陷入消沉的困境,中國兒童文學也出現暫時性中斷。”[4]一大批兒童文學作家、編輯在1937年后被迫終止了寫作,而仇重等作家卻在輾轉逃亡之時,依舊堅持著兒童文學的創作。抗日戰爭期間,仇重輾轉于東南浙贛地區,擔任《東南兒童》《現代兒童》《中國兒童時報》①等報刊編輯,其作品也散見于這些刊物。1937—1945年間,仇重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抗戰色彩,無論是童話還是小說都以抗戰為背景:《從風出來的地方》借春風給孩子講故事為由,串聯起四個抗戰故事。文本前言直述:“獻給抗戰中生長起來的中華兒童” “在敵人后方所發生的故事”[5]1。《海濱小戰士》將背景設置在戰時海濱處的村莊,講述了主角小寶幫助游擊隊員躲開日軍追擊的故事。在描述抗戰的同時,作家依舊注重其作品的兒童性,盡量貼合兒童的需求。“我寫時,竭力注意到兒童的閱讀能力,敘述時盡可能不用生僻字義……總想做到‘樸質,‘口語化兩點。”[5]78仇重的作品以其簡單易懂但跌宕起伏的情節、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傾注“抗戰”精神的文本內核,為戰時兒童提供了優質的精神食糧,是戰時兒童文學中具有積極、鼓舞作用的優秀作品。
1945年抗戰勝利以后仇重仍舊努力進行著創作。此時期仇重的作品對同時代乃至此后上海文壇的兒童文學作家們的創作實踐都有著啟發、指導作用,也成為戰后兒童文學復蘇運動的重要研究文本。抗戰勝利后,許多轉入大后方的作家又重新回到上海,仇重便是其中之一。他同一眾作家一起,針對當時政治腐敗、大量低俗刊物充斥市場的情況,成立了“中國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總結前期兒童文學成果,試圖改善并拓寬兒童文學市場。
在此種時代背景下,仇重的作品具有很明顯的教育性。他試圖引導孩童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現實,作品由此形成了“對兒童有益”的現實意義。仇重在1948年提出:“兒童讀物應當表現反映兒童生活,能啟發兒童情致,能收獲生活教育的效果,而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6]16這樣的觀點雖然在現世的評價體系中被認為有過度的說教意味,但這些觀點實際是符合當時的現實要求的。借教育兒童之口來改造社會風氣的創作手法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時代對人們和下一代的期望和要求。仇重的觀點較同時代作家而言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仇重認為:“兒童文學作家也需要關注現實,童話作品也需要社會意義”[7]。他的作品幾乎都有不同程度地同現實的接壤。《歡迎新年》一文展現了新舊社會的交替。故事中蘋兒遇見了準備在1933年同弟弟交接的1932年的老人。借蘋兒的視角,讀者能了解到1932年發生的大事:“譬如中國的大水災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的戰爭啦,帝國主義積極準備世界大戰喲!”[8]36《祖母的鈔票》以金圓券事件為背景,講述小聰祖母珍藏的鈔票買不來半袋米糧的故事。而其他故事中的角色則更多突出舊社會人物的負面色彩:苦難(被魔鬼借糧逼得走投無路的農夫)、貪婪(榨取家長們錢財的熊校長)、無恥(攔橋收費的貪官)。仇重試圖以此向兒童讀者們展示當時百姓在政治經濟上遭受的痛苦,控訴國民黨的腐敗。
仇重在作品中強調的“教育內容”并非對現實的生搬硬套。處在兒童教育荒蕪時代的仇重敏銳地意識到了兒童教育所存在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所謂的‘教育,是單純訴諸知力的……都是生硬的道德教條。”[6]16他認為教育不應當只取材于道德教條,并嘗試將科學性、歷史性的元素融入文本。他在《小朋友》《兒童知識》等雜志上發表圖文并茂的小故事,介紹知識。故事內容也涉及到聯合國概念、月亮形態、雞鴨的膆囊等生活常識。他的作品在顯出教育性和科學性的同時,也未曾失去對兒童的尊重。“凡事合于積極的標準的兒童故事,我們應當盡量選取來供給兒童,使他們建立起健全的人生觀、世界觀與生活態度。”[6]32可以說,仇重既試圖培養兒童健全的身心,又力求讓兒童獲得審美的體驗,注重兒童的興趣與愛好[6]32。仇重的創作實踐在“進步思想引領藝術”的風氣下并未拋卻兒童文學的藝術形式,重視教育而不死板,注重現實卻不生搬硬套,有效推動了兒童文學在上海的發展。
作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最早一批除棘刈草的開拓者,仇重在兒童文學浪潮中的創作、編輯、研究等活動,為現今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他對進步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之間的統一的重視,使他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地位[1]。他始終遵循著“兒童文學運動”中所提倡的“為兒童而藝術”的宗旨。在兒童文學刊物大量停刊、編輯隊伍四處零散的戰爭時期,仇重本人也幾近流離失所,但他從未停止過創作。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又火速加入中國兒童文學復蘇運動,以行動改善、拓寬兒童文學市場。仇重的創作實踐對于承接和推動中國兒童文學復蘇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健康與自由:兒童的日常身體呈現
中國兒童文學在“五四”之前一直處于“非自覺”的發展狀態,通常以童謠和民間故事為最基本的文體形式。作家們自覺運用兒童文學理論進行文學創作的行為則始于“五四”時期[9]。在此背景下,作家們開始關注兒童身體。這種關注表現為對“兒童身體”的各類書寫:兒童身體本身描寫(衣著、外形)、兒童身體內化描繪(心理、精神),以及兒童身體在多種語境中的符號化呈現(消費的主體、救亡的火種、真善美的化身等)。對兒童身體的書寫在不同時代呈現出動態的變化。“五四”以后,文學主流開始傾向于揭露社會的黑暗。兒童的身體由于其弱小的特征常被描寫為慘淡現實的犧牲品。三四十年代,由于革命浪潮迭起,兒童文學作家對兒童身體的描繪在現實主義直面人生的意味上更增添了革命傾向。
與當時的寫實風氣和革命批判話語不同,仇重雖也受到“為人生”的寫作觀念的影響,但其作品中更重視對日常生活的描寫。他認為:“幻想源于真實的生活,而生活故事要有活生生的血肉、生活的氣息”[6]16。其創作動機全然是出于“為兒童”的意識。仇重的一生顛沛流離,但卻時刻參與著兒童文學創作,并在創作期間不斷豐富其作品種類。他的作品類型有童話、寓言、兒童劇本等,幾乎囊括了當時兒童能接觸到的一切文學讀物的形式。作家黃伊極為肯定仇重的創作態度,他曾評價道:“在解放以前,一個人要專業或者說要堅持兒童文學創作,是很不容易的。”[8]2或許正是出于“為兒童”的意識,才使得仇重在革命救亡主題的文學洪流中,并非一味地在作品中輸入救亡意識,而將創作重點置于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兒童,在文本中凸顯出日常、本真的兒童身體。
隨著“五四”啟蒙運動后“兒童本位”論的提出,作家們通常將目光聚焦于兒童的身體訴求,揭示兒童生存環境的艱難和困難[10]。此種創作訴求一般是為暴露現實問題。作者們的預設讀者也并非兒童。因而在此種文本中,作者們表述的更多是成人對于“兒童生存條件”的關心,極少觸及“健康的兒童”。仇重的童話則與之不同。他的文本將身體表達集中于兒童的睡夢、玩耍、進食等日常活動,描繪兒童的身體狀況和感受,直接描繪了兒童“健康的身體”。同時,他站在兒童本位的視角,通過成人—兒童或兒童—兒童的互動形式,從身體外化(肉體)、身體內化(心情、精神)等三個方面展示兒童的自我需求。
在身體外化方面,仇重童話中的孩子都擁有著健康甚至強健的體魄。《蘋兒的夢》中的蘋兒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上海小康家庭的孩子。他活潑好動,“臉頰紅潤得像蘋果一樣”[8]54。《殲魔記》的主角阿土長得很“標致”[8]67、妹妹虎爪蔥有著“櫻桃嘴雪皮膚”,身著“粉紅短衫湖綠褲”[8]83。二人能夠在魔窟里大戰妖魔、跌倒爬起,甚至下河游泳都稀松平常。《笑得好看的人》中則有一段更為直接的描寫:“這孩子的臉,胖胖的,紅紅的,有兩個笑窩。笑起來,兩個笑渦深深地陷進去,就像成熟的橘子一樣,甜蜜極了。”[8]155這些描繪無一例外凸顯了仇重對于健康體魄的重視。不過縱觀其文本,其作品中的具體身體書寫僅是零星地分布于各處,表現得更多的是對兒童情緒、心理的關注。
仇重認為,“興味和愉悅,對兒童肉體的健康、心情的樂觀和道德的涵養,都是很有幫助的。”[6]26因而,在其文本中能夠找到精神價值取向完全兒童化的“自由的身體”:如《蘋兒的夢》中的蘋兒,他即使弄得一身泥漿[8]6,也愿意同小狗玩耍,他會覺得雄雞的樣子很威武[8]13,會不顧母親的阻攔出門堆雪人,會討厭一只偷了妹妹甜糕的花貓。蘋兒所展現出來的跳脫、變化的兒童思維,超越了種族、倫理。他的認知僅僅取決于個人的愛好,不受到外物的干擾,呈現出一種非功利的兒童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由于仇重創作時對于社會大背景的弱化,其童話中更凸顯出了兒童“日常的身體”。蘋兒精神富足,率真可愛,有著明確的喜好(泥人、小金魚、故事書和圖畫冊等等)。他不再是苦難社會中被拯救的對象,而是有著自己喜樂的個體。在故事中仇重鋪就了許多生活細節以突出蘋兒的性格:懶惰(非要躺著看書、穿著臟鞋就睡)、自私(不愿和朋友分享玩具)、純真(會相信父母所述的故事,改正自己)。這些細節都是日常生活中能在孩童身上觀察到,但又未被當時主流創作所記錄的。同時,仇重描寫的蘋兒、蘋兒妹妹和他們的伙伴的形象,都是切切實實處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兒童”。這些孩子對生活有著本真和直觀的感悟,傳遞著屬于兒童的純真與童趣。《向日葵的母親》展示了懵懂的孩童在家庭中學會向家人表達愛意的過程。《同月亮放紙鷂》《蘋兒怎樣生病的》中,蘋兒在夢中遇見了月亮、星星及雪人朋友。故事反映出孩童對于友誼的向往和需要。仇重的作品以其對孩童種種日常動態和心靈需求的描繪,顯現出某種超越時代的前瞻性。
仇重以兒童為本位,創作了符合兒童要求的作品,將帶有其他寓意的符號化兒童身體書寫回歸到兒童身體本身。他的讀本在真實生活的基礎上,反映了時代的發展,以滿足兒童的認知需求為創作導向,同當時社會現實中的兒童保持一致步調,以此來保證作品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內涵。仇重對日常兒童身體的描繪成為戰爭、革命主題之外的另一種表達,為兒童身體書寫增添了多元化的意義。
三、嬉戲與幻想:兒童生命形式的認可
仇重極為重視對兒童游戲行為的書寫。作為一種歷久恒長的人類文化活動,游戲的意義很早便為人們所關注。席勒認為“只有當人在游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11]。荷蘭文史學家赫伊津哈提出“人是游戲者”[12],指出游戲是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游戲的價值由此被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于孩童而言,他們對游戲的渴望出于天然地對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欲求。游戲更是他們最本質的主要生命形式,是一種非功利的純粹活動。象征著“游戲”的嬉戲與玩鬧在很長一段時間未受到成人的重視,處于被限制的狀態。隨著兒童本位論的提出,“游戲精神”才開始出現于作家作品之中。在仇重的作品中,讀者們能夠看到對游戲行為的認可和多樣化的描寫。
仇重并不將游戲視為負面行為。其童話中雖有道德教育的成分,但是他不會將批判游戲作為道德教育的媒介,不會借書中角色之口打壓孩童的游戲欲望。蘋兒被嫌棄的原因只會是“不清潔”而不會被歸咎為“貪玩”。同樣,祖父規勸蘋兒的理由是希望他改掉自私和暴躁的脾氣,而不是他擁有多種多樣的玩具。在《殲魔記》中,游戲更被作為一種推動劇情的方式。阿土通過騎馬游戲前進。虎爪蔥在追趕皮球的過程中掉進了魔窟,由此完成了遇見、打敗癩蛤蟆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說,仇重的童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滿足了兒童游戲的合理性。他對游戲的態度在當時有一定先鋒性。
仇重童話中出現的游戲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生活常態下的純粹游戲(堆雪人、放紙鳶)、弱小戰勝強大(孩子阿土戰勝了丑惡的癩蛤蟆和魔鬼)、歷險記形式(虎爪蔥和阿土在地底世界歷險)、人物出洋相(糟蹋西瓜的偷瓜小兔被抓住)、與其他生命形式的溝通(蘋果樹與果園師傅的對話)等等。縱觀這些游戲形式,可以發現,仇重童話中的游戲形式大部分可以歸納為真假交織、現實變形的幻想游戲。
李學斌指出:“想象游戲”作為兒童置身其中、樂此不疲的本體生命活動,在兒童成長中具有特殊意義[13]。兒童常以游戲的形式來理解成人世界,這同兒童的幻想心理也有關系。“同化心理”會讓兒童更多地從自我意識出發,通過自己想象的世界來調節和現實世界的沖突,以宣泄情感。童話中的幻想描繪同兒童階段的心理特征相符合。而作為童話中非理性的部分,幻想實際也需要同理性的現實相結合,構建于現實之上,于是最初的幻想便開始于對現實的無法解釋。古人無法解釋變幻莫測的自然現象——“泛靈論”應運而生:自然被賦以人格,萬物皆有靈性,甚至萬物等同。兒童眼中更是如此。他們會將能接觸到的事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同等的、可同其游戲的存在。為了契合兒童思維,兒童文學作家在突出“游戲精神”時,通常會采用幻想的手法。瑞士學者麥克斯·呂蒂提出:“童話是人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富有詩意的幻想”[14]。幻想是童話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甚至是其最基礎的存在形式。童話的故事情節歷來都被作家構建于幻想之上。
仇重的童話有著夸張又大膽的幻想色彩,又具備現實與幻想互融的特點。第一,是“純幻想”的特點。仇重在文本中設置了一些非現實場景,用于展示“有生命”的器物。蘋兒的夢中,一切都活了過來:墨水瓶、講義夾會發生爭吵;肥皂、藕粉會主動為主人擦洗帆布鞋;鯉魚會邀請蘋兒去參加婚禮。《殲魔記》第一章標題即點明“大家都在做夢”。于是,主角阿土結識了實質為一把三角凳的朋友“三腳馬”。他還能夠和蝸牛博士、癩蛤蟆溝通。第二,是“同幻想互溶的現實”的特點。《蘋兒的夢》中除去蘋兒做夢的幻想,他在清醒時就時常會對著祖父的照片說話:“‘祖父,你看我的妹妹好不好?祖父好像微微點點頭。泥人小妹妹呢?好像難為情得很。”[8]14而蘋兒在現實中的幻想又會對其純幻想(做夢)產生影響。在隨后的夢中,蘋兒所買的小泥人會嫌棄他自私的性格,而照片中的祖父則會開口教導他。這些幻想情節的描繪既符合少年讀者的理解,又表現了孩童幻想形態的延伸,體現了對孩童們自由暢想和游戲行為的認可和推崇。
仇重創作中的幻想情節顯然受到西方外國童話和中國民間故事的共同影響。在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潮流中,民間故事和神話作為精神資源一直不曾脫離過發展的主流。而在兒童文學界,周作人認為,“童話的實質也有許多與神話傳說共通”[15]。各類兒童文學雜志也頗為提倡民族化特色。鄭振鐸在《兒童世界》的宣言中表示,“因為兒童心理與初民心理相類,所以我們在這個雜志里,更特別多用各民族的神話與傳說。”[16]仇重認為,編寫兒童故事,一是創作,二是改編[6]28。創作故事的素材或是源于將國外作品通俗化,或是將“舊的故事”加以修正[6]30。
仇重的創作受到外國兒童文學的影響,其作品中尤其可見對《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提及和模仿。《蘋兒的夢》的最后一章《尋人》中提及蘋兒讀到此書后,發生了“變大變小”的神奇事件。《殲魔記》主角阿土“掉進洞穴”后遇見魔王。他妹妹虎爪蔥進入魔窟的方式是“追逐皮球跳入井中”。兩種進入幻境的方式相結合便是阿麗思進入奇境的方式(追逐兔子先生跳入洞穴)。故事中的魔王性格殘暴,聽信蛤蟆的讒言,也同喜歡砍臣民腦袋的紅皇后極為相似。在童話材料的吸收和選用中,仇重更為重視的,則是“本國氣味”[6]30。仇重創作時重視保留民族風格。在其原創作品中出現了許多中國民間話本元素,如《殲魔記》中的紅袍道士,人物以“福源” “書月” “超仙”等頗具古意的詞匯命名。仇重創作的后期有著部分改編作品。《烏嘴巴》改編自《格林童話》中《豌豆、木炭和稻草》。在此故事中,他將“木炭”換為中國孩子更易理解的“雞蛋”,將“豌豆”改為“小豆兒”。改編《哪吒父子》這類傳統讀本時,他則考慮保留人物原有的風貌。仇重有著極豐富的民間故事儲備,“1947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曾編寫過一本《兒童神仙故事》的小冊子。”[17]68在改編時,仇重更多地運用其豐富的經驗和歷史的依據,曾借助傳統文物塑造李靖形象:“李靖在傳說中都被稱為‘托塔李天王,不論塑像、畫像,都可以看到他手中托著個玲瓏寶塔;刪了這個情節,未免有失原來傳說面貌。”[17]71。
仇重童話對游戲的內容和形式的描繪符合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背景,有著相對具體的時代內涵,是一種展示時代風貌及舊時兒童體驗的文本。其童話中對游戲和幻想的描繪是對于兒童純粹生命形式的肯定,對中國兒童追求自我、認可自我有著推動性作用,具有現代性特征。
四、結語
仇重是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特殊的存在,他始終堅持兒童本位,重視進步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之間的統一,是中國兒童文學早期的開拓者,也是戰后兒童文學復蘇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對三四十年代孩童的描繪豐富了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兒童形象。他筆下重點描繪的兒童,有別于苦難命題下被拯救的孩童,也不同于戰爭、革命主題中承擔抗戰任務的小戰士:他們是處于日常生活之中,雖然普通,但是擁有健康身體、個人喜好和興趣追求,不再是被時代大潮淹沒了聲音的兒童。仇重作品對游戲和幻想的肯定,展現了他對于兒童快樂和成長需求的認知,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早期現代性觀念的發展。而他作品中的幻想內容,既參考了西方童話的寫作模式,又帶有中國獨特的民間傳統氣質,完成了較好的中西元素融合,對現今兒童文學創作仍有借鑒意義。仇重作品雖有著極強的教育性,但尊重兒童,時刻以兒童志趣為先。這種創作理念使其作品脫離了教條主義,成為極為出色的超脫時代的兒童文學作品。
注釋:
① 《中國兒童時報》在東南地區影響較大,銷量曾突破6 000份。
參考文獻:
[1]? 蔣風.中國兒童文學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645.
[2]? 賀宜.兒童文學研究:第17輯[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4:114.
[3]? 汪習麟.浙江藉兒童文學作家作品評論集[M].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14.
[4]? 方衛平.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史[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7:258.
[5]? 仇重.從風吹來的地方[M].永安:中國兒童時報社,1944.
[6]? 仇重,柳風,鮑維湘,等.兒童讀物研究[M].上海:中華書局,1948.
[7]? 仇重.童話和寓言的現實性[N].時事報,1948-06-16.
[8]? 仇重.仇重童話選[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
[9]? 劉緒源.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3.
[10] 韓雄飛.中國兒童文學的身體書寫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7:10.
[11] 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張玉能,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48.
[12] 赫伊津哈.人·游戲者[M].成窮,譯.貴陽:貴州出版社,1998:210.
[13] 李學斌.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0:5.
[14] 麥克斯·呂蒂.童話的魅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56.
[15] 周作人,趙景深.童話的討論[N].晨報副刊,1922-01-25.
[16] 鄭振鐸.兒童世界宣言[N].時事新報(上海),1921-12-28.
[17] 仇重.哪吒父子[M].天津:新蕾出版社,1981.
責任編輯:王維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