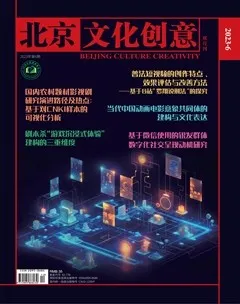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建構(gòu)與文化表達(dá)
方仕成 岳文立
摘要:當(dāng)代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研究,以電影意象論視角切入需要考量意象的觀摩視角與主體構(gòu)成。以此為基,不但可獲得獨(dú)具民族特色的創(chuàng)作思維,還能在此之上建構(gòu)當(dāng)代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本文以中國(guó)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為切入視角對(duì)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進(jìn)行分析,得出其以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和生生不息、周而不比的創(chuàng)作觀念為內(nèi)部構(gòu)建支撐;以文化思維、文化景觀、文化構(gòu)想三個(gè)層次勾畫民族之“象”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以詩(shī)“意”風(fēng)格為文化表達(dá)策略。
關(guān)鍵詞:電影意象 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 意象共同體 民族文化表達(dá)
一、引言
當(dāng)下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發(fā)展已經(jīng)步入新的快車道,動(dòng)畫電影市場(chǎng)正逐步站穩(wěn)腳跟,成為每年電影票房穩(wěn)定的貢獻(xiàn)者。這些動(dòng)畫電影無(wú)論是在故事內(nèi)容方面,還是在視聽表達(dá)方面大抵有相似之處:其一,都在以中國(guó)視角講述故事;其二,都努力走在新時(shí)代動(dòng)畫電影民族化發(fā)展的道路上。然而,與同期在中國(guó)上映的引進(jìn)動(dòng)畫電影相比,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創(chuàng)意與表現(xiàn)能力欠缺這一問題依然存在。當(dāng)下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無(wú)論是國(guó)際影響力、美學(xué)成就還是文化傳播等方面,距離意想達(dá)到的民族化高度還有相當(dāng)大的距離。有鑒于此,探究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民族化傳承與轉(zhuǎn)化的道路越發(fā)值得關(guān)注。
目前,包含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賈磊磊研究員①、潘源研究員②、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張宗偉教授、北京大學(xué)顧春芳③教授等在內(nèi)的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開始根植于當(dāng)下時(shí)代,逐步建立中國(guó)電影意象論理論體系。各方學(xué)者對(duì)此領(lǐng)域深耕,前有張宗偉教授發(fā)問“試圖讓電影故事超越影像脫離現(xiàn)實(shí),僅僅憑形式和技巧就想講好故事,豈不是緣木求魚?”④后有陳林俠教授表示“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需要從整體語(yǔ)境以大觀小,重視意象的生成性,所敘之事、所記之人從矛盾轉(zhuǎn)向差異,從沖突轉(zhuǎn)向和諧”⑤。綜上,可發(fā)現(xiàn)在諸多研究中擁有一個(gè)共同的觀點(diǎn):在電影意象論視域下,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空有故事內(nèi)容,卻忘記了對(duì)隱藏故事本體中情感之“意”的運(yùn)用,也正是“意”的缺失令中國(guó)電影失去了真正的民族特色和國(guó)際立足點(diǎn),陷入故事模式化、人物形象空洞化、主題口號(hào)化的囹圄。民族文化表達(dá)的方式也被片面地誤解為:故事題材是否取材于本土真實(shí)故事或神話傳說(shuō),制作環(huán)節(jié)是否實(shí)現(xiàn)了全流程,人物形象設(shè)計(jì)是否吸收了傳統(tǒng)美術(shù)造型元素,臺(tái)詞是否足夠“吸睛”這類手段上。
基于此,本文引入張宗偉教授提出的電影意象論核心觀念——電影意象共同體⑥,并以其概念作用于動(dòng)畫電影的研究角度出發(fā),以中國(guó)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發(fā)展為切入視角,從動(dòng)畫電影的創(chuàng)作思維、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兩方面出發(fā),進(jìn)一步探索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創(chuàng)作思路,探究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內(nèi)在邏輯與外在表現(xiàn),以求為當(dāng)下的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提供思路,以此錨定民族文化的表意路徑。
之所以選擇中國(guó)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為研究對(duì)象,是考慮相較于其他題材電影復(fù)雜多樣的材料和制作技術(shù),選擇以某一特定題材作為切口,研究特征不僅更直觀——同一題材往往會(huì)隨時(shí)間發(fā)展呈現(xiàn)出更多樣的形式,也從不同程度上展現(xiàn)了所處時(shí)代的獨(dú)特文化。如此作為研究切入視角,也可最大程度避免偶發(fā)性的影響因素介入。這里的“神話題材”采用劉守華在《中國(guó)民間故事史》①提出的廣義神話學(xué)概念,不僅包含狹義的創(chuàng)世神話,也包含民間傳說(shuō)、民間口頭文學(xué)等。以上述條件作為標(biāo)準(zhǔn)綜合考量,根據(jù)孫立軍教授主編的《中國(guó)動(dòng)畫史》②,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發(fā)展幾乎貫穿了以1922年動(dòng)畫廣告《舒振東華文打字機(jī)》為開端至今的中國(guó)百年動(dòng)畫史,新中國(guó)成立前有《鐵扇公主》(1941),建國(guó)后至二十一世紀(jì)初,時(shí)長(zhǎng)超過60分鐘的動(dòng)畫電影皆由神話題材改編而來(lái),具體有《大鬧天宮》(1961,1964)《哪吒鬧海》(1979)《天書奇譚》(1983)《金猴降妖》(1985)《寶蓮燈》(2000)《西岳奇童》(1985,2006)等。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第二個(gè)十年后,仍不斷涌現(xiàn)《西游記之大圣歸來(lái)》(2015)《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白蛇:緣起》(2019)《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新神榜:楊戩》(2022)等神話題材的動(dòng)畫電影。總體而言,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發(fā)展歷程清晰,數(shù)量也頗具規(guī)模,易于進(jìn)行系統(tǒng)研究。
二、從概念到應(yīng)用: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主體構(gòu)成與觀摩視角
“意象是客觀物象和主觀情思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藝術(shù)形象”③。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意象”鏈接了創(chuàng)作者與觀眾之間的精神觸覺,并利用電影影像訴諸和呈現(xiàn)“難以言盡”的生命情感。在這方面,動(dòng)畫電影與一般電影的創(chuàng)作理念并無(wú)二致,皆為寄托創(chuàng)作者“情思”的具體物象被觀眾識(shí)別并接收、理解。不過,動(dòng)畫電影與其他電影種類雖在時(shí)長(zhǎng)、放映機(jī)制、審美機(jī)制等方面有相似之處,但又在具體制作、表現(xiàn)形式等方面有所區(qū)別。因此,運(yùn)用電影意象論研究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需要找到合適的理論切入點(diǎn)。這個(gè)過程需要進(jìn)一步考察動(dòng)畫電影中意象的主體構(gòu)成與觀摩角度,因?yàn)檫@是理論的應(yīng)用根基,關(guān)乎我們應(yīng)如何體察動(dòng)畫中的大千世界,又應(yīng)從何種視角觀摩動(dòng)畫電影中的意象生成和構(gòu)建方式。此外,我們也要明確,考察也必須充分考慮動(dòng)畫本體的特殊性,不能偏離動(dòng)畫的本質(zhì)特征與現(xiàn)實(shí)情況。
(一)“分合有序”的主體構(gòu)成
張宗偉教授認(rèn)為“世界電影意象萬(wàn)千,但不外乎上述‘天地人三種,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天象、地象、人象分而能合,合而趨同則成電影意象共同體”④。這一點(diǎn)不僅點(diǎn)明了各象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也明確了電影意象融合的最終目標(biāo)。且電影的意象構(gòu)成自當(dāng)有其特征,既可以按特定物象進(jìn)行分類,又可以借助電影的整體意象進(jìn)行分析,此種方式也比較符合中國(guó)傳統(tǒng)觀念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觀照角度,即探索“人與自然、人與社會(huì)、人與自我意識(shí)這三個(gè)層面”⑤。但我們也必須明白,考慮到各“象”之間是動(dòng)態(tài)的關(guān)系,以此劃分意象是為了將意象構(gòu)成各個(gè)部分之間進(jìn)行暫時(shí)拆解,并不是割裂其各部分之間的關(guān)系,絕不能孤立地看待“意象生成”⑥這一命題。同時(shí),在動(dòng)畫電影研究中,意象的舉設(shè)與構(gòu)成要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理論的適配。
舉例說(shuō)明,動(dòng)畫電影中的“天象”包含兩類:其一為動(dòng)畫手段制作出的日月星辰等自然景觀或天氣等營(yíng)造出的電影人物的“心外”之象;其二為電影人物觀念中生發(fā)的“心內(nèi)”之象,如為了表現(xiàn)人物情緒低落運(yùn)用的暴雨,展現(xiàn)人物命運(yùn)變化的天地轉(zhuǎn)換等。動(dòng)畫電影中呈現(xiàn)的地上景觀都屬于“地象”范疇。“人象”與上述的“心內(nèi)”之象有所區(qū)別,是“‘近取諸身的結(jié)果,包括跟人的生產(chǎn)生活實(shí)踐緊密相關(guān)的物象”⑦,在動(dòng)畫電影中也指劇中人物行動(dòng)的最終結(jié)果與行為。此外,妖魔的角色也應(yīng)屬于“人象”。當(dāng)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即便是同一“象”也會(huì)有不同的表達(dá)和觀察方式,這就要求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論述動(dòng)畫意象的觀摩視角。
(二)“亂中有序”的觀摩視角
在觀摩視角方面,有取象者和取象對(duì)象兩個(gè)視角。“取象者”是“秉持相同的立場(chǎng)和視野來(lái)觀物”的創(chuàng)作者,“取象對(duì)象”是“觀取者立意的基礎(chǔ)”。①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特定觀摩對(duì)象的依據(jù),至少要滿足以下兩個(gè)條件:其一要有一定規(guī)模的作者、作品群,其二要形成穩(wěn)定的動(dòng)畫風(fēng)格。如20世紀(jì)中國(guó)動(dòng)畫呈現(xiàn)出幾乎以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的作品為主要代表的創(chuàng)作格局,其產(chǎn)出作品數(shù)量已成規(guī)模,且形成了以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技巧與時(shí)代技術(shù)相結(jié)合,以神話傳說(shuō)、志怪故事、民間童謠等為主要故事底本,糅合使用多樣民族器樂作為畫面補(bǔ)充的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完全滿足上述兩個(gè)條件,自可當(dāng)作一個(gè)取象者進(jìn)行研究。又如,當(dāng)代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制作大多數(shù)是以公司和工作室為主,雖然創(chuàng)作流程越來(lái)越趨于工業(yè)化流程,但類型化創(chuàng)作之下仍然保留有導(dǎo)演的個(gè)性化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因此,以創(chuàng)作者(團(tuán)體)進(jìn)行研究時(shí),取象者可以是以某個(gè)導(dǎo)演為主的工作室,也可以是當(dāng)下電影制作的動(dòng)畫公司。像追光動(dòng)畫的“新傳說(shuō)”和“新神榜”系列動(dòng)畫,不僅是由一個(gè)主體公司進(jìn)行開發(fā),還形成了一定的故事模式和畫面風(fēng)格,打造了區(qū)別于一般“改編”的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理念。彩條屋的“神話宇宙”則是對(duì)原有神話故事進(jìn)行續(xù)寫與重構(gòu)。這兩者即為按照以創(chuàng)作者(團(tuán)體)作為取象者進(jìn)行動(dòng)畫研究的范例。若在創(chuàng)作者(團(tuán)體)內(nèi)部進(jìn)行細(xì)分研究時(shí),則會(huì)出現(xiàn)單個(gè)導(dǎo)演進(jìn)行的美學(xué)實(shí)踐活動(dòng)。那便可以根據(jù)取象對(duì)象展開進(jìn)一步的劃分——取象對(duì)象為某一特指的物象,以成就特定風(fēng)格便于辨識(shí)。同時(shí),也可按照包括但不限于導(dǎo)演風(fēng)格、創(chuàng)作形式與題材、創(chuàng)作材料等取象對(duì)象進(jìn)行的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趙霽導(dǎo)演先后執(zhí)導(dǎo)《白蛇:緣起》《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楊戩》,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特征的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思維,可以當(dāng)作特殊的取象對(duì)象;《大鬧天空》《金猴降妖》《西游記之大圣歸來(lái)》是以孫悟空這一主要角色為取象對(duì)象的動(dòng)畫創(chuàng)作,《哪吒鬧海》《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都是以哪吒作為主角,《寶蓮燈》《新神榜:楊戩》的故事中都有楊戩,類似這三者的情況都可以從特定角色作為“取象對(duì)象”歸納研究;近年來(lái)的《秋實(shí)》(2018)、《深海》(2023)等水墨動(dòng)畫作為一類研究,與之相似的還有獨(dú)具特色的偶動(dòng)畫等。
此外,我們還需要進(jìn)一步理解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一方面,這個(gè)概念就當(dāng)下的“電影共同體美學(xué)”而言,順應(yīng)了后者“尚同”“存異”“崇和”“共美”②等理論的整體思維,強(qiáng)調(diào)各部分之間的互動(dòng)與協(xié)調(diào),甚至可以說(shuō)在一定程度上是當(dāng)下動(dòng)畫電影語(yǔ)言“再現(xiàn)代化”的理論產(chǎn)物。但“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與“電影共同體美學(xué)”也有所不同,前者重點(diǎn)放在以動(dòng)畫電影影像作為文化現(xiàn)象的研究,而后者則更強(qiáng)調(diào)電影作為創(chuàng)作者與受眾連接的橋梁;另一方面,本文試圖建構(gòu)“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不僅是為了達(dá)成前文所提及的動(dòng)畫電影敘事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更重要的是意圖突破當(dāng)下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跨文化傳播困境。尤其是在視效方面已漸成特色的當(dāng)代動(dòng)畫制作背景下,中國(guó)動(dòng)畫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是值得中國(guó)動(dòng)畫人持續(xù)關(guān)注和探究的問題。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理論正是對(duì)這一問題的時(shí)代應(yīng)答。因此,更有必要弄清楚這個(gè)理論的內(nèi)部構(gòu)建邏輯和外在表現(xiàn),以便更好地指引動(dòng)畫行業(yè)的發(fā)展。
三、創(chuàng)作表現(xiàn)與觀念:建構(gòu)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內(nèi)部支撐
就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而言,若將營(yíng)造“象”視為外在表現(xiàn),那么塑造“意”即為其內(nèi)部理念,兩者貫穿于創(chuàng)作中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由表及里,勾連、架構(gòu)了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若要探尋其內(nèi)部規(guī)律,可將這二者歸于創(chuàng)作表現(xiàn)與觀念之上,并以特定關(guān)照對(duì)象為切口進(jìn)行以小見大的討論。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大致發(fā)展經(jīng)歷可分為“神話美術(shù)片”“神話類動(dòng)畫電影”和“新神話”動(dòng)畫電影③三個(gè)時(shí)期,雖然影像風(fēng)格受時(shí)代變革、科技發(fā)展等因素影響各有不同,但仍呈現(xiàn)出一條較為清晰的發(fā)展路線。盡管各時(shí)期影片風(fēng)格和美學(xué)特征都各有特色,但導(dǎo)演或?qū)а輬F(tuán)隊(duì)卻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思維:即由“觀物”至“立意”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與兼具“生生不息”“周而不比”的創(chuàng)作觀念。可以說(shuō),這種思維應(yīng)是構(gòu)建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內(nèi)部支撐。
(一)“觀物取象”與“立象盡意”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
通常,電影創(chuàng)作是為了表“意”而非表“象”。就像《哪吒之魔童降世》是為了表現(xiàn)“我命由我不由天”,而不是靈珠嗜魔丸,《西游記之大圣歸來(lái)》是為了表現(xiàn)困頓潦倒之人的覺醒,而不是悟空降妖。包括動(dòng)畫電影在內(nèi)的電影創(chuàng)作不是對(duì)物質(zhì)世界的完美復(fù)原,而是要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造新故事的情感化、戲劇化。然則表“意”離不開對(duì)“物”的依賴。所以,一部?jī)?yōu)質(zhì)的動(dòng)畫電影絕不應(yīng)只追求視效奇觀,導(dǎo)演利用故事文本、畫面呈現(xiàn)、音畫相合等手段“立象”,讓“眼中之象”變?yōu)椤靶刂兄蟆边M(jìn)而生產(chǎn)“活動(dòng)影像”①,這便是電影創(chuàng)作觀念中完整的“觀象取物”“以象言意”的過程。正是對(duì)這種“以實(shí)載虛”的認(rèn)識(shí)與把握,塑造了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世界觀、美學(xué)觀,調(diào)動(dòng)了觀眾的情感。這種創(chuàng)作表現(xiàn)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
1.“神話——原型”思維對(duì)故事文本的觀照與移用
在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中,創(chuàng)作者往往延續(xù)了對(duì)某些神話故事背后原型的借鑒或移植,即我們看到的每一個(gè)電影故事背后,都有能引發(fā)我們情緒共鳴的原型故事。通過建立新故事與原故事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使觀眾看到故事后下意識(shí)地將個(gè)人情感與故事時(shí)空聯(lián)系到一起,以此完成文本層面的以象言意的過程。被動(dòng)畫復(fù)原的畫面搭建了共情的橋梁,并加入了宏大敘事的電影創(chuàng)作手法,這樣構(gòu)建的動(dòng)畫世界觀不再停留在虛構(gòu)層面,不僅讓觀眾不再成為單純的“旁觀者”,也讓動(dòng)畫電影的故事文本厚度發(fā)生了變化。在《西游記大圣歸來(lái)》中,江流兒為了救出孫悟空不惜犧牲自己去引誘混沌,卻不幸被山頂落下的亂石掩埋,孫悟空徒手在沙石中挖掘,卻只得見碎石中伸出一只毫無(wú)生機(jī)的小手。這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地震救援時(shí)的慘烈景象,“大手牽小手”的大圣不免隱喻了這一場(chǎng)景。相同的創(chuàng)作手法還出現(xiàn)在《大魚海棠》最后的神界浩劫上,天地失色,洪水奔涌,鳥獸四散,這極易讓人將其與洪水災(zāi)難聯(lián)系到一起。這種文化層面的摹畫達(dá)成了對(duì)觀眾精神世界的穿透性,調(diào)動(dòng)了觀眾的情感,也為后續(xù)故事線索的開發(fā)埋下種子。
2.“寫意”“留白”與畫外之意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這是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最直觀、最易感受的視覺表現(xiàn)。導(dǎo)演一般用三個(gè)方面實(shí)現(xiàn)對(duì)視覺之“象”的營(yíng)造:首先是畫面制作的技法層面。早年間中國(guó)美術(shù)片的發(fā)展就離不開對(duì)水墨畫技法的運(yùn)用,《天書奇談》中意蘊(yùn)飄遠(yuǎn)的遠(yuǎn)山與縹緲煙云籠罩的視效,人物動(dòng)作、形象借鑒于中國(guó)戲曲的《大鬧天宮》《哪吒鬧海》等,畫面無(wú)一不參考了中國(guó)畫中典型的造型風(fēng)格。事實(shí)上這樣的特質(zhì)在后續(xù)的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中得到了沿用。如在追光動(dòng)畫“新傳說(shuō)”“新神榜”系列中,每一部都呈現(xiàn)了利用現(xiàn)代技術(shù)制作的水墨動(dòng)畫片段,如白素貞的心靈空間、小青步入的黑風(fēng)洞、哪吒覺醒的神秘空間、楊戩落入的太極圖等皆是如此。其次是現(xiàn)代電影技術(shù)帶來(lái)的銀幕空間拓展。美術(shù)片的二維動(dòng)畫技法是平面內(nèi)容的表達(dá),“將中國(guó)繪畫中的技法和原理、造型觀念、空間概念兼收并蓄,融會(huì)貫通”②,接收動(dòng)畫之意主要是依靠對(duì)中國(guó)國(guó)畫的鑒賞過程。在后續(xù)的動(dòng)畫發(fā)展中,三維技術(shù)的引用打通了技術(shù)壁壘,觀眾感受到更立體的視覺效果,也助力導(dǎo)演對(duì)意象“留白”的營(yíng)造能力。最后是場(chǎng)景空間的畫外之意,即對(duì)電影空間“潛臺(tái)詞”的運(yùn)用。這一點(diǎn)與運(yùn)用何種技術(shù)關(guān)聯(lián)不大,更多有賴于意象引發(fā)的審美認(rèn)知,是觀眾對(duì)動(dòng)畫電影的具體情節(jié)、具象道具、特定物像等彌散而來(lái)的情感共鳴。如《大鬧天宮》中孫悟空扶搖直上,打碎了虛懸的“靈霄寶殿”牌匾。孫悟空作為無(wú)數(shù)人的精神凝結(jié)體,在虛構(gòu)的動(dòng)畫世界中完成了打破偏見和封鎖的時(shí)代課題,振奮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還有《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山河社稷圖不僅是世外桃源,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夢(mèng)幻圖景。
3.民族樂器的曲樂與造型元素打造出的獨(dú)特東方氣韻
在動(dòng)畫電影意象構(gòu)建的過程中,若放棄了音樂的參與,便失去了“立象”的重要手段。盡管當(dāng)下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中對(duì)視覺效果的重視已經(jīng)被拉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若缺少了聲音意象的配合,再精美的畫面也無(wú)法營(yíng)造生動(dòng)的想象空間。中國(guó)動(dòng)畫向來(lái)不缺少民族器樂的點(diǎn)睛運(yùn)用。如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黑化的畫面值得一提:周身環(huán)繞的火焰己帶給觀眾極大的視覺沖擊,此時(shí)嗩吶獨(dú)奏漸起,高亢嘹亮的聲音搭配“魔童”的形象渾然天成,再搭配眾人驚愕的表情,可謂用最少的筆墨便成功塑造了人物。還有《新神榜:楊戩》的影片開頭,撰滿姓名的封神榜在時(shí)空中游蕩,所過之處皆是斷壁殘?jiān)嬐庖襞浜蠑鄶嗬m(xù)續(xù)的口琴聲,蕭瑟悲涼的情感瞬間躍然于銀幕之上。
(二)“生生不息”與“周而不比”的創(chuàng)作觀念
以特定題材為“象”進(jìn)行分類,中國(guó)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大致有兩類創(chuàng)作形式:其一是固定“象”的開發(fā)與再創(chuàng)作,如“西游”“封神”系列;其二是重新確立新的“象”,如后續(xù)陸續(xù)產(chǎn)出的“白蛇”“山海經(jīng)”系列等。誠(chéng)然,這些題材是“由新到舊”的動(dòng)態(tài)過程,所以這里的概念也是一個(gè)較為流動(dòng)性的概念。但無(wú)論如何發(fā)展,整體看來(lái)都呈現(xiàn)出“生生不息”與“周而不比”的兩種創(chuàng)作觀念。
1.“生生之謂易”
在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發(fā)展中,同一題材在不同時(shí)代背景下總是常更常新的,是不斷解構(gòu)與重構(gòu)的。無(wú)論是我們熟悉的“西游”還是“封神”,其實(shí)也都是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拆解與創(chuàng)新。從《哪吒鬧海》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從《鐵扇公主》《大鬧天宮》《金猴降妖》到《西游記之大圣歸來(lái)》,相同題材背景與同一人物的解讀是隨著時(shí)代發(fā)展一路演化的,每一版本的故事和人物形象都是符合當(dāng)代發(fā)展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上述題材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一定還會(huì)出現(xiàn)其他的發(fā)展和演變。
2.“君子周而不比”
眾所周知,開啟20世紀(jì)50-80年代中國(guó)動(dòng)畫發(fā)展高峰的“中國(guó)學(xué)派”時(shí)期的重要標(biāo)志,就是中國(guó)動(dòng)畫人開始堅(jiān)定地回歸中國(guó)動(dòng)畫民族化的代表作品《驕傲的將軍》(1957)。而后經(jīng)過無(wú)數(shù)人的努力,最終有了享譽(yù)世界的“中國(guó)學(xué)派”。60年后,《西游記之大圣歸來(lái)》橫空出世,刷新了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既往認(rèn)知,甚至引發(fā)了“自來(lái)水”①效應(yīng)(即自發(fā)形成的水軍),當(dāng)即重新開啟了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新一輪的發(fā)展。此后的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逐步走出了“唯日美化”為主流的審美困境。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nèi)〉猛伙w猛進(jìn)的進(jìn)步都是在做好自身特色的前提上的,是杜絕一味模仿某類動(dòng)畫或單純以民眾娛樂為導(dǎo)向的。在發(fā)展中學(xué)習(xí)技術(shù)或理念吸納為我用,注入獨(dú)屬于中國(guó)的民族靈魂和本土精神,摒棄單純的“拿來(lái)主義”。正是這種創(chuàng)作觀念開啟了中國(guó)動(dòng)畫新一輪的發(fā)展,這也是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的文化自信,既不媚外,更不媚人。
四、民族與詩(shī)意: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外在表現(xiàn)與文化表達(dá)
動(dòng)畫電影作為新時(shí)代背景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之一,必須重視其本身的審美觀念與立意表達(dá)。落實(shí)在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中各意象的運(yùn)用上,各要素分而各立,合而一體,流動(dòng)性地搭建新時(shí)代動(dòng)畫電影的受眾審美。正是這種受眾審美的合力構(gòu)成了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無(wú)論是“象”的運(yùn)用亦或是對(duì)“意”的融合,其本質(zhì)都是為了達(dá)成這一目標(biāo)。縱觀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實(shí)際文本創(chuàng)作,這種創(chuàng)作實(shí)現(xiàn)途徑有兩個(gè);其一是精神世界的物質(zhì)轉(zhuǎn)化,即以影像符號(hào)表現(xiàn)民族精神;其二是對(duì)物象的辯證統(tǒng)一,即影像符號(hào)與民族精神的和諧共生。這不僅是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外在表現(xiàn),更是動(dòng)畫電影的民族文化表達(dá)策略。
(一)全球化趨勢(shì)的中式美學(xué)解碼——勾畫民族文化之“象”
神話作為古人對(duì)未知事件的描述,其本身不僅蘊(yùn)含著集體無(wú)意識(shí),還飽含著對(duì)未知世界的浪漫想象。流傳至今的瑰麗故事不僅符合創(chuàng)作動(dòng)畫對(duì)想象力的需要,也是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取之不盡的題材源泉。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正是將其進(jìn)行順應(yīng)時(shí)代需求的民族化再創(chuàng)作,其中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目標(biāo)就是以動(dòng)畫審美活動(dòng)勾勒民族文化意象。必須要說(shuō)明,本文闡述的民族意象指的是中國(guó)精神的文化符號(hào),“是民族精神凝練的內(nèi)核象征”②。張宜山在《中國(guó)文化精神》中解釋說(shuō)“文化是一個(gè)包含多層次、多方面的統(tǒng)一的體系,或者說(shuō)是許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結(jié)構(gòu)的系統(tǒng)”③,這其中定然包括了蘊(yùn)含在物象內(nèi)的(民族)文化意象。筆者以為,若要正確運(yùn)用其中深意,可將這個(gè)意象分為文化思維、文化景觀、文化構(gòu)想三層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理解。
1.“不忘本來(lái)”的文化思維
張宗偉教授在《百年中國(guó)動(dòng)畫審美創(chuàng)造之路》的座談會(huì)中表示,“對(duì)于中國(guó)特色、中國(guó)學(xué)派而言,民族化的問題是根本問題,立足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忘本來(lái)是立身之本”④。亞洲第一部長(zhǎng)篇?jiǎng)赢嬰娪啊惰F扇公主》在萬(wàn)氏兄弟手下誕生,以動(dòng)畫的方式帶給無(wú)數(shù)國(guó)人以精神層面的力量。事實(shí)上,這部開中國(guó)長(zhǎng)篇?jiǎng)赢嬛群拥淖髌酚谥袊?guó)動(dòng)畫的影響,堪比《定軍山》對(duì)于中國(guó)電影的影響——?jiǎng)?chuàng)作與時(shí)代相符、滿足人民審美的文化作品,始終埋藏在動(dòng)畫創(chuàng)作者的潛意識(shí)中,也是中國(guó)動(dòng)畫創(chuàng)作人的思維根基。
2.“一體多面”的文化景觀
以近年上映的《白蛇:緣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為例,其故事圍繞前世、今生雙重線索展開,前一部描摹小白與許仙前世的緣分起點(diǎn),其中人妖愛戀是跨越物種和生死的重大情感,后一部則將故事線索放置在小青身上,又營(yíng)造了諸多與現(xiàn)實(shí)性格接近的男性形象。無(wú)論是“人和妖”還是“男與女”,其本身都是“物”層面的存在。他們彼此而立但又不會(huì)分離,如一體多面讓觀眾進(jìn)行思考。情緒的介入和故事的推進(jìn)為后續(xù)樹立“心象”奠定了基礎(chǔ),也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視角,突破了以往動(dòng)畫電影人物扁平化的困境。當(dāng)然,文化景觀絕不只是文本、視覺呈現(xiàn)這兩個(gè)維度,還要結(jié)合時(shí)代背景、風(fēng)俗民情、場(chǎng)景、道具服飾等一同進(jìn)行細(xì)致分析。
3.“美美與共”的文化構(gòu)想
文化構(gòu)想是多要素呈現(xiàn)的,也是一個(gè)國(guó)家、民族的時(shí)代形象和文化立場(chǎng)。欲成就這個(gè)構(gòu)想必須實(shí)現(xiàn)“‘共同體敘事的共情、共鳴與共振”①。動(dòng)畫電影經(jīng)由打造藝術(shù)價(jià)值訴諸對(duì)文化構(gòu)想的闡釋,毫無(wú)疑問,這個(gè)過程是根由物象達(dá)成觀眾心象的過程,也是經(jīng)由故事升華至民族形象的過程。主要角色在落入逆境之中,掙脫不得,然而一瞬永恒的思想頓悟最終點(diǎn)明了“意”的生成。如在《魔童降世》中,哪吒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使得其人物形象一瞬間變得貼近成年人,因而打動(dòng)了坐在熒幕前的觀眾。哪吒在迎接天劫咒前對(duì)雙親的跪拜,也不能只理解是單純的“孝”,還是一種與過往種種的和解與奮起,前路如何“由我自己說(shuō)的算”。《新神榜:楊戩》中,更是用“守護(hù)蕓蕓蒼生”確立了電影的最終基調(diào),楊戩元神向天庭“舊勢(shì)力”揮出巨斧的那一刻,像極了當(dāng)下新世代的年輕人對(duì)“舊思想”的宣戰(zhàn)。對(duì)于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而言,這些都是作為文化構(gòu)想的一部分,也是最終的民族精神的呈現(xiàn)。
(二)傳統(tǒng)文化與時(shí)代精神的再書寫——“意”無(wú)窮的詩(shī)性表達(dá)
米特里說(shuō),電影最后要達(dá)成“超越敘事意義的詩(shī)意層面”②。詩(shī)意不僅是優(yōu)質(zhì)電影的最高藝術(shù)表達(dá),更是導(dǎo)演與觀眾心靈溝通的最終歸宿。但隨著當(dāng)下動(dòng)畫電影市場(chǎng)的逐步建立,一種類型化的動(dòng)畫創(chuàng)作模式逐漸彌散開來(lái)。徐洲赤曾提出“強(qiáng)調(diào)電影的詩(shī)性,是希望電影能夠回歸真正的心靈,保持創(chuàng)作的激情,最大限度扭轉(zhuǎn)電影工業(yè)的平庸化趨勢(shì)”③。這一點(diǎn)建議對(duì)創(chuàng)作動(dòng)畫電影依然適用。
從歷史維度來(lái)看,中國(guó)動(dòng)畫詩(shī)意風(fēng)格的形成產(chǎn)生于一定的過程,但毫無(wú)疑問,在百年動(dòng)畫歷程中,其巔峰就是“中國(guó)學(xué)派”時(shí)期。然而,改革開放后國(guó)外動(dòng)畫電影對(duì)中國(guó)市場(chǎng)的擠壓遠(yuǎn)超預(yù)期,以至于中國(guó)動(dòng)畫人在二十一世紀(jì)前十年進(jìn)行的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幾乎變成了蒙眼過河,不停地追問是美式還是日式?其實(shí),這種迷茫的思維“除了受資本的影響所導(dǎo)致的過多看重經(jīng)濟(jì)利益,而輕視藝術(shù)性,以及來(lái)自美日動(dòng)畫電影的沖擊和從業(yè)人員心態(tài)上的急功近利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國(guó)學(xué)派自身的傳承斷代,在新視覺技術(shù)與產(chǎn)業(yè)化語(yǔ)境下沒能對(duì)東方神韻進(jìn)行很好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④。如此,丟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詩(shī)意呈現(xiàn),就等同于抽掉了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真正的民族之魂。
幸運(yùn)的是,中國(guó)動(dòng)畫新生代導(dǎo)演并沒有因?yàn)槌砷L(zhǎng)空間被國(guó)外動(dòng)畫侵占,就放棄對(duì)中國(guó)本土美學(xué)的追求。盡管當(dāng)下從業(yè)人員對(duì)如何借助電腦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呈現(xiàn)的效果轉(zhuǎn)化,技術(shù)水平還稍顯不足,但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開發(fā)已經(jīng)走在了一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道路上。這個(gè)過程不是效仿日本作者動(dòng)畫或好萊塢工業(yè)動(dòng)畫,這一詩(shī)意風(fēng)格是視覺與聽覺的詩(shī)意風(fēng)格,糅合了中國(guó)特有的時(shí)代價(jià)值、故事與人物,這一特質(zhì)在光怪陸離的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中呈現(xiàn)得更為明顯。通過張弛有度的敘事手法、音畫相合的視聽語(yǔ)言、立體飽滿的人物形象,鐫刻了屬于新時(shí)代的情感體驗(yàn)與精神意蘊(yùn)。如《姜子牙》中主角站在輪回大門前直面灑來(lái)的夕陽(yáng)余暉,而后又在天梯之上對(duì)真理的不停追問;《白蛇2:青蛇劫起》的黑風(fēng)洞里小青與法海的對(duì)抗運(yùn)用了傳統(tǒng)電影創(chuàng)作觀念中的時(shí)空概念,達(dá)成了“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的具象奇觀等。可以說(shuō),在經(jīng)歷了高峰與低谷后,在明晰了功能定位、文化底蘊(yùn)和技術(shù)手段后,“中國(guó)學(xué)派”播撒下的詩(shī)意種子已經(jīng)發(fā)芽。
五、結(jié)語(yǔ)
在當(dāng)下電影工業(yè)化進(jìn)程日趨完善的語(yǔ)境中,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逐漸擺脫低齡化趨勢(shì),開始深入探索時(shí)代價(jià)值與故事內(nèi)涵和諧轉(zhuǎn)化的發(fā)展道路。運(yùn)用電影意象論的理論觀點(diǎn)進(jìn)行研究,可以為當(dāng)下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鋪設(shè)一條新的民族化創(chuàng)作思路和以自身發(fā)展為依據(jù)的動(dòng)畫電影理論框架。這個(gè)過程既要遵循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生生不息”與“周而不比”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規(guī)律,也應(yīng)秉持以精神世界的物質(zhì)觀表達(dá)、受眾價(jià)值觀轉(zhuǎn)化為內(nèi)在邏輯,達(dá)成全球化趨勢(shì)的中式美學(xué)解碼,傳統(tǒng)文化與時(shí)代精神的再書寫為外在表現(xiàn)的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之發(fā)展趨向。此外,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或是新時(shí)代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民族化展現(xiàn)的最終成果之一,其既可以形成一面彰顯中國(guó)形象的旗幟,又同步構(gòu)建了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理論話語(yǔ)。筆者自知學(xué)識(shí)有限,且包括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在內(nèi)的中國(guó)電影意象論也處在動(dòng)態(tài)構(gòu)建的初期階段,定有不足之處以待后續(xù)深入研究進(jìn)行補(bǔ)充,這也將是本人后續(xù)的研究動(dòng)力與方向。盼此文能用作拋磚引玉之用,以待更多專家、學(xué)者加入到動(dòng)畫電影意象共同體的研究之中。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在讀研究生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資助項(xiàng)目“中國(guó)‘新生代電影意境中季節(jié)意象文化內(nèi)涵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CXZZSS2023173)階段性研究成果;河北傳媒學(xué)院第14屆校級(jí)重點(diǎn)課題項(xiàng)目(研究生教育專項(xiàng))“電影意象論視域下中國(guó)神話題材動(dòng)畫電影的民族文化表達(dá)研究”(編號(hào):KTYJS202202)研究成果
作者:
方仕成,河北傳媒學(xué)院研究生院2023屆碩士研究生,江西軟件職業(yè)技術(shù)大學(xué)新媒體學(xué)院教師,研究方向:影視編劇,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創(chuàng)作
岳文立,河北傳媒學(xué)院影視藝術(shù)學(xué)院影視文學(xué)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視編劇
(責(zé)任編輯:谷明哲)
Abstract: To study Chinas contemporary animated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lm iconograph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viewing angle and constituent subject of image. Based on this, the creative thinking with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achieved, and the image community of contemporary animated films can be constructed on top of that. This paper analyzing from the starting viewpoint of Chinese myth-themed animated films, the creative expression of abstracting images from viewing, and using imagery to express meaning as well as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life and growth in nature, and broad-minded but not partisan act as the support fo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mage community of contemporary animated films; while outlining the “image” of nation and the style of poetic “meaning” from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ultural thinking,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act as its external manifestation and its strategy for cultural expression.
Key Words: Military Film, Chinese Animated Film, Imagery Community, Na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