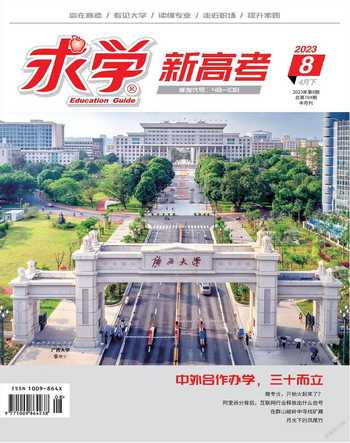假如人生可以觀看
1964年,在倫敦富裕地區(qū)肯辛頓的一所私立學(xué)校里,學(xué)生們穿著得體,正在課堂上用拉丁語唱著《叢林流浪》。課間,有三個男孩接受了采訪,其中一個男孩說:“在這里畢業(yè)以后,我會去考雷特公學(xué),然后去讀威斯敏斯特寄宿學(xué)校,再接著努力進入劍橋大學(xué)。”另外兩個男孩也不約而同地說出了類似的求學(xué)路線,理想大學(xué)不是劍橋大學(xué),就是牛津大學(xué)。這一年,他們7歲。
同時,生活在倫敦東區(qū)、約克郡和福利院的幾個孩子也被問到未來的打算,有的說想成為騎師或宇航員,有的說希望工作之前能到處走走,還有的孩子一臉茫然地問:“大學(xué)是什么意思?”
7年后,肯辛頓地區(qū)的三個男孩14歲了,他們按部就班進入了理想學(xué)校,并開始為成為律師、作家而做準備。又7年后,他們21歲了,三人中的兩位進入了牛津大學(xué)法律系,另一位則入讀杜倫大學(xué)歷史系。
而那位想成為騎師的東區(qū)男孩,14歲就開始在賽馬場打零工,21歲在賽狗場幫人下賭注,28歲成為一名出租車司機。
希望成為宇航員的孩子,14歲時,他開始覺得那個愿望只是7歲孩子的美好想象;21歲時,他是倫敦大學(xué)的在讀學(xué)生,對未來的規(guī)劃還有些迷茫。
其他的孩子,大多沒有讀大學(xué),21歲的年紀,或在工廠上班,或在工地搬磚,他們有的后來甚至依靠政府救濟為生。
在所有家庭經(jīng)濟條件一般的孩子中,只有一個男孩依靠獎學(xué)金讀完了私立寄宿學(xué)校,考入了牛津大學(xué),最后移民美國,成為一名大學(xué)教授。
上述孩子的故事源自中文譯名為《人生七年》的英國系列紀錄片。《人生七年》攝制組想要探索“一個人出生的社會階級,將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他的未來”,而英國有一句俗語“Give me a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可以理解為我們常說的“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于是攝制組找了14個不同階層的7歲英國小孩,請他們聊聊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此后每隔7年重新訪問一次,記錄下他們生活的變化。
目前,《人生七年》已經(jīng)拍了9部,分別為《7up》《14up》《21up》《28up》《35up》《42up》《49up》《56up》《63up》,是以主人公們當(dāng)時的年齡來命名的。
隨著拍攝的展開,這一紀錄片的導(dǎo)演意識到自己拍攝的并不是“一部關(guān)于英國社會階層的政治電影”,而是“一部正在進行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是如何在快速的社會變革以及充滿偶然與意外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和幸福的。
這一拍攝時間跨越了半個世紀的紀錄片展現(xiàn)了幼時的家庭環(huán)境對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軌跡確實有著極大的影響,但人生是不斷變化著的,意外和災(zāi)難隨時都會突然發(fā)生。
“精英三兄弟”中的約翰在28歲時如愿成為一名律師,后來還成了皇家律師。但他也說過,并不是出身好就代表不需要努力。他在《56up》中透露,其實他的父親在他上大學(xué)前就已去世,家里一度出現(xiàn)財政危機,他憑借獎學(xué)金才讀完了大學(xué)。
富家千金蘇西,在21歲接受采訪時,看起來有些叛逆,大概受父母離異的影響,她提到自己不相信婚姻,對于組建和經(jīng)營家庭還需要再好好想想。但到了35歲,蘇西已經(jīng)步入婚姻,有了兩個孩子,做起了家庭主婦。
中產(chǎn)階級出身的布魯斯在7歲時就說,希望自己長大之后能去到非洲,去幫助、教育那些有困難的人。他從牛津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畢業(yè)之后,確實如他小時候說的那樣,成為一名支教老師,致力于落后地區(qū)兒童的教育事業(yè)。那時,他住在政府的救濟房與學(xué)校宿舍里,對物質(zhì)生活沒有強烈的欲望。四十多歲時,他回到了英國,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依然從事教育工作,但進入了私立名校。
同樣出生于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尼爾,7歲時提到自己長大后想做一個大巴司機,帶著大家去海邊玩耍,滿臉天真爛漫;14歲時一門心思應(yīng)付學(xué)業(yè),眉眼間略帶憂郁;21歲時考上了阿伯丁大學(xué),但沒讀一年,便輟學(xué)打起了零工;28歲時成了靠政府救濟的無業(yè)游民,在英國到處流浪,居無定所。但后來,他的故事又出現(xiàn)了轉(zhuǎn)折。42歲的尼爾回到倫敦,成為社區(qū)的自由黨議員,開始為選民奔走。之后幾年,他開始學(xué)習(xí)大學(xué)課程,業(yè)余時間做牧師、寫小說。
除了尼爾,片中變化較大的人物當(dāng)屬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出生在英國約克郡的鄉(xiāng)村,父母都是農(nóng)民。14歲的尼古拉斯表現(xiàn)得相當(dāng)害羞,面對鏡頭一直低著頭,顯得有些不自信。然而,之后的尼古拉斯卻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21歲時,他是牛津大學(xué)物理系的高才生;28歲時,他已取得博士學(xué)位,同他的校友結(jié)了婚,并在美國當(dāng)教授助理;42歲時,他已升任大學(xué)教授。他被認為通過讀書實現(xiàn)了人生的逆襲,但他的人生并沒有從此一帆風(fēng)順。之后,他還經(jīng)歷了科研項目失敗、離婚又再婚、患上喉癌等一系列事情。
片中工人階級的代表——托尼的人生體驗亦十分豐富。他從小立志成為一名騎師,但在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做騎師的天賦后,就改當(dāng)出租車司機。除了開出租車,他還去電影里跑龍?zhí)祝陀H戚開酒吧,去西班牙置地……幾乎每個階段,我們都能看到托尼的新進展。
7歲時生活在福利院的西蒙長大后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一家肉類冷凍公司做底層工作,中年的時候離婚了。不過,在走進第二段婚姻之后,他改掉了自己懶惰、悲觀的處事方式,在2019年播出的《63up》里,他和妻子經(jīng)營的寄宿家庭累計幫助并撫養(yǎng)了超過130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從1964年到2019年,從7歲到63歲,將近60年間,孩子們長大成人,有成功也有心碎,經(jīng)歷了結(jié)婚或離婚,有人提前退出了拍攝,有人退出又重新加入,也有人在中途離世。可以說,《人生七年》這一紀錄片,除了展現(xiàn)受訪者人生的巨大反差,同時也暗示著人生的“不可預(yù)測性”。
另外,這一紀錄片也引起了人們對教育的討論。有人說:“想要實現(xiàn)階層流動,教育是關(guān)鍵。”片中的主角們也提到了自己對于讀書的看法。安德魯說:“人無法確定能留給下一代什么財富,但是至少可以確定,一旦給了他們好的教育,他們終生都可以受用。”托尼在21歲時表示教育不是很重要,但在28歲又提到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顯然會獲得更多的機會。當(dāng)年不知道大學(xué)是什么的保羅,在56歲時說:“不管做什么行業(yè),我都會勸家里的孩子多讀書,我希望教育系統(tǒng)能夠改變,因為受到的教育才是奪不走的。”
在中國,高考被看作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改變命運最重要的途徑。不過,我們也應(yīng)意識到:人生的成敗和意義,不是全部由大學(xué)決定的。沒有上過大學(xué)的蘇和杰基在回憶過去的人生時,表示自己的生活比她們所預(yù)料的更充實、更快樂、更多樣、更有趣。
這十幾個受訪者的故事還在繼續(xù),盡管紀錄片所呈現(xiàn)的他們不夠全面,但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比物質(zhì)的影響更為深遠,而健全的人格是面對苦難最好的解藥;任何的成功與失敗,從來不是平白無故出現(xiàn)的,諸事萬物都有跡可循。
也許,《人生七年》用56年的時間證實了階層和原生家庭會在一個人的人生中起主導(dǎo)性作用,但它永遠無法作為一個簡單的標準,決定一個人最終的命運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