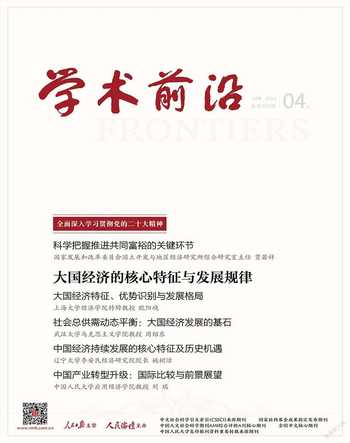數據規則建立與完善之要義
吳飛
【摘要】數據規則涉及面廣,諸如數字鴻溝、數字治理、數字平臺治理、數字市場準入、數字貿易、數字貨幣、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安全等,這直接影響到全球的經濟、軍事、社會治理等領域的未來走向。當前,中國擁有全球最豐富的數據資源,但數據規則的建立起步相對較晚,存在數據安全防護薄弱等問題。因此,需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完善數字中國的數據規則和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開放與共享,確保使用數據的公正性,保障數據安全,為數字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關鍵詞】數據規則? 大數據? 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G20?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9
數字技術的進步,如算法、數據分析技術、物聯網、云存儲等技術的誕生,使得個人或機構的數據可以被采集、存儲和復制,大數據應運而生。據IDC發布《數據時代2025》的報告顯示,全球每年產生的數據將從2018年的33ZB增長到175ZB,相當于每天產生491EB的數據。[1]數字技術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方式,也改變了國家間的互動方式,數據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是社會發展的新能源和動力,是人們創新的力量源泉。[2]在現實生活中,基于數據計算得出的分數(一種數據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個體和企業的命運,成為評估不同國家的自由、幸福、繁榮的標準。人們似乎不是生活在現實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各種數據排序安排好的數據世界里,個體的感知和判斷不是基于自己的觀察和判斷,而是基于他人的評價和算法的推薦指數。
數據與數據規則
“數”的產生是基于人類認識和精確分析自然現象與物的需要以及社會治理的需要,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巴比倫有較為發達的文明,數字知識因勢而生。他們利用數學知識來服務商業活動、交換商品、計算稅收、劃分土地和遺產,甚至用于水利工程和天文觀察。但一直到大數據出現之前,“數”仍然只是自然與社會的一種計算和測量的尺度,是知識得以精確表達的工具。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人與物被數據化呈現,“數”的另一種價值被發視了。人們不再重點討論數字是否是構成宇宙的本質,而是重新思考萬物皆數的“數”到底是什么?今天人們不再將數據看成是財產、關系、能源的一種計量值,而是將它看成是一種新的資源和能源。因此,重新思考在信息時代,“數”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與社會治理等方面有怎樣的意義和挑戰就成為前沿議題。
據ISO/IEC信息技術國際標準的定義,數據“主要體現在數據的數量、種類、速度和/或可變性等特征上,這些特征需要一種可擴展的技術來進行有效的存儲、操作、管理和分析”。[3]“大數據”這一概念真正進入理論學術的視野是在2000年之后,云計算技術出現后大數據的價值才凸顯出來。2006年,谷歌提出云計算概念。2007~2008年,社交媒體迅猛發展,大數據應用開始涌現。2008年起,大數據成為熱詞,同年9月,《自然》雜志推出“大數據”封面專欄。2011年,麥肯錫發布報告《大數據:下一個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前沿》,對大數據概念進行界定,即大小超出典型數據庫軟件工具收集、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并提出“大數據時代”到來。2012年,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庫克耶合著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出版,同年10月,《紐約時報》刊發《大數據時代》一文,大數據概念風靡全球。
有人將2013年稱為“大數據元年”,不管這一提法是否科學,但這一觀點的出現,表明人類正在思考數據對于人類的意義。智能技術發展迅猛,數據似乎已經取代了原子、實體、物質,成為理解這個世界的新“本質”。數據主義(Dataism)者就認為,一切事物、人、人際關系、文化、價值都可以還原為不同算法模式下的數據,[4]甚至認為生物也只是算法,而人的主體性的確立也不過是人類算法的暫時性勝出。這種將一切理解為數據并以數據為中心的世界觀,“不僅表達了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信念,還表達了對人類未來生活樣式、存在意義的理解”。[5]盡管數據主義受到不少批評,但“數據的應用仍在不斷推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6]因此,對數據的科學、合理運用,就成為各國近幾年建構數據規則的核心議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規則是法治社會運行的基礎。
西方國家較早認識到了確立數據規則的重要性,將數據作為維護本國政治安全、輸出價值觀、實現國家意志的戰略手段。美國政府認為一個國家擁有的數據規模和運用數據的能力將成為國家間、企業間競爭和爭奪的重點。2012年,美國白宮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建議組建“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把大數據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奧巴馬政府甚至將大數據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從“五眼聯盟”到“棱鏡”計劃、從帕蘭提爾(Palantir)到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先后構建了系統的大數據的資源體系、科研實驗體系和產業服務體系。
如今,歐盟、美國等數字技術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出臺了大量與數據相關的法規條文,努力讓數字發展成果更多造福人類。據悉,目前全球194個國家中有157個國家制定了保護數據和隱私的立法。就信息數據保護規則而言,歐盟制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和美國出臺的《加利福尼亞州消費者隱私法案》最具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據規則的重視已經形成基本共識,但立法目的不同,具體的條款也有差異,對是否從人格權的定位來把握數據權益的看法也不一樣。因此,還需要有更深入和系統的思考,尤其是有關人的全面數據化問題,更需要從人的本質是什么以及人類社會治理的目的等層面來反思,畢竟數據不僅僅是人與物的虛擬存在的表征,而且是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關系的度量,“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7]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連接是能夠交互反饋的。
數據規則是信息時代的制度基石
“任何數據都是文化的產物,數據內生于特定的社會系統,必然受該系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影響。”[8]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大數據發展日新月異,我們應該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布局、力爭主動,深入了解大數據發展現狀和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我國大數據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9]在信息時代,數據問題涉及面廣,諸如數字鴻溝、數字治理、數字平臺治理、數字市場準入、數字貿易、數字貨幣、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安全等,數據規則的確立會直接影響全球的經濟、軍事、社會治理等的未來走向,會影響人類的命運走向。
從經濟角度看,數據被廣泛隱喻成新型“石油”,而貨幣也在開始數字化,這必然影響經濟布局與全球貿易。《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研究根據數據性質完善產權性質”。“因為大數據技術和產業的發展均以數據為基礎,從而使得數據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10]但數據的價值具有不確定性,[11]且對于哪些數據可以用來交易缺少清晰的界定。因此,建立明晰的數據產權制度,有利于數據產權保護,促進數據交易。2022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提出要探索“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的交易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對風險可控數據交易的一種有效指引”。[12]
從政治角度看,數據成為新的政治權力來源,數字平臺已經成為新的權力機構,正在影響各國的政治力量博弈。“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在于軍事或貿易,還在于其收集、提煉和運用數據的能力。”[13]智能算法可以透過我們在網絡中形成的數字痕跡,精準地描繪出數字的“自我”,這個自我并不在我們內部,而在數字世界之中,它并非“由我們的理性的自我意識構成的,而是由無數我們有意或無意的行為留下的數據構成的”。[14]這使得數據跟蹤與技術分析,成為信息時代一種全新的權力手段。Twitter、Facebook、Google等平臺的數據不僅可以發現恐怖主義行蹤,明確國家風險,還可對特定人群進行精細劃分,對政治態勢進行整體感知,對危機進行預測預警,以輔助政治決策和輿論宣傳。“許多看似無關的多維異構數據在比對、關聯和有效融合后,仍可以推斷出具有穿透力、威懾力的致命信息,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15]
從軍事角度看,對社交媒體的大數據分析,有助于部隊指揮官獲取情報,了解戰場局勢。例如,美國國防部正在實施一系列大數據計劃(如XDATA)以增強防御能力。一般而言,軍事應用通過大量情報、監視和偵察(ISR)傳感器生成大量數據,[16]并且這些數據也可以通過實時、虛擬和建設性模擬生成。[17]此外,將戰場上各種戰斗實體和事件的數據收集在一起會有很好表現,如美國陸軍研究實驗室(ARL)使用分類和回歸樹來預測,準確率達到了80%左右。[18]
從治理角度看,大數據已經覆蓋到社會各領域,包括車、物和人員的流動信息,流行病、氣候變化等信息,社交媒體上的人與社交機器人的互動信息,以及電商平臺不斷更新的消費者偏好數據等。透過這些數據,可以觀察到人與物的流動趨勢、流行病的傳播軌跡、社會輿情的走向與集中度,以及社會上存在的數據鴻溝與數據不平等。這些信息可以為制定公共政策、實施輿情監控、預測犯罪行動和研判反恐形勢等提供更科學的依據。如IBM利用大數據技術,整合、分析交通數據和社交媒體的數據,幫助波士頓政府解決長期困擾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19]
從傳播角度看,平臺在哪里,人就在哪里,而人在哪里,傳播就在哪里。截至2022年5月數據顯示,全球最受歡迎的前五大社交媒體平臺分別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和TikTok。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的全球粉絲增長緩慢,今年甚至出現首次下跌。與此相反,TikTok似乎已經從一個社交平臺變成一個媒體平臺,不少西方主流媒體已經開始入駐該平臺,如美國的ABC News、NBC和英國的BBC、Daily Mail、Sky News等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積極開發TikTok資源。這些平臺擁有巨大的個人、機構方面的信息數據,使動察公眾心態和情緒成為可能。
劉易斯·芒福德曾認為,隨著科學的發展和機器越來越普遍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的秩序正在從實施個人控制的絕對統治者手中轉移到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宇宙中,轉移到我們稱之為機器體系的一些特殊的裝置和規則手中”。[20]也就是說,應當對新的機器體系和新規則給予高度關注。他的《技術與文明》《機器的神話》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議題是機械文明中人類的自由問題。他擔心現代技術造就了一種高度權力化的復雜的大型機器,而權力的壟斷會“導致人格的壟斷”。[21]在信息時代,人們雖然可以用數據技術來闡釋一種新文明——數字文明的興起,但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技術也可以制造死亡和破壞,以及自我毀滅。所以說,健全的數據規則是信息時代的制度基石,也是數字文明的基石。信息技術、數據技術雖然確實在重構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重構我們對于他/它者的感知,權力、客觀性、集體意識、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都會受到影響,但對于人類自身而言,作為人類的“我們”,包括我們的自由、我們的主體性和我們的福祉才是更應該守護的。因此,我們不能盲目持有“數據至上”的理念,更不能用技術思維來解決社會問題,如將綜合治理問題降維成數據技術問題,不能因忽視綜合治理的復雜性而陷入“技術烏托邦”誤區。[22]
數據規則建設的核心要素
2014年5月1日,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發布了總統顧問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牽頭完成的《大數據:抓住機遇、保留價值》報告。該報告提出六點建議,即(1)推進《消費者隱私權利法案》;(2)通過國家數據泄露立法;(3)將隱私保護擴展到非美國公民;(4)確保所采集的學生數據僅用于教育目的;(5)擴充技術特長以阻止歧視;(6)修訂《電子通信隱私法》(ECPA)。應該說,這一報告涉及了數據權益方面的核心內容,中國在健全相關規則制度時可以借鑒。雖然在數據確權方面,歐盟通過統一立法對個人數據進行了強有力的人格權保護,但其法律管轄范圍甚至可以突破歐盟地域限制;美國則通過“分散立法+行業自律”的方式進行隱私保護,在鼓勵創新和保護權利之間達成平衡;中國對個人數據的保護與歐盟相似,建立了完整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框架,《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制個人信息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規制線上和線下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規制網絡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同時具有保護個人信息和隱私的相關規定。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數據規則的制訂有多重的社會要求,包括商業動機、個人人格權保護的動機、國家安全的動機等。目的動機不同,規則的具體內容當然也存在差異,但所有這些規則建立時無外乎都會考慮如下核心要素。
數據真實性。真實性意味著應該使用可信賴的數據,數據的真實與準確程度,直接影響數據使用者的決策與判斷。如客戶的在線評論對商品的系統排名十分重要,虛假評論或欺騙性評分會對客戶的選擇產生誤導。這是各國建立數據規則時重點考慮的內容,如2019年5月,新加坡通過《防止網絡虛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該法案旨在保護社會免遭惡意行為者在網上制造謊言和進行操縱的風險,提高網絡政治廣告及相關事項的透明度。總之,對有關人類公共生活的數據都必須保障最大程度的真實性。
數據共享性。數據科學的發展,源于人類對于數據共享的訴求,而數據也只有在共享中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開發和運用。現階段,數據基本掌握在政府和平臺型公司手中,公民對數據的采集和運用還相當困難。因此,建立數據開放共享機制,就成為數據規則的主要方向之一。相較于歐盟和美國而言,中國雖然已經開始制定數據共享規則,但仍然存在不少差距,在數據共享交換、交易流通方面還存在法規不完善、數據開放程度較低等多方面的問題。
數據安全性。在國際環境復雜、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中國要盡快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數據存儲、流通和使用的安全問題,不僅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民個人隱私保護的重要內容。盡管“促進個人數據自由流通仍然是個人數據保護法的基本目的”,[23]但云計算的發展使國內數據(Domestic Data)的定義越來越模糊,“這可能嚴重威脅個人的隱私權、企業的商業秘密以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24]所以數據的自由且安全的流通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中國、俄羅斯等國向聯合國提交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強調“不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包括網絡實施敵對行動、侵略行徑和制造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合作打擊利用信息技術包括網絡從事破壞他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等行為。[2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2015年9月發布的《理事會關于為了經濟和社會繁榮的數字安全風險管理的建議》中,將數字安全風險界定為“在任何活動過程中與數字環境的使用、開發和管理相關的一類風險”;它們可以“通過破壞活動和/或環境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從而破壞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實現”。[26]201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授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應對敏感個人數據對國家安全的威脅。[2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家網信辦”)2022年7月21日依法對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處人民幣80.26億元罰款,對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程維、總裁柳青各處人民幣100萬元罰款。國家網信辦指出,滴滴公司存在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給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數據安全帶來嚴重安全風險隱患。
數據公正性。人們較早關注到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問題,發現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使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存在不平等問題,包括南北數字鴻溝、代際數字鴻溝等。在數字基礎設施有了較大改進的情況下,應關注數據鴻溝,即數據平等問題,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數字基礎設施、硬件或軟件,或者能夠有效使用數據或數字資源的金融或教育功能,并非所有潛在用戶都能夠將他們的訪問轉化為有意義的應用程序和用途,[28]所以可能導向“強者恒強”的后果,這使得數據規則的建立需要考慮兩方面的情況:一是人們使用數據的公正性,二是數據的使用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能否促進社會公平。這兩方面都會涉及數據的流通、數據共享機制、算法的透明度、代碼的開放性等多方面的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數據正義包括三個核心層,即“數據使用的可見性、技術使用是否事先約定、反對不公平對待”。[29]從數據控制者責任的角度來看,需要確立基于風險防范的個人信息使用規則。從數據使用者的角度看,則要強化合規使用;而對數據擁有者(生產者)而言,則是要盡可能開放數據并共享代碼;對政府而言,要保障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平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就明確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利用個人信息進行自動化決策,應當保證決策的透明度和結果公平、公正,不得對個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不合理的差別待遇”。2022年4月22日,拜登政府發布《促進使用公平數據》的建議書,這是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1月20日簽署的“通過聯邦政府促進種族平等和對服務欠佳社區的支持”第13985號行政命令的后續結果。該建議書指出:“公平數據(Equitable data)是指政府的數據政策和項目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公正與平等的采集、分析和使用個人數據。為實現這一愿景,該戰略提出,所有行為者都應參與到整個數據生命周期中,并致力于促進分類人口數據的收集、保護、管理、分析、傳輸、使用和銷毀。”雖然這一建議書還有待完善,但促進數據公平這一做法還是值得關注的。
數據公共性。大數據可以改變或改善公共生活。數據的公共價值應建立在個體的合理預期基礎之上,有限度地賦予公民以相關信息權利,避免信息權利的泛化與極端化。[30]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算法虛假注冊賬號、非法交易賬號、操縱用戶賬號或者虛假點贊、評論、轉發,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過度推薦、操縱榜單或者檢索結果排序、控制熱搜或者精選等干預信息呈現,實施影響網絡輿論或者規避監督管理行為。”這樣的規定顯然是為了保障信息傳播的公共性。數據的收集與分析,應以促進信息的合理流通與使用,促進包括公民個人在內的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我國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一般是將其放在名譽權范疇內,僅保護了個人不愿意公開的生活和財產方面的信息,而不涉及人格尊嚴和個人數據自由的人格權保護。因此,需完善公民數據隱私權保護的相關法律。
結語
人類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目的在于追求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到人類的主體性存在對于世界當下和未來的掌控性。但世界本就處于運動變化之中,而人棲居在世界之中,所有的實踐活動都讓這個紛繁的世界變得更為復雜,掌控就成為人類存在的宿命:知其不可為,又不能不為。近年來,新一輪信息革命浪潮帶來更為復雜的數據世界,如何掌控信息時代的數據運用,建立起合理的數據治理秩序,事關人的“在世存有”與“棲居”的根本。
歷史上人類創造的技術和工具,基本上是人體的延伸,人借助技術來強化自己的肢體技能。但數據技術是一種新的方向,它創造了人類生存的全新的數字鏡像世界,這是人的“在世存有”的新尺度,一定會作用于人類自身。如今,社會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已然成為全球浪潮,已經影響到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影響到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甚至能夠改變世界政治格局以及人類文明的走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因而,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信息時代,完善的數據規則是依法治國的制度基石。中國擁有全球最豐富的數據資源,但數據規則的建立起步相對較晚,存在數據安全防護薄弱等問題,而數據規則的建立和完善,事關人民福祉和國家安全,應當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據悉,中國正式組建國家數據局,這標志著中國在數字治理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媒體環境下公共傳播的倫理與規范研究”的中期成果,課題編號:19AXW007)
注釋
[1]IDC, "Data Age 2025: The Evolution of Data to Life–Critical", April 2017, 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21572.
[2]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頁。
[3]劉金瑞:《數據安全范式革新及其立法展開》,《環球法律評論》,2021年第1期。
[4]林建武:《數據主義與價值重估:數據化的價值判斷》,《云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5]高兆明:《“數據主義”的人文批判》,《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6]彭蘭:《“數據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與人生》,《蘇州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7]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5頁。
[8]J. Cheney–Lippold, "A New Algorithmic Identity, Soft Biopolitics and the Modulation of Contr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6, 2011.
[9]《習近平: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2017年12月9日,https://news.12371.cn/2017/12/09/ARTI1512803587039877.shtml。
[10]申衛星:《論數據用益權》,《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
[11]有學者認為,數據權利的結構不僅是形式的,也是實質的,前者意味著它可以抽象出普遍化的邏輯結構,后者意味著它必須立足于具體場景,識別、考量、權衡各方主張,設置特定條件下當事人的“當為”及“可為”。參見許可:《數據權利:范式統合與規范分殊》,《政法論壇》,2021年第4期。
[12]丁曉東:《數據交易如何破局——數據要素市場中的阿羅信息悖論與法律應對》,《東方法學》,2022年第2期。
[13]L. Lizhi, "The Rise of Data Politics: Digital China and the Worl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21.
[14]藍江:《外主體的誕生——數字時代下主體形態的流變》,《求索》,2021年第3期。
[15]楊力:《論數據交易的立法傾斜性》,《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6期。
[16]D. Smith and S. Singh, "Approaches to Multisensor Data Fusion in Target Tracking: 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006, 18(12).
[17]D. D. Hodson and R. R. Hill, "The Art and Science of Live, Virtual, and Constructive Simulation for Test and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Defens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pplications, Methodology, Technology, 2014, 11(2).
[18]J. F. O'May; E. G. Heilman and B. A. Bodt, "Battle Command Metric Exploration in a Simulated Combat Environment," Army Research Lab, Computationa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DIR, 2005.
[19]劉瓊:《大數據時代的美國經驗與啟示》,《人民論壇》,2013年第10期。
[20]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陳允明、王克仁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第285頁。
[21]劉易斯·芒福德:《機器神話》上卷,宋俊嶺譯,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第231頁。
[22]單勇:《數據主義對犯罪治理體系的重塑及其反思》,《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23]高富平主編:《個人數據保護和利用國際規則:源流與趨勢》,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代序言第4頁。
[24]蔡翠紅:《國際關系中的大數據變革及其挑戰》,《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5期。
[25]《中俄等國向聯合國提交“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文件》,2011年9月13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jksxwlb_674635/201109/t20110913_7666326.shtml。
[26]OECD, "Digital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sperity," October 2015, https://www.oecd.org/sti/ieconomy/digital-security-risk-management.pdf.
[27]"CFIUS Reform: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August 2018, https://www.sullcrom.com/files/upload/SC-Publication-CFIUS-Reform-The-Foreign-Investment-Risk-Review-Modernization-Act-of-20181.pdf.
[28]M. B. Gurstein, "Open Data: Empowering the Empowered or Effective Data Use for Everyone?" First Monday, 2011, 16(2).
[29]L. Taylor, "What Is Data Justice? The Case for Connecting Digital Rights and Freedoms Globally," Big Data & Society, 2017, 4(2).
[30]丁曉東:《論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思想淵源與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實踐”的分析》,《現代法學》,2019年第3期。
責 編∕肖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