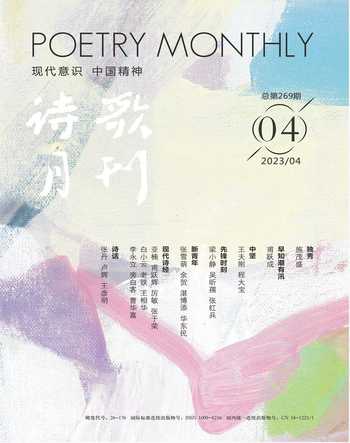第一首和最后一首
施茂盛
唯有詩是這樣的,第一首的降臨總是像天賜一般。它從一個靈感而來,或者是閃過腦海的一個碎片,被我們的一個詞、一個未加修飾的句子所捕獲,爾后在我們各不相同的語調中被確定下來。這是詩和其他文本不同的地方。它不需要鋪陳,甚至不需要謀劃。它就是這樣毫無防備、毫無預兆地把這一饋贈給予詩寫者。也只有詩寫者,才有如此機緣獲得這種慰藉。我因此也相信,是那個“更大的存在”依然認定這個世界需要詩寫者,認可這個世界詩寫者的存在,才會有詩寫者的這個命運。我甚至感到,那個“更大的存在”已經向詩寫者交代了使命和目的地。我把它看作是那個“更大的存在”對詩寫者的眷顧。每天,詩寫者是沿著他所指引的方向在掘進,就像每天向他所指引的方向不斷掘進已經成為每個詩寫者的宿命。
對于詩寫者來說,他的第一首一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它是一次突然的打開。從此以后,每一位詩寫者才真正來到詩寫的軌道。我的第一首也大抵如此。雖然我已經不能清晰地記起它的樣子、記起它的每一行句子,甚至都忘了它寫的是哪個主題,涉及哪些場景、哪些意象。但它發生的過程,它從我腦海中走出來的過程,我還能記起。我相信它肯定和我生活的這座小島、這個小鎮有關。我的第一首必然來自于我在這座小島、這個小鎮生活的某個瞬間,來自于某個瞬間的一次停頓、一次定格。詩寫者之于詩,不僅僅只是機緣巧合,還是一種因果關系。我想,正是因為我生活在這座小島、這個小鎮上,我才會在某個微風徐緩的早晨或夜晚,寫出了人生的第一首,并從此加入了詩寫者競走的行列。但我說不出究竟是這一首還是那一首,是我的第一首。這也正好是我要表達的一個觀點。或許對于一個詩寫者來說,任何一首新寫出來的詩,都是他的第一首。
而我要表達的另外一層意思是,我的第一首或者所有的詩,雖然都和我在這座小島、這個小鎮上的生活有關,但它肯定不是生活現場的臨摹和模仿,甚至都不是生活劃過我身體的傷痕和印記。在這座小島、這個小鎮上,我有自己養家糊口的職業,有自己對職業的態度。更早的年紀時,還喜歡時不時邀上一二好友,小酌或快飲一番。日常中,內心向善,樂意助人,散漫而隨性。當然,我也經歷過自身難以擺脫的茫然與無奈,經歷過任何一個人會經歷的刺和釘子。但這些都不是我的詩,或者說,它不足以構成我認為的、我要書寫的詩。詩一定是突破了生活現場的界限的產物,它躍出生活本身要去完成的是進入一個未知領域的使命,這個未知領域才是它的目的地。一旦它抵達,它就成為一個自足體。它所展示的,應該是經過語言之“思”鍛造過的,應該是聚精于神的,也應該是言不可及、言而不及和言之不盡的。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詩與其他文本有所區別的根本所在。這才應該是詩的“善”。詩的“善”,就是詩的“真”的全部。我多么希望,我記不起的那第一首已經領悟了這一要義,而所有的詩全部涵蓋在了這第一首中。
那么,這最后一首呢?是不是有這最后一首?布魯姆在《論詩人們最后的詩》中,曾把詩人“最后的詩”歸類為三種:字面意義上的詩人最后的詩;意圖去宣告終結,盡管詩人在這之后依舊活著并繼續創作;對于一段詩歌生涯的想象性總結。按照布魯姆的說法,我的最后一首似乎還未出現。首先,詩寫是言說和觸及我隱秘世界的“器”,它讓我擺脫生活的各種陋習,讓我對生活依然充滿好奇和興趣,讓我在生活現場得以自我提煉與涵養,它幾乎滿足了我在兩個迥異世界平行飛行的所有良愿,其中也難免包含了對日常所攜帶的遺憾的補償,所以詩寫是我余生必然將繼續的一個技藝活。再有,在我的詩寫中,我一直都把每一首當作第一首,把所有的詩寫都匯聚到這第一首中,構成我的第一首的一部分。每一首向我降臨時,我都希望它是不斷有所精進的那一首,我還沒有準備好用一首自認為可行的詩作為總結,以完成帶有自我色彩的某個體系的構筑。況且,我的詩寫沒有達到源頭性的高度,也沒有要為其他詩寫者提供參考的沖動。我之于詩寫并無野心,更多的是一種情懷。絕大部分情況下,是一種自我試探、自我觸及、自我愉悅、自我閱讀和自我省思而已。
但近兩三年來,我越來越感覺到在我的詩寫中,那“最后一首”的影子時不時地在某處晃動。我還不能很清晰地歸納和表述它。或許因為在我的詩寫中,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有一個新的主題闖入了進來。習詩以來,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內,我的詩寫所觸及的素材、場景、鏡像,絕大部分來自我生活的這座小島、這個小鎮,以及與之形成某種適度的緊張、對峙、映照和呼應關系的對岸那座城市。所有詩的邏輯、取舍和確立,都圍繞這些而關聯、生成。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堅持、持續推進的詩寫緯度,是一條橫向詩寫的路線。總體上它是向內的、閉環的,并未擺脫地域性詩寫的界限。有一天,我的詩寫出現了神奇的一幕,一些新的元素和新的“思”涌向我,一下子打開了我的詩寫。它已經完全不同于我之前那種橫向的、需要照顧現場的廣度和覆蓋面的詩寫。它是一種縱向(經度)詩寫。它是開放的、繁復的、螺旋狀的,又是混沌的、渾然的、單一的。它更多關注的,或是對秩序的玄秘生成、或是對物(實和虛)經由語言的賦形、或是對日常細節的神性的詩寫。它與前者構成了我現在的詩寫坐標,給我帶來了新的詩寫場域。
這個變化,也必然讓我的詩寫狀態和詩寫風格發生變化。或許,那個“更大的存在”在告誡我,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中年寫作后,我可以過渡到晚年寫作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也有更多信心迎接這一刻的到來。或許在晚年寫作中,我所謂的“最后一首”也會在某一時刻得以呈現。這不是布魯姆所說的“字面意義上的詩人最后的詩”,而是終于確立了與晚年寫作相協調、相呼應的一種風格后,對自己整個習詩經歷的最后總結。但這“最后一首”,仍是我的第一首,仍是構成我的第一首的一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