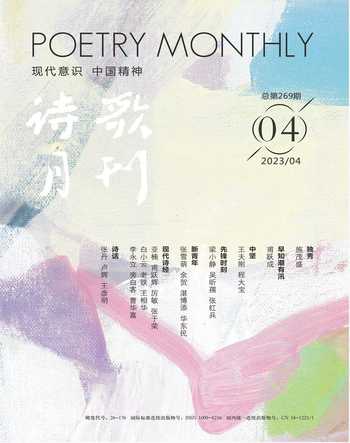訪談:回到河流歌唱的時刻
王夫剛 程大寶
1.緣何寫詩?
王夫剛:詩歌跟我產生隱秘的交集之前,我寫下了第一首詩。當時并沒有看清詩歌的面孔,因此無法準確回答為什么要寫詩——如果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可能是我有話要說,但又不具備講故事的才能,于是詩歌來到我的面前。過了很多年,現在,回過頭再看,寫詩既非生活所逼迫,也談不上青春之恩賜,無非命運的隱形饋贈先入為主地惠澤了我,教育了我。
程大寶:一閃念,就像彈去煙灰,煙灰中的火星令人深思。一個點撥,一次聚會,一位詩人的一席話像是一根鐵簽,他的一撥動,暗紅的火爐吐出了發聲的火舌。一沖動,也不算沖動,就像一壺慢慢加熱的水,總會有蒸汽涌出,總是想有一點動靜,至于發出什么聲響,達到什么音量,那是另外一回事。
2.你的詩觀是什么?
王夫剛:詩人通過文字記錄那些被忽略的生命細節,挽留那些被遺棄的少數光陰,不是責任而是義務。潮流面前,詩人必須擁有相反的清醒和格格不入的力量,既要在竹籃打水的游戲中獲得探索的樂趣,也能夠從水泥鋼筋澆筑的理想中回到樹木,回到綠色,回到河流歌唱的時刻。
程大寶:把物界內化,而內心能生萬物。
3.故鄉和童年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夫剛:故鄉是一個詞匯,也是一種不設選項的記憶,始終提醒著我們命運中已知的坐標。童年是另一個詞匯,也是一束記憶深處溢出來的光芒,永恒地清理著生活中未知的塵埃。我很慶幸多年以后我依然擁有礦藏般的故鄉和遺跡般的童年,在那里,我曾經獲得的歡樂和依賴不但未有任何變化,而且生出了越來越多的追根溯源的啟迪,召喚著我的最終歸來。
程大寶:故鄉常在我夢里,夢里的真切我自己都時常驚嘆,但越真切越難捕捉,危如累卵,讓人難以承受。童年常在我心中,所以,知天命也不能驅逐,似乎進入我的細胞,以至我每一步都是童年,甚至是對童年的模仿。我時常學步蹣跚,無法自控,這也是我對文字的態度。
4.詩歌和時代有著什么樣的內在聯系與對應關系?
王夫剛:詩歌和時代的關系取決于詩人的個體訴求:如果詩人迎合時代,他就會在時代的巨大陰影中丟失自己的影子。如果詩人無視時代,他就需要虛構一個時代安置自己的呼吸和聲音。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卻這樣寫詩告誡后來的人:“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九百多年前,蘇軾就已替我們很好地回答了這一提問。
程大寶:詩歌有時代性,但我認為詩歌是前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引領人們開疆拓土,播谷撒種,日漸抵近蔥郁的終極歸宿。當然,這種歸宿是有使命感的,那就是向前、向上、向善。就像我在一首詩中所述:“一條魚吹出水泡,它看見了水底的裂痕和水面漣漪的對應。”
5.對于當下的詩歌創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王夫剛:別人的詩歌創作有沒有困惑我不甚清楚,我自己的詩歌創作似乎并沒有顯而易見的困惑,我寫下的,都是我需要寫的,我能夠寫的。沒有困惑的原因,并非我的寫作已臻佳境(恰恰相反,我的寫作一直處于四處漏風的狀態),而是因為個人的寫作困惑只能由個人解決——既然寫作的困惑不是一個公共話題,那么談論寫作的困惑就缺少了足夠的必要性。
程大寶:我沒有困惑,無知無畏。我也有困惑,文字是草原上的一匹匹駿馬,一些人自在駕馭,馳騁蹁躚,好一派山舞銀蛇,原馳蠟象,一代天驕。而我,時常從馬背上摔下來,面目全非。我現在要做的是——怎么樣才能不從馬背上摔下來。
6.經驗和想象,哪一個更重要?
王夫剛:我們在一首詩中讀出了經驗,或者讀出了想象,一般不會做出非此即彼的排斥性選擇,因為經驗和想象都是詩歌的重要元素和優秀品質。換言之,一首詩可以通過經驗而勝出,可以通過想象而勝出,也可以通過經驗和想象的共同努力而勝出,這時候我們會恍然發現,詩歌的復合價值遠遠高于詩歌的單項力量。
程大寶:經驗是我們成長的經歷、痕跡,而想象是我們捕捉經歷、痕跡進行萃取和升華的過程。沒有經驗就沒有文字,而沒有想象,就無法安放文字的榫卯。這種安放需要一盞燈,需要內心的一念溫情,需要溫情被傳遞的介質,這樣,我們才能找到那條回家的路。這就是我理解的經驗和想象。
7.詩歌不能承受之輕,還是詩歌不能承受之重?
王夫剛:詩歌本身并不會承認承受了什么,因為每一首詩的背后,都站著它的一個主人,即使匿名之作也不例外。對于罕見的詩篇來說,輕重之承受,允許照單全收,對于泯然眾人的詩篇來說,輕重之難以承受,則是另外一種照單全收。
程大寶:輕、重有二個屬性,一個物理屬性,一個精神屬性。輕和重是一種彈撥后的震顫,就像琴弦,金屬或者皮質的質地,是物理的重,但由此而發出的旋律和聲響呢?是輕嗎?就像我們的肉身,有物理的重,但我們的內心呢?如何平衡?我認為重和輕是文本的隱喻和升騰,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該怎么承受。我們只有嘗試用肉身去承載文字,文字讓我們周游,尋找棲息之地,如能安放,輕重自有為之。
8.你心中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王夫剛:十年前,我接受《江南時報·中國詩歌地理》采訪,就這個問題給出過個人答案:適度的幽默,隱形的智慧,對傳統的有效繼承以及嫻熟掌控文本的能力。在我這里,一首詩如果具備以上四個要素,就可以稱之為好詩。而有些時候,暴力答案往往是這樣的:好詩就是好詩,不好的詩就是不好的詩!要命的是,這種暴力答案有時具有紙上爭論完成不了的使命。
程大寶:能讀,愛讀,不時讓你合卷看向遠方。
9.從哪里可以找到嶄新的漢語?
王夫剛:永遠不存在一個“人人皆源頭”的漢語事實。李白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杜甫寫“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居易寫“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今天依然是嶄新的漢語服務于我們,哪怕時代好像已經更名為“科技的時代”。讀者可以從詩人的文本中尋找嶄新的漢語嗎?我認為是可以的,詩人可以在自己的文本中創造嶄新的漢語嗎?我認為詩人應該擔當這個責任,古往今來,眾多卓有建樹的詩人也已做出了具體的榜樣。
程大寶:重要的是表達和踐行,在表達和踐行中去發現和修繕漢語,然后用情感來熔煉和純化漢語,使得它們成為自己的鉆石。
10.詩歌的功效是什么?
王夫剛:人類的歷史和文明的長河沒有詩歌長相伴隨會是一種怎樣的后果?或許這是一個杞人憂天的話題,但詩人必須對此懷有并非杞人憂天的自信:如果詩歌缺席,人類的歷史和文明的長河將變得了無生機,難以想象。眾皆狂奔的道路上,偉大的詩篇已成體系,卓越的詩篇自帶光芒,優秀的詩篇推己及人,詩歌的功效不是滿足我們的虛榮心,而是把我們心靈中的虛榮成分剔除出去:在美食、藥品和服裝無力企及的地方,誕生了詩歌的天然優勢。
程大寶:治愈自己的心靈空虛癥,然后分享。
11.你認為當下哪一類詩歌需要警惕或反對?
王夫剛:陳詞濫調的詩篇,巧言令色的詩篇,無病呻吟的詩篇,欲望失衡的詩篇。
程大寶:物有萬象,心有萬壑。需要警惕或反對的不是詩歌,而是詩人——如果不是一個大而遠的詩人,應當警惕;如果不是一個能給人以慰藉和溫暖的詩人,則可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