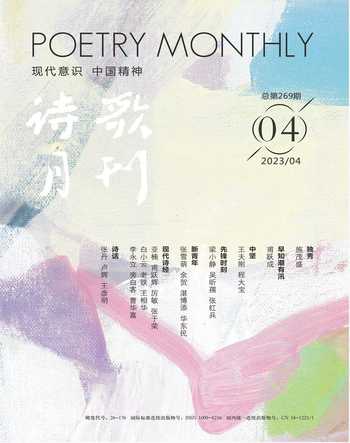詩到語言實現其客觀主義為止
韓東的《我將如此生活》是一首現實的倒影之詩。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倒影與事物總是呈現為一種顛倒的對應。之所以稱之為現實的倒影,是因為詩中所寫與生命的真實發生了這樣一種顛倒的對應關系。欣賞這樣的一首詩,我們要帶著反觀和還原現實的思維步驟:整首詩的詩句都指向了現實倒過來之后的影子——“若有來生”,對應于實際只在此生;凝視一件事物,對應于現實中,我們的目光持續移動于每一件事物(也就是詩中說的目光檢索);愛中包含了死亡,對應于死去的愛或死亡終止的愛;由潰爛還原的果實,對應于永遠在逐漸潰爛的果實。
表現了這幾組與現實顛倒的對應,詩人在詩中寫他的生存與審美理想為:“我將如此生活,凝視即永訣。”整首詩包括這句話令人疑竇叢生——詩人為什么希望過這樣的生活?這是一種什么生活?凝視為什么是對事物的永訣?我們不妨稍微辨認一下現代生活的現實。我們通過游走于對應關系的兩端,已經知道,此生、目光流轉、事物移換、死亡和潰爛終結了生與愛,才是當下人生存不可避免的現實。現代生活的時空流動特征致使事物永遠在不斷移動和改變,具體生存總是包含著對現實的若干介入和參與,不完美和變動因此幾乎無時不在發生,必然走向死亡與潰爛成為生的鐵律,不斷消解著生的目的和意義。這當中存在著藝術和生命的兩難:我們審視當下正處于(介入)其中的時刻,總是帶有情緒或各種具體化的因素(比如功利的目的),因此很難冷靜和提煉出真實的水晶。而如果任由生命之流無限運動,無限時空的無限運動,無盡的生死,則導致生命淪為一團變化的影子,虛無主義也在這里滋生。哪里、何時才是生命的真實,在這樣的時代成為語言難以攫取的對應物。
詩人希望展開一種保持距離的靜觀,正是針對于這樣一種藝術與生命的兩難之境。帶有距離,人事物之本來的樣子才得以在我們的意志、情感之外如其所是地呈現;而靜觀,則才有可能從因無限運動而無法看清的生命之流中抽取一個個冷靜客觀的瞬間,從而得以看清生命真實的形貌與色彩。回到引發我們疑慮的詩句,進一步說,凝視之所以是對事物和生命的永訣,是因為只有和事物保持距離時,我們才可能觀看事物,而非伸手(介入)去碰觸和改變,而觀看時的凝神,則去除了無限時空帶來的運動因素,使真實的水晶浮出。這種真實的純度和硬度,足以構成生命的實體。
由此,我們知道了,現實與真實,在韓東的詩歌與詩學中并不是可以互換的。現實的倒影,并不意味著這首詩的對象是非真實的。現實生存中的流動、虛空、缺憾、必死、無法重來,當然皆是真實。然而也正如韓東所欣賞的法國現代哲學家西蒙娜·薇依(韓東有不止一首以薇依為名的詩作)的觀念——所有真實之物在世界上皆有與之顛倒的對應物。比如在理解善惡問題上,薇依即認為惡是善的一種顛倒對應物,如同善的倒影,兩者皆是真實的。因此,與現實生存中的永遠流動、虛空、缺憾、被死亡壓倒的愛與生、人生的無法重來,兩相對應的倒影,即在生命的想象世界里能為人生確定位置的靜態之點、實存物、完美、大于死亡的愛、回到圓滿,也不可否認是真實的。正是這種對應關系表現出另一種現代主義之道,即詩歌中的語言,總在對應或努力對應著生命中的真實。
之所以強調對應,是因為對應作為一種語言方式有別于象征。影響整個世界的現代文學是以象征主義詩歌為其開端的。運用象征意味著詩人只需要在其語言系統中,擇取自認為具有意義的物象進行暗示即可,而這個意義無需說明,比如,A可以認為字母O具有蘋果的芳香,B則認為字母O具有橘子的橙色。其目的在于暗示某種形象,只有當事人及參與者才能領悟或自以為領悟象征的含義。將自身封閉在自我言說語言系統中的象征因其主觀隨意性和運用的泛濫,致使現代詩歌與生命的真實分別,具有晦澀難懂的一面。對應,則要求一物與另一物有確切的彼此相對,對應的兩端缺一就可能淪為象征。詩歌語言要求對應,總是意味著語言指向語言外部,運用對應而非象征的詩歌通過語言走出自我,向生命、他者和世界求取真實。一種追求真實的詩歌觀念,必然試圖要求詩歌的語言去容納事物及其倒影中皆存有的生命之真。
帶著對這首詩的如是理解,韓東那句著名的詩學命題“詩到語言為止”,似乎也應該得到一種廓清。詩到語言為止,這看上去是一種常識,也不會有什么別的意義。但恰恰在這一句常識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韓東的這句詩歌宣言與其詩歌是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馳的;也有人認為,韓東的詩作大于這句話的內涵,因為韓東的詩歌很顯然包含了日常生活和生命的真實。這種理解預設了這樣一個邏輯前提,那就是把“詩到語言為止”理解為語言之詩,認為詩歌是在語言內部的符號游戲,認為語言歸語言,真實歸真實。一首包含真實的詩注定不會是一首語言詩。這樣的認識忽視了人的感知和語言活動總是在所處的具體時空展開,時間、空間皆圍繞人所身處其中的時與地延伸開去。為了立足和扎根,這一時與地永遠地要求真實確定性,換句話說,要求為之建構起能夠對應的意義之時空。生活在別處,或詩在遠方,恰恰是以象征為表征的現代詩歌對詩歌的一種誤解和遮蔽。因此這類解讀也就沒有真正理解韓東的這個詩學命題所隱含的對真實的訴求。
作為一種語言藝術,詩的確到語言為止。需要追問的,是詩的語言中是不是對應了真實?而這種沒有說出來的詩語追問,才是韓東詩歌和詩學所尋求的。在語言中,真實感被確定,語言完成其符合真實的意義建構,詩就重新回到人間。詩到語言為止,不是指向自我封閉和更新的語言系統,與純語言的或純詩南轅北轍。它要求語言不斷去對應真實,重新觸碰真實,讓人在語言中真正歸家,來恢復語言的尊嚴。這個命題恰恰要求人們回歸常識,回歸真實,語言并不應該如其在現代詩歌中的普遍表現那樣,與真實割裂。相反,這是另一條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道路:語言在多大程度上對應于生命的真實,考驗著詩真正的限度。或許可以用“詩到語言”實現其客觀主義為止來拓展這一命題。詩到語言為止,是詩想要終于抵達對應真實的語言,而人的生命與生活不休,感嘆與思索不止,這條充滿活力的詩路就要始終延伸。
附:
我將如此生活
韓東
若有來生,我會靜靜地看一眼。
我的每一瞥目光都將靜靜的,
只看一件東西。看完,
就把它擱置一邊,再看另一件。
我將如此生活,凝視即永訣。
不再用目光檢索,
只將它用于愛,
這愛中包含了死亡。
比如一只精美的果子,
我不再吃掉它,只是看著,
直到表皮潰爛,
同時在我的心里復原。
張丹,1989年生于四川遂寧。現就讀于四川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