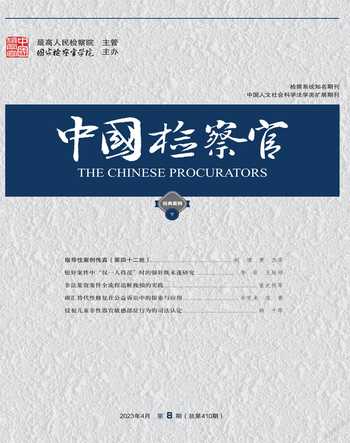論網絡環境下侵犯著作權罪中的“復制發行”
雷知仁 胡松
摘 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權罪中將信息網絡傳播與復制發行并列,經此修訂,對“復制”行為的認定,應當堅持在物質載體上固定作品的要求,對“發行”的認定則應堅持以轉移所有權的方式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復制件,且“發行”和“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之間相互獨立、互不包容,從而協調刑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之間的關系,消解司法實踐中民事裁判和刑事裁判的沖突,維護法治體系統一。
關鍵詞:侵犯著作權罪 復制 發行 信息網絡傳播
一、網絡環境下“復制發行”的認定爭議
[基本案情]2018年1月至案發,梁某某以營利為目的,成立相關公司,組織人員開發“人人影視字幕組”網站及移動客戶端,將境外網站下載的未經授權的電影作品,翻譯后壓制、上傳至網絡服務器,通過網站和客戶端向用戶提供在線觀看和下載服務。期間,梁某某等人以接受“捐贈”、收取廣告費、銷售含有盜版電影作品的硬盤等方式獲取經濟利益。經審計及鑒定,“人人影視字幕組”網站及移動客戶端內共有未經授權的影視作品32824部,會員683余萬人,經營額總計達1200余萬元。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梁某某有期徒刑3年6個月,罰金15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1]
有觀點認為,本案涉案人員實施了復制發行行為,完全符合侵犯著作權罪客觀要件。[2]但是,通過互聯網傳播盜版影視作品,是否能被解釋為侵犯著作權罪中的“復制發行”,并非毫無爭議。本案尚需就三個焦點問題進行分析:一是涉案人員通過境外網站下載未授權電影后,組織人員翻譯,添加字幕后上傳至網絡服務器的行為,是否構成“復制”;二是通過信息網絡向他人提供在線觀看和下載服務,是否構成“發行”;三是刑法中“復制發行”,是否應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相關術語的內涵保持一致。有觀點認為,網絡時代,復制從占有轉變為感受,發行也突破了有形載體的束縛轉變為無載體發行,對刑法概念的解釋不必以民法的規定為前提。[3]2004年《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4年解釋》)將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他人作品的行為視為“復制發行”,2011年《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11年意見》)再次明確網絡傳播屬于發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將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單獨入罪后,前述觀點是否合理、司法解釋相關條款是否依然有效值得探討。
二、網絡環境下“復制”行為的認定要點
2020年11月《著作權法》修改,在印刷、復印等典型的“復制”行為之外增加了“數字化”方式,而“人人影視字幕組”未經授權“數字化”再生產電影作品的行為能否被法律評價為“復制”進而構成犯罪,需要從復制權的構成要件出發進行分析。
(一)“復制”必須借助物質載體再現作品
法院將梁某某等人借助互聯網下載、翻譯、壓制、上傳盜版電影的行為定性為“復制”,這種網絡復制與傳統的實物復制具有顯著差異。我國《著作權法》所列舉的典型“復制”行為,印刷、復印、拓印都會形成作品的復制件,錄音、錄像、翻錄、翻拍都會將作品固定在物質載體上,復制的本質是在有形載體上穩定地再現作品。[4]是否在有形載體上再現作品,是《著作權法》上的復制權與表演權、廣播權的根本區別之一。[5]這一要件在域外法律中也有體現,《英國1988年版權、外觀設計和專利法》第17條就規定,與文學、戲劇、音樂或藝術作品相關的復制是指以任何物質形式復制作品,也包括通過電子方式將作品存儲在任何介質中。[6]借助物質載體重現作品,則必然產生作品的復制件,《美國1976年版權法》第101條明確,復制件就是用來固定作品的有形物,并且可以通過該復制件傳輸、復制、感知作品。[7]美國國會曾在立法報告中強調,復制件包括固定所有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的物質載體。[8]實踐中,美國法院也曾指出,法院以前沒有解決過通過互聯網未經授權傳輸數字音樂文件是否構成版權法意義上的復制的問題,但當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固定在新的物質材料中時,就會發生復制。[9]因此,要構成“復制”,必然需要通過物質材料再現作品,并形成一個復制件。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如“人人影視字幕組”這樣的網絡復制行為數量劇增,是否從根本上改變了“復制”的要件?前文案例中,電影等數字作品雖然是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看似無形,但其存儲的基礎是硬盤等物理硬件,對電子數據進行復制依然需要借助物質載體,下載和上傳電子作品都不可能脫離物質載體而單獨進行,前述英美的法律和司法實踐也印證了這一點。因此,互聯網的發展,并未改變復制權借助物質載體再現作品的要件,只不過是載體從傳統的實物載體轉換為了數字載體。那種認為網絡時代的“復制”體現出非物質化的觀點,違背我國《著作權法》的文義解釋,誤解了計算機運行的底層邏輯,不具有合理性。
(二)“復制”必須使作品“固定”
“復制”是借助物質載體再現作品的行為,但是,并非所有再現都能稱為法律上的“復制”,如借助投影儀播放電影。這就涉及到認定“復制”行為的第二個要點,即作品必須被“固定”在物質載體上,這種固定是相對穩定和持久的。[10]《美國1976年版權法》第101條就明確規定,作品以有形形式“固定”,需要足夠持久或穩定,使它能夠被感知、復制或以超過短暫長度的時段被傳輸。[11]美國國會的說明中也指出,對“固定”一詞的定義,從概念上將那些純粹轉瞬即逝或暫時的復制品加以排除,比如短暫地投射到屏幕上,在電視或其他電子顯示器材上顯示,或者在計算機內存中短暫存儲。[12]互聯網環境下,這一要件依然成立。將作品數字化后上傳到互聯網,將導致在網絡服務器的硬盤中固定作品,這種“固定”是相對穩定且持久的,只要不人為地擦除硬盤數據,常見的外部存儲器如普通固態硬盤理論壽命可達20年[13],數字作品可以長久地保存在存儲裝置中。
前文案例中,“人人影視字幕組”下載和上傳電影的行為,都借助計算機存儲裝置這一物質載體對數據作品進行了再現,且這種再現是持續而穩定的。只要服務器上的數據不被人為擦除,這些電影就可以“固定”在存儲裝置中。因此,即使《著作權法》未將“數字化”列為“復制”的方式之一,該行為也完全符合“復制”行為的構成要件。部分學者將關注焦點放在該案的字幕翻譯行為是否構罪上,在刑法未將盜版翻譯這種民事侵權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前提下,借道共犯理論論證翻譯行為構成侵犯著作權罪。[14]筆者認為這是誤讀了案件爭議焦點,因為本案的復制行為不是發生在翻譯環節,即使是合法翻譯,也不影響字幕組下載和上傳未經授權作品屬于非法“復制”的定性。另外,認為網絡時代對刑法第217條“復制”的解釋可以突破《著作權法》的規定,擴大為非物質化復制的觀點,既不符合刑法文義解釋的一般規則,還會導致刑法和《著作權法》適用上的沖突。因此,網絡環境下,對刑法第217條“復制”行為的解釋,還是應當堅持在物質載體上固定作品的要求。
三、網絡環境下“發行”行為的認定要點
《刑法修正案(十一)》將網絡傳播與復制發行并列規定,完全改變了《2004年解釋》和《2011年意見》的規定。對“發行”概念的解釋,既涉及到對刑法條文關系的理解,還涉及到刑法與《著作權法》銜接的問題。
(一)“發行”應當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
前文案例中,爭議焦點之一是梁某某等人實施的網絡傳播行為是否應當被視為侵犯著作權罪中的“發行”行為,因為網絡傳播并未像傳統的發行一樣向公眾提供諸如書籍等實物產品。根據我國《著作權法》,構成“發行”需要提供作品原件或復制件,這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規定一致。《美國1976年版權法》第106條就將發行權定義為向公眾發行有版權的作品的復制件或者錄音制品,而第101條將復制件定義為“有形物”。[15]《英國1988年版權、外觀設計和專利法》第18條規定,“發行”是將先前未在英國投入流通領域的作品復制件投入流通領域。[16]《歐盟版權指令》將發行權定義為成員國應就其作品原件或其復制件,賦予作者授權或禁止以出售或其他方式向公眾發行的專有權。[17]歐盟法院在判決中也指出,歐盟立法者在發行權中使用有形物的用語,是為了使作者能夠控制體現其智力創作成果的有形物的初始市場。[18]《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6條也明確指出,發行權是作者向公眾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復制品的專有權。關于該條約的議定聲明指出,條約第6條所用“原件和復制品”,專指可作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復制品。[19]結合我國《著作權法》及其他國家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以發現,發行權的對象是作品的物質載體,即原件和復制件,并非作品本身,構成發行必須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
厘清了發行權是向公眾提供作品的物質載體,即原件或復制件后,再來觀察前述案例所謂“網絡發行”就很清晰:梁某某等人將電影上傳到網絡服務器,數據本身構成作品,上傳行為是“復制”行為。數據上傳到網絡服務器后,當然也有物質載體,那就是服務器的硬盤,此時,行為人通過網絡向公眾提供電影下載和在線觀看等服務,傳播的是數據,即“作品”本身,而非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即存有該“作品”的硬盤。因其傳播的是“作品”本身,并非在向公眾提供原件或復制件,這種網絡傳播行為不符合“發行”的要件。
(二)“發行”必須轉讓作品所有權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發行”只有出售或者贈與兩種方式,不論是出售還是贈與,均會導致作品物質載體所有權的轉移。在采納狹義“發行”概念的國際條約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律中,發行必然導致作品所有權轉移。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第6條規定的發行方式就是通過銷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形式,《歐盟版權指令》也強調發行需要通過銷售或其他方式進行。歐盟法院曾指出,發行的概念,僅適用于轉移作品原件或者復制件所有權的情形。因此,不論是給與公眾使用受版權保護作品的權利,還是向公眾展示這些作品而不給予他們使用的權利,都不構成“發行”。[20]我國《著作權法》將出租等轉移占有形式單獨列出,規定為“出租權”等權利,很明顯也采取的是狹義“發行”概念。事實上,我國法院也早就意識到網絡傳播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發行”。1999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就曾在王蒙等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未經許可將其作品上網傳播侵犯著作權案中指出,通過網絡傳播作品,是作品使用的方式之一,與出版、發行、表演、播放等有不同之處,并認為網絡內容服務商未經授權通過互聯網傳播他人作品的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21]《著作權法》增加信息網絡傳播權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曾在源泉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訴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數字世紀網絡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財產權糾紛案判決中認為,發行權顯然需要轉移作品載體所有權或占有,發行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的側重點和范圍并不相同。[22]可見,構成“發行”需轉讓所有權,在域內外司法實踐中是必須條件。
既然發行需要轉移所有權,網絡傳播行為與發行行為的界限就更加清晰,如美國電子前沿基金會就曾借助音樂作品網絡傳播的過程來區分二者:電子傳輸通常涉及在A點讀取數據并在B點復制該數據。由于在A點的數據并不一定被讀取數據的過程所銷毀,在A點的人可能仍然享有原始數據,因此并未發生銷售或以其他形式進行的所有權轉移,通過網絡傳播音樂作品也不構成發行。[23]前述案例中,“人人影視字幕組”通過服務器將電影數據提供給社會不特定公眾下載,電影被使用者下載后就存儲在使用者的設備中,數據讀取過程中“人人影視字幕組”服務器上的數據并未被銷毀,依然享有原始數據,保留電影數據的存儲裝置(作品原件或復制件)也沒有發生所有權轉移,其結果是電影在新的物質載體上固定,形成了新的作品復制件,也就是作品復制件絕對數量的增加,這種并未導致所有權轉移的傳播行為,并不符合“發行”的構成要件。從法律的文字含義和我國的司法實踐及域外規定都可以得出,在解釋“發行”時,應當堅持提供作品原件或復制件和轉移所有權兩個要件,對于“人人影視字幕組”這類網絡傳播行為,不能將其定性為“發行”行為。
四、“發行”與“信息網絡傳播”相互獨立、互不包容
如前述案例般將網絡傳播定性為“發行”的刑事裁判,實務中認為網絡時代“發行”體現為無載體、所有權無須轉移的觀點,司法解釋將信息網絡傳播視為“發行”的規定,都非新鮮事物。早在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締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進行外交磋商時,美國代表團就建議在條約“發行權”中增加“通過傳輸提供作品原件或復制件”的表述。[24]美國法院也認為,版權法規定“發行”需要轉讓所有權,但在電子傳輸過程中這個要件可以被突破。[25]也許是受美國實踐的影響,我國有學者就認為只要意圖轉讓復制件,就構成網絡發行。[2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代表團希望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發行權中增加信息網絡傳播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相關專家曾指出,議定聲明對條約“原件”和“復制件”定義的澄清,是為了將任何形式的數字傳輸從兩個條約規定的發行權以及發行權用盡的范圍中排除出去。[27]而美國法院之所以對“發行”作出擴大解釋,源于其版權法上并沒有規定類似于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因此通過對發行權的擴大解釋來對此類行為予以規制。
在我國刑法和《著作權法》都已對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作出規定的情況下,如果今后仍將網絡傳播行為解釋為“發行”,會產生以下危害:一是會導致刑法第217條內部不協調。既然《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了“復制發行”與“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是并列的危害行為,從刑法文義解釋上看,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包容關系,而是相互獨立的行為,如依然把信息網絡傳播解釋為發行,那么這二者之間就完全重合,《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該處的修正也就成為具文。二是會導致嚴重的刑民脫節。《著作權法》早在2001年就增設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但刑法一直未作修訂,反而是《2004年解釋》和《2011年意見》將信息網絡傳播視為發行。曾有一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對刑法中“復制發行”的解釋,不以《著作權法》的規定為前提,二者的含義可以不一致,即在特定情形中,即使不構成民事侵權或行政違法,也可以構成知識產權相關犯罪。[28]這造成司法審判中嚴重的刑民脫節現象。如前所述,民事法官早就明確指出發行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范圍并不相同,但刑事法官卻只能依據司法解釋將“人人影視字幕組”通過網絡傳播的行為認定為“復制發行”,這種刑民裁判的不協調,不利于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也會損害司法公信力。在我們推進知識產權三合一改革進程中,前述觀念只會導致參加“三合一”審判的法官裁判時自相矛盾。[29]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對侵犯著作權罪進行修訂的情況下,今后在辦理類似“人人影視字幕組”這樣的案件時,應當堅持刑民銜接的基本觀念,在解釋“復制發行”概念及其與信息網絡傳播之間的關系時,應當以《著作權法》相關術語的內涵為前提。同時,應當明確司法解釋中將信息網絡傳播視為發行的條款已經失效,才能實現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協調一致。
五、結語
近年來,司法系統大力推行知識產權檢察職能集中統一履行試點、審判職能“三合一”改革,以綜合司法保護助力創新驅動發展。而以“人人影視字幕組”為代表的案例則顯示,推動改革向深里走、難點攻,不僅要重組機構、重塑機制,更需建立起以民事救濟為常態、行政處罰為主體、刑事懲治為補充的遞進式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保持部門法之間法律概念的一致性,促進實現法律適用統一、裁判結果一致、保護效果最佳,織密知識產權的法治保護網。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100875]
**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四級檢察官助理[430079]
[1] 參見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滬03刑初101號。
[2] 參見高衛萍、王思嘉:《“盜版型”侵犯著作權罪司法實務問題探析——以“人人影視字幕組案”為研究對象》,《中國版權》2022年第4期。
[3] 參見李小文、楊永勤:《網絡環境下復制發行的刑法新解讀》,《中國檢察官》2013年第6期。
[4] 參見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81頁。
[5] 參見王遷:《網絡環境中的著作權保護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6] 參見《英國1988 年版權、外觀設計和專利法》,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網http://ipr.mofcom.gov.cn/hwwq_2/zn/Europe/UK/Design.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3月6日。
[7] 參見裴安曼:《美國版權法》,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4頁。
[8] Se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No.94-1476,94th Congress 2d Session,1976,p.53.
[9] See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910 F.3d 649(2th Cir.2018).
[10] 同前注[4] ,第81頁。
[11] 同前注[7] ,第5頁。
[12] 同前注[8] ,第53頁。
[13] 參見呂新平、王麗彬:《大學計算機基礎》,人民郵電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頁。
[14] 參見王螢:《字幕組的恩怨江湖與相關知識產權犯罪分析|評“人人影視”字幕組涉刑案》,中國法律評論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kiHgpHUnHwNFeQ8Ljwx_Sw,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3月6日。
[15] 同前注[7] ,第24頁。
[16] 同前注[6] 。
[17] See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ticle 4.1.
[18] See Art&Allposters International BV v. Stichting Pictoright,Case C 419/13,22 January 2015,ECJ.
[19] 參見《關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的議定聲明》,WIPO網https://wipolex.wipo.int/zh/treaties/textdetails/12741,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3月6日。
[20] See Peek & Cloppenburg KG v. Cassina SpA, Case C-456/06, 17 April 2008,ECJ.
[21] 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1999)海知初字第57號。
[22] 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3號。
[23] See London-Sire Records, Inc. v. Doe 1, 542 F. 2d 153(D.Mass.2008).
[24] 參見王遷:《網絡著作權專有權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15頁。
[25] 同前注[23] 。
[26] 參見何懷文:《網絡環境下的發行權》,《浙江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27] 同前注[24],第119頁。
[28] 參見《上海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會議綜述》,上海審判研究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Rz8lIhkOH3k2RYuWw0ac5A,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3月6日。
[29] 參見王遷:《論著作權保護刑民銜接的正當性》,《法學》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