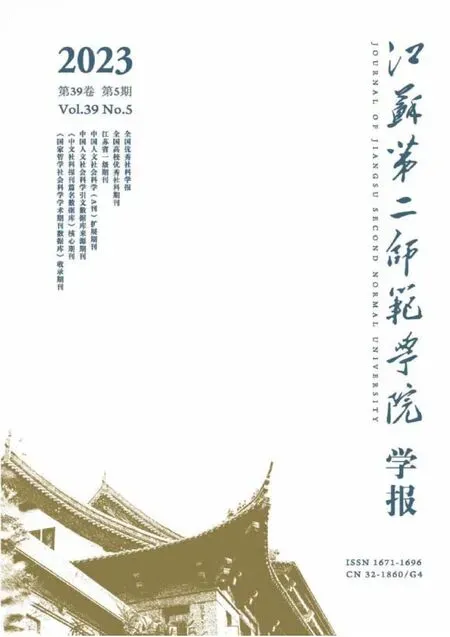林語堂的《水滸傳》外部研究*
陳 智 淦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英語語言文化學院, 福建漳州 363105)
林語堂偏愛明清文學,尤其推崇明清小品和小說。國內外學術界對林語堂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其紅學論著《平心論高鶚》(1966),有學者甚至認為,除了《紅樓夢》之外,“林語堂對其他中國古典小說可能主要停留在閱讀、了解和使用層面”[1]。其實,林語堂對《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等其他古典小說也曾進行過細致的研究和論述,他對《水滸傳》的研究雖然比較分散,但其研究深度僅次于《紅樓夢》。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把闡釋作品的本質和價值大體分為四類,即每一件藝術品必然涉及作品(文學作品)、藝術家(作家)、世界和欣賞者(讀者)等四個要素。除了把作品視為一個自足體孤立加以研究之外,“有三類主要是用作品與另一要素(世界、欣賞者或藝術家)的關系來解釋作品”[2]5;而勒內·韋勒克(René Wellek)和奧斯汀·沃倫(Austin Warren)同樣提出“文學的外部研究”和“文學的內部研究”之分野,他們除了研究作為自足體的文學作品之外,還“把作家研究、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以及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之類不屬于文學本身的研究統統歸于‘外部研究’”[3]8,除了對林語堂在各種著述中談論《水滸傳》的文學類型、文體語言、藝術手法等問題的“內部研究”進行系統梳理[4]之外,為了更全面理解林語堂研究《水滸傳》的深度,有必要以林語堂評論《水滸傳》的文本史料為基礎,進一步梳理林語堂對《水滸傳》與作者、世界和讀者等三要素之間的關系這一“外部研究”問題的判斷性文字論述,從而進一步完善林語堂作為學者型作家的形象研究。
一、《水滸傳》之作者
藝術家,即作者是文學活動的四大要素之一。韋勒克和沃倫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者。”[5]71如果作家未將其對社會生活的體驗、理解或感受行諸語言文字,文學作品的存在就無從談起。中國傳統文論中的“作者論”包括作者的身份定位、作者修養、創作目的和創作過程等幾個方面。林語堂多次論述《水滸傳》作者的身份定位和小說創作過程等問題。
首先,《水滸傳》作者身份定位的模糊性與小說這種文體不為正統文學所接受的社會現實、小說家的心態以及中國小說興盛較晚等主客觀因素有關。早在1913年12月,林語堂就在《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一文中指出,“中國文學愛好者一般喜歡詩歌、歷史、哲學經典,更普遍喜歡短小精悍的論說文名篇(masterpieces in short skillful treatises),但卻極少喜歡描寫中國社會及介紹女性角色的小說”[6]。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讀者既不尊重也不重視這種主要關注社會的小說”[6]。1935年9月,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書中探討中國學術時,對《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等選集依據正統標準而收入其中的著作頗有微詞,“雖然有更多著作受到贊譽,但僅在總目中進行簡要介紹,這些著作并沒有收入《四庫全書》而永存于世。像《水滸傳》或《紅樓夢》等真正有創意的作品當然不被列入其中……”[7]223。林語堂認為,中國小說的興盛比較晚,大量優秀小說值得保存,卻未被視為正統文學,這與作者的心態有關,“中國小說家害怕讓人知道他們竟然屈尊到寫小說的地步”[7]269,因此這些小說家通常匿名而作。1917年胡適考證《紅樓夢》而確定作者為曹雪芹,但《金瓶梅》在當時未知作者是誰,《水滸傳》亦是如此,由于受正統文學傳統的束縛,創作小說常常危及自身生命安全。“我們至今依然不知兩位涉嫌作者,即施耐庵或羅貫中,究竟何者為《水滸傳》的作者。”[7]269
林語堂還以一則民間傳說詳細介紹《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成書過程的艱辛。《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的故鄉江陰仍有一種傳說,該傳說講述施耐庵如何躲過一劫。據說,施耐庵具有先見之明。他拒絕在剛剛建立的明朝任職,當時他已寫完這部小說,過著隱居生活。一天,皇帝和施耐庵的同窗劉伯溫(當時已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來找他。劉伯溫看到了施耐庵桌上的小說文稿。由于他認識到施耐庵天賦奇才,遂設計想置他于死地。當時,明朝初建,局勢未穩,而施耐庵的小說宣揚非常危險的思想,包括盜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等平民思想。因此,劉伯溫隨即以此為理由,請求皇帝宣召施耐庵入京受審。圣旨到達的時候,施耐庵知道自己小說的手稿被盜,認識到死期將至,于是他便從某一友人處借白銀500兩以賄賂船夫,讓其盡量延緩舟程。“施耐庵得以在前往南京途中匆忙寫完一部幻想神怪小說《封神榜》(該小說的作者實為未知),以此讓皇帝深信自己精神不正常。施耐庵在假瘋掩蓋下得以保全自身性命。”[7]271林語堂不厭其煩復述有關施耐庵創作《水滸傳》的傳說說明,當時作家創作小說往往會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其次,林語堂還結合胡適、魯迅等人的觀點以及中國小說產生的歷史背景詳細概括小說中故事演變和作者身份的問題。1948年2月,林語堂用英文為賽珍珠再版《水滸傳》英譯本作序。他在這篇序言中并沒有評價賽珍珠《水滸傳》英譯本的質量,卻以較多篇幅探討該小說形成過程,尤其是作者的身份定位問題,他認為該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是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從12世紀初至16世紀,水滸好漢的故事經過民間說書人在口頭上不斷修改與完善,包括施耐庵和羅貫中的很多編者在此期間不斷改動故事、挪移事跡、變化人物名字和姓氏、變換重點人物的塑造,以富有的想象力和持續性的敘事手段,把許多水滸英雄的事跡或軼事有機串聯起來,寫作痕跡版本最終才以留存至今的形式逐步呈現在大眾讀者面前。林語堂依次列舉郭勛、李贄、胡適和魯迅等人的觀點詳細討論該小說不同版本的作者身份問題,比如:“胡適認為,施耐庵乃16世紀一位默默無聞作家之假名,他修訂了這部小說,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認同此說法。在1933至1934年,一個名為晁瑞廷的研究再次確定施耐庵的確存在,他證實施耐庵籍貫淮安,住于東臺,并證實施耐庵乃羅貫中的老師,他在江陰某徐家做家庭私塾教師時完成了當前這部小說。”[8]13-18可見,林語堂在該英文序言中評論《水滸傳》的重要論述焦點之一是該小說的創作過程和備受爭議的作者身份問題。
總之,如林語堂在《說本色之美》一文中所強調,“就是最好的小說,如《水滸》之類,一半也是民間之創作,一半也是因為作者懷才不遇……”[9]林語堂對《水滸傳》作者并未拘泥于某一特定的說法,而是對該小說身份定位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小說的復雜形成過程,即該小說創作主體、創作目的和創作過程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學理上的探討。
二、《水滸傳》之世界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總得有一個直接或間接地導源于現實事物的主題——總會涉及、表現、反映某種客觀狀態或者與此有關的東西”[2]4。簡言之,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條件,即“世界”“是由人物和行動、思想和感情、物質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覺的本質所構成”[2]4。就文學作品與世界的關系而言,西方傳統文論的模仿說強調現實世界對文學作品的影響。林語堂在論述《水滸傳》的世界這一問題上,重視現實世界對人的影響,多次強調文學作品是反映現實世界和反映作者心理狀態的主客體相融合的統一體,即《水滸傳》作者在創作時特殊微妙的心理過程。
1934年4月20日,林語堂在《論談話》一文中認為,有閑的社會才能產生偉大的藝術作品。“有閑并無罪,善用其閑,人類文化乃可發達,談話乃其一端……‘閑’有時是迫出來,非自求之”[10],除了周文王和司馬遷在監牢里分別寫出《周易》和《史記》之外,林語堂還舉施耐庵及《水滸傳》序言寫作為例,“或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憤于文章,如施耐庵,蒲留仙,便有《水滸》,《聊齋》出現。施乃深得談話個中滋味者。貫華堂古本序雖未必出施手,然其言朋友過談之樂,實太好了……其文其情皆合著書心境,也是有閑所致”[10]。可見,林語堂強調,作者所處的社會風氣、政治局勢等社會現實對文學創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1935年9月,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談及中國人的文學生活時指出,小說是在沒有教化的環境中發展并在不求回報的情況下誕生,它完全是出于作者內在的創作沖動。所有優秀的故事和小說完全是出于作者對創作的興趣,它與金錢并無關系。“再多的錢都無法讓沒有創作天賦的人講好故事。雖然安逸的生活有可能讓有創作天賦的人從事寫作,但安逸的生活從不產生作品。”[7]272除了塞萬提斯、薄伽丘、狄更斯等作家之外,“我們偉大的故事敘事者,比如笛福、菲爾丁、施耐庵和曹雪芹等,他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有故事要講且天生善于講故事”[7]271。可見,林語堂強調作者的創作沖動與創作天賦對小說的發展尤為重要。換言之,作者與社會現實以及人生遭際等因素的互相感應,引發文學創作的沖動。
1937年11月,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論述日常生活享受之一的談話時又一次強調“有閑”的重要性。“很明顯,只有在有閑社會中才能產生談話藝術;同樣明顯的是,只有談話藝術的存在才能產生優美小品文……有時這種‘閑’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我追求的結果。然而,許多優秀文學作品是在被迫的空閑環境中產生的。”[11]217-218林語堂在此除了再次舉周文王、司馬遷為例之外,還舉元朝畫家、劇作家以及清初畫家石濤和八大山人為例,“其他在科舉考試中落榜的偉大作家則把自己的精力轉化為創作,施耐庵給我們留下《水滸傳》,而蒲留仙給我們帶來《聊齋》,當屬此例”[11]218。林語堂同樣以更長的篇幅翻譯《水滸傳》序言,并對這篇英譯文做了相應點評,“我們認為《水滸傳》的序言為施所作,這是最絕妙的朋友間談話樂趣的一次描述……施耐庵的偉大作品就是在這種格調和情感之下產生的,朋友享受悠閑,才使該文的產生成為可能”[11]218-219。換言之,林語堂再次強調了悠閑的談話氣氛對藝術作品誕生的重要性。這和1934年《論談話》一文中的觀點基本一致。
1948年2月,林語堂在《水滸傳》英譯本的英文序言中認為,該小說的產生與宋代茶館里說書人的底本《宣和遺事》存在巨大關聯。“梁山泊盜匪的故事最早是由職業說書人口述的。如前所述,《宣和遺事》是根據眾多職業說書人的口述而產生的……這些只不過是說書人的底本,語言大都草率,敘事簡單,人物描寫也薄弱。《宣和遺事》毫無疑問屬于這一類型。”[8]16林語堂認為戰亂時期王朝更迭的社會現實,即“世情”使說書人有話可說,施耐庵以此為基礎,結合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和特殊的人生遭際,使其自身與社會現實之間產生相互感應,《水滸傳》由此生成。
1964年,林語堂在為其女婿黎明所著《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他說:“這些[文學]形式總是源自大眾娛樂和音樂的土壤。當某種文學表達形式(比如唐詩)的最后細微差別消失殆盡,某種強大的大眾藝術造就了新生活。宋詞只不過來自歌女,而小說(或故事敘事藝術)則來自茶館。諸如《三國演義》或《水滸傳》(《四海之內皆兄弟》)等偉大小說只不過是對茶館里早已為人所知的傳奇故事的編寫。中國文人素來‘抄襲古人’。當他們在技巧和詞匯互相抄襲至極致之時,某種創新再一次從大眾娛樂形式中煥發生機。”[12]vii換言之,外部社會因素是中國文學形式興衰之周期性循環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總之,林語堂論及《水滸傳》產生的前提條件與他大力提倡性靈文學和閑談筆調的小品文所需要的“有閑的社會”和“談話的藝術”等因素別無二致,該小說創作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悠閑談話。施耐庵經歷科舉落榜的人生遭際,他處于社會風氣盛行談話的現實世界,因而發憤著書《水滸傳》。可見,林語堂在《水滸傳》之世界這一問題上,注意到施耐庵與特殊的社會現實、人生遭際等之間形成的相互感應并引發他的藝術創作沖動。
三、《水滸傳》之讀者
艾布拉姆斯在藝術批評的四個坐標中同樣強調欣賞者(讀者)的重要性,“作品為他們而寫,或至少會引起他們的關注”[2]4。他把以欣賞者為中心的批評稱為“實用說”,這種實用主義批評其實是源自古代修辭學理論,即演說者為聽眾提供信息而感染其心靈,從而說服他們并獲得其好感。他認為,實用主義觀點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審美觀點,此學說強調作家應該重視讀者的閱讀感受。林語堂同樣多次論述《水滸傳》與讀者的關系。
1931年2月1日,林語堂在《讀書的藝術》中反復以《水滸傳》等小說說明,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書籍以及個人化的讀書才是最佳的讀書方法。林語堂認為,學生讀書本來是個人自由的事,與他人無關,但現在卻受到學校注冊部、父母或妻室等人的制約。相反,讀者自主決定閱讀小說的讀書方法才是真正的讀書之道。“學問之事,是與看《紅樓》《水滸》相同,完全是個人享樂的一件事。”[13]林語堂認為,只有以主動閱讀小說的方式而非強制的方式去閱讀某學科的書籍,才能真正學有所成,他對李清照興味到時隨手即讀這一閱讀方式的讀書之法表示贊賞。林語堂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看不懂的書,看不懂的書無非就是原作者筆法表達晦澀難懂或是作者筆法與讀者口味、學識等不相符合。換言之,如果讀者選擇興味和程度相近的書,讀者便可無師自通,如果遇到疑難,涉獵久后便可融會貫通,不存在閱讀障礙的問題。他再次以讀者看小說時遇到不懂字、句說明,所謂生字或難句等不會造成閱讀障礙的問題,“試問諸位少時看《紅樓》《水滸》何嘗有人教,何嘗翻字典……”[13]他同時認為,許多中國讀者優秀的中文功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主閱讀中國古典小說,頻繁接觸不懂的字句會提高中文閱讀素養,這種“習慣成自然”的讀書法也適用于讀專業或學術性質比較強的書籍。
1934年2月15日,林語堂在《論讀書》一文中指出,學校所讀之書并非學生真正該讀之書,他強調讀者自由看書和讀書,即自主閱讀的重要性。學校讀書的四大弊端之一就是:學校要求學生重點閱讀的教科書不是真正的書籍。他認為,閱讀《水滸傳》等小說的閱讀效果比閱讀一本小說概論要好,而閱讀《史記》的閱讀效果比閱讀歷史教科書要好。他反對苦讀,而是主張快樂讀書,偷看《水滸傳》等小說的人是在享受讀書之樂,“國文好的學生,有些是由偷看《三國》《水滸》而來,決不是一學年讀五六十頁文選,國文會讀好的……好學的人,于書無所不窺,窺就是偷看”[14]。可見,林語堂強調《水滸傳》等小說是讀者自由消遣和快樂閱讀的最佳書目之一。
1935年9月,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以小說的內容為標準進一步把中國小說細分為八種類型,而《水滸傳》為冒險小說(俠義小說)的典范。《水滸傳》的大眾影響力遠超神怪小說、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淫穢小說、社會諷刺小說、幻想小說以及社會寫實小說等各種類型的小說而位居榜首。這種看似奇怪的現象只能從讀者閱讀心理的角度去解釋,小說中的俠義之士因為過度關注民間百姓之疾苦而為其打抱不平,并因官司牽連而被迫放逐異地,最后又被迫落草為寇。《水滸傳》中官府眼中的綠林盜匪在普通百姓眼里卻是綠林英雄,“在一個沒有法律保障的社會里,堅持替窮人及受壓迫者打抱不平的人確實是一個‘堅不可摧’的硬漢……中國社會的這些安分百姓非常崇拜綠林好漢,猶如纖弱婦人崇拜面孔黝黑、滿臉胡須和胸毛蓬蓬的彪形大漢。閑臥被褥中閱讀《水滸傳》,對李逵勇敢和英勇行為贊不絕口,還有比這更安逸、更興奮的事?要知道,臥床閱讀小說在中國乃是家常便飯”[7]275-276。可見,林語堂注意到閱讀《水滸傳》等俠義小說時讀者的心理需求以及這類小說給讀者提供心理補償功能,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小說閱讀受眾的廣泛性。
1943年10月,林語堂在抗戰期間第二次回國時再次對中國思想的混亂狀態表示擔憂。他在《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一文中認為,把《水滸傳》等書列為有毒之書無助于本國文化自信心的建立。“外國文化,且不必說,本國文化也難有真知灼見的認識。但沒有真知灼見的認識,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心就不能建立。”[15]因此,林語堂并不認同《水滸傳》等中國古代小說有毒之說,也不同意小說里忠孝節義的思想有毒,而是強調《水滸傳》對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的傳承作用,而不刻意追究其歷史或社會負面效應。林語堂這種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接受態度在當時還引發一定的社會熱議。
1948年2月,林語堂為賽珍珠《水滸傳》英譯本撰寫英文序言中也論及《水滸傳》內部的藝術魅力同樣能夠給讀者帶來愉悅感。首先是該小說的故事材料打動讀者。他以翔實的文史資料進行闡述該小說贏得讀者的同情在于,水滸英雄彼此之間高度團結、忠誠,在蒙元時期,百姓深受異族壓迫和剝削,他們從綠林好漢的水滸故事中尋找慰藉便不難理解。換言之,林語堂對《水滸傳》這部“怒書”的理解就是小說的創作者貼近讀者的內心世界,作者與讀者感同身受而互為交融,這是讀者與小說作者在深層心理上,二者感應、共鳴、共振的最好寫照。其次是該小說的人物塑造打動讀者。林語堂認為,林沖、武松、李逵、魯智深和宋江等人物刻畫在小說中最為深刻,尤其是小說第20章至41章武松的故事、攻打江州及宋江在江州之戰后投奔梁山的敘事,以及第46章至49章攻打祝家莊、第62章至67章攻打大名府與曾頭市的征戰敘事。此外,“黑旋風”“小旋風”“豹子頭”等各種人物綽號的使用為小說增色不少。這些細節評論足以說明作為《水滸傳》書迷的林語堂對該小說的熟悉和喜愛程度,也代表了作為讀者的林語堂對自由閱讀作品的接受理念。
1966年3月14日,林語堂在《中央日報》“無所不談”專欄發表《論趣》一文,他再次以《水滸傳》等小說為例強調隨性讀書的重要性。他說,“讀書而論鐘點,計時治學,永遠必不成器。今日國文好的人都是于書無所不窺,或違背校規,被中偷看《水滸》,偷看《三國》而來的,何嘗計時治學?必也廢寢忘餐,而后有成。要廢寢忘餐,就單靠這趣字”[16]38。簡言之,現代的機械教育導致讀書論鐘點,不易啟發讀者的靈機或啟發心智。
1974年,林語堂在《論泥做的男人》一文中認為,《紅樓夢》文字技巧的出色之處是作者對小說人物兒女私情的描繪。他以《水滸傳》等為例進行幽默的比較評論:“紅樓一書英雌多而英雄少,英雌中又是丫頭比姑娘出色。所以他不像《三國演義》,活現的寫出關羽、張飛等一流人物;也不像《水滸》里,有武松一類的男人。我們不能據此而論,中國社會只有泥做的男人。我們看《漢書》,有范滂一流人物,也有范滂的母親,都是有節氣的人。那時還是封建社會,有義俠之風,睚眥必報……就像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風,也像日本的武士道,也像宋江忠義堂的義俠。”[16]46可見,林語堂對《水滸傳》等小說的人物形象進行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跨文化解讀,正是其“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體現。
總之,林語堂反復以《水滸傳》等小說為例說明讀者與作者、作品的緊密關系,以及讀者在文學接受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林語堂多次強調《水滸傳》是讀者自由閱讀和快樂閱讀的重要文本,這既是《水滸傳》本身巨大藝術魅力的體現,尤其是在故事材料和人物塑造方面對讀者的巨大影響,更說明《水滸傳》等俠義小說具有消遣娛樂和心理補償等作用,對包括林語堂在內的讀者一生讀書甚至個人寫作習慣的培養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
四、結語
林語堂非常重視《水滸傳》的外部研究,即關注小說的作者、世界和讀者等問題。林語堂在眾多論著和大量文章中以《水滸傳》與作者、世界和讀者的關系來評論《水滸傳》。他關注《水滸傳》的作者身份定位、創作目的及其復雜的創作過程,強調悠閑的談話氣氛對小說誕生的重要性。林語堂還探討《水滸傳》讀者的文學接受活動,即讀者與作者、作品存在一種相互對話、相互召喚的關系,讀者與時代也相互呼應,他從讀者閱讀《水滸傳》的主觀能動感受論述《水滸傳》是培養讀者自由、快樂閱讀以及個人寫作習慣的重要文本。總之,林語堂以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論述《水滸傳》的作者、世界和讀者等問題,既是他進行中國古典小說外部研究的重要例證,也是他向國內外學術界和讀者傳遞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