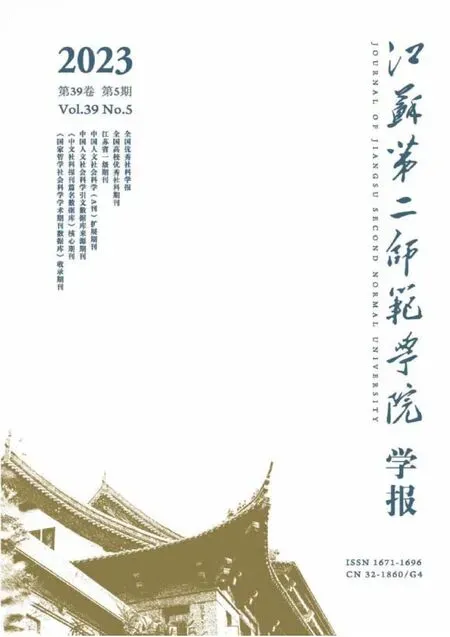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視域下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研究*
任麗曉 張更立
(1.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安徽蕪湖 241000;2.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學前教育學院, 江蘇南京 211200)
學前教育作為終身學習的開端,是社會發展與教育改革之根本。在我國經濟水平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人們對學前教育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切實提高學前教育質量已經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1]。幼兒園課程是幼兒園教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前教育質量的體現。幼兒園課程實施的基礎與前提就是課程資源,沒有課程資源也就沒有課程。近些年,“兒童優先”“兒童保護”“兒童友好”等理念逐漸進入我們的生活。2021年9月3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多部門印發了《關于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兒童友好”的內涵,并提出了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五大行動框架[2]。《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還針對兒童友好城市以及兒童友好社區建設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目標與策略措施[3]。由此可見,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已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兒童友好”理念也融入社會公共服務、城市建設、學校教育、醫療衛生等方方面面。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不僅提出了兒童優先、兒童友好的理念,還為幼兒園課程的開發提供了有效的資源支持。本研究通過分析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與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內在聯系,剖析目前兒童友好城市視域下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存在的問題,并為兒童友好城市如何為幼兒園課程資源的建設有效賦能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為今后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提供更寬廣的視野。
一、兒童友好城市:幼兒園課程開發的重要資源
1.課程資源的內涵
課程資源指的是能夠運用到教學活動中的各種條件和資源。課程資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課程資源指的是用于課程開發的所有條件和材料,狹義的課程資源指的是教師或學生用來開展教學活動的直接條件和材料。本研究在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視域下主要探討的是廣義上的課程資源。
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課程資源可以分為很多種類。第一種是根據課程資源的存在形式,可以將課程資源分為有形課程資源和無形課程資源[4]。有形課程資源指的是一些具體的物質資源,如教材、玩教具、儀器設備等;無形課程資源指的是一些范圍較廣、對課程的影響較為隱性的具有抽象意義的一類資源,例如教師的兒童觀、課程觀、教育觀等。第二種是根據課程資源的來源劃分,可以將課程資源分為校內課程資源和校外課程資源[5]。校內課程資源涵蓋了校內一切為課程開發所需要的環境資源、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等,校內課程資源在課程開發中起到了最為直接和基礎的作用;校外課程資源指的是家庭、社區乃至整個社會可運用于課程開發的所有資源,校外課程資源是一種輔助性資源。無論是校內資源還是校外資源,對課程資源的開發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美國著名課程論專家泰勒曾提出最大限度利用校內資源,加強校外課程資源的運用,幫助學生與學校外的資源建立聯系[6]123。第三種是根據課程資源的功能劃分,可以將課程資源分為素材性課程資源和條件性課程資源兩大類[7]。素材性課程資源是指能在課程中發揮作用并能作為材料或源泉的課程資源類型,條件性課程資源雖然在課程中發揮作用,并非課程自身的直接來源,卻在相當程度上確定了課程實施的深度與廣度[8]。
2.兒童友好城市建設與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內在聯系
(1)兒童友好:幼兒園課程開發的無形資源
“兒童友好”這一理念起源于兒童立場的確立,兒童立場是由兒童觀決定的,即人們對兒童的看法與認識。西方兒童觀在經歷了“小大人”“原罪說”這種“沒有兒童”的觀念之后,盧梭的出現將兒童從錯誤的兒童觀中解救出來,兒童立場在“兒童的發現”中得以初步確立。伴隨著杜威、蒙臺梭利等教育家對兒童的進一步研究與闡釋,兒童的獨特性與內在價值得到了體現,“以兒童為中心”的兒童立場逐漸成為指導教育實踐的基本理念。除此之外,“兒童友好”理念還起源于國際法案對兒童權利的認可與保護。1959年和1989年的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分別通過了《兒童權利宣言》與《兒童權利公約》,明確了兒童應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等權利。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全球環境會議上,《兒童權利公約》被提議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為響應《兒童權利公約》的號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下簡稱“兒基會”)與人類住區規劃署(以下簡稱“人居署”)于1996年聯合啟動了一項有關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舉措,以支持地方政府落實兒童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主張在一個城市或者一個社區里,孩子們的聲音、需求、優先事項與權利構成地方公共政策、程序與決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9]。
“兒童友好”理念在幼兒園課程開發中是以一種無形資源的方式所體現的,這種無形資源指的是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兒童觀、教育觀與課程觀。首先,“兒童友好”理念為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提供了“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兒童觀。在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中,兒童有獨立的想法、特有的發展規律,兒童不是被動接受課程的客體,而是課程資源開發的主體。其次,“兒童友好”理念為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提供了“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觀。幼兒園課程的開發應以兒童的生存權為基礎,以兒童的發展權為出發點,保護兒童最基本的權利并最大限度地使兒童有權參與到幼兒園課程建設之中。最后,“兒童友好”理念為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提供了兒童視角的課程觀。“兒童友好”理念下的課程觀應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視角,而非“自上而下”的俯視視角來理解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10]112。
(2)城市環境:幼兒園課程開發的校外資源
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標志,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全球的城鎮化呈快速發展的趨勢。聯合國人居署《世界城市報告2022》預計,到2050年全球城鎮人口的占比將從2021年的56%上升至68%。我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個百分點。城鎮化和城市高品質發展的關鍵在人,其中的重點人群是兒童。據聯合國兒基會統計,當今世界上40億城市人口中近三分之一是兒童。據估計,2050年全球近70%的孩子將居住在城市。城市除了可以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巨大的機會和希望之外,還可以為兒童生活、學習和茁壯成長提供有利資源,城市已成為兒童成長和發展的主要外部環境,這一趨勢日益顯著。
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為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提供了豐富的校外資源,這些校外課程資源與兒童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將教育看作生活中的一部分,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將生活作為教育的過程,這兩個理論的基礎是生活與教育不能分開,即教育的場所不限于學校,校外資源也是重要的課程來源。我國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也曾提出“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11]17,即把大自然和大社會作為構建幼兒園課程的切入點,使幼兒直接從大自然和大社會獲取知識。張雪門先生在論述幼兒園教材時也曾提出兒童的生活經驗來源于兒童自身個體發展、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城市中包含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城市與自然是對立的、隔絕的,我們認為真正的自然都在遠方。其實不然,城市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葉都可以成為幼兒學習與生活的來源,亦可成為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來源。同時,大社會也是兒童的世界,家庭是怎樣組織的,鄉鎮是怎樣自治的,社會上的風俗習慣是怎樣形成的,國家是怎樣富強起來的,世界是怎樣進步的,這一切社會的實際問題,都是兒童的活教材[12]18。城市是社會資源的聚集地,城市中的相關課程資源包含各種人力資源、物力資源以及文化資源,其中,人力資源包括城市中的各種職業角色的總和,物力資源包括城市中的商場、工廠、寫字樓、醫院、超市、公共交通、公園以及社區公共活動空間等,文化資源包括城市中的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大中小學以及當地的風俗文化等。這些與兒童生活息息相關的城市社會資源都是開發幼兒園課程的優質資源。
(3)社會合力:幼兒園課程開發的條件性資源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提出了生態系統理論,他認為個體的成長是在由家庭、社區以及國家所組成的多元背景下發生的,并受不同層次系統的影響。幼兒園課程存在于這一生態系統之中,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同樣受到多層次環境系統的影響,在這一系統的各個要素之間不斷發生著轉換與排列組合。幼兒園課程資源就是可用于幼兒園課程目標達成的各方面因素的總和。因此,凡有利于幼兒主動學習以及全面和諧發展的各種資源均應開發利用[13]。我國《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也曾明確提出:幼兒園必須與家庭和社區密切合作,與小學緊密銜接,充分利用各種教育資源,共同為幼兒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14]。
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聯合家庭、社區以及社會多方力量,可以為幼兒園課程提供條件性資源,這些資源雖不直接作用于課程,卻是影響幼兒園課程深度與廣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家庭是兒童成長的重要場所,家長在兒童學習與成長中不可或缺。家長的職業、家庭的育兒經驗以及家長對孩子成長過程的了解都是幼兒園課程開發的重要資源。同時,家長也是幼兒園課程建設中重要的參與主體。家長在參與幼兒園教育活動時,應積極支持幼兒園課程建設與改革,為幼兒園課程建設提供各種建議,為班級教育教學活動提供各種信息和材料。其次,社會各方力量也是幼兒園課程開發的條件性資源,可以為幼兒園課程建設提供寶貴的支持和幫助。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呼吁社會各界力量達成兒童友好的共識,發揮社會公共資源的引導與撬動作用。它們不僅可以為幼兒園提供豐富的社會服務和資源,還可以為幼兒園提供社會文化知識和技能,為幼兒園課程開發提供創新思路,從而提高學前教育質量,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二、兒童友好城市視域下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存在的問題
1.城市建設中幼兒園課程資源友好性不足
杜威曾提出:“學校的最大浪費是由于兒童完全不能把在校外獲得的經驗完整地、自由地在校內利用;同時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應用在學校學習的東西。”[15]58這就是學校與生活相割裂的現象,這種割裂現象同樣也出現在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與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之中,即幼兒園課程資源建設沒有將校內資源與校外資源很好地相融合,對要開發的城市資源如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等多樣化校外課程資源重視不夠。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缺乏兒童教育視角。隨著2021年《關于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的頒布,各地政府都在為創建兒童友好城市做出努力。目前推動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創設適兒化城市公共空間,為兒童成長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和環境。但是,在快速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城市建設還是多以成年人群的活動方式以及使用需求為依據,有些地方只是將兒童的發展看作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附帶問題,導致以兒童為中心的服務供給、設施配備建設以及空間規劃等方面有所缺失[16]。城市建設與兒童教育的關系更是被忽略,兒童教育是“兒童友好”的最大體現,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也是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還未考慮到對幼兒園課程資源的友好性,城市的建設與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未實現友好地聯結。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不是簡單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社區及城市公共空間資源要發揮重要的教育功能,為幼兒園課程的開發提供重要的校外資源。就教育功能以及幼兒園課程資源友好性而言,兒童友好城市建設還需要繼續努力和探索。
2.幼兒園課程建設中自然資源利用不足
幼兒園課程是感性的和行動的課程,因此,特別需要豐富多樣的課程資源來支撐[17]。在現實的教育場域中,雖然目前已出現園本課程、班本課程等多樣化的課程資源形式,但課程資源結構單一、課程資源載體過分依賴已有教材的問題仍然存在,課程資源的獲取范圍也比較狹窄。其中,幼兒園課程對城市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明顯不足。“大自然缺失癥”是美國作家理查德·洛夫在其著作《林間最后的小孩》中提出的一種現象,一般是指那些遠離自然環境在城市中長大的孩子所表現出來的現象,這種現象同樣也體現在城市中幼兒園自然資源使用不足這一方面,即“幼兒園課程自然資源缺失癥”。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中的第八種智能就是自然觀察智能,它是指有強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敏銳的觀察能力以及善于觀察自然界的一切,能夠認識一切事物之間的細微差別并將其區分、歸類的本領。在信息化、智能化時代背景下,在高科技生活的包圍下,生活在城市的孩子被平板電腦、電視和手機所吸引,他們的玩樂方式多限于室內的游樂場,有的孩子甚至在自然環境中表現得不知所措,進而喪失了與自然親密接觸的本能,兒童的自然觀察智能沒有機會被發掘,由此帶來一系列身體與心理健康的問題。幼兒園課程資源充斥著許多現成的音像資料、網絡課程資源包、電子繪本等信息化課程資源,信息化課程資源雖然增加了幼兒園課程的娛樂性、趣味性以及便利性,但是剝奪了兒童了解自然、探索自然的機會和權利。
3.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中兒童參與不足
參與權是所有兒童的基本權利,兒童不論年齡、性別、能力、社會階層都享有平等的參與權。讓兒童有機會參與影響兒童自己的決定,是對兒童尊重與認可的體現,也是實現《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其他權利的手段。因此,在兒童友好城市倡議中,保障兒童的參與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但是,呼吁兒童的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目前更多是一種倡導的理念而非運用的理念。我國幼兒園課程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教育專家、教師等成人,學前兒童很少參與[18]。在文獻檢索的過程中,有關研究兒童參與課程決策的文章僅有幾篇,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兒童在課程決策中的作用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兒童在課程中的主體性地位沒有得到真正的體現[19]。學前教育發展至今,以兒童為中心的學前教育觀已被廣泛認可,教育工作者越來越重視兒童在教育中的作用與地位。在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過程中,成人更多地將兒童看作是課程資源的享用者、受益者,教師更多地將工作重心放在如何為兒童提供更好的課程資源上,忽略了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存在,導致兒童在課程決策中缺乏有意義的參與。兒童友好城市視域下所提出的兒童參與權試圖扭轉兒童的地位,使之從被動接受成年人的照顧和保護轉變為積極參與相關事務,發揮主觀能動性。因此,僅僅讓兒童參與到課程中是不夠的,要讓兒童有機會真正意義上參與到課程決策之中。
三、兒童友好城市建設中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策略建議
1.發動社會多方力量,構建“兒童友好”課程資源觀
從國家到社會、從幼兒園到家庭,幼兒教育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幼兒園課程資源也滲透在兒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課程資源觀是人們對課程資源的認識與看法,課程資源觀直接影響著課程資源的開發程度。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僅靠學前教育內部支持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向社會各界注入“兒童友好”的理念,共同致力于兒童發展。首先,國家層面需要完善相應的政策實踐。我國兒童友好城市的政策實踐還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努力解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經費問題[20]。同時,地方政府還應出臺有關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指導手冊,為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提供政策保障。其次,社會要加大對“兒童友好”理念的宣傳與實踐,城市規劃要引入兒童視角,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應以兒童需求為本,社會公共資源配置應回應兒童優先的原則。這種“兒童友好”的社會氛圍本身就是優質的幼兒園課程資源。再次,幼兒園肩負著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的重要責任。園所要積極將“兒童友好”理念背景下的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納入課程改革的計劃之中,教師要更新教育觀念,并在課程實踐中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最后,家庭資源始終都是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重要來源,家長在幼兒教育中是無人能替代的。“兒童友好”的幼兒園課程資源觀需要和諧的家庭氛圍、良好的親子關系以及家園合作的意識與能力。
2.重視兒童主體地位,促進兒童有意義的參與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將兒童的“參與權”定義為不論是兒童個體還是兒童群體,均有權對直接和間接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形成自己的意見并自由發表這些意見。幼兒園課程是兒童成長的需要,兒童的參與也是構成幼兒園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參與關乎自身利益之事務的規劃決策是一種基于成長的內在需要,也是兒童基本參與權的體現。有研究指出,實現兒童有意義的參與需要做到以下4個方面:第一,為兒童營造安全、包容的空間,供兒童形成和發表自己的意見;第二,兒童有權通過其選擇的媒介和方式自由發表意見;第三,必須以尊重的態度傾聽兒童的意見;第四,必須就兒童發表的意見采取適當的行動,即兒童的意見要形成影響力[21]。基于此,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開發首先要做到征求兒童的意見,由此認識兒童的生活經驗并了解兒童對幼兒園課程資源的需求與想法。同時,兒童還要參與到課程決策中,與成人一同制定課程決策,兒童的參與要對課程資源的開發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兒童在課程決策的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成人主要起到輔助和協調的作用。在這種有意義的參與狀態下,兒童可以自主發起有關課程的任何活動并自行開發課程資源。此時,兒童的課程不再是以成人的建議或想法為藍本,而是兒童之間通過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確定哪些問題對他們最為重要、哪些問題亟待解決,以此作為課程資源并享受這些課程資源帶給他們的成長與進步。不過,這種兒童有意義參與課程決策的狀態還需要幼教工作者不斷地努力和探索,這也給學前教育課程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
3.多元開發城市資源,豐富幼兒園課程資源庫
幼兒園課程有其生活性和潛在性,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兒童,影響兒童的發展[22]。兒童的日常生活經驗成為幼兒園課程內容的基礎,幼兒園教學活動的開展緊密圍繞著與兒童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環境。因此,與兒童生活相關的人、環境、事物都是適宜兒童發展的幼兒園課程資源。張雪門也曾提出幼兒園教材面廣量大,凡是兒童在家庭、在社區、在街道、在幼稚園所能感受到的各種刺激,都可稱為幼兒園教材,這些教材正是鮮活的、生動的、無形的優質幼兒園課程資源[23]3。幼兒園課程資源廣泛存在于城市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之中,需要充分地開發和利用。首先,幼兒園課程要拉近兒童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建立兒童與自然之間那種與生俱來的聯結,讓兒童在真實的世界里學習[24]。打破傳統意義上的只在園內種植區或園內戶外環境中讓兒童親近自然的課程形式,讓兒童進入城市里的自然環境,從戶外活動、漫步與野營、野外垂釣、在野外觀賞動物等方面發掘幼兒園課程資源。其次,幼兒園可以充分利用城市中的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展覽館、美術館、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高等院校、商場、工廠、社區等有形的公共空間來豐富課程資源,讓兒童在參與城市公共活動以及公共事務管理之中生成課程資源。最后,幼兒園的課程內容應當根據當地文化的特點來設計,靈活地探索和開發具有本土特色的課程資源。
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是一個不斷反思、不斷創新、不斷改革的過程。在兒童友好城市理念的影響下,幼兒園課程資源開發在面臨著新的挑戰的同時,也迎來了新的機遇,幼兒園課程改革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