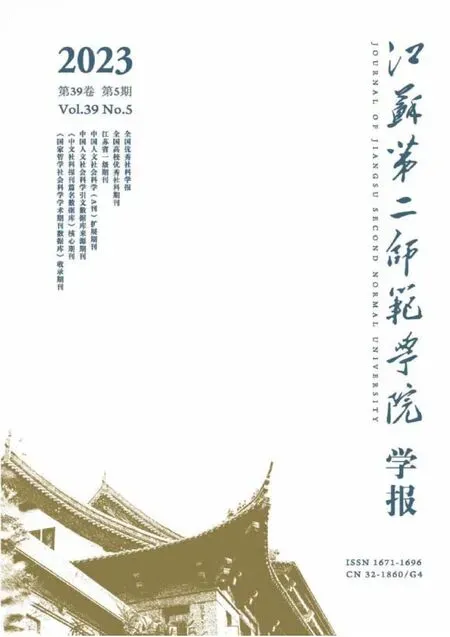近代以來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問題述論*
孫 煜
(1.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1189;2.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室, 江蘇南京 211102)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指出要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并重點強調了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實施好長江十年禁漁[1]。長江是中國的母親河,覆蓋沿江11個省市,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板塊,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21%,人口、地區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占全國比重分別達到46.4%、43.0%、54.7%(1)此數據系筆者根據2021年度沿江各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計算。。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是支撐長江經濟帶乃至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長江流域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2016年在重慶提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2018年在武漢明確指出應正確把握“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2020年在南京強調“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示范帶”。走生態優先發展之路,實現長江流域可持續發展,是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環境問題的發生和發展機制極其復雜,需要回到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中去認識其本質、發生原因和發展規律[2]。基于此,本文擬通過對近代以來長江流域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梳理分析,歸納其中的經驗教訓,并結合當前長江流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提出有關對策建議。
一、近代以來長江流域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問題
1.晚清、民國時期長江流域行業發展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1)行業結構的變動
1840年后,中國進入近代階段,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近代長江流域人口密集,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1850年),中國人口數目增至2億4千余萬。道光三十年(1850年),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下降至道光十年時的1.5畝。清政府為緩解人口過多帶來的經濟壓力,鼓勵長江流域小農分散性地開荒拓地,無系統規劃地開發造成土地濫墾,增加了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造成對自然生態的極大破壞。長江下游由于種植經濟類作物效益更好,使得傳統農耕活動轉向長江中游,主要產糧區轉移至湖廣地區。此時長江流域產業主要以農耕為主,雖然手工業逐漸興起,但缺乏大規模、持久性的工業生產,重化類工業很少。不過,此時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已經開始顯現。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長江流域區域間產業分工和區域內經濟結構的變動。
(2)手工業和工商業發展及其影響
早在17世紀中葉,在江南地區,棉農專業種植棉花,從事棉紡織手工業,形成專業化分工,開始高度商業化[3]48-51。1843年上海開埠后,隨著上海地區工業的發展以及城區的擴展,近郊農村所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尤其是在寶山縣江灣一帶,制革等工廠造成化工污染,如“沿淞滬鐵路天通庵與江灣車站之間,有威士制革廠,傍江灣河而立。凡廠中穢水,皆洩于河中。江灣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飲之有害……”[4]。近代以來,長江沿江多數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多次出現人口變動的高潮,突發性戰爭和工商業變動引起的人口迅速增長導致工商業凋敝、市政設施衰落、城市經濟倒退,各種社會弊病加深加重,以至整個城市功能趨于萎縮[5]369-426。
(3)農業開發及其影響
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勢平坦,沿江湖各州縣大都設堤塍護城捍田,圩田大規模存在。如安徽無為州,四境之內“圩居強半焉”,僅靠奧龍河及西門附郭圩田即達二千余頃[6]78-88,長江中游湖廣地區更多。咸豐九年清丈時,湖北監利縣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處,“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頃三十七畝”。同治時“南堤之內,有田數千頃,俱作堤塍御水”[7]43。圩田需要江水灌田,又要防止洪水潰堤造成破壞。圍湖墾田使湖面縮小,抗洪能力減弱;濫伐森林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導致河床抬高,江面逐漸變窄。加之大面積森林被毀,氣候環境日益惡劣,暴雨成災,給長江中下游人民的生產生活帶來重大影響[8]。
2.晚清、民國時期長江流域區域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
(1)江漢平原
道光年間,由于人口壓力加大,部分湖廣居民遷徙到鄂西和秦巴山區,刀耕火種的墾殖方式給平原地區帶來水患。清人魏源曾總結了盲目墾山的后果:“湖廣無業之民,多遷黔、粵、川、陜交界刀耕火種,雖蠶叢峻嶺、老林邃谷,無土不墾,無門不辟,于是山地無遺利。平地無遺利,則地不受水,水必與人爭地,而向日受水之區十去五六矣。山無余利,則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敗葉陳根,歷年壅積者,至是皆鏟掘疏浮,隨大雨傾瀉而下,由山入溪,由溪達漢、達江,由江漢達湖,水去沙不去,遂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淺,近水居民,又從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區,十去其七八矣。”[9]84-85
長江中游支流兩岸蓄留水的能力不足,導致山洪頻發,加大了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壓力;在長江各支流下游及荊江河段,流失水土沉降淤積導致水位抬高,對堤防威脅增大;而江河湖泊淤積,加之人工圍墾,行洪水面進一步縮小。江漢、洞庭平原以圍墾為特色,兩地都靠堤防保護,由于江漢平原經濟地位相對重要,逐漸形成“棄南保北”趨勢,但是結果卻并沒有對江漢平原形成保障。大量江水挾帶泥沙沉入洞庭湖,導致大規模圍墾,湖面面積縮小,進一步降低了對長江洪水的調蓄能力。長期南向分流及泥沙淤積,使荊江“南岸地面較北岸地面平均高出約5米,汛期,洪水位則高于荊北地面10—14米”[10]14,結果使得江漢平原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1736—1911年間江漢地區出現的洪災頻率在長江流域內最高。民國時期,水災仍是江漢平原地區最普遍的自然災害之一[11]12。上游山區毀林開荒所引發的水土流失,抬高了江漢河床,增加了對堤防的威脅,圍墾新淤又減少行洪水面。這加大了江漢地區的水災頻率,使其成為清代長江流域環境最不穩定的地區[12]。
(2)秦巴山區
在秦巴山區,森林在山區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除了大規模的木材采伐業,農業墾殖面積的擴張,造紙業、冶鐵業、煮鹽業等行業的發展,林地都是重要的墾辟對象。在農業墾殖方面,我們無法準確計算出有多少田地面積由森林面積變換而成,但明清時期農業墾殖擴張主要是靠毀林開荒;在造紙業方面,就有“擇有樹林、青石、近水處方可開設。有樹則有柴”之說法。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從資源利用上講,木材采伐和土地墾辟起到非常重要的社會經濟意義;從環境演變上講,卻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森林植被的消耗與生態環境的破壞[13]524-525。從長遠看,生態環境的破壞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甚至導致糧食生產的停滯與倒退。光緒《洋縣志》稱:“其在山中,昔時香菌、木耳、鐵、紙、木料等廠,今皆無之,唯紙廠尚余二一。”道光年間,山中的工廠因受資源開發影響,也已日漸衰退。如“山內西鄉紙廠二十余座,定遠紙廠逾百,近日洋縣亦有小紙廠二十余座”[14]178。光緒《佛坪廳志》對清代晚期的工廠衰落有所反映:“廳治向有板號、鐵廠、紙廠,自兵燹后,無復業此者。唯蓄耳樹收伏耳,養蜜蜂收蜜蠟尚獲利焉。”[15]29在山區內,經濟作物與經濟林木的經營略好,但光緒年間,受大環境影響,茶產業受阻,紫陽縣出現毀掉茶樹的情況。道光《寧陜廳志》中記載:“人煙漸以眾多,山林日見開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在一些山區,糧食生產萎縮和手工業衰敗,迫使大量山內人口流向山外。同治《宜昌府志》載:“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墾者甚眾,老林初開,苞谷不糞而獲,每市斗價值四十文,較官斗僅值二十丈。迨耕種日久,肥土為雨潦洗凈,糞種亦有不能多獲者,往時人煙輻糕之處,今皆荒廢。”[16]318一些地方稍遇歉歲,“糧價立致翔貴”,造成糧食嚴重緊張[17]357。光緒年間,鳳縣、定遠、寧羌等州縣人口數較道光初年減少。清代后期,受戰亂、自然災害等影響,山區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嚴重衰退[13]517-522。
(3)三峽地區
人地矛盾突出、薪材建材短缺和自然環境惡化的情況在三峽地區尤為典型。清代后期,三峽地區坡地已多墾殖,大面積森林轉換成了農田,萬縣一帶“承平既久,生聚漸繁,墾殖益廣”;大寧河沿岸山坡已“俱辟水田,田隨山勢之高下如梯級”;秀山一帶則“墾辟皆盡,無復豐草長林”;酉陽一帶“雍正以來黔楚江右一帶流民墾荒邱、刊深箐,隨山低谷結茅店,豎板屋”。但總體上,明清以來,煮鹽業和礦冶業發展對三峽生態的影響遠超過墾殖[18],煮鹽業、礦冶業等山區資源經濟開發對林木的破壞非常嚴重。煮鹽業的快速發展對林木資源造成極大破壞,奉節城南岸“村樹中,板百戶商民,設廠燒鹽,云煙繾繞”;大寧河一帶“柴塊居積如山,用以熬鹽”,由于大寧河地區遠離老林,鹽井薪柴取用困難,為了取薪熬鹽,流民深入大巴山中,形成“冬春之間籍燒炭營生者數千人”。從礦冶業來看,云陽、萬縣一段長江兩岸因產炭而“少竹樹”。礦業開發對環境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對植被的破壞。在找礦過程中,先要對植被進行清除,尋找礦苗,整座山被扒皮,經常出現“有礦之山,概無草木”。各生產環節都需要大量木材,比如開采時要用木材支撐坑道、用柴火破石等。特別是煉銅對周邊森林植被消耗極大。云南大廠,盛時每年出銅在一千萬斤以上。以一千萬斤計算,每年用炭便要超過一萬萬斤,這些炭都要靠礦廠附近的林木來供給。礦廠初開時,柴炭來自近山,隨著礦廠采冶時日已久,采冶愈久愈盛,其所能煉得的銅產已不抵其采運工本時,礦廠的發展走到盡頭,“山荒”導致礦廠廢棄[19]64。鴉片戰爭后,近代礦業誕生,洋務派興辦礦產企業,開始以較高強度開發礦產資源,從而為軍工企業和民營企業提供燃料。礦產資源開發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這種破壞主要包括土地的污染和森林植被的損毀,由此礦區生態環境問題影響范圍不斷擴大。
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江流域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失衡與逐步協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為了加快實現工業化的步伐,優先選擇發展重工業,依循構建工業化體系的鮮明導向,提出“以糧為綱”“大辦鋼鐵”等口號,體現“大躍進”的生產思路,生態環境形勢急劇惡化,導致長江流域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嚴重失衡。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污染,從前一時期的農業污染源轉向農業與工業污染源并存。農業方面大力興修灌溉設施、圍湖造田、興建梯田,這在促進農業生產力有所發展的同時,也造成長江流域嚴重的水土流失和環境破壞。
改革開放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在東部沿海地區,東中西區域經濟差距逐漸拉大。從長江流域總體情況來看,各省份的沿岸重工業、鄉鎮工業以及農業雖然實現了較快的發展,但整體上還屬于粗放型經濟發展的模式。盡管國家環保力度逐漸增大,環境保護被列為基本國策,但由于環保體系的構建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因此長江流域內的水土流失和點源、面源污染依然凸顯,農業面源污染和三廢排放問題比較嚴重。不過,長江流域第三產業的發展比較迅速,長江經濟帶沿線地區產業結構開始向偏輕型化轉變,這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部分環境壓力。
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市場化目標的確立,中國開始逐漸邁入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整體上看,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的快速增長,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這一時期,上中下游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也在不斷地擴大。區域經濟重工業等傳統工業部門仍占主導地位,人地矛盾進一步激化。
2002年后,中國工業表現為重工業快速增長,所占比重不斷增高。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經濟發展分化趨勢明顯,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后,中西部增長速度略快,但在經濟總量和經濟質量上,始終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長江經濟帶三大區域的發展階段不同,產業結構呈現東高西低明顯的梯度差異,中上游地區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下游地區開始步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伴隨城鎮化以及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長江經濟帶開發治理壓力增大。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生態環境治理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長江經濟帶的生態環境依舊面臨惡化的危機。
2016年以來,為了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長江經濟帶確定了“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總基調和大方向,專門成立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建立問題臺賬并督促地方整改;系統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以“三生融合”理念推進長江岸線整治與優化,持續推進騰籠換鳥。具體措施包括搬改關轉化工企業8 091家、長江干流沿線碼頭實現船舶垃圾設施全覆蓋等。在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同時,長江經濟帶持續優化新興產業布局,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產業規模占全國比重超過了一半。但生態環境問題仍然存在,其中,長江經濟帶礦山生態治理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監管缺位、無序開采、尾礦庫及尾礦渣處置不當、廢水排放不達標、土壤污染評估缺失等[20]。總之,長江流域產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有了很大進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長江流域的環境治理依然任重道遠。
二、近代以來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舉措
近代以來,面對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影響,民眾和政府也在不同時期采取了一些舉措,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1.農田保護式開發與修復治理
其一,在長江下游。總體而言,清代長江下游南岸平原地區的土地面積、農民一年勞動日數和每茬作物的畝均勞動投入等與明代比較變化不大,但清代這一地區更加合理地利用農業資源,或提高復種指數即普及稻麥輪作的一年二作制,或在減少糧食作物的同時增加桑、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提高生產的集約化水平即增加單位面積的勞動與資本投入。而且明清時期,隨著資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生產區域專業化分工逐漸顯現,在長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平原形成了三個作物種植區,分別是太湖東部和北部沿江沿海地帶的棉區、北部地帶的稻區和南部地帶的桑區[21]。清代,蘇州地區對土地的合理利用對處于同樣嚴峻的人地矛盾中的其他地區具有很好的啟示作用。蘇州人民因地制宜,采用基塘的綜合經營,將水稻種植、畜漁養殖和栽桑養蠶等結合起來,綜合經營,合理種養,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優化生態環境。另外,徽州山區的森林保護意識及清中后期驅逐棚民后所采取的封山育林等措施,使徽州山區的生態環境在清中后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
其二,在長江中游。以秦巴山區為例,圩田修筑是治田和興修水利的有力嘗試。“茲體大圩也不足抬高水位,只有統一的地區性統一管理圩田系統,才能達到這個效果。這種技術非個人或村莊所能完成,必須依靠國家或地方治水組織的力量。”[22]3“鄖屬六邑惟房猶號裕米之鄉,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巖溜山溪,源流不遠,秋淫夏潦,沖沒尤多。茍非蓄潴有備,分泄得宜,何以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耶?”這是清朝房縣以堰塘引蓄的案例,鄂西北山區稻作灌溉的方式多種多樣,以堰塘設施作為引蓄的工具是其中多用的一種[13]336。
其三,在長江上游。以四川地區為例,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其中,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具有典型性意義。清代都江堰地方官在既有的基礎上,關注對堰工技術和管理方法加以改進,力求使灌溉面積進一步擴大。至道光年間,該堰灌區灌溉面積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歷史最高水平[23]43-44。清代,由于梯田增多,冬水田在丘陵、山區分布普遍。道光年間,王培荀稱,四川“江流不經之處,甚多山田,層累而上,山上可種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頂,層層如梯”[24]315。冬水田是一種有利于促進旱改水的農作制度,這種小型的蓄水工程適應于四川廣大丘陵山區自然條件,非常適合普通農戶經營和生產[25]619-624。
2.恢復被破壞的生態
第一,植被修復,設立采伐區和禁伐區。明清以降,受皇木采辦影響,清水江流域豐富的野生林業買賣經濟效益豐厚,大量森林被砍伐,災害頻發,人居環境破壞,生態失衡。當地民眾設立采伐區和禁伐區,形成約定俗成傳統。采伐區用于林木開發,20年一輪,砍伐后人工造林,在原地上栽下杉苗等待植被恢復。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土地,在杉苗未栽之前或初長時,還采取了“林糧間種”的措施,輪種玉米、紅薯、小麥等作物。清乾隆十四年(1794年),貴州巡撫記錄:“山多戴土,樹宜杉。土人云,種杉之地必預種麥及苞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春至則先糞土,覆以亂草,既干而后焚之,然后撒子于土,面護以杉枝,厚其氣以御其芽也。秧初出謂之杉秧,既出而復移之,分行列界,相距以尺,沃之以土膏,欲其茂也。……樹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26]177
光緒年間,錦屏縣大同鄉章山村民眾重新將遭受重創的樹木培育成風水林。民國六年(1917年),錦屏縣啟蒙鎮歸固村高增寨鄉老集體商議,做出決策,栽樹培育風水,“每戶栽風水木二十株,勒石禁砍”[27]63。采伐區與禁伐區的并存,既符合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保證了生態系統的維護。
第二,制定規約用以引導監督。清水江流域的侗、苗等民族制定的規約早期主要通過口頭傳誦,口頭傳頌的規約也被編成條文刻于石碑。比如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十二月的天柱縣藍田鎮貢溪《承先永禁》碑,被用來禁止通過河溪運送杉木,以實現保護河壩、橋梁等的目的:“原夫貢水之曲流于溪也,其有關于糧田、墳墓功德者大矣,從未有條木通行而使堰壩有損,命脈有傷,橋梁有虞者也。況國賦不可空懸,原賴堰壩以為灌溉之功,風水不可損失,培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即陶渡之橋,上通黔南,下達京廣,功德亦彰彰矣!是此溪之前后左右所系非輕,我先世祖人爰隨此溪兩岸立禁陰陽風水者也,已會議各禁,但今歷年久遠,碑記殘涂,我后人則體前人之遺意,而繼立新碑。仍使貪金之徒無由損人利己,而通放條木以壞墳、壩、橋梁也,是為禁。”[28]338
民間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規約,經過集體討論后,一旦確定,要求人人遵守。各地關于環境保護的規約不同,有的罰款后還要“稟官究治”[27]63。這些規約,一方面用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另一方面,刻于石碑傳于后世。很多內容相同或近似的碑刻,碑文中常將眾人商議形成的意見稱為公議。
第三,官方干預參與治理。雖然民間制定關于環境保護的規約起到警示作用,但仍有損害環境的事件發生。官府對于因林木砍伐運輸引起的損壞稻田、橋梁、破壞風水林的控告,積極受理并明文禁止。光緒二十年(1894年),天柱縣邦洞鎮章程村《不準開江》碑載的即是一道文告:“嗣后販木商人由旱道肩運出河,不得由溪沖放木條杉桐,以免沖壞田橋車壩,倘敢故違,一經告發,定是提案嚴懲并將,所有木植概行充公,絕不姑寬。”官方禁止帶來環境破壞的開發,刊刻于光緒八年(1882年)前后的天柱縣《邦洞鎮岳寨淘金禁碑》,記載了禁止地方開采金礦禁令的內容[29]。
3.張謇的治江實踐
實業家張謇在治理長江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摒棄古代各地立足行政區塊劃分解決水患問題的治水思路,組織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各省市共同治理流域內部水患問題。1909年,張謇成立了江淮水利測量局;1913年,擔任全國導淮水利督辦;1914年,推動成立中國近代第一個全國性流域管理機構——全國水利局。1921年,面對“揚子江下游水勢兇猛,年年漲潮沖毀沿江堤壩,致使沿江居民無不處于受災之地,損傷慘重,而長江其他支流水道年久失修,災情正處擴大之勢”[30],以及“英國人雖遠在歐洲,但對長江上游宜昌至下游崇明、寶山一段的測量已將近二十多年”[31]38,張謇提出著名的“治江三說”:設立長江委員討論會;從河海工程學校中挑選優等生參加討論會;對江蘇省境的長江干流統一規劃,分段治理。1922年,他與孫寶琦、李國珍等共同推動成立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
4.當代治水方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防洪減災是治江工作的重點,生態環境保護進入新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1991年)《長江河道采砂管理條例》(2002年)《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2016年)《長江保護法》(2021年)等綜合涉水法律法規先后頒布實施,為保護長江形成硬約束機制。以三峽工程為代表,東江、萬安、隔河巖、五強溪、二灘、向家壩、溪洛渡等大型水利樞紐,南水北調、滇中引水、引江濟淮、鄂北水資源配置等流域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設,形成長江流域堤防為基礎、干支流水庫分蓄洪區河道整治以及蓄引提水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結合的綜合防洪體系和抗旱體系。1989年起實施長江上游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流域水土流失面積實現由增到減的歷史性轉變,森林覆蓋率大幅提高。持續推進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管理體制,多層次、多類別的流域水資源保護協作機制逐步建立。根據《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長江干線岸線要實現功能分區(保護區、保留區、控制利用區、開發利用區),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等,都是對歷史上做法的延續和創新。
三、新時代長江流域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思考
1.近代長江流域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經驗教訓
近代以來長江流域環境與經濟互動變遷的歷史進程給我們提供的經驗教訓值得認真汲取。
就教訓而言,歷史表明,經濟發展和產業變遷是人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需求發展的過程。不論是無系統規劃開發造成土地濫墾,還是工業發展尤其是化工產業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圍湖墾田、濫伐森林導致的水土流失,都是簡單粗暴地向自然進行進攻和索取,把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轉化為物質財富,由此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高度緊張,最終必然受到自然的懲罰。受自然條件和地理影響,長江流域發展基礎始終呈現梯度差異性,產業梯度轉移的相關安排是有歷史和現實依據的,但盲目的產業轉移不利于承接地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下持續發展。歷史上為了保護一方水土而犧牲另一方利益的做法并不可取。
從經驗的角度看,近代以來為了保護遭受破壞的自然生態環境,政府和民眾也都在不同時期采取了一些舉措,包括各種方式的農田保護式開發與修復治理、利用集體規約引導監督和官方干預參與治理來恢復已被破壞的生態,并取得明顯的效果,這些在經濟開發過程中的環境保護智慧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值得認真加以總結或推廣。張謇“加強對長江流域干支流、各江岸和河道的協同治理工作,盡量弱化行政區域劃分對協同治理的影響”的思想,頗具科學性和前瞻性,它啟示我們要從長江流域各區域、各行業的實際利益出發,樹立大市場觀、全局觀,將局部問題置于更大的范圍去考量,從綜合的國家利益出發、從全局性視角論證重要政策建議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推動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落實。
2.促進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協同共進的建議
第一,形成正確的生態文明觀。一是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長江流域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協同推進的歷史中總結規律,深度挖掘“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轉變發展理念,促進生態文明意識持續不斷提升,不斷筑牢推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共同思想基礎,引導政府、企業、公民及全社會形成正確的生態文明觀。二是激勵各級領導干部樹立大歷史觀,從長江流域發展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出發,立足長江大文明特別是生態文明去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結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等國家戰略工程,系統、前瞻、創造性謀劃長江治理工作的頂層設計,平衡產業發展的烈度和環境保護的強度,未雨綢繆“治未病”,以長江經濟動脈涵養千年文明紐帶。
第二,推動沿江產業綠色低碳發展。一是通過優化用能結構、綠色原材料替代,提升清潔生產水平,推進循環發展、強化綠色低碳技術引領,以智能化、融合化帶動數字發展等方式推動傳統產業“調優調綠”、戰略性新興產業綠色化發展。推動生態資源向旅游、農業、養生資源轉化,加快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創新。二是優化產業布局,充分發揮區域資源稟賦優勢和產業發展基礎,以綠色低碳發展為導向,招引經濟項目,建設綠色工廠、供應鏈、工業園區形成綠色集群,打造形成一批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綠色高端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三是鼓勵科技創新,以市場主體帶動創新能力,全面提升制度創新。
第三,推動長江流域問題整改和生態環境系統恢復。一是抓好突出問題整改。持續系統推進城鎮污水垃圾處理、沿江化工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沿江尾礦庫治理,實施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嚴格執行長江經濟帶發展負面清單。二是強化生態環境系統保護修復。優先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做到在“一張圖”上定規劃、畫紅線、管空間,全流域規劃布局、全產業鏈調整升級、全要素優化配置;堅持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長江岸線高效利用和有序更新,推動長江沿岸地區生態修復;加快推進岸線集約騰退和整治修復,抓好長江生態環境大普查、嚴控重點領域污染物排放、嚴格執引長江十年禁漁,從源頭上系統開展生態環境修復和保護;強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種生態要素的協同治理,加強綜合治理系統性和整體性,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三是推進鐵水聯運,限制水泥、平板玻璃、硫酸、純堿、燒堿、砂石、煤炭的運輸距離,解決好鐵路運輸“最后一公里”。
第四,推動長江流域政府、市場、區域協同合作。一是統籌提升流域管理機構層級。貫徹落實《長江保護法》,強化提升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長江辦、長江委、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局等國家層面組織機構的作用,整合水利、國土、環保等有關部門資源信息,強化行政和法律監督管理職能手段,提高議事、協調和仲裁能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流域協同管理和綜合治理。二是積極推進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創新。綜合發揮國家項目、地方政府主導、小流域自發交易等不同層面力量,依托長江經濟帶現有自貿區、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示范區、共同富裕示范區等平臺載體,實現區域政府間的生態治理協同。三是設計完善環境生態補償、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和水權等市場化交易機制,把保護長江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環節。四是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補充協調促進的格局。政府要認真聽取市場意見,完善頂層設計,“軟硬”兼顧營造更好營商環境,高效布局產業,促進產城融合,協同推進減污、降碳、擴綠、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