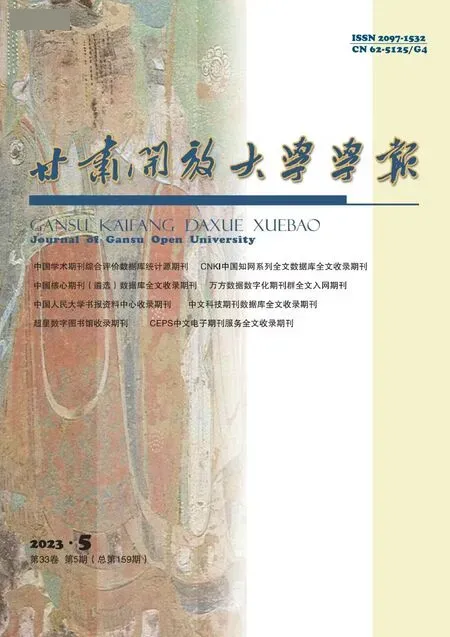從荒島看人類與現代社會
——評孫頻《我們騎鯨而去》
楊 朵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東廣州 510000)
縱觀歷史長河,人類以曲折的軌跡無限趨向文明,而在滾滾向前的文明巨浪中,發展的負面性使得緬懷歷史成為人類永恒不變的主題。在孫頻的中篇小說《我們騎鯨而去》中,“我”、老周、王文蘭被置于封閉的荒島之中,以現代人的身份回到幾百萬年前的文明之始。作者巧妙地將空間與人物的現代性并置,以此來展現舊時空和現代人之間產生的張力,進而討論人性,以及人類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一、人類孤獨的主題
荒島文學是文學史上一大經典主題。島嶼作為一個特殊的空間環境,與小說人物有著不可分離的聯系。一方面,在西方文學史上,島嶼的出現具有偶然性。對于具有開拓精神的西方人來說,島嶼是土地擴張、產品儲存的場所。島嶼的發現象征著人們對資本積累的追求以及對資本家冒險精神的贊揚。例如《魯濱遜漂流記》中,魯濱遜憑借頑強生命力在荒無人煙的小島上進行生產活動,馴服奴隸,最后得以返回故鄉,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島嶼在地理環境上的封閉性以及發展的落后性,島嶼被賦予孤獨、荒涼的寓意。荒島被浩瀚翻涌的海水包裹,自身像一座靜止的監獄,獨立于時間之外。在《我們騎鯨而去》中,作者以島嶼作為敘事空間,老周、“我”和王文蘭三個不同性格的人物相繼來到島上。人物身上烙刻的現代文明的痕跡與文明始前的島嶼形成對立。但與傳統的荒島文學不同,作者雖然將人物放置在偏僻的島嶼之上,并沒有完全將現代文明的產物杜絕在外。人物可以通過城市駛來的補給船獲得淡水和糧食,他們無需像魯濱遜一樣與自然環境、物質需求作斗爭。顯然作者以荒島作為小說環境,意在借用荒島這樣一片偏遠、人跡罕至的場域來探討人類孤獨的精神世界。正如學者王春林所說:“孫頻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把老周、王文蘭以及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也即楊老師,以一種‘孤懸’的方式放置到永生島這樣一個看起來極不起眼的封閉空間,正是為了充分地展開她對特定情境下人性狀態的觀察與思考。”[1]
小說中,島嶼的寓意隨著視角的轉變而前后變化。老周因才華橫溢遭人嫉妒,失手殺人,逃到島上。“我”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小科員,與老婆離婚后,“我”為了躲開人類,逃避與人打交道,主動要求到島上守礦。殺死了家暴丈夫的王文蘭,出獄后發現兒子車禍死亡,悲痛欲絕,受雇到島上看護小洋樓。三個主人公共同代表著擁有黑暗過往,被社會排擠,欲追求詩意世界的社會邊緣人。他們以處在現代社會的視角遙望島嶼時,島嶼是偏遠而又獨立的,像一個可以裝載一切不適宜和錯誤事物的巨大容器,是邊緣人類逃離現代社會的理想之所。作者在小說中化用了中國古代“桃花源”的典故,將島嶼變成一座海上桃花源。島上“沒有國家,沒有戰爭,沒有朝代更替,直接就從恐龍時代過渡到了現在”[2]2的歷史狀況與桃花源暗合。主人公老周是三人中第一位登島者,他長期生存在島上,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其生存狀態與武陵人“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形成呼應。模擬桃花源來書寫島嶼,說明島嶼承載著小說中三個人物的理想,是人物企圖擺脫黑暗過去,擺脫現代社會生活的精神處所。顯然,當人物以城市為中心時,島嶼即作為一個理想的彼岸出現。
但這個彼岸是主人公在現代社會受難后設想出來的場域,與現實的島嶼存在差距。當“我”以在島上生活的視角反過來審視這座島嶼時,“我發現在這島上最可怕的事情竟然是沒有人可說話”[2]21。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將“時間流程中止”[3],“我”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不斷書寫在這座沒有四季的島上閑逛時看到的椰林、欖仁樹、橙花破布木,撿到的各種稀奇的貝殼、越南小孩的尸體、像女人頭顱一樣的椰子,等等。線性的時間跟隨“我”的步伐和見聞被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空間,“長成各種形狀的時間正在那里走來走去地閑逛。”[2]1在敘述中,雖然小說的情節時間在不斷地流逝,但人物內心的感受使得時間被分解成無數個零散的碎片,小說的敘述不再是推進情節發展,而是將有限時間無限延長,以細致片段的方式去呈現在島上生活的細枝末節。時間的緩慢和行為無休止地重復增加了人物的空虛感、荒蕪感,島嶼由桃花源變成了一座孤寂的牢籠。島嶼的荒僻象征著島上生物的孤獨,而四周圍繞的海水則代表了人與人心靈間的城墻。在這島上“我”自身也幻化成了一座漂浮的孤島,島嶼和城市雙重空間體驗的對比,更襯托出了島嶼這一場域帶給人類孤獨的痛苦和危機感。最終,平靜和孤獨的自由帶來的毛骨悚然使得“我”逃離人類的初衷消失殆盡,本能地產生了與其他人相依為命的感覺。
“我”情感的轉變揭示了人類孤獨的主題,人類本身就是一座孤島,而對于長期處于社會生活中的人類來說,人群必是人類最終的歸屬,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附性是人類不可逃避的本質屬性。
二、透視人性本質
島嶼作為一個封閉的地理環境,既是人類設想的遠離人群的世外桃源,又是創造極端條件的人性煉獄場,是現實社會本身的縮影。按照小說人物對于島嶼的期待,島嶼將會是人類實現終極自由的理想空間。然而在故事的不斷演進中,桃花源式的空間逐漸倒塌。在《桃花源記》中,武陵人通過辛勤勞動在桃花源中實現了世世代代的安居樂業,文章中記述了武陵人質樸的避世追求,卻沒有呈現在長期發展中桃花源的脆弱性。可以認為,《我們騎鯨而去》進一步向讀者呈現了人類在桃花源生存狀況的一種可能。小說中的三位主人公代表了外在力量對島嶼的侵入,他們自身攜帶的現代社會屬性決定了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必定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在荒島的空間中,主人公無意識的外來理想以及人本質的屬性被激發了出來。當主人公為了逃避人群中的撲朔迷離來到島嶼時,他們發現權力依然存在。在荒島上,權力并不指由社會制度進化帶來的社會地位的高低,而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由于社會行為的某種優勢所帶來的能夠影響和控制他人的隱性權力。心理學研究者們從社會認知的角度,將權力看成一種心理狀態,認為大多數人在生活中的某個時刻都能體驗到權力,當人們體驗到權力時,他們的社會認知、社會行為就會受到權力的影響。[4]
權力在三個人物身上來回流動,制約著人物間的關系。當島上只有“我”和老周兩個男士時,我們自然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平衡關系。而這種穩定的平衡在王文蘭上島后被徹底打破。三個人無形中構成了一個小型的人類社會。起初,主人公“我”和老周形成一個和諧整體,以“先到者”的身份殷勤地接待王文蘭。隨后,“我”和老周逐漸因為王文蘭更親近誰而表現出嫉妒心理,作為力量中心的王文蘭顯然也感覺到了三人間微妙的關系,權力在小說人物間悄然產生。王文蘭上島后產生了發展旅游業的想法,為了讓“我”幫忙向朋友宣傳小島,她隔三差五過來幫“我”收拾房間。這時,“我”成為了王文蘭依附的權力對象。但王文蘭發現“我”在故意疏遠她后,她又開始拉攏老周報復“我”。在三人的情感角逐中,“我”產生了對王文蘭既厭惡,又渴望親近的矛盾心理。最終,王文蘭手握的權力促使“我”的行為超越自身意志,“我”不得不向王文蘭示好表示屈服。
在一個集體中,各成員經過長期的磨合后會自然尋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當穩固的秩序由于外因或內因遭受破壞,各成員的位置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采取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小說中的三個人物雖然沒有組成一個緊密的契約集體,缺乏強有力的制度也使他們無法形成統一的秩序,但基于人類本能的依附心理,三人無形中已經構成了一個松散的共同體。權力也依附于共同體在三個本為了逃避權力上島的人物中繁衍出來。在權力的運作下,排擠、孤立的人際互動現象反復上演。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定義為社會排擠,即“個體沒能得到家庭成員、同伴或某一社會團體的接納,被排斥在這些關系之外,個體的歸屬需求受到阻礙的社會現象”[5]981-986。社會排擠將會對個體的情緒造成嚴重影響。當“我”被孤立在外時,“我”對老周帶王文蘭出海打魚的行為感到憤怒進而演變為恐懼。“我”逐漸產生了幻覺,并每天給陌生人打電話,懇請對方不要掛電話。“我”的個體認知在被社會排擠中變異。反過來,社會排斥又將“導致人際關系的重構行為”[5]981-986,“我”因為害怕會發瘋,更加殷勤主動地迎合王文蘭和老周。小說中的三個人物經過多次人際情感的博弈最終形成某種具有約束力的交易關系,即個體通過滿足他人利益來實現個人利益。在交易中,人際關系是三人交易行為的唯一目的,人際情感也因此成為了三人小型社會相互制衡的權力武器。
故事發生至此,已經完全背離主人公上島的初衷,他們通過操縱自身潛在的權力去追求社會生活和致富夢。“我”最初為了逃避權力的羽翼來到這里,但最后卻發現即使沒有現代制度的介入,有人類的地方依然會產生權力。
三個人的孤島遭際和變化揭示了人類渴望的桃花源世界即使在封閉的情況下仍然無法實現,潛藏在人性中的黑暗和對權力的渴望也并不會因為社會環境和制度的變化而消失,反而會在極端狀態下被激發出來,人性的弱點是人類無法逃避的現實。
三、以桃花源對抗現代社會的悖論
從最初把荒島作為建設桃花源的場域,到最后小說中的三個人物最終走向了不同的結局,揭示了現代人以桃花源對抗現代社會的失敗。
小說中,作者設置“補給船”這一因素把現代文明的“福音”帶到島上,作者雖然沒有大篇幅地介紹與島嶼相對的現代社會的狀況,但現代文明卻源源不斷地通過船只傳播、運送到了島上。“補給船”的出現,從根本上否定了主人公可以通過魯濱遜式的開發來實現物質自給自足的可能。后期因為寒潮,補給船延期到來,小說人物雖然還保持著面上的禮儀,但他們內心的交鋒和狀態變化,以及殘忍地獵殺不知名的動物,更加證明了現代人對現代生產的依附性。此外,“我”和老周對香煙的癮癖也展現了人類與現代文明、現代生產的不可分割。香煙是“我們”在原始的荒島上對抗時間和孤獨的丹藥,當島上的香煙全部抽完后,“我”和老周漫島尋找地上的煙頭,最后不得不抽葉子來聊以慰藉,但原始的植物并沒有抽煙的感覺。
小說最后,三位主人公陷入與現代文明徹底割裂的絕境中。因為物質缺乏,“我們”面臨著未知的恐懼,潛藏在人內心深處的黑暗躍躍欲試。最終,荒涼的恐懼感和游蕩的食人欲望促使“我”提前結束與公司的兩年合約,跟隨終于到來的補給船回到城市。離開小島后,“我沒有再回去過一次,也避免打聽關于它的任何信息”[2]157。“我”的決然離去徹底標志了“我”作為一個現代人企圖以逃離的方式對抗現代社會的失敗。島嶼的生活經歷證明了回歸是“我”必然的歸屬,而“我”所指向的則是全體人類。
主人公老周克制住了求生欲望,拒絕吃王文蘭煮的無法辨認的肉。在表演完最后一場木偶戲后,他像長出魚鱗的人類祖先重返大海一樣,永遠消失了。老周的形象指向了小說標題的“騎鯨”意象,“他身上既有中國古代隱士的高雅與淡泊,又有尋仙般的灑脫與自在,還有那種對赴死的通透與堅定”[6]。正如“我”在小說里所說,“王文蘭與我更接近人類”,“老周其實更像那個樹上的男爵”。[2]90“樹上”代表了人類真正的心靈棲息之所,從城市到荒島再到潛入大海隱逸正是老周尋找“樹上生活”的過程,預示了老周和現代社會及人性變異的徹底割席。老周的隱逸就像“樹上的男爵”一樣,展現了其對人類無干擾、無限制狀態的追求,對人類本質的追求。在現實主義背景下,老周這一人物揭示了作者對于風骨氣質的追求,體現了作者對于深處繁復現代社會的人類的反思和憂慮。同時,老周的形象也反襯出了現代人類內心的空洞和思想性的喪失,警示人類,我們將會失去詩意世界。但從現實角度出發,老周最后以帶有中國神仙隱逸趣味的方式突然在島上消失,暗示了人類無法像作者想象的那樣重返文明之史,即在現實世界中像老周一樣完全否定現實存在,沉浸在虛幻的世界中去尋找詩意的棲居是無法實現的。
和“我”一樣更像人類的王文蘭最終選擇留在島上。她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在島上發家致富的愿望支撐她獨自留下。在島上發展旅游業是王文蘭的精神寄托,展示出她自身強大的精神內核以及抵御困難的能力,但小說也暗示了王文蘭的留島計劃必然走向失敗。首先,作者在小說中不斷暗示王文蘭的愿望天馬行空。在不適宜的土地上種土豆和紅薯,用海上漂流瓶來宣傳小島旅游,如愚公移山式的積攢礁石、蓋石頭旅館等笨拙的行為都決定了王文蘭發展旅游業的理想性和她持久留在島上的不可靠性。其次,王文蘭的行為姿態也說明了人類必須在他者中建立自身。王文蘭產生建設小島想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向他人證明自己。她多次聲稱自己害怕別人的目光,實際上也體現了她對他者評價的在意。小說中兩次提及王文蘭的紙巾,她反復強調“這可是質量好的紙巾”,仿佛在他人肯定紙巾同時,她自身也會得到肯定。“他者是塑造穩定自我的根本途徑”[7],對王文蘭來說,獲取他者的肯定是她汲取力量的源泉,因此她也必將存在于人類社會中才能不斷確立自己。王文蘭的選擇代表了試圖逃離現實世界去追求人類本質的堅持,但回歸社會將會是人類最后的選擇。
老周和王文蘭皆隱射了人類對于自我價值的追求。但他們命運的夢幻性和不可靠性襯托出“我”回歸現實社會、回歸群體生活的必然性。孫頻在采訪中談到:“我一直試圖探討的一個命題就是關于個體與時代的關系。個體與時代之間的復雜共生關系幾乎構成了個體們創傷的源頭。”[8]“我”選擇逃離到回歸的路徑事實上就是孫頻給出的答案,“我”的命運隱射了全體人類的命運。
四、結語
在荒島文學《蠅王》中,為了逃避人類戰爭流落荒島的孩子,最終被船只帶回了正在發生原子戰爭的社會。《我們騎鯨而去》也呈現出了同樣的命運路徑。小說中的三人為了逃避現代社會主動奔向島嶼,最終“我”由島嶼回歸到恐怖的現代社會,象征了人類終將從“樹上的生活”回歸現實存在的事實。
作者將人物引入設想的桃花源,卻發現即使人類逃到荒島之上,也無法擺脫激烈地自相魚肉。島嶼無形中構成了一個小型社會,其所呈現的人類生存狀態與相處狀態就是人類社會的縮影,是現實社會的隱射。從構建桃花源到逆轉式地解構桃花源,揭露島嶼與現實世界的共通性,展現了作者對于桃花源存在的質疑。作者在小說中打破人類桃花源的愿景,意在強調人類與現代社會的共生關系,逃離必然指向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