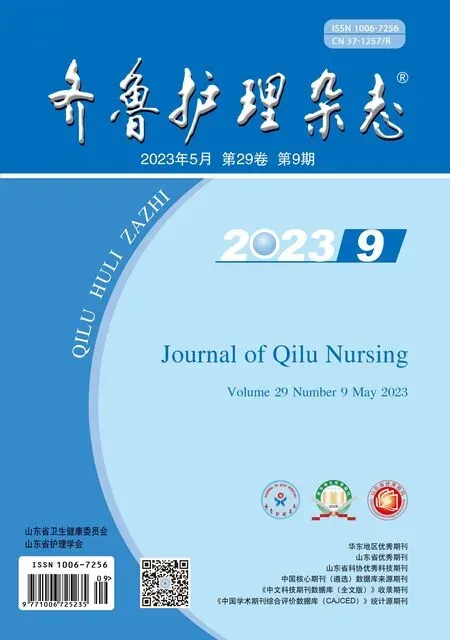健康行為互動模式對腹膜透析患者遵醫行為、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質量的影響
田 興,袁 媛,姚 嵐,梁小麗,劉 曉,苗金紅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河南鄭州450000)
腹膜透析(PD)為終末期腎病患者的常用治療方式之一[1]。PD操作較為簡便,價格相對較低,且可在家中實施,廣泛應用于臨床[2]。但PD屬于長期治療措施,治療過程中,患者的殘余腎臟功能、免疫功能及營養狀況均可隨之下降,從而導致患者出現腹膜炎、代謝紊亂、隧道感染等,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3]。同時,患者因受教育程度、PD認知度有限等因素的影響,其長期治療過程中的配合性、依從性逐漸下降,從而對治療效果形成不良影響,且增加并發癥發生風險。因此,需采用有效的干預措施改善PD患者的治療配合性。健康行為互動模式(IMCHB)為臨床新興的一種健康教育模式,主要為醫護人員在了解、評估患者的背景和情緒后給予鼓勵和支持,而醫護人員與患者雙方的行為互動是其執行的基礎[4]。IMCHB可調動患者治療、干預、護理的主觀能動性,有利于患者行為向健康方向轉變,但目前臨床關于IMCHB對PD患者效果的研究較少。故本研究主要探討IMCHB對PD患者遵醫行為、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質量的影響,為臨床制訂PD患者的干預方案提供參考。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1年7月1日~2022年9月30日收治的126例PD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②PD時間>3個月;③神志清楚,有讀寫能力,能良好配合研究者;④患者、家屬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近1個月內存在急性感染者;②伴有惡性腫瘤、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者;③接受其他腎臟替代治療或腎臟移植治療者;④心、肝、脾等存在嚴重病變者;⑤存在肢體障礙者;⑥存在精神病史或腦卒中病史者;⑦近期已參與相似研究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63例。觀察組男33例、女30例,年齡30~68(47.29±6.15)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8例,中專或高中21例,大專及以上24例;居住地:農村42例,城鎮21例;工作情況:在職5例,非在職58例;婚姻情況:有配偶54例,無配偶9例;原發疾病:腎小球疾病26例,高血壓腎病18例,糖尿病腎病13例,其他6例。對照組男32例、女31例,年齡31~69(46.88±6.07)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6例,中專或高中25例,大專及以上22例;居住地:農村44例,城鎮19例;工作情況:在職3例,非在職60例;婚姻情況:有配偶50例,無配偶13例;原發疾病:腎小球疾病25例,高血壓腎病20例,糖尿病腎病11例,其他7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相關倫理原則。
1.2 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具體包括:護理人員為患者建立個人檔案,其中包括患者的背景資料、PD執行情況、實驗室檢查結果等;指導PD操作流程、注意事項,強調遵醫行為的重要性;為患者組織PD相關教育講座或小課堂,講解PD相關知識,如PD操作手法、護理方式、用藥指導、并發癥處理等。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采用IMCHB,具體措施如下。①建立PD小組,組員由透析專業醫生、腹膜透析專科護士、責任護士等構成。小組成員詳細了解患者的性格特點、受教育程度、健康知識認知度等背景資料,然后以IMCHB理念為基礎,為患者制訂個體化護理方案,小組護理人員根據方案細實施相關措施。②為患者制訂個人信息調查表,收集患者年齡、性別、家庭結構、經濟情況等基本信息,使用心理狀態相關調查問卷評估患者的情緒狀態和性格特征,從而了解患者關于遵醫行為的內在驅動力。③加強醫護人員與患者的交流和互動,向患者普及疾病知識、PD常見并發癥、危險因素、處理方式等知識,以一對一的方式與患者進行針對性交流互動,從而提高患者疾病知識認知度,強化遵醫意識,對PD給予專業指導,并提供專業護理服務,及時解答患者的疑問,囑患者遵醫囑進行日常飲食、服藥。④提高與患者的溝通和互動頻率,通過電話隨訪及時了解患者需求,并提供情感支持;同時,與家屬密切交流,向其說明情感鼓勵、支持的重要性。患者出現負性情緒時,鼓勵和激發其與疾病做斗爭的積極性。囑患者定期復查,并關注其身體狀況,出現水腫、腹膜炎時,及時通知醫生進行處理。兩組均干預1個月。
1.3 觀察指標 ①遵醫行為:于干預1個月后評估患者的遵醫行為,其中完全遵從為患者用藥劑量、用藥時間、用藥種類等均完全按照醫囑執行,同時完全根據醫囑使用透析設備、規范飲食,并按醫囑定期復查;部分遵從為患者基本遵從醫囑進行飲食、用藥、操作設備、復查等,僅存在部分出現違背醫囑行為;不遵從為患者的飲食、用藥、操作設備、復查等大多數不符合醫囑要求或與醫囑相違背。患者醫囑遵從率為完全遵從與部分遵從所占比例之和。②自我管理能力:于干預前、干預1個月后采用維持血液透析患者自我管理量表(HD-SMI)進行評估,HD-SMI共20個條目,分別從問題解決(5個條目)、情緒處理(4個條目)、自我護理執行(7個條目)及伙伴關系(4個條目)4個維度進行評估,每個條目為1~4分,總分值為20~80分,評分越高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強。③知識掌握度:于干預1個月后通過醫院自制的PD相關知識調查問卷進行評估,問卷采用百分制,主要從PD設備操作方法、注意事項、護理注意事項、并發癥特點、應對方法等方面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分為優秀、良好、一般、較差4個等級,其中≥90分為優秀、70~89分為良好、50~69分為一般、<50分為較差。患者知識掌握度(%)=(優秀例數+良好例數+一般例數)/總例數×100%。④生活質量:于干預前、干預1個月采用健康調查簡表(SF-36)評估兩組生活質量,包括軀體功能(PF)、情感角色(RE)、社會功能(SF)、心理健康(MH)、角色限制(RP)、健康自評(GH)、軀體不適(BP)、活力(VT)8個維度,每個維度采用百分制,評分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高。

2 結果
2.1 兩組遵醫行為比較 見表1。

表1 兩組遵醫行為比較[例(%)]
2.2 兩組干預前后HD-SMI評分比較 見表2。

表2 兩組干預前后HD-SMI評分比較(分,
2.3 兩組知識掌握度比較 見表3。

表3 兩組知識掌握度比較[例(%)]
2.4 兩組干預前后SF-36評分比較 見表4。

表4 兩組干預前后SF-36評分比較(分,
3 討論
長期PD治療可對患者的生活質量產生不良影響,且打擊患者應對疾病的積極性[5]。而有研究表示,采取有效措施對PD患者進行干預,可有效改善患者情緒狀態,引導其形成健康的行為習慣[6]。而本研究主要分析IMCHB對PD患者遵醫行為、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質量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醫囑遵從率高于對照組(P<0.05),提示IMCHB可提高PD患者的遵醫行為。患者長期進行PD治療后,其身體機能、生活習慣等均隨之變化,且軀體癥狀反復出現,影響其心理狀態。當患者應對病情變化時,內心信念和希望均可隨之下降,從而導致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的積極性下降,影響治療效果[7]。且部分患者由于對疾病的認知度有限,忽視了不良用藥習慣、飲食習慣對療效的影響,從而增加并發癥發生風險[8]。而IMCHB以醫患互動為基礎,從日常飲食、用藥指導等方面給予患者幫助和干預。通過溝通、交流了解PD治療對患者情緒狀態、生活習慣造成的影響,及時給予鼓勵和支持,引導患者逐漸形成健康的行為習慣,從而獲得外在支持,且向家屬強調關心、鼓勵的重要性,使患者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增強其內心信念、希望,調整心態,積極配合醫囑[9]。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兩組HD-SMI評分高于干預前(P<0.05),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P<0.01),提示IMCHB可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PD患者日常飲食、水分攝入量均可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身體健康,故患者對飲食、攝水量等控制能力越強,越有利于患者對自身健康狀態的維持作用[10]。IMCHB可提高患者自身容量管理的參與積極性,使患者的內在動機被激發[11]。同時,通過普及疾病知識,激發患者關于控制飲食、運動、用藥等方面的責任感,提升其自我管理的意識、行為水平。護理小組基于患者基本情況制訂有效的管理目標,通過目標的導向作用,可對患者的行為改變、心態調整發揮正面引導作用,并幫助患者將治療過程中的問題以正常化態度對待,從而降低患者對解決問題的抗拒性,使其主動解決問題,從而進一步對患者的行為和形態形成正向轉化作用,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觀察組知識掌握度高于對照組(P<0.05);干預后,兩組SF-36評分高于干預前(P<0.05),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P<0.05,P<0.01),提示IMCHB可提高PD患者的疾病認知度、生活質量。IMCHB強調醫患雙方的互動和交流,而通過交流可加強患者對醫護人員的信任感,因此有利于疾病和健康知識的普及,從而提高患者的疾病認知度。PD可造成食欲減退、水腫、疲乏等軀體癥狀,從而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2]。而患者知識掌握度的提高有利于患者對自身行為的調整和轉變,并有利于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習慣,進而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軀體癥狀,并降低并發癥的發生風險,如患者通過對自身容量的管理可有助于改善胸悶、水腫等癥狀,進而改善其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