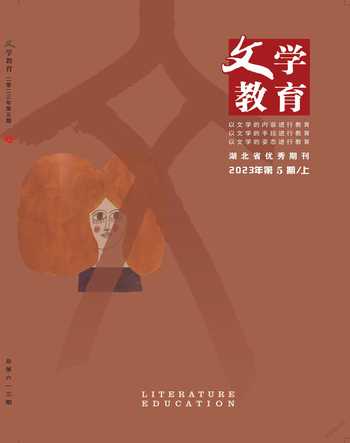哈羅德·品特早期戲劇風格探索
張文
哈羅德·品特,1930年10月10日出生于倫敦東區的一個家庭。不到20歲,他就開始在期刊發表詩歌。1949年至1957年,品特擔任職業演員,隨后開始戲劇創作。他的第一部戲劇《一間房子》(1957)在布里斯托爾演出。1958年,倫敦上演了他的另一部戲劇《生日聚會》。之后的作品包括《送菜升降機》《輕微的疼痛》《夜出》《看門人》《情人》《歸家》《沉默》《昔日》和《無人區》等。品特后期作品包括《一種阿拉斯加》《在路上》《山地語言》《聚會》和《歸于塵土》。2005年,哈羅德·品特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英國著名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被譽為二十世紀的莎士比亞,曾創作《房間》《情人》《背叛》以及《歸于塵土》等多部作品,獲得過1973年的歐洲國家文學獎、200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及同年的卡夫卡文學獎等,為20世紀的荒誕派戲劇的發展及文學創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品特創作的早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荒誕派戲劇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為西方文學的重要分支,以薩繆爾·貝克特及尤金·尤奈斯庫等為代表的荒誕派作家創作出大量優秀作品,他們的作品從題材、內容到形式等都對當時以及后繼的作家們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品特早期的戲劇創作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貝克特的影響,品特本人卻拒絕被貼上荒誕派劇作家的標簽,他將人們標簽式的評價斥為“荒誕的垃圾”(absurd rubbish),同時在戲劇創作中他又自覺抵制著傳統的現實主義情節。由于品特的戲劇具有荒誕與現實的雙重因素,我們既無法將品特簡單地歸為荒誕派,也無法將他劃為現實主義范疇。其戲劇風格獨樹一幟,具有鮮明個性,亦有學者將品特的戲劇獨成一派,稱為“品特式”(Pinteresque)風格。本文擬探究品特早期戲劇風格,選取《房間》《送菜升降機》及《看管人》三部作品為研究文本,分析戲劇中現實主義和荒誕主義的因素,以期發掘品特戲劇的內涵及其獨特性。
一.“房間”意象下的生存焦慮
品特的戲劇背景通常是一間密閉而狹小的“房間”,如《送菜升降機》中,主人公住在一間封閉的地下室房間,緊貼著后墻有兩張床,一個傳送小紙條的升降機;《房間》的主人公租住在大宅的一間房,場景內僅有一扇門、一個煤氣取暖器、洗水槽、一扇窗和一些桌椅等。此類場景由于貼近現實,通過幾個簡單的詞匯便能傳達給觀眾。由此不難看出品特對于現實背景的鐘情,而這份鐘情同時也緣于品特自身的生活經歷。1939年,為躲避德軍空襲,10歲的品特與另外四十個孩子被遣送至康沃爾,之后又與母親遷居鄉下,法西斯對家鄉的瘋狂轟炸,以及藏身于狹小的防空洞中的生存恐懼都深深印刻在了品特的心中。婚后,品特與妻子及孩子租住在倫敦破敗街區的地下室,他回憶那一時期的生活:“那確實是個貧民窟,薇薇安為人洗衣,我做司爐工的工作,我們才得以免費住在那里……”(Billington,1996:76)童年的苦難與婚后艱辛的租房生活激起了品特對空間的渴望,這在品特第二任妻子安東尼婭·弗拉瑟所創作的傳記中也有所體現:“不過,以此為起點,我們有了自己的套房,哈羅德對套房有著超乎尋常的執念。套房內有一間起居室,一間茶室,兩間臥室,一間給他,一間給我(因為接電話的原因,我堅持要求有一間自己的臥室)。”(Fraser,2010:18)
生存空間的煎熬也同樣投射在品特早期戲劇人物的形象上。他們大多居無定所,將“房間”視作庇護地,“房間外的世界是可怕的……我們都置身其中,棲身于一間房,房間外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恐懼的、好奇的和擔憂的世界。”(Esslin,1984:42)《房間》中的羅斯喋喋不休、語無倫次,不斷強調著房間是溫暖的,地下室是可怕的,外面非常冷。“房間”將她與外界未知的威脅隔絕開,她對“房間”這種病態的依戀既反映出作者對空間的占有欲,也映射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實——二戰后,英國底層民眾的物質、精神空間被急劇壓縮,生存焦慮籠罩著流浪中的貧民,窮人迫切渴望擁有屬于自己的生存空間。“房間”的意義由此也跳脫出生活居所的單一概念。“房間”是貧民躲避殘酷現實的避難所,是流浪者心靈的安全島,是隔絕未知威脅的港灣,“房間”已被不同的劇中人賦予了不同的含義。
品特以象征和隱喻的手法向讀者揭露了一個比現實更為殘酷的世界,這個世界源自現實,又非現實本身,“房間”這一貫穿其早期劇作的意象正是這一手法的體現。“房間”的設定本身具有荒誕性,場景又來自現實。劇中人固守狹小的一隅以求得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但劇中世界脆弱不堪,人物企圖在“房間”中得到庇護,最終都因“入侵者”的闖入而瓦解。品特借密閉空間設定以夸大人內心潛藏的恐懼。他巧妙地將生活的碎片拼湊起來,這些碎片是現實,又非完全刻畫現實。品特的劇作是他內在世界的映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底層民眾的生存焦慮。由此可見,盡管戲劇創作來源于現實生活,卻又凌駕于現實之上,這也是品特想要傳遞的思想核心之一。
二.身份重構背后的自我迷失
在品特的作品中,人物身份常具有不確定性,他們或是身份模糊,觀者對其過去和未來知之甚少;或是沉溺虛幻,習慣用謊言篡改現實記憶,使觀者對人物真實身份陷入迷思。
在《房間》中,羅斯被賴利喚做塞,這個不為人知的名字與羅斯的過去有著密切的聯系。姓名作為人物身份的重要象征,在品特的劇作中具有不同的意義,一個人物或無名無姓,或擁有多重身份。這看似荒謬,卻暗合著某種現實。很顯然,《房間》中的主人公羅斯,她“拋棄”了自己過去的名字。這種“拋棄”可能是對過去自我的否定,記憶的不完美疊合人性的脆弱與敏感,人們選擇“拋棄”以掩藏“自我”。人物的內像和外像因此產生矛盾,更模糊了人物的身份和形象。
在《看管人》中,戴維斯作為一個無家可歸、衣衫襤褸的流浪漢,他竭力在阿斯頓面前表現出尊嚴和體面,使自己成為一個干凈的、聰明的、與之對等的人。
戴維斯:他們全都是衣衫襤褸的人,伙計。搞得象豬一般的人。我也許已經到處流浪好幾年了,不過你可以相信我,我是整潔的。我努力使自己過得去。這就是我離開我妻子的原因。我和她結婚兩個禮拜以后,不,沒有兩個禮拜這么久,不超過一個禮拜,我一揭開平底鍋,你知道里面裝著什么?她的一堆沒有洗過的貼身內衣褲。那是炒菜用的平底鍋。菜鍋。就在那個時候我離開了她,從此再也沒有見到過她。(Pinter,1996:7)
在戴維斯的謊言中,“妻子”是邋遢的、懶惰的,自己則與之相反,盡管事實并非如此。現實和期望之間不可逾越的沖突,正是戴維斯謊言的根源。謊言同時也揭穿了人物內心最真實的恐懼。他們內心渴望成為全新的自己,便以謊言粉飾,內像和外像由此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在品特的劇作中以看似荒誕的形式展現,卻也揭示出人物身份重構背后的真相,這份真相是劇中人也是作者品特與“自我”的矛盾。作為東歐猶太移民后代的品特,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無論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我都未曾想過自己是一個猶太作家,我只是一個碰巧寫作的猶太人”。(Billington,1996:110)品特也曾將自己源于父姓的名字Pinta改為Pinter以更好地融入英國社會,品特對自己的猶太身份似乎有著刻意回避的嫌疑。品特的妻子弗拉瑟也曾寫道:“我猶記在巴黎時,我與哈羅德討論赫斯特這個人物明顯是猶太人(我有幾個猶太朋友都叫赫斯特)。哈羅德生氣地說他是用約克郡板球隊員的名字給他命名的。現在他卻說:‘人物的名字都很合適,斯普納和赫斯特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Fraser,2010:22)顯然,品特雖未與自己的種族身份決裂,但他對自己猶太后人的身份同時又倍感糾結、矛盾,這也促使他做出了回避并重構自我身份的行為,而他對自身多重身份的迷失及重構身份的訴求最終又投射于其劇中人物,造成了其戲劇人物身份的不確定性。
三.話語壁壘表象下的情感回避
亞里斯多德詩學體系將戲劇界定為“對行動的再現”或“模仿”,而語言則是實現這種“再現”和“模仿”的媒介(方柏林,1996:40)。然而,在品特的劇作中,語言更像是一種無法跨越的壁壘,而非一種交流的媒介。盡管品特的戲劇語言都取自現實,但它卻并不具備交流功能。在品特的劇作中,語言的理性被荒誕性沖淡,人物說話不以傳情達意、表達清楚為目的,對話中充斥著令人困惑的重復、沉默和停頓等。觀者在對話中獲取的信息十分有限,又常被其中荒誕的重復與沉默等所誤導,因此陷入思維的困境。而這種困境也正是由品特戲劇語言兼具現實性和荒誕性的雙重特征所導致的。
1.沉默
品特用沉默寡言的神秘性突破了傳統的現實主義戲劇。(品特,2010:2)沉默是品特戲劇語言的最典型特征和精華所在。在品特的劇作中,沉默呈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無言的靜默,一種是忽略對話對象的喋喋不休。在兩種形式中,前者較容易理解,后者相對復雜。在后一種形式中,說話者為了回避沉默而沒話找話,對話雙方在語言中傾注的真心微乎其微,在環境和語境的襯托之下,語言便成了掩蓋說話者思想沉默的工具。
在《送菜升降機》中,本和格斯同住在一間骯臟的地下室房間里,他們互相攀談,談論新聞、足球和香煙等等,他們的話題不斷轉換,后一個話題常常與前一個毫無關聯。在等待升降機送來新的小紙條的過程中,他們是孤獨而恐懼的,對話在漫長的等待下更像是一種別無選擇的行為。對話并未將雙方的距離拉近,與之相反,本和格斯都始終固守著自己的“領地”,所有的對話內容都避重就輕,語言反而加深了二人之間的隔閡。
在《看管人》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沉默”。
戴維斯:那末,這是你的房子,對嗎?
[停頓]
阿斯頓:我負責管理
戴維斯:你是房東,對吧?(他把煙斗放在他的嘴里,抽著,并未點火)的確,我注意到它們,又笨重又大的簾子從窗子那兒拉過。我想必定有人住在那兒。
阿斯頓:一家印度人住在那兒。
戴維斯:黑人?
阿斯頓:我沒有看的很清楚。
戴維斯:黑人,嗯?(戴維斯站起,四下走動)(Pinter,1996:10-11)
戴維斯向阿斯頓確認他是否是房主,阿斯頓停頓了片刻,只回答“我負責管理”。當戴維斯詢問關于鄰居的事時,阿斯頓的回答同樣模棱兩可。對話雙方一個嘟嘟囔囔、邏輯混亂,一個沉默寡言、言辭模糊,兩個人都沒有完整表達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而這段支離破碎的對話也側面映射出對話雙方內心各自存在著不安和恐懼。
2.日常對話中的障礙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品特的作品揭露了潛藏在人們日常絮談后的危機。這是由于品特的戲劇語言大多直接取自20世紀工人階級的日常對話,非常貼近現實生活,與此同時,他的戲劇語言又是充滿荒誕性的,他的劇中人常常答非所問,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呈現出令人費解的談話障礙。語言成為劇中人掩蓋自身真實情緒的武器,讓他們在自己與談話對象之間豎起防御壁壘,以最終達到回避交流的目的。如《看管人》中的這段對話:
阿斯頓:這是微不足道的幾個錢。
戴維斯:(拿著硬幣)謝謝你,謝謝你,祝你好運氣。我剛才偶然發現自己缺點錢。你知道,我上禮拜做了整整一個禮拜的工,一個錢也沒有得到。情況就是這樣,就是這情況。
[停頓]
阿斯頓:那天我去了一個小酒館。叫了一杯基尼斯黑啤酒。他們把它盛在一個厚厚的大杯里給我。我坐下了,但我喝不了。我不能從一個厚厚的大杯里喝基尼斯。我只喜歡用一個薄的玻璃杯喝。我呷了幾口,但我喝不完。
[阿斯頓從床底下拿起一個螺絲起子和一個插頭,并開始擺弄這個插頭。]
戴維斯:(非常帶感情地)要是天放晴就好了!那我就能去錫德克普了!
阿斯頓:錫德克普?
(Pinter,1996:17)
對話中阿斯頓關于基尼斯啤酒的話題出現得十分突兀,與上文也毫無關聯。作為對話的另一方,戴維斯并未對此做出反饋,而是擺弄起床底下的螺絲起子和插頭,接著他又自顧自地談論起天氣。人物間的對話充斥著驢頭不對馬嘴的口是心非,語言是他們耍弄權力的工具,他們的真實情感都被牢牢保護在無實意的文字之下。
然而,無論是沉默,亦或是對話障礙,都不代表著交流的失敗,品特表示自己的劇中人在沉默中也交流得非常好。馬丁·艾斯林認為品特對戲劇語言的運用間接地表達了一種心理真實。傳統戲劇過分重視語言的邏輯性和合理性,品特恰好打破了傳統戲劇語言對創作者的桎梏,他合理運用日常對話中重復、沉默及停頓的語言現象,在創作中突出語言的此類特質,反而賦予了作品更強的戲劇張力及威脅感。
艾斯林在自己的《荒誕派戲劇》一書中將品特列為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也承認荒誕派戲劇一詞不能替代對個別作家的準確分析。有部分學者根據品特劇作對現實生活的塑造,將品特定義為現實主義作家,卻遭到了品特本人的否認,他表示盡管自己劇本里講述的都是現實的故事,但他的表現手法并不是現實主義的。實際上,“對品特來說,在追求現實主義和激發了他的處境的本質荒誕性之間沒有沖突。”(艾斯林,2003:241)我們雖然能在品特的劇作中看到大量的現實的細節及日常的對話,但這并不等同于現實主義的實質。在品特的早期劇作中,荒誕和現實本就不相矛盾,荒誕的象征意象、神秘莫測的人物身份以及難以理解的話語壁壘等等,它們都是品特為透視現實所憑借的荒誕主義的表現手法。對品特而言,荒誕主義或現實主義任意一方的標簽都是理由不充分的,他的創作風格更介于荒誕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他不是批評家口中薩繆爾·貝克特的翻版,也不是任何傳統戲劇派別的沿襲者,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功也并非偶然,而是緣于他對戲劇創新的勇氣和魄力。品特對戲劇風格的創新精神值得當代學者和作家學習借鑒。
參考文獻
[1]Billington,Micheal.The Life and Work of Harold Pinter[M]. 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
[2]Esslin,Martin.Pinter:The Playwright[M].London:Methuen,1984.
[3]Fraser,Antonia.Must You Go?---My Life with Harold Pinter[M]. London:Christopher Falkus,2010.
[4]Pinter,Harold.Harold Pinter:Plays Two[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
[5]艾斯林;華明譯.荒誕派戲劇[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6]方柏林.哈羅德·品特的語言劇[J].山東外語教學,1996(4):38-41.
[7]品特;華明譯.送菜升降機[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