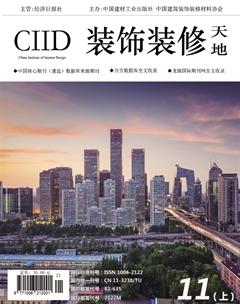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生態(tài)建筑學(xué)運(yùn)用
付晨
摘 ? ?要:伴隨著我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各個(gè)行業(yè)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資源消耗量日益增加。我國(guó)的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逐漸加重。嚴(yán)重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然而,根據(jù)建筑行業(yè)的發(fā)展情況分析,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才能確保建筑行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因此,在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不斷深入,生態(tài)建筑理念逐步滲透到建筑設(shè)計(jì)中,并且得到廣泛運(yùn)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生態(tài)建筑學(xué)運(yùn)用。
關(guān)鍵詞:高層建筑;生態(tài)建筑學(xué);建筑設(shè)計(jì);應(yīng)用
1 ?引言
伴隨著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深入發(fā)展,城市水平得到不斷提升,很多外來(lái)人口進(jìn)入到城市,隨著而來(lái)的就是住房壓力加重,由此高層建筑在城市中逐步興起,同時(shí)對(duì)環(huán)境造成了一定的程度的影響,導(dǎo)致土壤環(huán)境污染嚴(yán)重,土壤資源出現(xiàn)明顯的短缺。然而,在建筑行業(yè)發(fā)展過(guò)程中,生態(tài)建筑學(xué)逐步應(yīng)用到高層房屋建筑工程建設(shè)過(guò)程中,從而實(shí)現(xiàn)了建筑工程和周邊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減少了施工過(guò)程中的資源浪費(fèi)問(wèn)題和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
2 ?生態(tài)建筑學(xué)概論
生態(tài)建筑學(xué)是生態(tài)學(xué)和建筑學(xué)結(jié)合而成的一種學(xué)科。其基礎(chǔ)是生態(tài)學(xué),進(jìn)而對(duì)建筑進(jìn)行科學(xué)的設(shè)計(jì)。生態(tài)建筑學(xué)主要依據(jù)該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特征,合理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和建筑設(shè)計(jì)學(xué)的基礎(chǔ)原理和先進(jìn)技術(shù)等,科學(xué)處理建筑和其他因素的關(guān)系。從而使建筑和周邊環(huán)境監(jiān)理良好的循環(huán)系統(tǒng)。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中應(yīng)用生態(tài)建筑學(xué),主要是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充分根據(jù)周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構(gòu)件建筑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統(tǒng)一體系。與此同時(shí),在建筑施工階段要盡量使用綠色材料和能源等,進(jìn)而避免出現(xiàn)能源和材料浪費(fèi)問(wèn)題,有效的降低工程施工成本。在確保建筑工程整體質(zhì)量的同時(shí),要重視對(duì)周邊環(huán)境的保護(hù),促進(jìn)經(jīng)濟(jì)效益和社會(huì)效益的統(tǒng)一。
3 ?高層建筑的生態(tài)建筑設(shè)計(jì)原則
3.1 ?節(jié)能減排
在高層建筑工程施工過(guò)程中,每個(gè)階段都會(huì)有資源消耗和浪費(fèi)問(wèn)題,在進(jìn)行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的時(shí)候,要嚴(yán)格根據(jù)生態(tài)建筑學(xué)的基本要求,堅(jiān)持節(jié)能減排的原則,有效的控制高層建筑施工過(guò)程中的能源消耗,科學(xué)運(yùn)用創(chuàng)新型能源,實(shí)現(xiàn)真實(shí)意義的節(jié)能減排,進(jìn)而有效的改善城市生態(tài)環(huán)境。
3.2 ?和諧共生
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加強(qiáng)對(duì)施工現(xiàn)場(chǎng)周邊環(huán)境的保護(hù),全面落實(shí)生態(tài)建筑學(xué)相關(guān)要求,避免施工過(guò)程中對(duì)周邊環(huán)境帶來(lái)的影響,在高層建筑施工過(guò)程中要科學(xué)運(yùn)用生態(tài)建筑學(xué)維護(hù)和諧共生的居住環(huán)境。
3.3 ?以人為本
在高層建設(shè)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應(yīng)用生態(tài)建筑學(xué)可以改善建筑周邊環(huán)境,改善人們的生存環(huán)境。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人員要堅(jiān)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充分達(dá)到建筑基本需求,從而提升建筑室內(nèi)外環(huán)境標(biāo)準(zhǔn),提升高層建筑的綜合設(shè)計(jì)水平。
4 ?生態(tài)建筑設(shè)計(jì)中存在的問(wèn)題
4.1 ?高層建筑的存在會(huì)影響局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高層建筑工程在建設(shè)過(guò)程中會(huì)耗費(fèi)大量的能源和材料,特別是在建筑密集區(qū)域,對(duì)周邊生態(tài)環(huán)境產(chǎn)生嚴(yán)重的影響。高層建筑不但會(huì)影響得到人們的日照需求,同時(shí)會(huì)帶來(lái)空氣質(zhì)量問(wèn)題,嚴(yán)重的會(huì)導(dǎo)致一些區(qū)域出現(xiàn)氣流導(dǎo)管或者局部的風(fēng)谷。
4.2 ?巨大的能耗和溫室氣體
盡管高層建筑工程的建設(shè)規(guī)模和功能存在一定的差異,會(huì)耗費(fèi)大量的電力、自來(lái)水和燃?xì)饽苣茉矗瑫r(shí),有些寫字樓會(huì)有空調(diào)、消防、應(yīng)急等消耗問(wèn)題。在高層建筑施工過(guò)程中能源消耗巨大,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的溫室氣體。
4.3 ?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
高層建筑在使用過(guò)程中會(huì)產(chǎn)生很多的污水、垃圾、廢氣,同時(shí)由于建筑物的玻璃會(huì)出現(xiàn)光污染問(wèn)題,影響到駕駛員的視線,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問(wèn)題。然而,高層建筑施工材料會(huì)引發(fā)城市熱島效應(yīng),使城市內(nèi)部溫度高于城市周邊溫度。此外,高層建筑工程建設(shè)過(guò)程中會(huì)出現(xiàn)局部交通壓力加劇,導(dǎo)致該區(qū)域的空氣質(zhì)量比較差。
5 ?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中生態(tài)建筑學(xué)的應(yīng)用
5.1 ?建筑的朝向設(shè)計(jì)
生態(tài)建筑學(xué)理論是現(xiàn)代化的建筑理念,將其充分運(yùn)用到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中,可以將朝向設(shè)計(jì)和生態(tài)建筑學(xué)相互結(jié)合,最大程度的確保建筑的通風(fēng)和采光,從而充分利用自然資源,減少對(duì)建筑室內(nèi)空調(diào)和燈光的應(yīng)用,從而實(shí)現(xiàn)節(jié)能減排的效果。在高層建筑朝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充分勘察建筑周邊環(huán)境,充分了解工程施工狀況,明確建筑的最佳朝向,為了滿足建筑物內(nèi)部采光要求,要增加窗戶的總面積,通過(guò)在窗戶上設(shè)計(jì)格柵可以增加遮陽(yáng)效果,從而提升高層建筑的綜合設(shè)計(jì)水平。
5.2 ?建筑的平面設(shè)計(jì)
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人員要重視建筑體形和熱量散失的比值。在建筑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將建筑生態(tài)學(xué)應(yīng)用到平面設(shè)計(jì)中。在建筑西側(cè)設(shè)計(jì)電梯、管道、發(fā)電機(jī)房等設(shè)施,減少日光對(duì)建筑的照射。還可以通過(guò)空中庭院的模式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然通風(fēng)的效果,從而實(shí)現(xiàn)節(jié)能目標(biāo)。
5.3 ?建筑的綠化設(shè)計(jì)
在高層建筑工程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加強(qiáng)綠化方面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科學(xué)的綠化體系,提升建筑周邊環(huán)境,逐步改善空氣質(zhì)量,調(diào)整水分和其問(wèn)題,從而達(dá)到最佳的建筑外部環(huán)境。在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通過(guò)綠化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改善高層建筑外部的熱環(huán)境,從而實(shí)現(xiàn)環(huán)保節(jié)能目的。
5.4 ?建筑的遮陽(yáng)設(shè)計(jì)
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為了確保合理的遮陽(yáng)效果,在設(shè)計(jì)外立面的時(shí)候通常采用挑出的設(shè)計(jì)方式,確保建筑室內(nèi)形成一定的遮陽(yáng)區(qū)域,在減少能源消耗的基礎(chǔ)上可以保證生態(tài)系統(tǒng)在應(yīng)用過(guò)程的平衡性。在進(jìn)行窗戶設(shè)計(jì)的時(shí)候,要根據(jù)高層建筑的高度特征,全部設(shè)計(jì)成為節(jié)能窗,確保窗戶具有一定的防風(fēng)降噪的效果。針對(duì)光源對(duì)建筑帶來(lái)的污染問(wèn)題,設(shè)計(jì)人員要對(duì)窗戶的玻璃材料和邊框顏色的改變,將遮陽(yáng)系數(shù)和傳輸熱量系數(shù)以及光源透射系數(shù)控制在節(jié)能范圍之內(nèi)。在選擇窗戶材料的時(shí)候要根據(jù)該地區(qū)的具體情況,選擇遮陽(yáng)效果比較好的材質(zhì),提升高層建筑的整體設(shè)計(jì)水平。
5.5 ?建筑的水循環(huán)系統(tǒng)設(shè)計(jì)
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嚴(yán)格根據(jù)生態(tài)建筑學(xué)的核心理念,依據(jù)該地區(qū)的地質(zhì)條件、氣候環(huán)境等因素,在設(shè)計(jì)建筑給排水和雨水系統(tǒng)的時(shí)候,要加強(qiáng)資源的循環(huán)利用,注重收集建筑產(chǎn)生的污水廢水和雨水。應(yīng)用循環(huán)再利用系統(tǒng)可以對(duì)雨水和人工回收的中水循環(huán)再利用。進(jìn)而有效環(huán)境水資源緊張問(wèn)題。可以將這些中水應(yīng)用到消防用水、清掃道路、衛(wèi)生間沖水等,減少水資源浪費(fèi)問(wèn)題。
5.6 ?建筑生態(tài)表皮設(shè)計(jì)
在高層建筑的外圍護(hù)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通過(guò)生態(tài)化的設(shè)計(jì)模式,由于建筑外墻體消耗能量占據(jù)總消耗量的三分之一,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充分考慮到建筑物的功能,科學(xué)分析建筑外圍護(hù)結(jié)構(gòu)的支撐作用。在具體設(shè)計(jì)過(guò)程中要構(gòu)建建筑雙層結(jié)構(gòu),同時(shí)設(shè)計(jì)隔熱玻璃和多孔通風(fēng)層,確保建筑具備良好的散熱和通風(fēng)效果,從而使建筑內(nèi)部空氣達(dá)到凈化的目的。當(dāng)通風(fēng)層接收到外部空氣的時(shí)候,通過(guò)將空氣轉(zhuǎn)變?yōu)榫彌_氣流,可以避免建筑受到外部風(fēng)力的影響。從而創(chuàng)造出自然風(fēng)的效果。在高層建筑的表皮設(shè)計(jì)中,要充分分析居民的生活舒適感和環(huán)境輻射的影響。從而為人們提供健康的居住環(huán)境。
6 ?結(jié)束語(yǔ)
總之,伴隨著我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各項(xiàng)資源的消耗逐漸增加,同時(shí)帶來(lái)了嚴(yán)重的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直接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提升。然而,建筑行業(yè)作為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支柱產(chǎn)業(yè),在促進(jìn)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要重視建筑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因此,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應(yīng)用生態(tài)建筑理念,是建筑行業(yè)發(fā)展的主要方向。生態(tài)建筑學(xué)的運(yùn)用不但可以降低環(huán)境污染問(wèn)題,同時(shí)可以解決人們的住房問(wèn)題。進(jìn)而為人們提供舒適的居住環(huán)境,減少資源浪費(fèi)問(wèn)題,從而實(shí)現(xiàn)建筑行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 熊培清.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生態(tài)建筑學(xué)運(yùn)用[J].江西建材:建筑與規(guī)劃設(shè)計(jì),2017(24):29~37.
[2] 薛潤(rùn)澤.生態(tài)建筑學(xué)在高層建筑設(shè)計(jì)中應(yīng)用探析[J].建筑工程,2018(2):26.
[3] 萬(wàn)文娟. 建筑設(shè)計(jì)中的生態(tài)化模式及策略研究[J]. 居舍,2019(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