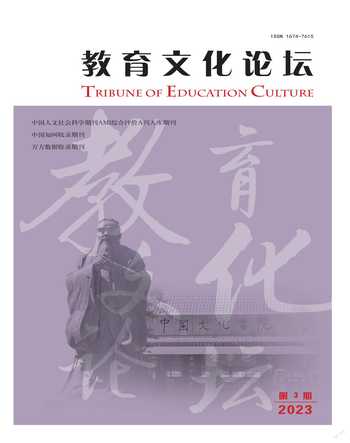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創(chuàng)意實驗
繆學(xué)超 趙薏涵
摘 要:“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項課程改革實驗,通過在中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融入經(jīng)過編輯的電影片段,引發(fā)青少年對電影中人物行為及其背后原因的討論與思考,進而幫助青少年澄清價值觀。雖然該項目持續(xù)的時間不長,但卻為青少年直面與探討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個“安全環(huán)境”,彰顯了電影作為教學(xué)媒介的活力與價值。就“進步主義教育運動”而言,“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對青少年尤其是社會中下層青少年群體予以特別關(guān)注的體現(xiàn),也是以凱利赫為代表的進步主義教育者對社會問題理解與關(guān)切的結(jié)果。從這一意義而言,“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在“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頗具創(chuàng)意。
關(guān)鍵詞:“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教育電影;“進步主義教育運動”;青少年;課程改革實驗
中圖分類號:G519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3)03-0026-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3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項目是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頗具創(chuàng)意的實驗。它將電影作為課程整合的一種方式,通過在中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融入經(jīng)過編輯的電影片段,引發(fā)青少年對電影中人物行為及其背后原因的討論與思考,以幫助青少年在家庭與社會關(guān)系中定義自己并確立價值觀。該項目由“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elations)主席愛麗絲·凱利赫(Alice V. Keliher,1903—1995)負責(zé)。它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20世紀40年代初由于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撤回對普通教育項目的主要資助,該項目被迫終止。雖然該項目持續(xù)的時間不長,但卻被視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最為激進的教育電影項目。到1941年,美國超過3 000所學(xué)校的課堂教學(xué)都曾引入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對“大蕭條”所造成的社會變化的反應(yīng)。1929—1933年,美國爆發(fā)的經(jīng)濟危機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困、饑餓導(dǎo)致了普遍的不滿和抗議;法西斯主義泛濫對美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構(gòu)成了嚴重威脅;生活水平下降造成家庭關(guān)系緊張,家庭收入減少及教育經(jīng)費銳減導(dǎo)致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失學(xué)或失業(yè)。兒童和青少年成為經(jīng)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1]150。“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將學(xué)校作為實踐社會民主的場所,回應(yīng)“大蕭條”背景下青少年對個體生活適應(yīng)性、家庭關(guān)系、人際關(guān)系及個人與社會關(guān)系的需求,不僅拓展了學(xué)校職能,革新了中學(xué)課程與教學(xué)形式,彰顯了電影的社會價值和教育價值,還為我們審視“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目前,已有研究對進步主義教育的概念與性質(zhì)[2-3]、進步主義教育的基本邏輯及其歷史變遷[4]、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5],以及杜威、克伯屈、約翰遜、康茨[6-9]等進步主義教育家進行了關(guān)注。關(guān)于“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及實驗,已有研究梳理了“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概念及歷史發(fā)展[10],并重點關(guān)注了“八年研究”實驗[11]、帕克學(xué)校[12]以及庫克實習(xí)學(xué)校[13]的實驗。“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實驗類型多樣,但目前國內(nèi)學(xué)界對教育電影項目實驗卻缺少關(guān)注。鑒于此,本文擬梳理“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開展情況,以引起人們對教育電影價值的關(guān)注。
一、“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產(chǎn)生? 20世紀30年代,美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一些關(guān)鍵性組織和個人的推動,以及“成功的秘密”(Secrets of Success)項目提供的前期經(jīng)驗,為“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產(chǎn)生提供了條件。
(一)商業(yè)電影對青少年的不利影響催生了規(guī)范電影的需求?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電影在美國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尤其是兒童。到1936年,美國供影院播放的電影已達5萬部,其數(shù)量是教育電影的5倍。僅在1936年,美國好萊塢電影公司生產(chǎn)的故事片、電影短片和新聞短片數(shù)量高達2 500部,而在同年生產(chǎn)的教育電影卻僅有兩三百部[14]。為了考察商業(yè)電影可能對青少年產(chǎn)生的有害后果,1929—1932年間,佩恩基金會(Payne Foundation)資助了一系列有關(guān)電影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佩恩基金研究表明,當(dāng)時的美國青少年大約每周去一次電影院,影院中72%的電影主題涉及犯罪、性和愛情,并且電影鏡頭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當(dāng)時的違禁品,如煙草和酒等。佩恩基金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電影對青少年產(chǎn)生了影響,其中許多影響不為父母、宗教領(lǐng)袖和其他人所贊同[15]。時任“社會價值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Values)主席的教育心理學(xué)家馬克·梅(Mark A. May)也參與了一項佩恩基金研究,他在研究報告《電影迷的社會行為與態(tài)度》(The Social Conduct and Attitudes of Movie Fans)中指出:“電影可以改變兒童的態(tài)度,經(jīng)常看電影的兒童在學(xué)校的表現(xiàn),不如那些不看電影的兒童。”[16]8
隨著無線電技術(shù)的發(fā)展,進步主義教育家們也發(fā)現(xiàn)電影這一媒介可以納入課堂教學(xué)之中,并且這種直觀、有趣的教育方式更容易讓青少年接受課程內(nèi)容,從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當(dāng)‘傳統(tǒng)教育仍然側(cè)重于教科書、講座和背誦時,‘新教育也即進步主義教育,已經(jīng)引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興趣,而這一興趣最為高漲的部分就是創(chuàng)新性地使用課程和教學(xué)材料,其中就包括電影的引入。”[17]272盡管當(dāng)時相關(guān)研究已經(jīng)證明了電影在教育方面的獨特價值,但由于學(xué)校不愿意將大量資金投入播放電影的設(shè)備之中,能夠運用電影開展教學(xué)的師資缺乏,再加上教育電影數(shù)量少且不能滿足中小學(xué)課程教學(xué)要求,學(xué)校并未對電影產(chǎn)生特別的興趣。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一些機構(gòu)開始組織教師參加利用電影開展教學(xué)的培訓(xùn)。但地方學(xué)校卻認為,有充足的適合課堂教學(xué)的電影材料,才是開展電影教育的前提。在這一背景下,一些協(xié)會和組織嘗試將已有的院線電影剪輯成隱含教育目的的電影素材。其中,較為典型的是“社會價值委員會”和“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
社會價值委員會在“美國電影制片人與發(fā)行人協(xié)會”(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的資助下于1931年成立。它的主要職能是作為“電影制片人”,將已有的院線電影和供娛樂用的故事片剪輯成教育電影,通過向?qū)W校、學(xué)院、教堂、社會機構(gòu)和社區(qū)分發(fā)電影的形式,對學(xué)生、教會人員和社區(qū)群眾開展品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是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成立的下屬委員會,1935—1942年間,凱利赫擔(dān)任該委員會主席。它與“中學(xué)課程委員會”(Commission on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學(xué)校與學(xué)院關(guān)系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一起,主要負責(zé)開展“八年研究”(Eight-Year Study)實驗。在分工方面,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主要承擔(dān)青少年人際關(guān)系的研究工作,具體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對青少年提出的各種有關(guān)生活、社會和職業(yè)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搜集、整理與加工;在此基礎(chǔ)上,由不同領(lǐng)域和學(xué)科的專家就不同問題組織材料、提供解釋[1]166。在凱利赫的領(lǐng)導(dǎo)下,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主要開展了三方面的活動:一是出版了一系列為青少年、教師和家長編寫的書籍,二是將無線電和運動圖片這一新興傳播媒介引入課堂教學(xué)之中,三是開展了一項旨在幫助青少年澄清價值觀和探索人際關(guān)系的電影項目[18]。
(二)“成功的秘密”項目提供了前期經(jīng)驗? “成功的秘密”與“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電影史上最值得關(guān)注的教育電影項目。“成功的秘密”項目的發(fā)起與1929年在波士頓開展的一次將電影用于宗教教育的討論有關(guān)。1930年,一項針對在教堂播放電影的新教徒群體的全國性問卷調(diào)查,描述了電影如何應(yīng)用于宗教教育以培養(yǎng)人的品格,并確定了一些已經(jīng)被成功地運用于宗教教育的電影[17]274。為了能夠?qū)ΜF(xiàn)有的電影資料進行編輯,使其更好地服務(wù)于教會,社會價值委員會成立。之后,該委員會又提出將編輯好的影片向?qū)W校分發(fā)的想法。最終,經(jīng)該委員會編輯和制作的21部影片被投放到教堂、學(xué)校和社區(qū)。“成功的秘密”系列電影因強烈的新教信仰以及對“正當(dāng)品格”(proper character)的明確界定,為青少年提供了真正的教育體驗,而不僅僅是普通的大眾娛樂。因此,“成功的秘密”項目的成功之處,在于使電影發(fā)揮了“隱匿”的宗教教育功能。但實際上,該項目的真正成功,在于從社會價值的角度詮釋了電影的價值。“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借鑒了“成功的秘密”項目。
“成功的秘密”項目借助電影開展道德教育的方式,為“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在學(xué)校課堂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提供了思路。“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將編輯好的電影融入課堂教學(xué),這種用影片作為課堂教學(xué)的補充材料,以引發(fā)學(xué)生討論與思考的方式,相比于以往使用單一的教學(xué)方法有著更為明顯的教學(xué)成效。此外,“成功的秘密”項目中的一些電影經(jīng)過改編后,也被應(yīng)用于“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中。例如,在“成功的秘密”項目中,《破碎的搖籃曲》(Broken Lullaby)旨在“把教會教育作為促進和平的一個重要途徑,讓每個觀看電影的個體感受到他們對戰(zhàn)爭的責(zé)任”。在“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中,這一電影主題的宗教成分被弱化,而突出強調(diào)“一個敏感的男孩對殺戮的反應(yīng),以及在歡呼聲中男人把兒子送上戰(zhàn)場的責(zé)任”。
(三)凱利赫促成了項目的啟動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負責(zé)人是凱利赫。她是一位有著豐富電影經(jīng)驗的兒童教育研究者。1930年,博士畢業(yè)的凱利赫在耶魯大學(xué)心理發(fā)展研究所(Yale University Psycho-Clinic)就職。工作期間,她拍攝了大量關(guān)于嬰兒的資料,用于對嬰兒進行自然主義研究,之后她被介紹加入芝加哥大學(xué)與耶魯大學(xué)的教育電影研究團隊。1933年,凱利赫從耶魯大學(xué)辭職,1935年正式擔(dān)任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主席。在凱利赫參與“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之前,她就已經(jīng)主持和參與一些旨在解決與青少年生活、社會和職業(yè)有關(guān)問題的活動。其代表作《生活與生長》(Life and Growth)不僅論述了青少年的身體發(fā)育、遺傳、智力發(fā)展等問題,還著重考察了處于青春期的中學(xué)生所面臨的人際關(guān)系問題,并提出了相應(yīng)的解決策略。這本書適合中學(xué)生和家長閱讀,也作為參考書目被編入“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的使用指南。凱利赫在教育電影領(lǐng)域有著較高的聲譽,在管理上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較強的組織能力,其工作也得到了“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領(lǐng)導(dǎo)的認可。她與“美國電影制片人與發(fā)行人協(xié)會”的成功談判,使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將首批75 000美元的贈款用于與凱利赫合作。這筆贈款成為“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啟動資金。
當(dāng)時,有一些文件記錄表明,“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實際上只是“成功的秘密”項目的延伸。例如,1936年6月的一份備忘錄顯示,馬克·梅曾提到,在“普通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的資助下,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將開展一項“成功的秘密”擴展項目[16]5。從1938年的一份報道中也可以看出,普通教育委員會的第二筆撥款雖然支持的是“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但這一項目也只是作為“成功的秘密”項目的更名而已[19]。但凱利赫卻始終堅持“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與“成功的秘密”項目有所不同。
“成功的秘密”項目具有明確的宗教目的性,從教育電影的角度而言,其更多是探索性的;而“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為重建中學(xué)課程而進行的教育改革實驗。自項目運行以來,凱利赫及其團隊始終將它與“八年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八年研究”主要涉及中學(xué)的課程改革,具體包括減少傳統(tǒng)學(xué)科的內(nèi)容和時間,使課程組織形式更加靈活以及注重增加新的教學(xué)內(nèi)容。在“八年研究”的合作學(xué)校中,有一類被稱為“青年需要方法”的核心課程,其出發(fā)點是幫助兒童和青少年更好地處理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1]171-172。凱利赫從“八年研究”的實驗學(xué)校中,選擇了9所作為“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前期實驗點,也期望實驗結(jié)果能夠反哺“八年研究”的工作。不同于“成功的秘密”項目中預(yù)設(shè)的品格和道德教育目的,“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在教育目的上保持開放性和不確定性。該項目旨在傳遞“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更加強調(diào)通過觀看影片的方式引發(fā)學(xué)生對同一問題的討論和思考,并使他們表達在建立民主國家的愿景下的個體性和社會性需求。
二、“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實施? 在對當(dāng)時的社會問題和人類尤其是青少年的需求進行分析的基礎(chǔ)上,凱利赫開始組織專業(yè)人員編輯“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的片段。這些電影片段短則幾分鐘,長則二十多分鐘。由于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沒有電影版權(quán),這些電影片段以每周約4.5~5.5美元的價格租賃給學(xué)校。為了幫助教師更好地使用這些電影,凱利赫在55個地區(qū)為教師舉辦了電影工作坊,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為每部電影編寫了使用指南,具體內(nèi)容包括對電影的解說、參考書目以及一些建議在課堂上討論的問題等。
(一)確立項目理念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啟動之前,凱利赫及其同事就已經(jīng)對人際關(guān)系這一主題進行了相關(guān)研究,并逐步明晰了人際關(guān)系的內(nèi)涵。他們從“文化與人格”的相關(guān)理論出發(fā),認為人本身面臨著來自社會文化和人格的雙重沖突,而社會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格的發(fā)展。因此,青少年群體需要將自己的個性與社會文化和社會規(guī)范結(jié)合起來,并努力消除個體在“平衡”和“調(diào)整”二者關(guān)系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心理障礙。人際關(guān)系應(yīng)該置于“青春期”這個新興的概念之中去理解,在身體發(fā)育、智力、社會和情感等多方面將人際關(guān)系看作一個沒有明確開始時間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界定人際關(guān)系,目的是使青少年“在社會交往環(huán)境中,真正地尋求到個體的適應(yīng)……并認識到個人動機根植于社會,個人信念產(chǎn)生于社會環(huán)境”[20]。凱利赫認為,青少年應(yīng)該被視為一個“功能完整的整體”,而不是像“品格教育運動”所設(shè)想的那樣,是在社會、情感或智力等方面單獨發(fā)展的個體[17]280。對青少年人際關(guān)系內(nèi)涵的理解,指導(dǎo)了凱利赫及其同事對好萊塢電影的選擇和編輯。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旨在平衡青少年的個性與社會文化和社會規(guī)范之間的關(guān)系。這意味著教育者應(yīng)以青少年群體的家庭關(guān)系、社會關(guān)系和個體生活適應(yīng)等問題為重點,培養(yǎng)他們的社會包容性和群體合作意識,減少他們?nèi)谌肷鐣畹淖璧K。凱利赫相信,青少年不僅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還具有開展建設(shè)性行動的能力,并且參與社會實踐活動是尋求各種社會關(guān)系問題平衡的重要途徑。她指出:“這些解決方案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攻克應(yīng)包括盡可能地采取實際行動,以防止‘什么也做不到這種令人沮喪的感覺,或是‘光說不做就夠了的感覺。”[16]6凱利赫鼓勵學(xué)生將對電影的討論與社會行動相結(jié)合。例如,電影《魔鬼是個娘娘腔》(The Devil is a Sissy)講述了一名青少年進入新學(xué)校后所遭遇的困難,學(xué)生們觀看之后自發(fā)成立“歡迎委員會”進行討論和演繹;電影《死胡同》(Dead End)描寫了一個社會階層的住房事件,學(xué)生們觀看之后開展了社區(qū)住房調(diào)查實踐,教師也鼓勵學(xué)生們?yōu)椤吧鐓^(qū)住房運動”建言獻策;觀看了《寂寞芳心》(Alice Adams)之后,學(xué)生們還計劃建造一個社區(qū)娛樂中心,以為大眾提供無歧視的社交娛樂場所。
(二)編輯制作“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的片段? 凱利赫曾在一次《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采訪中指出:“學(xué)校不僅有機會使用像電影這樣強大的媒介,也有義務(wù)引導(dǎo)青少年在電影中看到它所包含的社會材料。”[21]從1936年開始,凱利赫開始聘請約瑟夫·洛西(Joseph W. Losey)為指導(dǎo),海倫·凡·東恩(Helen van Dongen)為電影剪輯與制作人,弗朗西斯·霍爾(Frances Hall)為技術(shù)助理,編輯已有的好萊塢院線電影,使其能夠應(yīng)用于課堂教學(xué)。到1941年,他們制作了《破碎的搖籃曲》(Broken Lullaby,1930)、《監(jiān)獄風(fēng)云》(Big House,1930)、《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1931)、《阿羅史密斯》(Arrowsmith,1931)、《羅宮春色》(The Sign of the Cross,1932)、《動物王國》(Animal Kingdom,1932)、《列兵瓊斯》(Private Jones,1933)、《亂世春秋》(Cavalcade,1933)、《明天總會來》(Theres Always Tomorrow,1934)、《寂寞芳心》(Alice Adams,1935)、《魔鬼是個娘娘腔》(The Devil is a Sissy,1936)、《狂怒》(Fury,1936)、《黑色軍團》(Black Legion,1936)、《死胡同》(Dead End,1937)以及《怒海余生》(Captains Courageous,1937)等60個電影片段。這些電影涉及公民教育、跨文化教育和社區(qū)活動教育等不同主題,但從本質(zhì)上它們都揭示了人在變化的社會中產(chǎn)生的新需求,人對自我表達的需求,以及人在社會群體乃至世界中被認可與尊重的需求。
公民教育主題系列電影主要通過描繪一些與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問題有關(guān)的故事,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公民意識和民主觀念。例如,電影《魔鬼是個娘娘腔》被剪輯為三個獨立的片段:第一個片段主要講述作為英國貴族的克勞德由于自身所特有的一些貴族式“優(yōu)雅”舉止被其他同學(xué)排擠,最終因為家境落魄而被其他同學(xué)所接納的故事;第二個片段講述吉格的父親因加入黑幫觸犯法律而被電死的故事;第三個片段講述下東區(qū)的黑幫成員吉格、巴克和克勞德為了給吉格的父親支付墓碑費用,從一個富人家里偷玩具的故事。表面上看,第一個片段主要涉及人際關(guān)系的處理,旨在通過克勞德的經(jīng)歷幫助學(xué)生形成正確的交友觀念;后兩個片段著重引起學(xué)生對違法犯罪行為的關(guān)注,并引導(dǎo)他們遵守社會和法律規(guī)范。但實際上,這部電影意在引起學(xué)生對上述問題產(chǎn)生原因的思考,讓學(xué)生認識到父子之間缺乏關(guān)愛、信任、鼓勵和尊重,是導(dǎo)致孩子出現(xiàn)人際交往問題甚至產(chǎn)生違法犯罪行為的根源。電影《怒海余生》也旨在通過15歲男孩哈維的冒險經(jīng)歷,揭示他渴望得到回應(yīng)、關(guān)愛與信任的強烈意愿。
跨文化教育主題系列電影更多關(guān)注種族歧視、種族暴力、戰(zhàn)爭以及一些社會問題背后所隱藏的文化沖突問題,期望通過直觀的影片故事引起學(xué)生對不合理種族觀念的反思。這些影片主要包括《狂怒》《黑色軍團》《破碎的搖籃曲》《亂世春秋》以及《列兵瓊斯》。其中,《黑色軍團》改編自1936年一名底特律的天主教徒查爾斯·普爾被法西斯團體“黑色軍團”殘忍殺害的故事,展現(xiàn)了法西斯主義泛濫的社會背景,直觀地呈現(xiàn)了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帶來的危害,反映了消除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的迫切性;《亂世春秋》描寫了一個來自英國的母親先后送自己的丈夫和兒子走上抗擊法國的戰(zhàn)場的故事,以母親的視角表達了對戰(zhàn)爭的厭惡之情;《破碎的搖籃曲》則講述了一名法國籍的音樂家在戰(zhàn)爭中殺死一名德國人,而后又專門前往德國尋求被殺者父母原諒的故事。后兩部影片以英法、德法之間的戰(zhàn)爭為背景,通過兩個不同的家庭視角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危害。
與宏大的主題敘事不同,社區(qū)活動教育主題系列電影從小處著眼,將一些社區(qū)事務(wù)和社區(qū)活動融入電影,揭示出青少年對自我表達、父母、伴侶以及同伴群體的需求。這類主題的電影主要有《寂寞芳心》和《死胡同》。其中,《寂寞芳心》中愛麗絲·亞當(dāng)斯表現(xiàn)出的善意謊言和虛飾行為,實際上表達了她對伴侶的需要以及對愛與被愛的渴望。《死胡同》的故事發(fā)生在紐約皇后區(qū)大橋附近的貧民窟中,講述了由湯米·戈登、迪皮、安吉爾、斯皮特等一群街頭頑童組成的“死胡同團體”,因為貧困、家庭破碎、父母忽視、政府冷漠和教育缺失等原因相繼走上犯罪之路的故事。這部影片特別提到一個場景:即便是殺死8個人的“惡棍”,最后仍希望回到他的前女友和母親身邊,期盼能夠從她們身上得到愛。因此,影片不僅從住房的視角揭示了貧富階層之間的差異與矛盾,更在深層次上揭示了父母對孩子信任與愛的缺失是導(dǎo)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所呈現(xiàn)的人際關(guān)系沖突背后,實際上是價值觀的沖突。“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試圖理解和改變?nèi)祟愃媾R的困難、問題和悲劇產(chǎn)生的原因?”[22]凱利赫認為,對原因的探求是具有理性的人應(yīng)該邁出的第一步,而下一步才是為消除這些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保持目標(biāo)的開放性,強調(diào)通過建構(gòu)的電影材料,引導(dǎo)學(xué)生對人類行為問題尤其是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理性思考,進而澄清學(xué)生的價值觀,學(xué)生觀看電影也被視為“思想的自由娛樂”(the free entertaining of ideas)[17]283。
(三)“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在富蘭克林高中的實踐? 本杰明·富蘭克林高中(Benjamin Franklin High School)創(chuàng)建于1934年,位于紐約市東哈萊姆區(qū)(Harlem),招收了來自該區(qū)34個種族背景的1 800名男性青年。校長倫納德·科維洛(Leonard Covello)是早年從意大利來到東哈萊姆區(qū)的移民。他認為,學(xué)校作為一所公共機構(gòu),應(yīng)該讓社區(qū)參與學(xué)生的教育,這也是學(xué)校開展第二代移民教育的基礎(chǔ)。“以社區(qū)為中心”的辦學(xué)定位,以及學(xué)生本身的多種族和移民背景,凸顯了跨文化教育和公民教育在這所學(xué)校的重要性。1936年,在富蘭克林高中正式開展“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實驗之前,科維洛校長就在高二年級的英語課堂上引入了電影欣賞。從1937年開始,富蘭克林高中在英語課、西班牙語課和社會類課程中開展了“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實驗,這不僅得益于凱利赫的推動,也與當(dāng)時國家開展跨文化教育的趨勢有關(guān)。凱利赫曾在1937—1939年對60所高中開展實驗的情況進行評估,在評估報告中她特別提到了富蘭克林高中的實驗。她指出:“我們?yōu)閷W(xué)校正在使用這些電影感到自豪……因為學(xué)生在討論中發(fā)展了對電影中所呈現(xiàn)社會問題的卓越洞察力。”[21]
1937年8月9日和10日,富蘭克林高中的亞伯拉罕·波內(nèi)曼(Abraham Poneman)老師和路易斯·雷林(Louis Relin)老師,分別在英語課上播放了電影《魔鬼是個娘娘腔》和《狂怒》。
學(xué)生觀看《魔鬼是個娘娘腔》電影片段后,波內(nèi)曼立即組織了有關(guān)這部電影內(nèi)容的討論。其中,有一場討論涉及違法犯罪行為和低收入階層的貧困問題。
學(xué)生討論小組組長:“為什么人們會犯罪?”
男孩1:……人們之所以會這樣(犯罪),是因為他們從小就認為,整個世界是斗爭的,是與他們?yōu)閿车模麄儽仨氁阅撤N方式斗爭。
男孩2:我相信他們[上一個男孩所指的人]是對的……在貧民窟里,人們很難在生活中和睦相處。你只有付出比在溫和環(huán)境中多出一倍的努力,才能擁有更多的東西,生活才會更容易一些。
男孩3:到12歲就要出去打工謀生。有時他必須為很少的薪酬而工作,即便是這樣,他仍覺得必須要為想得到的東西而不斷奮斗。[21]
東哈萊姆區(qū)是當(dāng)時紐約市最為貧窮的地區(qū)之一,基礎(chǔ)設(shè)施落后,就業(yè)機會奇缺。從小就在大城市里為生存而“奮斗”的特殊經(jīng)歷,使得學(xué)生們能夠以更加微妙的視角看待電影中因貧困和犯罪而帶來的各種棘手問題。
雷林老師是富蘭克林高中跨文化教育的積極倡導(dǎo)者。1937年8月10日,他在課堂上播放了電影《狂怒》中關(guān)于處以私刑的片段:
一個趕去結(jié)婚的青年喬·威爾遜在目的地附近因涉嫌綁架而被拘留。威爾遜參與綁架的故事被傳到附近小鎮(zhèn)并激起了大眾的憤怒,他們決定給這個“綁架者”以教訓(xùn),于是沖進監(jiān)獄。在行動受阻后,這些憤怒的居民放火燒毀了監(jiān)獄,監(jiān)獄中的威爾遜也因這場大火而殞命。但實際上,威爾遜在后來被證明并未參與綁架。之后,威爾遜的兄弟通過地方檢察機關(guān)起訴有罪的小鎮(zhèn)居民,但地方檢察機關(guān)與小鎮(zhèn)居民串通一致,認為小鎮(zhèn)居民沒有參與監(jiān)獄起火事件。在威爾遜兄弟堅持不懈的調(diào)查之下,22名小鎮(zhèn)居民被帶到法庭受審,即便法官能夠通過當(dāng)時的新聞圖片確定這22名小鎮(zhèn)居民就是監(jiān)獄放火者,但居民的辯護律師卻堅持認為威爾遜當(dāng)時根本就不在監(jiān)獄之中。直到這22名受審者中的一名女性,聽聞威爾遜未婚妻的痛苦遭遇后才承認小鎮(zhèn)居民所犯的罪行。
這部影片從《暴民統(tǒng)治》的故事改編而來,展現(xiàn)了個人信仰和內(nèi)在善良被腐敗的制度、暴力的統(tǒng)治所踐踏的無奈,美國境內(nèi)的非裔美國人所遭受的種族暴力,以及官方在這場暴力中相互勾結(jié)的現(xiàn)狀。觀看影片后,學(xué)生們開展了一場關(guān)于私刑起因的討論。有學(xué)生指責(zé)這部影片并未突出種族背景,另一名學(xué)生則堅稱“每個人都知道這部電影在說什么”。其中一名學(xué)生為小鎮(zhèn)居民維護社會治安的行為進行辯護,指責(zé)政府未能將真正的罪犯繩之以法;另一名學(xué)生則認為,地方政府應(yīng)該推動將私刑定為聯(lián)邦罪行,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控制私刑犯罪。
學(xué)生對電影《狂怒》的反應(yīng)表明,富蘭克林高中的課堂教學(xué)并沒有回避學(xué)生所處時代的緊要乃至具有創(chuàng)傷性的社會問題,而是以電影的形式呈現(xiàn)社會問題,并引發(fā)他們的爭議與討論。針對《狂怒》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學(xué)生們也并沒有草率地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而是試圖去理解社會問題的復(fù)雜性。實際上,將電影融入課程的方式為富蘭克林的學(xué)生提供了一個機會,即能夠就當(dāng)前社會問題發(fā)出個體公民的聲音[23]。通過這種方式,高中生將個人經(jīng)歷與更廣泛的社會發(fā)展及當(dāng)時的社會文化相聯(lián)系,凱利赫關(guān)于電影社會價值的信念在富蘭克林的高中課堂上得到彰顯。
三、“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的意義? 20世紀40年代初,由于洛克菲勒基金會撤回對普通教育項目的主要資助,“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也隨之停止。但在凱利赫的參與下,1937年,名為“教學(xué)電影保管者”(Teaching Film Custodians)的組織得以建立。在1954年的電影保管目錄中,可以查詢到“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的片段。20世紀四五十年代,人際關(guān)系系列的部分電影也仍然在一些學(xué)校如富蘭克林高中被用于開展跨文化教育。
作為“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項實驗,“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及凱利赫等進步主義者對“大蕭條”所帶來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問題的反應(yīng),是對青少年群體予以特別關(guān)注的結(jié)果,更是進步主義教育由對“社會中上層兒童”群體的關(guān)注轉(zhuǎn)向?qū)Α吧鐣邢聦忧嗌倌辍比后w關(guān)注的體現(xiàn)。1932年,康茨在《進步主義教育敢于進步嗎?》的演講中指出:“進步主義教育要真正是進步的,它就必須從這個階層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勇敢和果斷地面對一切社會問題,逐步應(yīng)付嚴酷的生活現(xiàn)實,與社會建立一種有機的聯(lián)系,發(fā)展一種現(xiàn)實的和可以理解的福利理論,形成一種關(guān)于人類命運的富于挑戰(zhàn)和咄咄逼人的觀點。”[1]160“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表現(xiàn)出了進步性。它將關(guān)注點聚焦于受經(jīng)濟危機影響最大的青少年群體,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青少年群體,以電影的形式直接呈現(xiàn)由種族歧視和貧困所引起的違法犯罪及政府私刑等棘手的社會問題,就“進步主義教育運動”而言,是具有轉(zhuǎn)折意義和創(chuàng)新意義的。
“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實際是一場中學(xué)課程改革實驗:從教學(xué)形式而言,利用電影這一新興媒介引入社會問題的故事和場景,引起學(xué)生討論進而發(fā)展學(xué)生理性的方式,比傳統(tǒng)課堂教學(xué)模式更能激發(fā)學(xué)生興趣。從教學(xué)資料與內(nèi)容而言,項目所選擇的電影揭示了社會變革背景下青少年的新需求;電影對復(fù)雜社會問題的呈現(xiàn),揭露了個人力量的局限性以及過分強調(diào)自我的危害性;電影接近社會底層的意識,有助于引導(dǎo)學(xué)生對公共福祉的關(guān)注,以及培養(yǎng)增進公共福祉所需要的團結(jié)、合作等集體主義品質(zhì)。總之,電影建構(gòu)了一個讓青少年直面與討論社會問題的“安全環(huán)境”,在最大程度上實踐著“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從課程職能而言,“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不僅引發(fā)學(xué)生對人與人、人與人群之間關(guān)系的討論與思考,還注重引導(dǎo)學(xué)生在社會實踐中運用這些思考,并努力解決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際關(guān)系問題。例如,學(xué)生在觀看電影之后成立“歡迎委員會”,開展社區(qū)住房情況調(diào)查,設(shè)計公共住房建筑模型等。這些舉措表明,“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不僅擴展了課程職能,更是對“學(xué)校應(yīng)當(dāng)努力成為民主的范例”[1]162的具體實踐。
此外,就“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本身而言,其眼光是非常獨到的。這種“獨到”的眼光與人際關(guān)系委員會開展的相關(guān)研究密不可分。社會實際上就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而當(dāng)時成千上萬的青少年作為“大蕭條的流浪者”[1]150,正在破壞著社會秩序。“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從社會的本質(zhì)出發(fā),直接指向社會面臨的最嚴重的青少年人際關(guān)系問題,體現(xiàn)了以凱利赫等為代表的項目發(fā)起者對社會內(nèi)涵的科學(xué)把握,以及對青少年群體的獨特關(guān)懷。從這個意義而言,“人際關(guān)系系列電影”項目是“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中一項頗具代表性的實驗。
參考文獻:
[1] 張斌賢.社會轉(zhuǎn)型與教育變革——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張斌賢.“世紀難題”:什么是進步主義教育[J].教育研究,2020(1):61-74.
[3]張斌賢.超越“克雷明”定義:重新理解進步主義教育的出發(fā)點[J].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18(4):17-28.
[4]陳露茜.美國進步主義教育的基本邏輯及其歷史變遷[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18(7):87-91.
[5]張斌賢.話語的競爭:進步主義教育協(xié)會史[J].高等教育研究,2014(2):70-83.
[6]張斌賢,錢曉菲.杜威與進步主義教育的關(guān)系:一樁懸而未決的“公案”[J].教育研究,2021(6):70-81.
[7]涂詩萬.“兒童中心”與“社會改造”的抉擇——克伯屈教育思想新論[J].教育研究,2018(7):135-145.
[8]張斌賢,錢曉菲.約翰遜:被進步主義教育埋沒的進步主義教育家[J].教育學(xué)報,2016(5):106-115.
[9]涂詩萬.進步主義教育家中的保守主義者:重新認識康茨[J].教育研究,2020(6):55-63.
[10]張斌賢.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概念及歷史發(fā)展[J].教育研究,1995(7):25-30.
[11]楊捷.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八年研究”述評[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06(3):171-175.
[12]吳嬋.進步主義教育的標(biāo)兵:帕克學(xué)校[J].教育科學(xué)研究,2016(4):70-78.
[13]楊帆.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開端:庫克實習(xí)學(xué)校實驗[J].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18(3):76-83.
[14]MAY M A.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of Motion Picture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1937,11(3):149-160.
[15]E.M.羅杰斯.傳播學(xué)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M].殷曉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193.
[16]KRIDEL C.Examining the Educational Film Work of Alice Keliher and the 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 and Mark A.May and the Secrets of Success Program[R].New York: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Publications Research Reports,2010.
[17]ORGERON D,ORGERON M,STREIBLE D.Learning with the Lights off:Educational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8]KRIDEL C,BULLOUGH R V JR.Stories of the Eight-Year Study:Reexamin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M].Washingt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101.
[19]GREEN A.Rockefellers Grant Still Another MYM69,000 for Classroom Films[J].Variety,1938,130(8):4.
[20]AITKEN R.“An Instrument for Reaching Into Experience”:Progressive Film at the Rockefeller Boards,1934—1945[J].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2017,30(2):284-314.
[21]RABIN L M.The Social Uses of Classroom Cinema:A History of the Human Relations Film Series at Benjamin Franklin High School in East Harlem,New York City,1936—1955[J].The Velvet Light Trap,2013 (72):58-71.
[22]Commission on Human Relations.The 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M].New York: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1939:11.
[23]ACLAND C.Useful Cinema[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377-396.
Abstract:The "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 program was an experiment in curriculum reform during American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in the 1930s. By presenting the edited film clips during the middle school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ers could stimulate teenagers to discuss and think about the behavior and its motives of people in the film, and then help them to illuminate their values. Although the program didn't last long, it had provided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eenagers to face up to and discuss social issues, and also highlighted the vitality and value of films as a kind of teaching media. As far as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is concerned, the "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 program is a manifestation of giv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eenagers, especially the ones from middle and lower class, and the resul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about social issues of progressive educators represented by Kelliher. In this sense, the "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 program is quite creative for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Key words:"Human Relations Series of Films"; educational film;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youth; curriculum reform experiment
(責(zé)任編輯:楊 波 鐘昭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