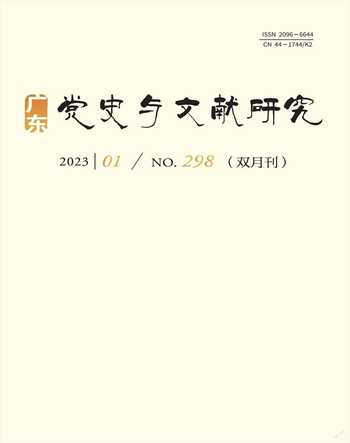改革開放口述史研究之省思
現(xiàn)代口述史學不同于中國古已有之的“采風”,有其自身規(guī)范章則,屬于史學重要分支。一般意義而言,現(xiàn)代口述史的起源往往可追溯至美國學者阿蘭·內(nèi)文斯,以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創(chuàng)建口述歷史研究室。20世紀80年代現(xiàn)代口述史傳入中國,歷經(jīng)數(shù)十年發(fā)展,就目前形勢而言,正處方興未艾之勢。雖然現(xiàn)代口述史在中國的傳播與發(fā)展未與改革開放嚴密同步,但其與改革開放的深化存有顯著共時性。現(xiàn)代口述史學不僅能給集體記憶的建構(gòu)提供資源,而且能創(chuàng)新歷史書寫的思維模式。改革開放史與口述史結(jié)合之改革開放口述史的實踐成果也頗為豐富,其中不乏優(yōu)秀之作。改革開放史除需要利用檔案、報刊、日記等傳統(tǒng)史料外,也宜利用口述史料更好地還原改革開放過程中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維面相,進而深化相關(guān)研究。當代中國口述史學發(fā)展至今僅30余年,改革開放史的勃興也屬晚近之事,二者本有諸多關(guān)聯(lián),在豐富的改革開放口述史實踐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行理論總結(jié)顯得相當必要。
一、研究現(xiàn)狀
改革開放史研究與其他時段的歷史研究相較,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即屬于進行時。這使其研究具有較強的現(xiàn)時性特點,不難看出,諸多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成果,在特定意義上都有“口述史”的特點,因研究者既是改革開放的研究者,又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正因這兩重身份,使改革開放史研究有了更多的“敘事”色彩。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推行至今已有40余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可以說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發(fā)展與推進,改革開放史研究也不斷豐富和深入。改革開放史理應受到重視,但某些研究者秉持“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原則,長期以來改革開放史研究略顯薄弱。所幸近年來改革開放作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guān)鍵抉擇,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guān)注。改革開放日益深化的同時,從歷史維度進行探討并予以現(xiàn)實關(guān)照的著述逐漸增多。
較有代表者如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著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百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新時期)》、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編著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李正華撰寫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起步》、田曾佩主編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以及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廣東改革開放發(fā)展史(1978—2018)》等。縱覽這些著述的參考文獻和資料選集,多為領(lǐng)導人文選、黨政報告、報刊文章以及國史基本史料,包括《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其中尚未見口述史料的大量采用和深度解析。
據(jù)研究者統(tǒng)計,到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時,改革開放史研究出現(xiàn)了顯著高潮。其中,著作超過800種,論文超過3萬篇,這些著述包羅萬象,涵蓋改革開放方方面面,雖然經(jīng)濟體制改革依舊是重要內(nèi)容,但民主政治、法律建設(shè)、科教文衛(wèi)、思想演進、社會變遷等方面皆有研究成果出現(xiàn)。可見,改革開放史研究已經(jīng)有了極大發(fā)展和推進,而這些與改革開放實踐的深化關(guān)系密切。
改革開放史研究著述中有一個典型特色,即各種回憶錄、口述實錄、親歷記紛紛出版發(fā)行,這些從大的范圍而言皆可歸入“口述資料”。改革開放口述史異彩紛呈,亦證實改革開放史的不少研究者本身即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歐陽淞、高永中主編的《改革開放口述史》,精選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決策和重大事件,訪談萬里、谷牧、陳錦華等老領(lǐng)導人,用口述史的形式呈現(xiàn)改革開放諸多重大決策出臺的過程,通過親歷者說話或更具權(quán)威性。曲青山、吳德剛主編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史》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口述史”書系之一種,訪談了胡福明、袁寶華、王夢奎等當事人,回顧改革開放進程中重大事件的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這些口述史訪談豐富了世人對改革開放的認知,使諸多歷史真相呈現(xiàn)于世。不少改革開放時代領(lǐng)導人的訪談錄、回憶錄等也有出版,不僅使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有了較清晰的面目,同時也豐富了原國家領(lǐng)導人的日常生活場景。如《信心與希望:溫家寶總理訪談實錄》《溫家寶地質(zhì)筆記》《李鵬回憶錄(1928—1983)》《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等諸多原國家領(lǐng)導人的“口述資料”,極大豐富了國家層面改革開放史的研究。
此外,諸多地方性改革開放口述史著述紛紛出版,使地方改革開放進程與細節(jié)更為清晰。如今改革開放口述史編寫隊伍呈多元化趨勢,已取得斐然可觀的成績,特別是深圳、汕頭、珠海、上海、小崗村等一批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的口述資料整理成果頗豐。如《深圳口述史(1992—2002)》(上、中、下卷),《口述深圳:一位農(nóng)民建筑工的城市夢想》,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廣東改革開放決策者訪談錄》、《廣東改革開放決策者訪談錄》(第二輯),廣東省檔案館編著的《廣東改革開放先行者口述實錄》,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與上海市現(xiàn)代上海研究中心編著的《口述上海——改革創(chuàng)新(1992—2002)》,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安徽農(nóng)村改革口述史》。其他還有如曲青山、吳德剛主編的《改革開放口述史(地方卷)》,以及不勝枚舉的各地改革開放口述史,諸如曲青山主編的“改革開放口述史叢書”,有廣東、陜西、安徽、重慶、山西等地方卷。“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也出版有嘉定、金山、奉賢、上海、普陀、青浦等各卷。這些口述史成果不僅紀念和講述著改革開放歷史,而且為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歷史經(jīng)驗。
二、研究特點
改革開放口述史作為改革開放史研究中的一道亮麗風景,具有以下三個方面顯著特點。
第一,改革開放口述史具有相當強的可讀性。諸多口述訪談材料往往能提供更鮮活的事件細節(jié),改革開放口述史作為其中一種自然也不例外。正因強調(diào)事實,也使其更具可讀性。如作為工作人員親身經(jīng)歷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陳開枝,講述廣州改革開放之初遭受的爭議:“改革從一開始,就存在很大爭議,包括在高層。當中央同意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試辦經(jīng)濟特區(qū)時,中央有關(guān)機構(gòu)搞了一個文件,叫《舊中國租界的由來》,這是警告你,特區(qū)可能變成租界。主要的爭議就在于廣東是否‘變天了,成資本主義了。就在這種爭議聲中,廣東的改革開放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陳開枝生動地描繪出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激烈的思想碰撞。黎子流回憶當年廣州建地鐵時所面臨的諸種困難,包括如何解決資金不足、缺乏在南方建設(shè)地鐵的相關(guān)技術(shù)和經(jīng)驗、拆遷量很大等問題。他正是在應對這些困難的基礎(chǔ)上,力排眾議積極處理,才使廣州地鐵建設(shè)順利進行。這些口述訪談如講故事般娓娓道來,其中牽涉多方矛盾,具體情節(jié)生動頗有吸引力。
第二,改革開放口述史具有相當強的史料性。《安徽改革開放口述史》主要反映改革開放40年來安徽黨組織帶領(lǐng)廣大人民群眾推進農(nóng)業(yè)建設(shè)的歷程,從側(cè)面突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對于研究中國農(nóng)村改革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如在滁縣地委工作的王郁昭回憶包產(chǎn)到戶、包干到戶的前前后后,其回憶使人們更深刻了解了安徽農(nóng)業(yè)改革背景和經(jīng)過,更清晰認識全國關(guān)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如何推動安徽農(nóng)業(yè)改革,為研究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提供豐富史料。《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史》口述采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之一的胡福明、“包產(chǎn)到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nóng)戶帶頭人嚴俊昌、堅持廣州率先放開菜價的朱森林等改革開放初期的探索者、親歷者,還原波瀾壯闊洪流中真實鮮活的細節(jié),為研究改革開放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第三,改革開放口述史具有相當強的思想性。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改革開放出現(xiàn)在生活各方面,影響了整個國家和民族。改革開放親歷者的口述采訪搜集他們關(guān)于改革開放的記憶,總結(jié)改革開放40多年歷史經(jīng)驗,不斷豐富改革開放歷史大進程中發(fā)展的民族精神及其內(nèi)涵,有助于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改革創(chuàng)新教育。《親歷改革開放:廣州改革開放30年口述史》采訪近百位廣州改革開放親歷者、見證者,講述他們在廣州改革開放中的所作所為、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使人們更深刻認識廣州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推進。如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的梁靈光講述其在接替楊尚昆前往廣州開展工作時,中央領(lǐng)導人與他談話的經(jīng)歷。這段經(jīng)歷也讓人們了解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探索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
改革開放口述史不僅具有記錄史實、豐富史料的作用,而且在引領(lǐng)思想政治、凝聚民族精神、堅定人民信仰方面亦具有重要作用。記錄和回顧重大事件既能總結(jié)改革開放歷史經(jīng)驗,也能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提供寶貴素材,其鮮活性、生動性是其他歷史素材與記述難以比擬的。
三、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口述史在短短時間里取得如此多成果,既與口述史隊伍的發(fā)展壯大有關(guān),也與改革開放史本身的特點有關(guān)。毫不夸張地說,改革開放口述史與其他重大事件的口述史相比,具有天然的便利性,具有獨特的研究意義。
第一,改革開放口述史能發(fā)揮資政育人的功能。資政育人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功能,常言道“讀史使人明智”,而改革開放口述史因其現(xiàn)時性更是如此。改革開放史研究有別于其他時段的史學研究,與時政關(guān)聯(lián)頗為密切。優(yōu)秀而成功的改革開放史著述既要有可讀性、理論性,還應有資政性,即必須凸顯改革開放史資政育人的功效,而改革開放口述史能較好地實現(xiàn)該功能。因改革開放口述采訪對象多選取某些精英人士或領(lǐng)導人或企業(yè)家進行個人回顧和工作總結(jié)。改革開放正處進行時,不僅僅具有歷史性,更具資政屬性,因而鑒往啟今知來的功用明顯強于其他時期的史學研究。改革開放口述史包括有各省各地領(lǐng)導人、企業(yè)家的所作所為,也有文化名人的所見所聞,還有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想。有研究者稱,相較于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歷史研究關(guān)鍵是要進一步增強解釋力,說清楚這些巨大成就背后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故改革開放口述史研究要從有利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研究一些問題,以史為鑒提出解決之道,更好發(fā)揮資政育人功能。改革開放口述史應該起到保存歷史與面向未來的雙重功用。
第二,改革開放口述史能革新研究范式。改革開放口述史體現(xiàn)出研究范式的革新。某些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權(quán)威著述所用史料多為領(lǐng)導人文選、黨政報告、報刊文章以及國史基本史料,屬于“信得過”的資料;當前還出現(xiàn)利用親歷者口述,從新視角審視改革開放的著述,即“改革開放口述史”,但被質(zhì)疑能否稱為“信史”。某些改革開放口述史的編著者認為并非“修史”,而是通過有限報道“為中國未來改革者壯行助威,為下一個30年前行提供點滴啟示”。但似乎不必糾結(jié)于此,未來的改革開放口述史在審視改革開放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把握未來發(fā)展脈絡(luò),為深入研究改革開放史提供基本資料,并有革新改革開放史研究范式的可能。親歷者通過詮釋所經(jīng)歷事件的深層背景,能彌補官方文件記載的不足;親歷者的敘述也可弘揚解放思想、敢為人先的改革開放精神。改革開放口述史是改革開放史與口述史交叉發(fā)展的結(jié)果,它與傳統(tǒng)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既應保持各自特色,也應互學互鑒。改革開放口述史可以在尊重受訪者意愿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其他史料進行潤色修改,而非原原本本地將錄音轉(zhuǎn)換成文字而成為簡單訪談錄,失去其應有意義與價值。傳統(tǒng)的改革開放史研究如能以時間、事件為線索,在考究求證基礎(chǔ)上恰當使用口述史料,必將大有裨益。
第三,改革開放口述史能拓展研究對象。改革開放口述史能察及傳統(tǒng)改革開放史研究向來不太為人關(guān)注的層面,特別值得注意者即改革開放口述史對社會底層的觀照,賦予改革開放史新的面相,進而深化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農(nóng)民、工人等普通群眾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要比精英階層少得多,以往口述史也較少關(guān)注他們的生活處境、思想情感。改革開放口述史應關(guān)注這些對象,讓農(nóng)民、工人等社會群體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聲音。普通民眾口述所形成的資料無疑將有利于進一步了解其心路歷程,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提供諸多觀測點,也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切入點。改革開放口述史不應忽視社會底層力量的發(fā)掘,通過口述史料的搜集更加深入地了解各階層群體的利益訴求和社會處境,在反思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的同時,找尋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發(fā)展道路。普通民眾也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及親歷者,他們的觀感理應受到社會的重視和歷史的尊重。社會底層群體的口述史為口述史理論應用于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即改革開放史在加強重大人物、重大事件研究的同時,也應觀照改革開放中的普通群眾及其心態(tài)心理變化,發(fā)掘社會底層的記憶。改革開放口述史應采訪各種人士,用以建設(shè)“全”改革開放口述史資料庫,在此基礎(chǔ)上將口述資料分門別類,進而形成各地各行各業(yè)的記憶庫,可擴大改革開放史研究主題,并深化研究內(nèi)容,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出謀劃策。
[郭輝,歷史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