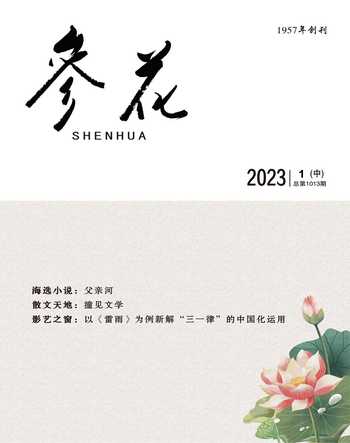解析《嘉莉妹妹》中的藝術手法
一、引言
德萊塞創作《嘉莉妹妹》時,美國正處于社會高速發展、工業文明不斷占據人們日常生活的時代。小說通過描寫女主人公的個人發展和對社會地位的不斷追求,揭露出當時的整體現狀。除了巧妙獨到的情節構思,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德萊塞對各種藝術手法的嫻熟運用也極具特色。不論是搖椅這一貫穿始終的意象,又或者是小說前后辛辣的對比和反諷,都值得人們深入探討和品味。本文旨在通過分析小說中的藝術手法,考察它在刻畫人物性格特征、成長經歷,以及主角之間人際關系的重要作用,從而加強對小說主題的理解。
二、象征手法
縱觀全文,德萊塞描寫搖椅的頻率非常高。搖椅不只是環境描寫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個意象,坐在上面的不同角色賦予了它不一樣的意義,其中,德萊塞對嘉莉和赫斯渥坐在搖椅上的描述最為豐富。作為使用搖椅次數最多的人,嘉莉在屋子里的描寫總是會伴隨著搖椅的出現。小說最開始,坐在搖椅上的嘉莉是貧窮的,她要寫信給杜洛埃,讓他不要來找她,因為她的自尊心不容許讓別人看見她住在這么寒酸的地方。這時,搖搖晃晃的搖椅正像嘉莉忐忑的心境一樣,一方面,她對這個城市抱有極大的幻想,希冀著過上富太太們珠光寶氣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為貧寒的現實生活而沮喪。很長一段時間,搖擺的搖椅象征著嘉莉時而充滿美好期望,時而又苦惱沮喪的糾結狀態。
而當嘉莉投靠杜洛埃后,嘉莉時常坐在搖椅上思考她的情感需求以及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比之前富裕的生活并沒有換來她的滿足,相反,她感覺到失落空虛,因而當比杜洛埃更顯體貼富有的赫斯渥出現時,嘉莉情感的天平逐漸偏向了赫斯渥。這時,不斷搖晃的搖椅象征著她和杜洛埃之間岌岌可危的關系,嘉莉即將拋下這些舊的生活與人物,轉而迎接生命中新的轉折。
在跟隨赫斯渥到紐約做家庭主婦的日子里,搖椅是嘉莉唯一的情感寄托,無人訴說時,她坐在上面回憶艾弗里會堂成功的表演,借此安慰自己不甘的心。同時,她又在搖椅上不斷構想著如何實現自己擠進上流社會的美夢,搖椅為她提供無盡的力量,供她一次次在殘酷的現實里頑強地生存下來,讓她一直保持著向上奮斗的野心與欲望。故事最后,看似已經實現所有美好夢想的嘉莉,依舊坐回了她的搖椅,這一次,她腦海里出現的不再是由各種奢侈品組成的美好生活,她開始幻想一種好像永遠都得不到的幸福。搖搖晃晃的搖椅意味著她的夢想永遠沒有盡頭,她終將不能實現夢中的幸福。
隨著故事展開,坐在搖椅上的常客又多了一個赫斯渥。與嘉莉逐漸向上的命運相反,赫斯渥的命運在紐約急轉直下,搖椅一直伴隨著他從上流社會淪落到中產階層,進而破產,走向自我墮落的道路。不同于嘉莉日漸豐富忙碌的工作生活,赫斯渥的生活軌跡越發狹窄,最后停留在了小小的搖椅上,他的心理活動全都表現在搖椅晃蕩的弧度里。德萊塞對赫斯渥破產后的描寫,常集中于他坐在搖椅上的時候,他喜歡坐在搖晃的搖椅上,攤開一張報紙,能從早看到晚。這樣無聊的日子,他卻覺得滿意舒適,究其緣由,是因為這時的搖椅不再只是一件家具,它成為赫斯渥用來緬懷美好過去、甩開殘酷現實的工具。起初,赫斯渥坐在搖椅上,只是為了短暫地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失敗,可就像沒有堅實底盤的搖椅一樣,赫斯渥的精神也不堅定,最后,在這種日復一日的搖晃中消失殆盡。之后他放任自己,漸漸沉迷于坐在搖椅中回憶在芝加哥的那種生活。這時的搖椅象征著他所追求的一切——體面的工作、優渥的生活、和睦的家庭,以及奮斗的欲望和野心都在搖晃中一點點消失,每當他認為可以追求到什么的時候,這一切就像搖椅搖晃一樣,又被晃走了。
從體面的經理到終日沉溺于躺在搖椅上看報紙的失敗者,赫斯渥可以說是那時人們的代表,他們習慣于由各種奢侈品、名譽、地位堆砌成的空虛生活,樂于在爾虞我詐、推杯換盞中尋找虛榮感,對自己的家庭卻缺少責任感,甚至為了一時的激情與欲望背叛家庭。搖椅的出現象征著嘉莉與赫斯渥“對于過好一點的日子的欲望毫不隱瞞——漂亮衣服、財富和社會地位”。[1]無論是貫穿始終的搖椅,又或者是諸如報紙、窗戶和鏡子等其他意象,都幫助德萊塞豐滿了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出兩個被欲望推著走的可憐人。
三、對比手法
作為藝術創作中常見的藝術手法,對比無聲無息地吸引著讀者的注意,讓事物在兩相對比中顯得更加鮮明起來。運用這種手法,有利于充分顯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征,加強文章的藝術效果和感染力。[2]文章的情節發展和嘉莉的成長隨著小說中無處不在的對比展開。作者正是通過嘉莉和赫斯渥完全顛倒的命運和地位,表現出命運無常的戲劇性。小說主要講述了嘉莉和赫斯渥的成長變化,同時,又不局限于這兩個人的對比中,嘉莉在遇見杜洛埃后的兩次交談,也是相當具有諷刺性的對比。
嘉莉和杜洛埃的第一次交談是在開向芝加哥的火車上。彼時,18歲的嘉莉還只是一個除了幻想,什么都不懂的鄉村姑娘,她只攜帶了一點行李,乘坐火車去投奔姐姐,前途未知。而與之相對的,無論是從搭話的技巧、體面的穿著,又或是紳士的舉止,都可以看出推銷員杜洛埃是一個有著一定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熱情浪漫的中產階層男人。很快,嘉莉便被這個和家鄉男性完全不一樣的人深深吸引。這是兩個背景相當懸殊的人物,可以對比兩人對話時的語言選擇,據此分析兩人此時的性格和所處的地位。在兩人的對話中,善于交際的杜洛埃一直把握著對話的節奏,他說話的次數遠高于嘉莉,并且不斷拋出話題。靦腆害羞的嘉莉則處于守勢,言談舉止都極為局促,在杜洛埃熱情而積極的攻勢中,才漸漸放下了防御和克制,開始和他交談并約定下次見面。如此可見,杜洛埃在兩人的談話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除了語句數量的對比,還可以對比兩人使用的句子種類。杜洛埃在對話中多采用問句,例如“你對這一帶地方不熟悉吧?”[3]這一問題可以很好地幫助一個人獲取對方的信息,提問的人通常在對話關系中扮演著更主動、更強勢的一方。相比之下,用簡短的陳述句回答問題的嘉莉,便一直處于被動的位置。在一問一答的情況下,意味著回答者嘉莉一直跟隨著杜洛埃的思路,處于被他牽制的狀態。當然,嘉莉在對話中也拋出了幾個諸如“啊,你真認識嗎”[4]這樣的疑問句,但這種疑問語氣通常意味著把話語權又重新交還給了對方,讓自己置于被動的聆聽者的位置。另外,在這場對話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洛埃多次使用了祈使語氣,“你一定要逛逛林肯公園”。[5]這是一種比較強勢的語氣,而嘉莉全程沒有使用過這樣的語氣。
告別杜洛埃的嘉莉,開始獨自在芝加哥找工作,屢屢碰壁后,在殘酷的現實和她日益膨脹的欲望中,她最終選擇投入杜洛埃的懷抱。可當她遇見赫斯渥后,她的眼界隨之開闊,心思也活絡起來,不再滿足于眼前的生活。她把赫斯渥當作進入上流社會的橄欖枝,因此,當杜洛埃把赫斯渥有家庭的事告訴嘉莉后,嘉莉一時無法接受美夢落空,而與杜洛埃爆發了爭吵。這時對比兩人爭吵中選擇的語句,可以發現兩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首先,嘉莉代替了杜洛埃,成為對話中一直掌控方向的那個人。她不斷地質問杜洛埃,給他施加壓力。從她密集的話語和咄咄逼人的語氣中,可以看出嘉莉開始學會反抗。其次,與之前的對話相比,嘉莉兩人都傾向于選擇各種具有情感色彩的詞語來表達自己,例如“現在,你卻鬼鬼祟祟地回來”,[6]激烈的語氣和強勢的表現,都反映出兩人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而德萊塞描寫嘉莉時也常使用“咬牙切齒,跺著腳,叫了起來”等非常具有情緒化的動作描寫,這和之前靦腆害羞的鄉村姑娘的形象完全不一樣,因為這個時期的嘉莉的心理已經逐漸成熟,敢于為自己發聲。可以看到,嘉莉的語言風格是符合她的成長變化的。同時,嘉莉常使用感嘆句,或者“呵,唉”等詞語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這也符合她作為女性角色的特點。最后,雖然杜洛埃也使用了一些問句和表示情感的詞匯,但他并不專注于在談話中壓過對方,他只是企圖保持自己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和地位,實際上并不想破壞兩人的關系,這符合杜洛埃畏手畏腳的個性特征。
總體而言,這是嘉莉在文中第一次用嚴厲的語氣來表達她的情緒并反抗加諸她身上的不公,相反,一直是花花公子形象的杜洛埃在對話中敗下陣來,試圖安撫嘉莉的情緒,穩固好兩人的關系。對比前后兩次交談,雙方語言選擇的變化反映出兩人身份地位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女主人公嘉莉的成長,在經受過經濟威脅以及心靈自由上的脅迫后,她逐漸成長為一個思想進步的新女性。
四、反諷手法
H·R·耀斯曾指出,“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諷性的作品。”[7]小說中反諷的運用不僅體現出嘉莉和赫斯渥命運變化的戲劇性,也明確地表達了德萊塞對物質、消費等的批判態度。該小說的反諷主要集中在情境反諷上。情景反諷一般用于表現小說人物的期望與實際情形的反差,作者用強大的命運操縱著角色離她的目標越來越遠,以達到一種徒勞無功的滑稽感,實現對人物的嘲諷。當嘉莉來到芝加哥之前,作者描述她為,“她正十八歲,伶俐,靦腆,滿懷著無知的年輕人的種種幻想”,[8]這時的嘉莉對大城市抱有許多期盼。在找工作之前,她以為這里遍地是機會。但當她真正去找工作時,才發現這個燈紅酒綠的城市早已把人劃分,像她這種既沒經驗,又比較挑剔的鄉村姑娘,最后的結果正如文中所寫,“這么嚴重的失敗,使她的精神頹喪不振”。[9]但即使嘉莉看清了這里虛偽的本質,她仍然沒有放棄她想要變得富貴的愿望,這種在姐姐看來不切實際的想法,以及看戲等奢侈的做派,都和古板守舊、生活拮據的姐姐一家形成了鮮明對比。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嘉莉對上流社會的積極追求和她的出身十分不符,她不具備任何吃苦耐勞的性格,卻慣于模仿富家小姐的身姿做派。最后走投無路的嘉莉在杜洛埃那里找到了喘息的機會,她一度待在杜洛埃為她購置的套房里做他的金絲雀,甚至于當她結識到更加富有的赫斯渥以后,她又把她的心交給了體貼的赫斯渥,甚至和他相伴去了紐約生活,她就這么一步一步,變得越來越富有。
而就當讀者們以為這樣愛慕虛名的嘉莉必然會落得一個不好的結果時,因為她所具有的特質與傳統道德觀念是如此相悖。德萊塞為情節的戲劇化發展帶來了一個新的轉折,嘉莉“既沒有被餓死,也沒有失去美麗的容顏或者懷孕,她不像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或克蘭恩的《麥琪》中墮落的女主角那樣不得不死去”。[10]相反,在紐約這個具有魔力的城市里,嘉莉和赫斯渥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實在讓讀者倍感意外。嘉莉從一個鄉村姑娘變成了上流社會的一員。而曾經上流社會的代表——赫斯渥卻一跌再跌,直至落魄死去。曾經圍繞在他身邊的人竟沒有一個還能想起他,都只專注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情節的發展儼然與讀者的預期背道而馳。這樣顛倒的命運完全出人意料,但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赫斯渥畏手畏腳,和當時大膽追求享樂的潮流不一致,因此,他在這個充滿野心的地方里無法向前,必然會被拋棄。而當極度渴望物質財富的嘉莉熟悉了這里的本質后,她的價值取向逐漸被它同化,因此,她的蛻變是自然的結果。作者在小說中運用反諷手法,刻畫出兩位立體的人物以及他們被這個欲望環境推動著隨波逐流的命運。德萊塞正是借用對嘉莉和赫斯渥的對比與諷刺,將所有情節以及情感推至全文高潮,表現他對當時流行的消費風氣的批判。這樣辛辣又無處不在的諷刺,著實為主題的表達增色不少。
五、結語
《嘉莉妹妹》的成功,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德萊塞運用了精湛的藝術手法,真實再現了當時的現狀。小說圍繞嘉莉的成長展開,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嘉莉逐漸成熟的心態,都揭示出在繁華社會下糾結的人性,也展示出19世紀開始蘇醒的女性心理變化。嘉莉也不再只是小說中的角色,而是廣大普通群眾的代表,她的變化映射出普通人在那時所受的影響。作者對芝加哥和紐約這些大城市的描述,不再局限于珠光寶氣與生機勃勃的面貌,轉而揭露了它的本質。在德萊塞的筆下,嘉莉的成名和赫斯渥的落魄,印證了重視物質的風氣帶來的種種危機。
參考文獻:
[1]High,Peter B.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Longman Inc,1986:113.
[2]肖建云.麥克白悲劇之探究——淺析《麥克白》中對比手法的運用[J].語文建設,2014(32):55.
[3][4][5][6][8][9][美]德萊塞.嘉莉妹妹[M].裘柱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0;22;22;310;18;37.
[7][德]漢斯·羅伯特·耀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282.
[10]Cunliffe,Marcus.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M].Virginia:R.R.Donnelley&Sons Company, Harrisonbury, 1986:244.
(作者簡介:黃彬冰,女,碩士研究生在讀,黑龍江大學,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