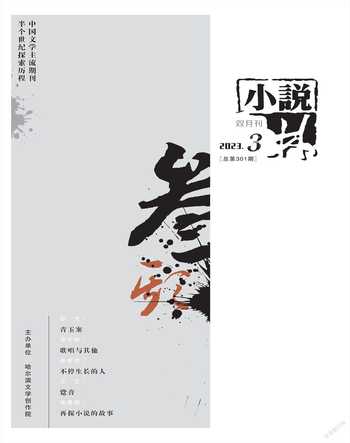師燈
司玉笙的微小說《師燈》,寫師生戀,很多人愿意往“刺激”的方向寫,本文不然,將種種純純的美好情感層層疊加,釀出純美、高尚的愛情,寄托在照亮黑夜,帶來光明和希望的“師燈”上。良頭喜歡向老師,并向老師明確地表白。但這份喜歡并不體現在瘋狂地追求,而是反映在從一個上課不學的搗亂分子,變成一個渴求知識的優(yōu)秀學生。向老師也漸漸愛上了這個學生,同樣不是體現在卿卿我我,而是反映在糾正愛人情書中的錯字,糾正愛人人生路上的偏離。作者已將這份愛寫得足夠動人,如果讀者能品出“恢復高考第二年,兩人雙雙接到錄取通知書”一句暗示的時代背景,則更能體會到教師的偉大,正如文中校長所說:“夜里有燈光的地方,往往會有老師;有老師的地方,往往有希望……”
微小說這種文體因其篇幅特點,標題往往即是作品主題所在,抑或是貫穿全文的線索,情節(jié)圍繞之迅速展開。本期于秋月的微小說,題目“三金加兩萬”,初讀,算是條線索;至于主題,頗難把握——作者難道就想說老王太太這人很有意思,寫她的幾件事?細細再品,發(fā)現“三金加兩萬”,實在不只是線索而已,更是主題的“提示”:老王太太初將心愿寄托在“三金加兩萬”上,與老王大哥散了,卻又后悔失去的生活;老王大哥為“三金加兩萬”立下寧可一個人過的誓言,卻苦苦承受著長長的孤單。究竟自己心愿為何?究竟生活想要怎樣?似乎沒人說得清。這份人性的復雜與無奈,被“三金加兩萬”從不同側面輕巧地、深深地點出。
初讀陳德鴻的《請戲》這篇微小說,會有種“小題大做”的感覺——無非是村里要請劇團來演幾出戲,卻上演一場“生死時刻”,被作者一番精彩描摹,可謂驚心動魄;最后身殘村長那句“我們村沒有白看戲的傳統(tǒng)”,又是何等義正詞嚴。作者這是采用后現代所謂戲仿的手法,要將某種價值加以解構嗎?細細再品,卻覺得恰恰相反——作者在努力構建一種價值:為了村民的利益,全力爭取,又分毫不讓;而對于施舍,卻絕不降格乞求。事情確實發(fā)生在小小的村子,施舍的也不過一場縣級劇團的演出,可那份為鄉(xiāng)鄰囑托全力以赴的責任心,靠自身努力而不接受施舍的原則性,讓人肅然起敬。
——特約欄目主持:袁炳發(fā)
向老師是這學校里最年輕的代課教師。她能來代課,實在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于是,經校長多方努力,高中畢業(yè)的她就來到這個中學頂崗,拿工分的那種。
那年代還沒有通電,這個偏僻的鄉(xiāng)村中學晚上最好的照明用具就是帶玻璃罩的煤油燈。
每到夜闌人靜時,向老師簡陋的寢室就會亮起一盞那樣的燈。如果門縫兒沒合嚴,可以看到她專注備課、改作業(yè)的神情。
這天夜里,聽到窗外有什么動靜,向老師便出門觀察。見一泓燈光外,立著個黑糊糊的身影,她就緊張起來,厲聲問,誰?
我。
你是誰?
良頭。
一聽是良頭,她就松了口氣。
初到,她就聽說班里有個學生中年齡最大的,坐在教室最后排,上課經常搗亂,還曾經把一位老師氣哭過。可年輕的她一站到講臺上,教室里立刻就安靜下來。特別是最后排的那個,向上杵著脖子,定定地向前看。如若前排有交頭接耳的,他就會一巴掌掃人家的后腦勺。這一掃,小動作就沒了。然后,他就認真地把眼光全都聚在向老師身上。
這學生并不是像人家說的那么皮呀?向老師心里納悶。待良頭出現在這暗夜中,便不由得又警覺起來。
這么晚你來干啥?
看你屋里亮著燈,想過來問一道題。
時候不早了,趕緊回家睡覺,作業(yè)明兒拿到課堂再問。
不問清楚俺睡不著。于是,身子就移到燈光里,接著尾隨進了室內。返身想掩門時卻被向老師喝住,別關門!
良頭掏出一本折頁的書,顫顫地問,這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啥意思?
啥意思,我也弄不懂。
老師,您是不想懂哩。良頭眼光亂掃,一只胳膊便架在桌子上,歪頭默默看燈。看著看著,鼻尖兒慢慢湊近那燈,身子卻像無意似的挨到向老師。向老師往旁邊挪挪。
這燈真好看,你也是——第一次聽你講課俺就給迷住了。良頭說。
你這個學生呀,人小鬼大,孬!向老師臉上現出慍怒。
俺人孬心不孬,喜歡就是喜歡。
你個子長成了,心還沒有,好好學習吧……
聽你的聽你的,向老師……
倆人的目光交織在一起,火辣辣的。
自這以后,有人看見良頭經常往向老師寢室跑,或在寢室外徘徊,站崗似的。打個煤油、取個書報啥的,也是他代勞,時不時地還在向老師那里吃飯。反映到校長那兒,校長說,夜里有燈光的地方,往往會有老師;有老師的地方,往往有希望……
恢復高考第二年,倆人雙雙接到錄取通知書,良頭是中等師范的,向老師是本科學院的。入校后,良頭給向老師寄去一封信,其中一句是,敬愛的向老師,就著那燈光,我想請你給我挑一輩子錯別字……
焦慮中等來了她的回信,其中一句是,那盞煤油燈我一直帶在身邊……
幾封書信來往之后,稱謂就有了變化。
畢業(yè)后,良頭回到鎮(zhèn)里的一個小學任教。晚他兩年畢業(yè)的向老師本可以留在省城,卻也回來了,在縣教育局任職。一年后倆人按當地風俗完婚。隨身帶來的嫁妝中,還有那盞煤油燈。莊里人都覺稀罕,將院里院外圍得水泄不通。一看,新娘正在廚房里忙活,無一不咂嘴兒。
婆婆過去奪過新娘手中的家什,嗔道,向老師,這來家頭一天咋能讓你下手?
媽,進了這個家門我就是您的孩子……
婆婆轉身出去,找到良頭,逮住就捶,你這孩子忒孬,娶了老師還讓老師當廚師!
媽,她是世上最好的廚師,不光爛葉子壞梗子她都能挑出來,還有我的錯別字……
母親住了手,念叨著什么,躲一邊顫肩喜泣。
校長也過來慶賀,調侃道,這學生攤上了一個好老師……
婚后,兩人育有一女。若干年后,出嫁后的女兒笑問,媽,當初我爸是怎樣把你給誆騙到手的?
那不是誆騙,是守護……
我看有老師娶學生的,可很少有學生娶老師的。
我給他挑出來不少錯別字,他改正了,那就是你爸……
如今,無論在什么場合下,從校長崗位上退休下來的良頭依舊喊愛妻為“向老師”,從未改口,盡管她僅比自己大三歲。夜靜時,倆人常在明亮的臺燈光下,一字一句地品讀那些保存完好的書信。讀到錯別字就笑。笑著笑著相擁淚下。
面前,還是那盞被擦得干干凈凈的煤油燈。
作者簡介:司玉笙,河南省小小說學會副會長。1978年開始發(fā)表作品,已出版?zhèn)€人專集九部。作品多次被《讀者》《小說月報》《作家文摘》《青年文摘》《小小說選刊》《微型小說選刊》和大學教材等選用。多篇作品被譯介至美國、加拿大、日本、東南亞諸國或改編成電視短劇。小小說代表作有:《書法家》《高等教育》《老師三題》《錯變》《不倒樹》《永遠的陽光》等。獲中國小小說金麻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