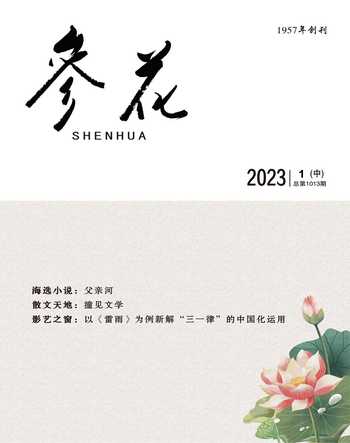生態美學視閾下李娟散文的意蘊探析
生態美學是一種極富生命力的理論,中國當代生態美學自1987年萌芽至今,堅持樹立“自然萬物的和諧協調發展”等三大美學理念,這不僅繼承了我國“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古典生態智慧,更是對我國傳統生態發展模式的反思。李娟的散文極具地域特色,通過描寫戈壁灘、荒野里的地窩子、逐水草而居的哈薩克牧民等意象,將北疆地區的人物風貌和自然風光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還表達了她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土地鹽堿化等問題的憂慮之情。其散文不僅展現出了原始詩性思維,更體現出“在蒼涼的生命境遇中,也仍然要熱愛生活”的樂觀、豁達的精神。
一、李娟散文中生態美學思想探源
李娟著有《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走夜路請放聲歌唱》《遙遠的向日葵地》、“《羊道》三部曲”等散文集。其中有許多對北疆阿勒泰地區生態風貌的描寫,作品中沒有華麗的辭藻,但質樸的語言卻流露出作者對生命和自然的感悟,引發讀者對邊疆地區人文景象的無盡遐想。這種獨特的生命體驗既來自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和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也是形成其生態美學思想的土壤。李娟幼時和母親一起在阿勒泰山區生活,有過和哈薩克牧民轉場的經歷,離開單位后再次回到草原,與哈薩克牧民在冬牧場一起生活。這種“四海為家”的獨特人生經歷使她與大地、草原,以及一直跟隨她“搬家”的小動物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一路上,她看到了萬畝葵花地在經歷大旱天氣和鵝喉羚的“襲擊”之后,終于“唱出金色的高音”;也目睹了“堅硬、發白的已經死去的土地”、荒涼的戈壁灘、密布在曠野中的干涸的河床。見過荒涼,才知繁盛尤為珍貴。她目睹了干旱給農民和土地帶來的傷痛,又深知對于那些世世代代以土地為生的人而言,一塊塊“死去的土地”意味著什么,這也引發了她對人與土地關系的思考。例如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她感嘆道:“就算是力量再單薄的土地,對生存于此的人們來說,也是足夠應對生存的。”在她所展示的粗糲如沙暴一般的影像中,流露出她所具有的強烈的生態意識,以及對這個地區生態問題的擔憂,可以說,她的生活經歷是其生態思維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
曾繁仁先生指出:“一定民族的哲學與美學是其特有的思維模式與民族精神的表現,是其特有的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的產物。”新疆的地理環境形成了此地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千百年來,游牧民逐水草而遷徙,這種文化中蘊含著我國古代“順應天命、不違農時”的樸素生態智慧。李娟在《冬牧場》中寫道:“從阿爾泰深山一直到天山北部的開闊地帶,牧人們每年遷徙距離逾千里。搬遷次數最多的,一年之中平均每四天就得搬一次家。”這種四海為家、居無定所的艱苦游牧生活,只是為了保護這片養育游牧民族的草原。這個民族完全依附著自然的恩惠繁衍生息,自然是他們的棲身之所,他們用最肥沃的養料回報自然母親。在沒有泥土、沒有樹、沒有石頭的冬牧場,李娟與牧民們一起搭地窩子,用羊糞砌墻,當春天來臨,牧民們離開時,這些羊糞就化作養分,滋潤這片養育了牛、羊、牧人的草原。李娟與哈薩克游牧民族生活在一起,這種異質性的生命體驗和游牧民族文化不僅影響了她的生活習慣,也引發了她對自然、對人生的無盡思索。因此,她的文字仿佛是對自然進行“復魅”,重新為自然披上圣潔的外衣,讓自然最大限度地保持其本身的神秘性。
二、李娟散文中蘊含的生態美學觀
李娟的生態美學觀主要體現在“美是走向荒野”“美是生命的和聲”“美是勞動帶來的生命健康”三個方面,不難發現,李娟所有的生態美學觀念均直指個體精神的滿足,也就是作為審美主體應該呈現的美感才是她想要在創作中進行描述的。
首先,“美是走向荒野”的生態美學觀與新疆北部地廣人稀、戈壁、荒野、深山廣布的獨特地理環境密不可分。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在《哲學走向荒野》一書中提出應該從實用價值和生命支撐價值兩個角度之外去理解自然的審美價值。他說:“要能感受到這種審美價值,很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將它與實用價值及生命支撐價值區分開,只有認識到這一區別,我們才能把沙漠與極地凍土帶也看作是有價值的。”在李娟筆下,荒野是人們寄居的場所,人煙稀少、植被稀疏的無庇荒野,像是毫無保留地對人們敞開了懷抱。人們在荒野上安家,動物們在荒野上奔跑,幾縷炊煙緩緩升起,這便是荒野上閃爍著的零星生機,除此之外,是無邊無際的寂靜,這種荒涼即便是經歷了一輩子風雨的外婆都難以接受。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李娟寫道:“她拄杖沿著地坑一側的通道艱難走上地面,轉身四望,快要哭了”“她九十多歲了,一生顛沛流離,數次白手起家,仍難以接受眼下的荒涼”。李娟筆下的荒野是荒涼的,更是純粹的,她看到的是荒野給予人們的力量。這一觀點突破了以往的審美價值判斷,并且告訴人們:在一望無際的曠野中,個體顯得尤為渺小,是無力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抗爭的,但是人們能在苦難和挫折中磨煉自己的意志,依靠智慧、辛勞和堅韌、毅力,頑強地生存下去,對自然萬物都保持著一種“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親和之情。這便是李娟書寫的“荒野哲學”。
其次,“美是生命的和聲”的生態美學觀實際上是對一切有生命之物在生物鏈中一種和諧共處狀態的歌頌。正如喬治·桑塔耶納所言:“美,是一個生命的和聲,是被感覺到和消溶到一個永生的形式下的意象。”在《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展現了秋日里河邊樹林的“一場演唱會”:河水經過盤根錯節的樹根,沖刷掉覆在根部的樹葉,仿佛是娓娓道來的敘事曲;原來在河邊洗衣服時那塊半露的大石頭,被拋到岸上,仿佛是奔放的狂想曲;水流經過傾斜的地勢,匯入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池塘,又像是三角鐵發出的顫音,這便是自然譜寫的生命之歌。《遙遠的向日葵地》中,一家人吃完晚飯去散步,這里所言的“一家人”,實際上包含了家里的雞、兔、貓、狗,“大部隊”就這樣浩浩蕩蕩地走在土路上,圓月當空,晚風徐徐,構成了一幅“人物風情兩相宜”的和諧美景圖。他們在荒涼的大地上彼此慰藉,互相陪伴,這也是人類與自然生態中所有生命的和弦、共振,共同吟唱出的優美和聲。
最后,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李娟塑造了黝黑的母親與壯碩的“大紅花”兩個典型的勞動者形象,其中隱含著“美是勞動帶來的生命健康”的生態美學觀。她在回憶自己的母親時說道:“她終日鋤草、間苗、打杈、噴藥,無比耐心。”于是在太陽日復一日地曬烤下,母親的皮膚變得黝黑,擁有了自然賦予她的顏色。災年時,母親的向日葵地被鵝喉羚給“偷襲”了,種一茬被啃光一茬,很多人放棄了這塊地,選擇離開,而母親卻前后播種了四遍,她帶著鐵锨雄赳赳地走在地里,在李娟心中,此時的母親仿佛是頭戴王冠、手拿權杖的女王。自然磨煉了母親的意志,使她擁有了如此驚人的精力和耐力,永遠充滿昂揚的激情和生命力。“大紅花”是一個哈薩克婦人,她“花白頭發,大嗓門,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往那兒一站,中流砥柱般穩穩當當,雷霆不能撼之”。正是得益于這樣一個壯碩的身體,其干活時所向披靡,效率極高。健康且有力量的身體、遇到困難從不輕易放棄的頑強意志力,便是大自然對她們勤懇勞作的饋贈,她們是美的,這種“美”是一種最自然、最本真的美,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美是一種因辛勤勞動而帶來的身強力壯,精力充沛,面色紅潤的生命健康”。母親和“大紅花”由內而外散發著的原始生命力,是她們經過日復一日的勞動積淀下來的,而支撐她們的,是對腳下那片大地的無盡信賴,她們從自然中汲取生機,又播撒下希望的種子,回報大地。
三、李娟散文中的生態審美價值
生態美學不僅注重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問題,更是對人類精神生態困境的一種關照。李娟的散文為人們提供了“像山那樣思考”的生態思維和“生態審美”的生存方式,以至于當代人可以找尋自己“詩意棲居”的道路。“像山那樣思考”意味著要像山一樣對待山中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動植物和土壤。也就是說,人不應將自己的主觀想法強加在自然身上,應該感知自然界。李娟的散文中就體現著“像山那樣思考”的生態智慧,例如,戈壁玉在純粹的藍天的庇護下是美麗的,離開了這里,它的美麗便迅速枯萎;大地最雄渾的力量是萬物的生長,每一株葵花都吸吮著地底深處的根系。她認為,人不應該想方設法地改變自然規律,而是要順應自然規律,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生物鏈環的平衡。因此,召喚當代人“像山那樣思考”,培養當代人“和而不同”的思維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只有與自然中的一切處于和諧狀態時,人們才能擁有“深層意義”上的生態審美態度以及生態審美的生存方式。無論是向日葵地,還是戈壁灘、蒙古包、地窩子,作者都看到了“最大限度的美”,這種美不僅是向日葵地的金光閃閃,蒙古包在大地上凸起的線條,更是這片土地上一切生物頑強生長的生命力之美,具有崇高的生命價值。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作者提到很多人去戈壁灘撿玉石,戈壁玉需要經過常年的外力作用才能形成,作者描述了玉石被挖開后的場面:“露出身下和自己同樣形狀的洞窟。看到蟲子四散奔逃,植物白嫩的根系坦曝在日光暴曬之中”。尊重自然意味著人們對自然應該懷有敬畏之心。此外,海德格爾在《荷爾德林詩的闡釋》一書中說道,“一切勞作和活動,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終只是并且永遠就是一種棲居的結果。這種棲居卻是詩意的。”北疆的戈壁沙漠環境相對惡劣,但是在李娟的文字中,人們看到的是真正的、和大地有關的生活:荒野無私地給予人類精神上的療愈,游牧民逐水而居,他們都與自然融為一體,在自然中,他們從“遮蔽”走向“澄明”,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荒野中人與人的關系是親密的,當途經游牧民族的蒙古包時,他們便會拿出發酵好的純手工酸奶和奶疙瘩來招待你,從未謀面的人會在這里圍成圈、跳支舞,寒暄也充滿溫情。作者所描述的城市中的生活與“真正的與大地有關的生活”的不同狀態啟示人們去尋找在城市中“詩意棲居”的道路,這也是當代城市生態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慢速美學和生態美學的發展,以及哲學的“荒野轉向”或許為人們提供了“詩意棲居”與“精神返鄉”的可能性。
四、結語
李娟的散文猶如一段年代久遠的錄像,為人們呈現了遼闊邊疆中那一片罕為人知的土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用他們的生態智慧告訴人們:究竟應該以什么方式存在于自然之中。首先,人們應該摒棄主體與客體的認識論模式,只有從根本上突破主客二分的對立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才可能和諧統一。其次,作品中對游牧生活的回憶,也傳達出不同于現代城市中“物盡其用”的生活方式,出于對水資源和草場的可持續使用的考慮,牧民們通常會“逐水草遷移”和“輪耕輪牧”,這樣的生活方式恰如美國生態理論家大衛·雷·格里芬所說:“我們必須輕輕地走過這個世界,僅僅使用我們必須使用的東西,為我們的鄰居和后代保持生態的平衡……”這對于當代城市的生態文明建設給予了一種啟示:應該著力培育人們的生態審美觀,使人們具有一種自覺性,為自然、為自己、為后代留有余地,在那一方天地之中,所有生物都能夠和諧相處,從而詩意棲居。
參考文獻:
[1]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
[2]曾繁仁.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李娟.冬牧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4]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5]朱立元,主編.現代西方美學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221.
[6][德]海德格爾,著.荷爾德林詩的闡釋[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7][美]大衛·雷·格里芬,編.后現代精神[M].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夏文清,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方向:大眾文化研究)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