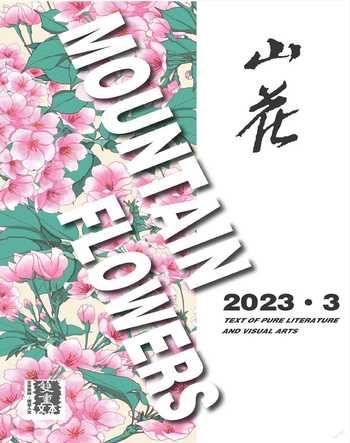消失
劉軼凡
說起來,第一次見到邱,是在幾個月前的一場冥想訓練上。當時,我從印度西北小鎮出發,沿著彎彎繞繞的山路步行了半小時,才找到Yoga House的標志牌,又走十多分鐘山路,兩邊茂密地生長著灌木。眼前視野很窄,很長的時間里,我懷疑是不是走錯了路線,直到看到一棟紅磚砌成的二層小樓,孤零零地立在路盡頭,外墻簡陋,樓梯沒有護欄,就這樣裸露著。
樓下有片空地,清掃得算是干凈。已經來了四五個西方人,都雙腿盤在坐墊上。冥想半小時前就開始了,我在角落坐下,閉起眼,試圖調節呼吸,但是沒辦法靜心,腦子里念頭雜亂,找不到起點。我集中注意力,強迫自己想昨天清晨看到的一只黑色大鳥,讓思路跟著黑鳥的雙翼在藍色幕布上滑行,雙目合上時,眼前是一片朦朧的昏黃色,黑鳥沉重的身體起先緩慢,忽又變得輕盈。過了一會,我半睡半醒,睜開眼睛,看著身邊坐著的白人中年女性,紅色長裙,臉上滿是雀斑,鼻尖微微滲出汗珠,我好奇她結婚沒,如果有的話孩子多大,為什么會單身來這里。
從小鎮上出發前,我收到了妻子的信息,她沒發文字,只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有著兩道鮮紅印跡的驗孕棒,另一張是醫院的檢查報告,能記住的只有“孕囊內胎芽已見”這幾個字。
就是無聲的譴責,對吧。我手指按在手機屏幕上又收回,沒回復。現在,我想到這事,就沒法入定了,干脆不出一聲,直到大家陸續站起,冥想差不多結束了。
空氣又活躍起來,我接過一個大胡子德國人遞來的手卷煙。他報了名字,很拗口,我沒記住,但對他似曾相識——這個德國人長得像哪個演員?還是說這些有著寬大身軀,消瘦臉頰的西方人留起胡子來都一模一樣?之前在伊朗旅行,就碰到過一個長相類似的德國人,我墊付了包車費用后,他沒打招呼就離開了。我接著向下聯想,直到被一個東方面孔走過來打斷,他大大咧咧坐在我身邊,在場有兩個東方人了。他梳著黑人臟辮,穿著當地樣式的寬大衣服,斜挎著牛皮腰鼓。幾個月后,我在瓦拉納西的河邊再見到他時,他依然是這個裝扮,只不過臟辮換成了板寸頭,腰鼓仍然斜挎著,像是長在身上的槲寄生。日光正傾瀉下來,他打了個招呼,懶洋洋地從我手里拿過煙頭,狠吸一口,我有點心疼,像是受驚的幼犬一樣,手以問詢的姿勢伸了出來,動物表達友好的方式,我們互報了姓名。
你來這多久了,以前怎么沒見過你?邱問。
半個月吧,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冥想。我回答。
不是說冥想,鎮子這么小,沒見過你。
我在這邊做志愿者,污水凈化,平時沒怎么在鎮上逛,一般晚上吃完飯就回了。
邱不置可否地笑笑說,挺好。
你呢,感覺你在這挺久了。我禮貌地問。
是非常久,比你時間長得多。邱眼神亮了一下,回答。
接著,邱開始談論印度。他思維很跳躍,從飲食衛生講到種姓制度,我接不上話,最后他說自己常住瓦拉納西,偶爾來山里轉轉,過幾天就回。
你去過那里沒有?邱問。
沒有,但肯定得去,哪有來了印度不去恒河的。我想起遠藤周作,他在恒河轉了一圈,寫了《深河》,最后放在自己的棺材里。
我對邱有些莫名反感,半個月來,我才是山里旅居者中唯一的東方面孔,這讓我有種自我欣賞。邱的到來讓我覺得被冒犯了,像是等左拐綠燈時油門踩慢了一步,被別人搶先加塞,我很想猛踩一腳油門打破日常邏輯,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只能和現在這樣,不得不接受邱在這陌生下午的闖入。
但是我還是對重新使用母語感到愜意,在這廣闊世界的孤單一角。如果有個長鏡頭,像綠巨人電影的片尾一樣,從太空中看到藍色地球,不停拉近,速度越來越快,接著急剎車一樣定格在我倆面前,日光還在流動,空氣燥熱不安,院里的大狗耳朵耷拉著趴在地上。
半個月來,我每天就是在辦公室里更新網站,發布志愿者招募信息,偶爾去項目上對著嘰里呱啦說著當地語言的工人發呆。不過來之前,我也沒預想什么,所以不存在太大落差。我對邱沒有追問污水凈化項目有些失望,但是轉念想,似乎也沒什么可介紹的,就跟妻子沒有追問我來印度的原因一樣。
一個月之前,我向公司請了長假。我含混地向人資部熟悉的大姐咨詢了社保公積金等問題,心中盤算著離職的可能性。大姐抬頭瞟我問,要辭職?我狡猾地笑,那不可能。在這家建筑國企從事行政管理七年時間,直到三十出頭,不能說一無所獲,但渾渾噩噩,越來越像萬能青年旅店歌里的“石家莊人”。我開始留心搜索,無意中查到了這個項目,很久前我就有在印度旅居的想法,便做了線上申請,第二天就收到了錄用郵件,讓我回復明確的抵達時間,根本沒給我多做思考的時間。然后我像上緊發條一樣開始籌備,從簽證機票,到必備藥品,盡量萬無一失。我知道妻子不會同意,一切都在暗中進行,想著她總能理解,自己像鴕鳥一樣埋頭,反而輕松許多。
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曾有念頭向妻子坦白自己的逃離計劃,但是十點剛過,妻子就已經哈欠連連,睡過去了。家里幾天沒收拾,茶幾上放著礦泉水瓶、餅干盒、茶杯墊,妻子看了一半的《捕鼠器》倒攤開,雜物堆放的空隙處灰塵滋生很快。收納盒里裝滿了妻子保留下來的各類票據,往返杭州的火車票,水電費賬單。我想過清理,但是妻子不許,她不肯丟掉生活的任何細節,擔心日子會像過熱的橡膠一樣失去彈性,松軟無力。
我試圖將雜物理順,但是剛把書合起放到書架上,就退縮了。我把車鑰匙留在餐邊柜上的顯眼處,抬頭看見臥室前掛著的浮世繪門簾,兩個梳著怪異頭型的日本武士一高一低地睥睨著這混亂狹小的客廳,似乎對自己漂洋過海滿懷怨恨。我半夜去廁所,似乎就能聽見武士兄弟的咿呀不滿聲。
第二天早上,妻子著急去上班,問我為什么走這么晚,我說今天外勤,等會直接出門。妻子出門前,我心頭一熱,擁抱了她一下,無用的儀式感。她有點不知所措,出門后給我信息,你今天很怪,我回復了個表情,沒再多說。在陽臺抽完了半包煙,我開始收拾行李,臨走前去超市買了一周的牛奶和水果放在冰箱。起飛前,我復制了早就擬好的信息,轉發給她并道歉。最后補上一句,“就一個月,結束了就回來。我感覺自己非去不可”。然后我慌忙關機,祈禱趕緊起飛,像是匆匆逃離犯罪現場。
抵達新德里,辦好當地手機卡,我深吸一口氣,開啟網絡,手機便憤怒地震動不止,信息來自她,她爸媽,以及我爸媽。我自動過濾了那些辱罵和說教的字眼,內容相似,一股腦刪除了。我是一個自私鬼,終于來到一個陌生而吵鬧的國度,這才是我現在所需要的。
邱帶我去半山腰的小酒館吃晚飯,依然是磚瓦房,四面透風,搖滾樂開到了最大音量,身體的每個分子都在震蕩。我們點了鷹嘴豆,Samosa和Naan,味道很差,只能艱難吞咽。他似乎有很多熟人,帶著我四處和人打招呼,口燦蓮花。音樂聲突然停止,有人彈起吉他,鼓聲也隨之響起,大家合唱起Hey Jude,氣氛越來越活躍,不時傳來尖叫和放肆笑聲。邱早已不知所蹤,我提起啤酒四處轉,擠過熱烈的人群,啤酒花四處潑灑,我不停道歉。在房間的角落,我看見邱和一個印度女孩正打得火熱,他的手放在女孩腰上。
下山時,天色墨黑,我們像是剛冒險歸來,各自懷揣心事,艱難穿過危機四伏的林中路,至深處似乎有巨大的喘息聲。我感到胸腔起火,好一場盛大的野火,茫茫熾烈燒不完。
我們在山腳握手告別,互加微信,約好次日中午一起吃飯。他的朋友圈設置成三日可見,背景圖是他和一個女孩在長城前的照片,他一手摟著女孩,一手對著鏡頭比著手勢,抿嘴笑,女孩頭微朝向他,單腳向后踮起。
回到住處已近十一點,我只想倒頭睡去,但突然被悲傷籠罩,感到比之前更接近生活中的諸多恐懼,聚散離合,生老病死,在今晚被放大得過分真實,讓我執拗地想,亂得像山頭杜鵑,花枝招展不停。然后我開始上吐下瀉。知道自己可能是食物中毒,我勉強從床上爬起找藥,沖了杯電解質溶液一口喝完,癥狀稍微緩解,在止不住的呻吟聲中,我悵然若失地睡去。
第二天,雖未痊愈,我還是準時到了邱的住處。他寄宿在當地一家學校的教師宿舍,房間雖不大,但設施齊全。屋里隨意扔著他的個人物品,一個裝滿藥品的大箱子放在墻角,我湊過去看了一下,包裝都是新的。衣物應該是幾天沒洗,堆放在一起,房間里有一股情緒復雜的氣味。
帶過幾個女生回來。他見我多看了幾眼,解釋說。
看出來了。我并沒展開對話,不是不感興趣,而是跟他沒熟悉到這個地步。
我每次來都住這里,跟宿舍管理員比較熟,平時我不在這個房間也空著。邱說。
相對無言了,邱擺弄著自己的腰鼓,敲擊數聲,鼓聲沉悶。他一直敲鼓,不時望向我幾眼。
過了一會,他開始講起自己。之前他在國內讀數學系博士,爸媽都是大學教師,要求嚴格,他自己也爭氣,學習這塊沒讓他們操心過,一路三好學生,保研保博,順風順水。
但我就是不滿足。邱說。讀到博,就麻木了,總覺得生活不該只是這樣。剛好過暑假,幾個同學約著來印度窮游,只有我待著待著就不想回了。剛開始,導師礙于我爸媽的面子,還每天發郵件,找我視頻,他們也一直電話轟炸,苦口婆心地,接著先是導師放棄了,再是爸媽下最后通牒,不回去就斷絕關系,我看了覺得可笑。
現在呢?我問,讓對話繼續漫無目的飄著。
確實很久沒聯系了,前段時間我媽生日,我一直記著,發了個問候,她當天沒理我。第二天她問我想明白沒,我說挺明白的,不回了。她說,那我當你死外面了。我說,挺好,早該這樣了。
我說,你也沒必要話講這么絕,畢竟是自己爸媽。
邱說,我心里清楚,知道對不起他們。但沒辦法,我自己都沒想明白怎么活,總不能回去繼續給他們活著。現在多好,就晃悠,北到南,東到西,這個國家大,交通又不方便,正適合我打發時間,從加爾各答到班加羅爾,花上幾天,哪怕在火車上熱得睡不著,像蒸桑拿一樣,但就是快活。
我想起從新德里開始的火車旅行,車廂里混雜著人畜,腐敗的水果,咖喱和劣質煙草的味道,時間被放大到無窮倍數。
我不擅長和陌生人迅速建立關系,熱情正在快速消退,低頭看微信,不停放大縮小妻子發來的圖片,腦子里空落落的,最后還是下決心回復,“照顧好自己,我會盡快回來。”半晌,手機再次震動,她的回復干脆利落,“滾”。
我沒忍住,跟邱說了家里的情況。
那你是得回去,你不像我,無牽無掛的。邱說。
隨后,我們去鎮上的一家餐廳吃飯。這是個以瑜伽和冥想聞名的小鎮,只有一條主干道,東西走向,彎曲延伸,坑洼不平,電線隨意地糾纏密布,像張巨網。眾多小樓分布在道路兩側,高矮不一,像長壞了的牙齒,廣告牌色彩鮮艷,印滿了花花綠綠的印地語和英語,幾乎所有的店鋪都在外放音樂,突突車、摩托車、行人、牲畜的眾多聲音交織,被狹窄的道路收攏如擴音器般放大,讓人迷失方向。
鎮上的西方旅居者很多,多是嬉皮士裝扮,不分季節地穿著麻布衣、裙褲、人字拖,女性大多盤著發髻。因為往來游客多,長期蹲點的乞丐也多。身穿簡陋紗麗的婦女坐成一排,嘰里咕嚕交談,一群黑瘦的小孩圍繞著瘋跑,像是參加每日的家庭聚會。
后垮掉的一代。邱總結說,或者說每一代都有垮掉的我們。
我正準備表示贊同,看見大胡子德國人帶著女伴迎面走來,他穿著黃色馬丁靴,工裝短褲,短袖上印著巨大的海明威頭像,脖子上卻纏著條圍巾,里外三層裹得嚴實。女孩卷黑頭發,素色連衣長裙,拉丁人種,面容姣好。他們輕聲交談,女孩笑得前仰后合。我們錯身而過,擊掌示意,邱不住回頭,我知道他的注意力都在女孩身上。
你不是有女朋友么,還這么眼饞?我拍了拍他說。
邱對我戲謔一笑。我又沒結婚,社會公約對我不適用。他雙手插兜,微微下蹲,正跳過一個水溝。
她在國內等你多久了?
我跟她說過,不用等我,短時間內我沒有回去的打算。她可以找別人,我不在乎。他停頓了下,又加上一句:我可不想太負責。
說話間走進餐廳,邱跟店主打了招呼,寒暄幾句,介紹新朋友,我也被迫迎來又一股濃重體味的擁抱。
我們被引到樓頂的露臺位置就座。邱卷了根紙煙,遞給我。我還沒從昨晚的狀態里恢復,搖頭拒絕。他點燃,火星濺起,劣味的煙霧飄來,令人惡心。我沒有點餐,只要了杯檸檬水。
露臺風大,視線隨之飄散,我看到許多平時未留心的小道,像毛細血管一樣,脈絡清晰,從小鎮的各個岔路口向外延伸,散布林間,五顏六色的鐵皮屋頂上全是垃圾,遠處神廟的金色塔尖一圈圈繞開,被陽光撥弄得正耀眼。
我突然想起邱房間里整箱未開封的藥品,沒忍住問,你現在靠什么生活?
就做些貿易,買來賣去,掙點生活費,這邊費用低,活下去不難。然后他欲言又止,一只手擎著快燃盡的煙頭,一只手捏住勺柄,在咖喱燴飯上不停畫圈,若有所思。
邱講得神秘,我也沒繼續問,哪怕他說自己正等待著某項不可知任務,我也全盤接受。
用完餐,他加了兩杯奶茶,味道濃郁,我的食欲被打開,要了一份Kebab。
等會帶你去附近的村子走走?這個季節的北印度挺美的。邱又卷了一根紙煙,向樓下不停張望。
我沒有反對,但他突然像是想起來什么一樣,匆忙起身說,要不兩點吧,我剛想起來有點急事。
他邊小跑邊看手機,三點吧,三點在餐廳樓下見。
我向樓下看去。果然,之前遇見的拉丁女孩正路過,單身一人。隨后,邱魚躍進入視野,三步并作兩步,在女孩身后慢下來,沒著急上前打招呼,他們一前一后在拐角處消失。
我付完兩人的賬單,只能回去休息,正午燥熱,陽光毫無阻礙地刺穿單層窗簾。我打開電扇,翻來覆去,依然難以入睡,起來看書,翻開幾頁又合上,想起一處描寫,一種強力的焦慮襲來,似乎那段話與我心態極為契合,不找到就無法生活下去,于是往前翻找,但怎么也找不到。
好不容易熬到三點,我準時到了餐廳門口,來回踱步,等了許久,仍不見邱的蹤影。撥電話過去,半晌沒接,正準備掛斷時,他的聲音被風聲裹挾著傳來,像是身處曠野。
哦,對不起,我事情還沒處理完,要不現在趕過來?他語氣慵懶而平穩。
不用了,我自己附近轉轉。我聽出了他言語中的客套。好的,再聯系。他迅速掛斷了電話。
我無事可做,隨意選了條岔路,信步走去,在山林中兜兜轉轉,找了根橫臥的樹根坐下,附近水聲潺潺,鳥鳴靈動,但是又無跡可尋,我很有抽煙的沖動,口袋里卻空空蕩蕩,這讓我很是沮喪。天快黑時,我才悻悻回到宿舍,覺得累極了,焦慮感又縈繞心頭。
半個月里,妻子除了兩張照片之外,再沒和我聯系,只有我媽鍥而不舍,堅持每天微信感化,我偶爾回復,她就長篇大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我爸經常晚上應酬,酒喝多了就給我打電話,接了就劈頭蓋臉一頓罵,我也不還嘴,只聽著。他發泄完了,就說,兒子,爸想你了,你別想不開。我說,知道了,我快回來了,然后立馬掛掉。其實,我最想聯系妻子,覺得只要解釋清楚,她總能理解。
七年前,妻子是個有著嬰兒肥臉蛋的女孩,笑起來臉頰通紅。她在北京讀研,而我在國內外邊打工邊游蕩,有太多事情值得體驗,每件都極端緊迫重要。但一個夏天的午后,我坐在伊朗北部小鎮的里海邊,看著海水漫過白色沙石,突然產生強烈的思念,于是我買了張單程票受驚似的回國。
等她畢業,結婚就順理成章了。母親有著中產階層的審慎魅力,全盤接手婚禮的所有環節,像自己再婚一樣。父親是公務員,職位在我看來雖無關痛癢,但他做事亦步亦趨,不敢逾矩,兩方親屬加起來才辦了十桌酒席。妻子有些不滿,覺得這和理想中的盛大婚禮有著天壤之別,但也只能作罷。儀式尾聲,司儀夸張煽情,我緊張地弄丟了戒指,在干冰升騰起的霧氣中尋找,妻子尷尬地笑,裙撐打消了她蹲下幫忙的念頭。當我狼狽站起,看到她過濃的妝容下,皮膚上的汗毛根根可見,感覺很是陌生,仿佛生活的全部細節提前展露無遺。
接下來幾天,我照常在辦公室、項目地和宿舍三點一線。經常遇見邱,每次他都和拉丁女孩一起,他們的關系進展迅速。邱看見我,只是點頭示意,我也不想顯得過分熱情。
有天傍晚,我返回宿舍,看見邱獨自走來,我約他去咖啡館坐坐,他懶懶地答應了。
我問他喝什么,他只是搖頭。我點了兩瓶啤酒。吞一口泡沫,聊天的語境就打開了。
那個女孩呢?我肯定要這么問。
已經走了。他揮揮手,做了一個灑脫的表情。她去斯里蘭卡,讓我一起,我沒建立長期關系的想法。
分手快樂。我舉起啤酒向他示意,瓶口相碰,發出清脆響聲。
還是有點舍不得,看來我定力不夠,仍需努力磨煉。他抿嘴笑,打了個響指說。總有一天,我能做到隨時消失。
又聊了半小時,他起身說自己明早就走,今晚早點回去休息。我們定下日子,約好在瓦拉納西見面。從咖啡館出來,我就找車票代理訂好了火車票,只盼著盡早離開。
一個月很快結束了,接替我的是一個美國男孩,才讀高中,假期過來社會實習,他熱情詢問各種工作和生活細節,我很想面面俱到,但不知怎么回答,只能用東方人特有的內斂的方式,描述了自己的不可知感受。交接完畢,我和當地的負責人告別,印度男人矮我半頭,體毛濃重,挺著肚子握緊我的手,不停搖頭對我一個月的無私奉獻表示肯定,歡迎我下次再來。我笑著說好,心里念著再也不見。
我乘夜間大巴,一路上客下貨,折騰得我一宿沒睡。到了火車站,又碰到大面積延誤,廣場上滿是七仰八叉躺著的旅客。趟過地上橫躺的人流,在站臺苦等,好不容易火車抵達,人群如浪一樣洶涌,戴著三角帽的警察上前維持秩序。有個印度小伙跟我站在一起,同我攀談,他說他為這樣的場景感到抱歉,我說沒事,在哪兒都一樣。
邱沒在瓦拉納西火車站等我,我把旅店地址給突突車司機,談好價格,被帶到一片城中村的入口,接著步行穿過數十條骯臟陌生的小巷,終于來到邱長住的久美子之家。
久美子是個嫁到印度的日本女人,她杵著肥胖的身子窩在狹小的客廳里,登記護照的間隙不時抬頭看,提醒我很久沒剃須了。她丈夫,一個印度老頭,戴著不合時宜的墨鏡,望向虛空。他穿著印度傳統的素色長袍,悶不吭聲地躺在靠椅上,青筋裸露,手臂干枯,布滿斑點,雙手戴滿碩大耀眼的戒指,空氣里充滿隱秘電流,戒指就是藏身其中的魂器。
旅店就在恒河邊,我放好行李,拾階而下。恰逢雨季,河水上漲很快,水位已經逼近神廟平臺的紅色立柱下沿,沒過了石梯的大部分,空氣里有股腥臭味。
來之前我看過很多照片,眾多樣式古怪的建筑,石梯延展聚集,朝拜似的伸入恒河的腹部,印度之母的深處。人在此處,看到色彩斑駁的小樓沿河聳峙,不知名的神像東一處西一處立著,透露出危險的構圖關系。石墻上粉刷著印地語,翻譯過來可能就是“水深危險”,頓時失去了美感。
傍晚時分,邱抵達旅店跟我會合,依然是老裝扮,只是換了發型。跟上一次相比,他有些萎靡,目光渙散。邱跟我說最近很忙,本準備爽約,但想著可能是和我的最后一次見面,就趕了過來。
天氣悶熱,我們在頂樓陽臺的藤椅坐下,不斷拍打身體,驅趕蚊蟲,我的手臂變成了甩動的牛尾。邱從黃色紙袋里拿出兩瓶啤酒,我們沉默無言,不停啜飲。天氣潮濕悶熱,我站起身,拉了拉短褲,跟邱目光相對,他犯錯一樣低下頭,顯得心事重重。
他用兩指輕撕著翹起的啤酒商標,又將指甲中的紙屑挑出,問我還準備待多久。
不能弄更糟了,這幾天我就準備回國。
難得來一次,不多待一段可惜了。
能出來這么久我已經知足了,比不上你。
邱的下巴微微收起,接過話頭。原來聽一個到處旅居的朋友講,我們這種人,一旦走出來就回不去了,都是無用的靈魂。開始還不信,現在看,我也差不多了。回國,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我點頭贊同,但不知道該附和些什么。
我來了兩年多,發現這里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時間像是會繁殖一樣,不停復制。
我低頭喝酒,清涼感從食道一直抵達胃部。我忍住了一股上涌的嗝意。
現在,我感覺已經掉進了時間的縫隙里了,用什么詞形容——時間的維度。我躲在這兒就行,不用對任何事情負責。當我想的時候,就可以砰的一聲消失。他手腳不停比劃,有些亢奮。
身前河面空曠,水位還在上漲,似乎觸手可及,壓迫感讓人喘不過氣。
邱站起來,興奮地來回走動,然后他雙肘壓住欄桿,向前半傾,對著恒河大聲喊叫起來。我微微起身,放下啤酒,緊盯著他。
邱回過頭,握住我的手,眼神里充滿光焰。走吧,你不是第一次來恒河么,我帶你去夜游。
我被他的狂熱嚇到,擠出笑意勸他。
邱不屑地看向我,眼神陌生。他迅速轉身,脫去上衣,便跳躍著向樓下跑去,只留下我不知所措。我追了幾步,又返身跑向欄桿,向下望,邱正試探著走到河水中。
你當心點。我大喊,聲嘶力竭。他回頭看我,做了個敬禮手勢,然后雙手合攏向前扎入水中,瞬間就被河水吞沒,幾秒鐘后,他露出頭,對我揚了揚手臂,調整了下姿勢,朝更深處游去。
待我趕到岸邊,邱已經完全不見蹤影了。我沿著河岸向上游尋找,河邊正舉行一場盛大的祭神儀式,衣著華麗的演員們拿著法燈來回逡巡。我又跑回酒店,向下游找去,一群孩子從二層小樓的窗臺挨個跳入水中,他們大聲呼喚彼此,循環反復,專注而狂熱,正如邱一樣。
我跑累了,癱坐在石梯旁,河水拍打著我的腳背。我突然自責,覺得這都是蝴蝶效應,如果不是我堅持來印度,如果不是和邱約到此處,自然也就沒有現在的困境。
我站起來,沿著石梯緩緩走進水中,用腳尖探路,直到腳下空空蕩蕩才止步。我的膝蓋已經完全沒入水中,水勢雖大,但很平靜,感官變得敏銳無比,似乎聽見了所有細微的聲響,很遠處,有人在讓我繼續走,不要停留。星空浩瀚,光亮異常,對岸神廟前,似是有人赤身裸體從水中爬出,和我相對而坐。我想象著那是邱,他必將枯坐整晚,直到白日來臨,萬物復蘇,當地人成群結隊,把尸體燒成一半送進水中,然后嘈雜交流,像是在談論彼此的一生。而他并未參與,只是靜坐發呆,眉毛緊蹙,好像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跟河水沒盡頭地游蕩下去,裝滿全部未來。
過了很久,我突然心頭一松,感覺發生的一切和我毫無關聯。我打起精神,快步回到旅店,去陽臺撿起邱的上衣,和他的行李一起放在床鋪上。
隨后,我去客廳泡了杯茶,撕開茶包,看著細碎茶葉上下翻涌,就像無數個邱在水面浮沉。久美子的印度老公顫悠悠從陰影中走出,表情怪異,嘴巴微張,發出連串難解暗語。
我走出門,撥打了妻子的微信電話,空響了很久,她接通的一瞬間,我終于痛哭起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醒來,邱的物件都不見了,我依稀記得昨晚熱醒去沖洗冷水澡,他的東西仍在原處。我去前臺問久美子,邱是不是回來過,她茫然地看著我,像是這個人從未存在。
回國后,我從原單位離職,重新找了工作,工作性質沒有太大變化。我仍然有意無意地發現自己的重要性,每天睜開眼,便覺得會有奇跡降臨。一天過去,什么都沒發生,便開始在夢里添油加醋,現實對我來說已經毫無分別。
現在,我正在醫院,電子屏上妻子的名字和紅色的“檢查中”并列顯示。我點進邱的朋友圈,仍然是三日可見,但背景圖換成了他在泰姬陵前的單人照,高昂著頭,放肆地笑。
已經過去幾十分鐘,妻子腹中躁動不安的生命將在這個八月降臨。在和瓦拉納西一樣燠熱的天氣里,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