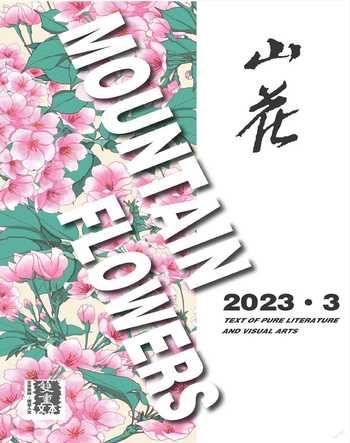第二真理
麥豆
吹 風
在夢中吹風
在夢中,一塊草坪上
與一個七歲的男孩,一起吹風
風很溫柔,吹過草尖
吹過我的夢境
有鳥在樹上鳴叫
有螞蟻在草叢間爬行
孩子用樹葉在草坪上
做一張床。
我們兩個,蹲在風中
彼此互不相識
我知道我們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不可能的人
七歲被風吹
三十七歲仍吹著風的人
一只螞蟻迷路了
一只螞蟻迷路了
在池塘中
一面荷葉上
爬行,我很好奇
它是如何來到
一面荷葉上的?
我用一片樹葉
將它從水中
引至岸邊
螞蟻上岸后
我卻更加迷茫了
我只知道螞蟻的家
在岸上,它在水中
是否還有一個家
人類并不知曉
我本該任它
在荷葉上爬行
但我卻想幫它
尋找它的歸宿
一只螞蟻迷路了
這是一件真實的事
沒有人能夠改變它
雨中或夢中
有人撐著傘
在雨中走
一行數人
說著他們的話
離我很遠
此刻
我在哪里?
我在一棵樹的后面
在我的檐廊下
望著他們
我知道此刻不止一個我
在不同的眼睛里
望著雨中的他們
望著他們在雨中
漸漸消失
此刻,我同時看見
一只黑貓
從身邊走過
悄無聲息
此刻,正午與夜晚
沒有區別
一切皆在一場夢中
在世界的某處出現,又漸漸
在世界的另一處消失
真正的我
仔細聽
是往昔的松濤聲
在代替
眼前的汽車
疾馳在雨天的馬路上
閉著眼傾聽
我知道此刻在代替過去
我知道我此刻
正站在雨的邊緣
人類的屋檐下
但也只是一個
我的想法
真正的我
在另一個世界里運行
這個我
只是在替他感受
徘徊在黑暗邊緣的人
白熾燈亮著
亮在白天
昏暗的地下室里
它亮著
要求我
望向頂棚
它在頂棚那里
發著白光
有一個人
打開了它
正午時分
外面的世界
異常明亮
人們紛紛
在太陽下散步
但這個人
視線向內
看見了我
并注意到
地下室里很暗
他于是將燈打開
在地下室散步
事物在靜止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八角金盆
我們稱呼它
將它從昏暗中
辨認出來
但我們是誰
喜陰植物
沒有語言
我們在地下室里
不停繞圈
走向那個
讓我們最終停下的位置
第二真理
被割掉頭顱的薄荷
又長出了新葉子
秋天還未到
它仍要將生命
蓬勃地實現出來
為什么割去
薄荷的頭顱
這是人的語言
遠非事件本身
在秋天之外
隨便找來一把鐮刀
鋒利的鐮刀
我稱它第二真理
一只白頭翁之歌
它站在樹巔唱歌
看見我,猶豫片刻
便飛上窗前的晾衣架
繼續唱歌
幾個單調的詞匯
被它反復念叨
沒有意義的言說
我的判斷告訴我
無法擺脫的判斷
它站在無聲的事物上
自由就在它那里
自由與它尚未區分
我望著它出神。
在朝陽中陷入反思,
我看見墻上
陽光中,那黑色的頭顱
我的痛苦源于我的頭顱
知道它看見了
窗口的我
我知道它是一只覓食途中的鳥。
它愉快無憂的歌唱
很快吸引來
另一只同類的鳥
它本想引起我的注意
但它知道,無論怎樣
它都無法落上我的手指
它在我的彼岸
兩棵不同的樹
一棵樹的種子
經過鳥的腸胃
被攜帶
落到另一棵的
枝丫處
開始發芽
長出鋸齒狀的
綠葉子
一棵樹
長兩種葉子
我們被它吸引
它什么也不說
但我們
仿佛理解它
為什么這樣做
電動門
電動推拉門
突然動了
無思想的它
感應到我
突然從一端
快速
向另一端移動
它的行為
令我困惑
天空下著雨
電動門
將我關在了門外
她
雨中走出的人
已在雨中
走了很久
濕淋淋的
一件塑料雨衣
包裹全身
濕淋淋的
一個頭盔
戴在頭上
穿越一場暴雨
長久的
沉默中
她和車
已是雨水的
一部分
她已不再
躲避
從天而降的雨水
她已不需要語言
與我打一個照面之后
便迅速消失于
一道兩邊
都是墻壁的
暗門之中
只有地上
濕漉漉的一道車轍印
直通雨中
這個場景不是夢
一個真實的人類
已穿過她的暴雨
霧氣彌漫
天空靠路邊的樹
撐著,不能再降低了
霧氣彌漫處不是天空
但它那么像我們的天空